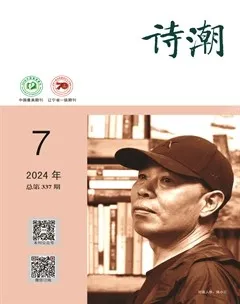诗学随笔二题

诗,是在行动中“爱这个世界”
1963年7月24日,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给好友肖莱姆(以色列著名学者,二人都是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好友)的回信中,她说:“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自己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我不能爱自己或者所谓自己的人的一部分。……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什么样的善呢?”一个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需要勇气,尤其是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当一个人只相信自己,一个民族也如是,怎么能会产生“善”呢?曾经犹太人的敌人也是如此自信。人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堆人在一起,人的有限性(罪性)就消失了。阿伦特的谨慎和特立独行是基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
阿伦特的“善”,是没有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就只爱犹太人,她“爱这个世界”,要知道,在犹太人眼里,不信耶和华神的人是外邦人,那个“世界”中的人,是污秽的。阿伦特恰恰要去爱这个“世界”中的人,她的言语、行为类似被犹太人厌弃的耶稣(阿伦特确实也引用耶稣的话)。阿伦特对“人”有清醒的认识,她对“爱”也有独特的认识:这“爱”是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无论种族。更重要的是,她的爱,是在世界之中,是知识分子能做到的切实的行动,是从哲学到政治学的转变。
1964年,在面对德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对方坚定地称阿伦特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则温和地拒绝接受这个称号。阿伦特是哲学家这毫无疑问,她在德国求学,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斯(Carl Jaspers)等哲学巨匠的入室弟子,她写的每部作品都清晰地显示出她是哲学家,但她为何拒绝这个很多人企慕的称号?
在以色列学者沙伊·图巴利(Shai Tubali)的考察中,阿伦特拒绝的不是哲学家的称号,她抛弃的是“学界思维”——那种“‘作为纯粹活动的思考’——在很多方面是哲学的定义——渐渐地被揭示出与阿伦特自己的思考实践渐行渐远。阿伦特经过多年的努力开始具有了与哲学内省的关键距离,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明显不同。随着她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她变得越来越担忧海德格尔关注点在她看来的严重缺陷——自我沉迷于远离真实世界的东西以至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绝对的自我主义,与同胞完全隔离开来’……阿伦特担忧的是这种思考,不断只反思自己就像一个封闭的圈子,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茫然无知。海德格尔公然卷入纳粹活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1933年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虽然并不是直接的联系。在这点上,他似乎确认了阿伦特的清醒认识:做哲学研究或许可能很深入,但并不自动导致思想者在世界上的道德参与。”说实话,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想,在“学界”的我,是否正是阿伦特的担忧。
学术研究有时可以不依赖人的现实经验,完全作为纯粹的观念的演绎,这个纸上的世界,它依赖学者强大、缜密的内在的思想能力(“内省”),20世纪恐怕没有人在这方面能赛过海德格尔,但阿伦特将这种“内省”定义为“返回自身,在灵魂中找到孤独的客体”。“在她看来,内省是孤独的:人们不再对世界感兴趣,只找到一个有趣的客体,即内在的自我。在这种孤独中,‘思考变成了无边界的东西,因为它不再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干扰,因为不再有采取行动的要求。’当世界和行动遭到拒绝时,内省也能填满人的生活……阿伦特觉得,这种内省倾向是她青年时期犯下的错误。所以她开始了远离传统哲学的旅程。”“通过发生在欧洲的历史和政治转变。她的思维类别变得更深入地与世界纠缠在一起,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那是积极思考。积极思考是参与程度很高的思维方式,让人准备好在真实世界里行动。但是此外,积极思考本身是一种行动,因为在思考行动本身,人们意识到他是有责任的世界参与者。虽然思考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从世界上隐居的方式,即脱离与事件的联系,转向沉默的内省,但是,积极思考像承诺负责任地思考:从舒服的旁观者视角离开,意识到只有通过参与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这种“与世界纠缠在一起”的“积极思考”相比,“毫不客气地说,通常的哲学思维几乎就像不思考”。
当我思想20世纪这位独特的女性,读她的文字,我想,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接近诗歌呢?还有怎样的人格比她的品格更接近我们对诗人的期待呢?如果诗不是这样,那不恰恰应了阿多诺(T.W.Adorno,1903—1969)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吗?
思,与诗,是不能分离的人两种面对世界的方式。当代诗人,如何以这种“积极思考”面对世界?我们如何“与世界纠缠在一起”?幸运的是,我也常常看到一些诗人,积极地借着体察与书写,以极为简略、通俗但极具批判性的文字在呈现这个世界上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他们的写作,不是建构理想之“诗”的“纯粹活动”,而是类似阿伦特那“爱这个世界”的“行动”。
注:201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著,译者孙传钊,也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的编者。
在点赞的时代,诗是向他者和否定性的敞开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有许多对今日社会的洞见。当今的人,在一种强烈的要做真实的自我的神话之中,“真实意味着自由,不被预设的、被外界事先规定好的表达和行为模式所囿。它强迫人们只像自己,只通过自己来定义自己、书写自己、创造自己。”“在真实性的强迫下,‘我’不得不去‘生产自己’。”这一点,我们去看看各人的微信朋友圈就知道了,谁不是在拼命地“生产自己”?
但这种“自恋的主体只是在自己的影子中领悟这个世界,由此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者消失了”。而事实上,没有对他者的凝望或者说在他者的凝视之中,人无法认识自我,也无法形成自我。做真实的自我的神话,带来的结果却是“同质化的恐怖”——“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与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体呈现的恰恰是最低级别的社交。”
“当今社会的特色是消除一切否定性。一切都被磨平了。为了相互逢迎,连交际也被磨平了……人们避免来自他者的任何形式的伤害,但它却以自我伤害的方式复活。在这里,人们再次印证了这一普遍逻辑:他者否定性的消失引发自我 灭的过程。”韩炳哲引用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的话(“十到二十年来,文学领域几乎一片荒芜,寸草未生。出版物如潮水般涌现,精神世界却一片死寂。其原因就是一场交际危机。”)并认为“文坛危机的源头乃是他者的消失”,而“艺术和诗歌的职责就在于,为感知去除镜面属性,使它向‘相对’、他者、他物开放”(而不是一切的写作只是如同镜子,“照出自己”)。

今日的文化是一种“点赞”的文化(想一想我们发圈之后对“朋友”认同的渴望和对否定性意见的恼怒),这种文化“拒绝任何形式的伤害和冲击。凡是想要完全逃避伤害的人终将一无所获。任何深刻的经验、洞见皆存在于伤害的否定性之中。单纯地‘点赞’,完全就是经验的最低等级。”而诗,是对这种文化的反拨。在诗歌写作中,人当面对他者,无论这他者是形而上学的道还是神学的上帝还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对他者的凝望与思忖、他者给予的启示,会给人带来许多否定性的洞见,人才可能不断心意更新。这种否定性虽然可能是“伤害”,但会使人更完全。诗作为一种思,因向他者开放而使诗人真实地面对人的问题,诗也唯有如此才能深刻、动人。
“诗歌的职责在于……使感知向他者开放”,这一思想要求今天的诗人不再沉溺于那种寻求某种世俗的认同与收集自我的荣耀的写作,而是在思忖与写作中不断寻求来自他者的“否定性”。诗是“新鲜的荆棘”,是来自他者的对灵魂的不断冲击。诗人的生命因此不断新鲜,虽然这种“开放”会使我们时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