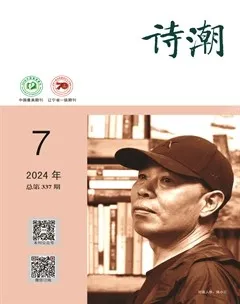李德武随笔
诗歌从不需要辩护
诗歌从不需要辩护!诗歌也不需要警察一样的机制来守卫。一个诗人专心于艺术,一种纯粹的写作态度就是对诗歌最好的捍卫!任何栽赃陷害等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都对诗歌无可奈何。诗歌是诗人的法身,诗人肉身受到怎样的侮辱,都不会贬损他诗歌的价值和地位!诗歌也不需要对他的攻击者予以回击,诗歌只回击值得它回击的东西,比如功利和死亡。可喜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诋毁或仇视诗人或诗歌的人,能够比诗歌活得更为长久!
从面前移开每一面镜子
写作的技术问题如果不能转化为一种存在方式就是对存在的逃避。
这种逃避常常以文化为伪装。文化是令我们产生告别感的东西,尽管在告别中难免会留恋或依依不舍,就像本雅明指出的“降半旗”的对象。
尝试处理自己拒绝的或不熟悉的经验和生活问题。在写作中把自己垒起的墙推倒。
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和文化的冲突问题,而是和存在的冲突问题。当然谁也离不开和文化的纠缠,问题是把文化处理成什么。处理成显在的存在,还是隐性的存在?处理成要素,还是基因?抑或回溯的界碑或里程表?
我把写作存在处理成不确定性。要努力直面空白,从面前移开每一面镜子、偶像和参照系。在技术上,一个诗人要敢于追求德勒兹的尖点,让心成为光的散射源,不要试图聚焦和成像。语言本身会有痕迹,所以一种风格不能持续太久,太久了就落自画像了。
诗当画(化)大千,画自己有何益?存在的本质是变。
AI时代,诗人何为?
列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谈到,在新媒体的术语里,“跨码”就是将一个事物转换成另一种格式。文化的计算机化进程也逐渐实现了所有文化范畴和文化概念之间的跨码,即,在含义和(或)语言层面,文化的范畴和概念可以替换为计算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用学所衍生的新范畴和新概念。
文化作为一种固化语言或塑性语言,它在转译中必然会不断地被选择、剪切、粘贴,像历史的图像一样被用来完成新景观的合成,意味着文化将沦落为机器语言(AI语言),那就留给人机对话吧,我们要说点机器说不出来的语言。
诗人应该关注技术对当下的影响,技术比文化对我们存在的影响更直接,也更迫在眉睫。
当代性!算了吧!
当代性,算了吧,还是不提这个概念为好,免得让它成为年轻就正确的理由,或者活着就先锋的理由。我们同时活在古代、当代和未来。谁也不能把古老的发音功能从嗓子里抠出去;谁也不能在他年老时,从骨头里剥离孩子时就已经铸就的骨骼。如果那些炫耀当代性的人为了时尚,那就直接说时尚,而不是当代性。时尚是流行的代名词,如果古典流行,古典也是时尚。诗人不是为他的当代性付出生命代价,而是必须为他的语言付出生命代价。无论他的语言向度如何!
阿甘本谈当代性,他在谈流行和时尚,这对服装行业可以,对诗歌不适用了。诗人的存在具有现象学意义以及语言学意义,但不能归结为当代性问题,当代性有助于对个性的含混概括,无助于对个别特征的细致辨认。时代特征或重大事件如果不是通过诗人个人化呈现,是没有艺术意义的。就好比不能把杜甫说成是安史之乱诗人一样。我们需要在艺术中化解时代痕迹,而不是刻录时代痕迹。伴随时代出现的应该是新形式、新语言和新理论,而不是泛泛的当代性概述,这在我看来等于什么也没说,显示出理论能力的匮乏和羸弱。德勒兹说艺术的创新来自对概念的创新。我们创新概念的意识和能力同样缺乏。已有的概念,比如口语、民间或先锋性,都已经代表不了今天更为复杂审美的需求和创作现实了。
要警惕诗歌写作的知识化倾向
要警惕诗歌写作的知识化倾向。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倾向,但至少这种倾向不该被大力提倡。知识化的写作(掉书袋或满身书斋气或教授口吻)不是把诗歌带向美,而是带向学问和对硬知识的贩卖。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感到像一丝智慧,其实是学问,拖着阅读滋生的长长尾巴。
如果我想了解知识,比如植物学、历史,我就去读植物学的书或史书,不会选择诗歌。诗歌里可以有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向人指示所是(包括引经据典,我对一首诗下面跟着一长串注解总感到不舒服,就像我在和恋人接吻却总是被敲门声打断),而是显示所美,暗示不是以及不确定。诗歌不拒绝知识是因为诗人有本事让死的东西复活。
这方面古代诗人中李商隐可能是做得最好的,“锦瑟无端五十弦”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无端”这个词太妙了。诗就应该是“无端”的,而知识是“有端”的。
诗是一种友善的力量
诗是一种友善的力量,一种通过把我们提升到对特别事物的沉思之中的安慰——因何而特别?嗯,因主体性。
——克尔恺郭尔
从主体性出发,诗人也是沉思者,只是,他不是利用逻辑手段沉思,不是基于承认普遍性沉思,他诗性地沉思。诗性意味着他的沉思始终是主体性的。所以,不能把诗人的沉思同哲学和哲学的任务相等同。那些把诗人的沉思与哲学的理性、体系、形式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相等同的人都未真正认识到诗之思的本质与特征。
克尔恺郭尔要比海德格尔更早肯定了诗人之沉思。他把苏格拉底看作是诗人,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没有体系,没有结论。他的结论就是一切智者都是值得怀疑的,而我知道的很少。
克尔恺郭尔发现了苏格拉底的反讽!诗人沉思时不是常用反讽吗?我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需要求证,我可以查查读书笔记),好像是亚里士多德,他说诗人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掩盖思想。这话一语道破诗人内心的秘密。
承认诗人沉思的主体性是区别诗人与哲学家的最基本标准。诗人沉思只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沉思,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沉思(康德、黑格尔)。
诗的沉思,包括对真理的沉思,都不能当作知识以及真理的依据,如果这些沉思也和真理有瓜葛,也仅仅貌似而已。如果我们还不能接受诗人沉思这一事实,那就请多玩味一下克尔恺郭尔的话:“诗是一种友善的力量,一种通过把我们提升到对特别事物的沉思之中的安慰——因何而特别?嗯,因主体性。”
我们真正应该怀疑的不是诗人的沉思,而是沉思的诗人为什么这样少?!
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都是审美的天敌
我在散步和做饭时脑子里冒出的想法要比我苦思冥想时的想法重要得多。以下就是一些无端的念头!
a.神是对人能力欠缺的补充!人力所不能及处,神就出现了。
b.一个精选的词就像一个从未校对过的时钟,开创一种与常规不同的陈述方式。
c.多产若不与语言和形式的自我革新相伴随,就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劳动。
d.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都是审美的天敌!
e.分酒器是把同一事物分给不同人的艺术。一首诗不仅是酿酒,更应该是分酒器。
f.我们从账目上看到负数也就看到了此生的亏欠!但减少并不都是坏事,我们只有依赖负熵才能久存。
g.在写作的高级阶段,内容几乎不是兴趣点,唯有形式才有考虑的价值。一个诗人越老就越在乎技艺。
为什么要看到世界的无限?
为什么要看到世界的无限?首先,如果诸多事实中,无限也是个事实,那么,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关于世界是不是无限的,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否定。所以,对世界是否是无限问题仍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其次,迄今人类发明或发现的各种规则和规律都是基于世界的有限性而言的,如果世界是无限的,那么,这些规律和规则将被重新定义。再次,人类的求知欲促使人类自身不断探究世界的奥秘,如果世界是无限的,意味着这种探究也将是无限的,人类不会在探究之路上止步。最后,世界的无限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的无限,人类对未来将充满期待!
江南的刻意
江南的本质就是个性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或者共同体。如果说才子属于个性的,那么,江南就是才子。上海算江南吗?这个地方更适合培养小资,而不适合培养才子。上海的问题在于文化太模式化了。上海人的自负、骄傲都可以找出模板。但江南人的自足是没有模板的。我把这种个性化特征说成是自私的、排他的。人们常说江南文化精致,精致是因为自私,小才能精致,大的东西都很难精致。大有大的好处,含纳、宽广。大的东西属于时空,不属于质料,比如金、玉之类的。在对待大的问题上,越模糊越正确,所以中国哲学都是模糊哲学、趋势哲学;在对待小的问题上,越具体越正确,比如苏州园林,一草一木都安放得精确妥帖。当然,小也有小的弊端,就是计较。江南的山水和文化都有些计较,你也可以说过于算计或过于用心。刻意这个词在北方是一个贬义词,在江南则是褒义词。谁要是不懂得刻意,谁就不懂得江南的精髓。
叠 境
江南不是词语的,而是图像的。白居易说苏州“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说的就是图像。苏州园林可以看作是苏州特有的语言密码,这个密码核心就是图像。网师园著名的一景“月到风来亭”也是图像。
词语的总有个语序次第,所以,说某个地方是词语的一定是说某种远近或主次的存在,比如历史多么久远,哪位知名人士在此居住或逗留,什么美味获得皇帝的宠幸,等等。词语地理往往是平面的或线性的,头绪多,扯得远。苏州不是词语的,因为苏州不仅是图像的,也是叠影的。相互映衬、呼应虚实、层层递延、回味缠绵才是苏州的风格。这样的气质在园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词语的属于时间,那么图像的就属于空间。苏州的本质属于空间。一座古城延续2500年,今天我们和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2500年的繁华与积淀都没有超出这座古城之外。每一物都不单是它自己,它本然地叠入到苏州的背景里。就像我们走在小巷或园林中,我们身边的图景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我们因为置身叠境之中而不分古今了。
在苏州,如果体会不到古今同在就不算得苏州真神。当然,在苏州你如果不把自己弄丢了,陷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就不算入苏州的叠境。
魔术的秘密
魔术师善于表演,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一套做一套,目的是遮人耳目,制造惊奇。高级魔术师看不出破绽,低级魔术师破绽百出。观众喜欢魔术无非是愿意以假为真。批评家是个讨嫌的差事,他总是把魔术的秘密说破,坏了观众的兴致。当然更不受魔术师喜欢。
原则与混沌
马拉美是一个用头脑写作的人,他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展现出实物无形的美,还在于他有自己鲜明的美学原则,就是不用经验和第一感官写作。他的诗不是制造梦幻,而是为思提供了无限可能。这是伟大诗人的标志。学马拉美的诗人很多,这些诗人中最糟糕的是对哲学思想的转译,最不诚实的是拒绝思想。
反对我所反对的
有一种人,他的观点和态度只有一个,就是反对。你说什么他都反对。但你说他刚刚说过的话时,他也反对。你和他对证,这是你自己说的呀?他说反对我所反对的。西方曾批评中国的中庸文化是转椅思维,反对我所反对的可见一斑!有人把这种思维提高到辩证法,但尼采批评说,辩证法是颓废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装置艺术的启示
今天,装置艺术打破了艺术品存在的主体性边界,在开放和带入性的艺术场域中,艺术不再谋求对风格的确立,即一种靠自我确立和重复来标定的特性。比如在卡巴科夫《获得苹果的20种方法,倾听莫扎特的音乐》中,每一个空着的椅子都是为观众设置的,而可能只有唯一的苹果属于卡巴科夫。装置作品在展示中完全摆脱了艺术家的控制,成为它自己的目的和动力,它抛弃了一切和成功学、功能学上有关的陈词滥调,使艺术成为无限敞开的领域。这是人在存在的层面日益陷入各种困束后(城市化、现代化、商业化、技术化)眺望无限的一种现实处境。艺术的变化不是作为形式的改头换面而出现,而是存在的形态和生命的样态多元化的显现。这意味着艺术的无限是生命存在对程式化生活的超越和抵抗,意味着对一种被忽略的隐秘的细微现实的洞见,意味着对多样化个性的凝视和尊重。当然,如果从福柯的角度来看,这也未免不是对语言权力的有效反抗。
开端创建:回到起源
诗歌写作进入到了一个开端创建阶段,即诗人克服谱系的约束,努力从源头建立自己的诗学。这是有责任感的诗人对写作的担当,也是开发语言可能性、拓展汉语的表现力和丰富性的一种冒险。写作的这一使命性不是今天才有的,这是历史性形成的诗人认同。相对诗歌在事件上具有的时代特征,诗歌的语言特征更具有时代的标记。同时,由语言和形式构筑的历史叙事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今天谈论史诗、悲剧一样,语言和形式从没有孤立于时代而存在,尽管它是超时代的,但我们总是愿意把它们视为自己的起源,视为与我们生命和灵魂夕夕相伴的东西。
在诗里,哲学不是死的
在诗和艺术的问题上,哲学并不带来建构,而是洞穿,它相对结构的部分,更是一种离散的力量,通常人们认为哲学显现的是那核心的东西,比如本质或灵魂,实际上哲学使唯一性瓦解在对艺术的随想之中。我们并不是带着要证明什么或者肯定什么的目标进入到对艺术的哲思中,相反,我们一开始就满怀不确定的兴趣和好奇心探究奇迹的存在。马拉美认为诗歌是偶然性的产物,但在偶然性中包含了无数的思想。这里的思想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衍生出的语言样态,与其说它是思维的,不如说它是感觉的、印象的、想象的,甚至无意识的。就像我们朝平静的湖面丢一块石子,湖面会呈现出无数扩散的涟漪。哲学的石子是涟漪的制造者,是的,我们如果从古老巫术看待哲学和诗歌的分化,就不难发现诗与哲学拥有同样的血缘。现在,我们要做的也许不是回到巫术时代,但我们已经找到了将诗和思合而为一的路径:一种跨界漫游!
语言始终是待解的谜
语言和我们是一种共在,语言并非先在完美(当然,对一个成熟的诗人而言,也绝不是拉康基于婴儿心理的镜像存在,以及所谓语言说我们这样的被动存在),语言是在人的不断表达中丰富起来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的本能,人存在深度和表层的语法结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语言是被创造出来的。语法仅仅规定了语言的一般规则,在不可言说层面,语言是非法的。非法不是说不可言说的语言不需要秩序,而是说它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即由它自身构建起的以此为范例的秩序。尽管它由诗人完成,但如果它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秩序不能成立,比如符合诗意的原则或符合美的原则,那么,这个秩序就不会有语言存在的生命力。正如很多隐秘的事物我们看不到一样,不可言说的语言依托并揭示的正是这些隐秘事物的存在。
“走路”与“舞蹈”
今天汉语诗歌存在两个硬伤,一个是白话运动造成的语言标准下移(以大众语言为尺度),一个是散文化(走路)造成的汉语“舞蹈”(瓦雷里语)诗性的丧失。
今天的诗歌越写越 唆,语言肤浅臃肿,过分迷恋叙述日常琐碎事件,这一切都是诗歌散文化的症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