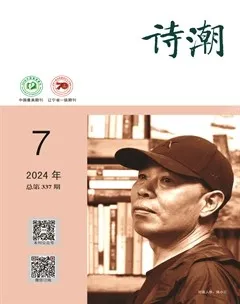馅 [组诗]
秋天的淘宝
我的购物车上是一把
削玉米的小弯刀
通知说,正在派送途中
从遥远的威海
那是一座海滨城市
年轻时我去过
秋天的海水
像一把弯刀削痛了
我的眼睛。在长江中下游
的一个平原小镇,秋天的
快递员,要投递的更多的是
枫叶,枫叶般的船桨
和鲜红的苦瓜
秋天的药品
如果一首诗
是一个有效的药方多好
我会小心翼翼地写下每一个字
让它精确无比。而我现在只能
无奈地写下我知道的
所有治疗咳嗽的药品的名字
复方甘草片,牛黄蛇胆川贝液,
百令胶囊,右美莎芬,复方福尔可定
口服液,强力枇杷露,蛤蚧定喘丸,
养阴清肺膏,布地奈德,沙丁胺醇
百合固金丸,桑菊感冒片
还有我的祈祷,在深夜
它会一直醒着,不停地念叨
它就是光,就是陪伴
愿这些都发挥药力
让世间永远没有咳嗽
馅
秋天的绞肉机里
不能有一丁点儿骨头
否则,再锋利的转刀片
也会发出咔嚓的刺耳声
整个绞肉机则会猛烈地抖动
你能发觉吗?
秋天旋转得慢一点
那些骨头碎成粉末的声音
你未必能听见
花瓣和水的骨头
怎样粉碎的,你想
俯在河面和树根去听吗?
这艳阳高照的秋日公园
落日的馅儿如此耀眼
秋天的机油
摩擦,轰鸣,震动,旋转
直到七百多摄氏度,甚至达到一千摄氏度
有氧化,有分解,有断裂
结束这一切的,只有秋天
灌下的机油。你可以看到
污浊的剩油被清除干净,时间的铁轴
在降温,转速变慢。深夜,
一只竹蛉的叫声,不能为秋天提供动力
但可以为一首诗提供动力
秋天的G3120高铁
经过昆山时,我与邻座的
一位中年妇女开始聊天
她是邻县蕲春株林镇的
带着一个小女孩儿,小女孩儿
睁着大眼睛,有些羞怯
车厢外的荷塘一闪而过
秋天的绯红令人心动
她说:“去上海旅游真好。”
她是带孩子去看病的
在秋天,一列飞驰的高铁
散发着艾草焚烧的浓烈气味
乡村的树林,一堆彩色的积木
哗啦啦地向后倒下去
记忆只是一堆盐
秋天的海在枯竭
盐,鱼骨到处都是
你讲不清的过去
破碎,闪亮
也许你已忘记在乡村
的焦虑时光,去小镇排队购盐
那些愚蠢的做法
现在想起来,可笑又温暖
你再也不会谈起大海
记忆只是一堆盐
雾
起雾了,鸟美丽的眼泪在其中闪烁
远航的人,看到了航标
一座寂然的城市,睁着巨兽的眼睛
向月亮港靠近,那是致命的欢乐剂
如果祈祷可以消灭咳嗽,我可以
一个夜晚,把整个天空写满诗
那些雾,也许可以变成一颗橘子
凭借它的香味儿,获得安宁
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秋天
突然发大水,河边的人多起来
雾在梦中散去,船走过的路
留下长长的塔影,在水上写的字
在天空写的诗,那些消失的动荡
压弯了石榴树的枝丫,秋天沉甸甸的一个笑
秋天的停车场
密密麻麻的车辆中
终于有一辆开走了
空出一个停车位
双河口的湖面上
起风了,有浪了
有一只水葫芦
从集体的葫芦丛中脱离
开始自西向东漂浮
秋天,那些紧挨在
一起的事物,有了松动
留出刀光一样的白
秋天的铜号
两个傍晚散步相遇的人
谈到一个熟人,其中一个说
那个人死啦,得喉癌死的
那个人我也认识
他喜欢在落日下的江边树林里
一个人唱歌,不唱歌的时候
就吹铜号。秋天的晚霞
被他吹落在江面
现在他死了,晚霞也灿烂地
覆盖在他的身上,像面旗帜
覆盖着秋天的烈士
秋天的秋葵
有一块菜园的人值得羡慕
相比那些种茄子辣椒的人
我会学着种植秋葵
这符合我一贯的想法
总喜欢做一些新鲜的事
我知道,我的父亲
一生都没有种植过秋葵
只有这样,每天早上起来
我才会保持
持续如初的生活热情
秋天的呼叫
一个人走到山的背面
没有一户人家,河水空荡荡
地清澈,天地无怨
这是一种怎样的吸纳能力?
一只黑水鸡在持续地啼叫
恍惚间,母亲呼喊着乳名
正是昨日,把母亲从乡下接过来
我在三楼晾晒衣物
突然听到母亲在喊我的小名
比黑水鸡的叫声更高亢、强烈
那是一种来自湖泊山林的自然之口
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小名
那一瞬间,似乎从山顶返回
又成了一个贪玩的小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