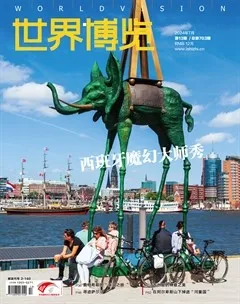在棕榈树荫下:西巴布亚原住民和他们的“森林亲族”


从方便面到润肤霜,配料表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成分——棕榈油。棕榈油因其稳定的性质、广泛的用途和低廉的价格,成为当今世界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植物油。然而,这个成分表里司空见惯的小小名词背后,却牵连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那是西巴布亚原住民马林德人(Marind)和他们的“森林亲族”的生命世界。
油棕树的疯狂扩张
西巴布亚省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端,属于热带雨林地区,地势低洼且平坦,蜿蜒的河流随着季风性降雨的节奏涨落。除了众多鸟类,还有鹤鸵、树袋鼠和鳄鱼等大型动物栖息于此。
2006年,印度尼西亚取代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出产国。棕榈油从油棕树(oil palm)的果实榨取而来,但油棕树并非印度尼西亚原生物种,而是从非洲引入。作为经济作物,油棕树在印度尼西亚的种植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直到70年代后才开始迅速扩张。西巴布亚省的原始热带雨林被开垦成为油棕树种植园,并由不同的跨国公司承包运营。
人类学家赵家芳(Sophie Chao)曾在2011年任职于国际人权组织。她深入西巴布亚的比安河上游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以记录油棕发展项目对环境和当地社会的影响。在村民们隐晦含混的表达中,她得知,在马林德人的村落,油棕树被看作一种现代图腾,它使时间停滞,使雨林流动的空间变为线性的世界。
在结束人权组织的工作后,赵家芳在2015年重返比安河上游地区,开展了18个月的民族志田野调查。通过探究马林德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她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马林德人如何定义这种由油棕树带来的社会和环境转变?这一转变如何重新建构马林德部落内部的人际关系及他们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在地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今天,这种植物与人类的动态关系又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他物种的纠葛?

多物种的生命世界
2022年,赵家芳出版了她的著作《在棕榈树荫下——西巴布亚的多物种生成》(In the Shadow of Palms—Becoming More-than-Human in West Papua),重现了马林德人的故事并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在本书中,她将马林德原住民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视角与阐释框架,去呈现、探究在油棕树种植园的扩张下,比安河上游村落的多物种生命世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便是Abu-Abu,这个巴布亚马来语词汇的含义接近于“灰色”或“不确定”。它表达了马林德人面对油棕树入侵最直观也是最富洞见的认知。Abu-Abu是介于白色与黑色之间的颜色,赵家芳将Abu-Abu与一种生命本质层面的特质连结在一起——对位(contrapuntal)或复调(polyphony)。对位法(counterpoint)本是一种音乐创作技巧,表示在同一段乐章中同时融合两个独立的旋律或声部。它们相互交织,呈现出和谐或冲突,最终产生强有力的戏剧张力。对于生活在油棕树荫下的马林德人,现代性的强势入侵与他们的多物种的生命世界构成了这一复调的两个基本声部。出于巧思的偶然抑或研究对象的必然,赵家芳也是根据这一对位法架构起全书的8个章节。两个基本声部在4个主题下——空间、动物、植物与时间——将雨林原住民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两个章节之间则是以马林德人对于梦境的叙述作为间奏。
其中,第5章《与西米椰棕相遇》和第6章《油棕树的对位》最能体现这一对位法的结构原则。西米椰棕(sago palm)是马林德人主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种原生于巴布亚雨林及太平洋群岛的棕榈树。它的树干内储存大量富含淀粉的汁液,经过加工,可制成颗粒状的西米。对于拥有多物种世界观的马林德人,西米椰棕不只是食物来源,更是他们的亲族。他们将西米椰棕和其他雨林动植物看作具有意志的存在,赋予它们或慷慨或崇高的人格。他们称西米椰棕为Amai,即祖父母。每一个马林德部落都与一组动物或植物Amai紧密相关,他们的名字也通常来自这些植物或动物,并以“-ze”结尾,意为“谁的孩子”。马林德人与动植物Amai的关系遵从互助与交换原则。Amai支持他们生存,而他们在雨林中与Amai相遇时需要表示敬畏或举行仪式。 通过在西米椰棕树丛中行走、收割、进食、吟唱、聆听,马林德人超越了人与自然的边界,将自己与雨林万物合而为一。即便是作为边界象征的皮肤,在马林德人看来却是与人类之外的生命联通的器官。触摸西米椰棕的树皮即是交换皮肤(exchanges of skin),通过劳动提取树汁,制作并进食西米则是交换体液(exchanges of wetness)。


同样,马林德人认为油棕树也会具有情感与道德。在他们的叙述中,油棕树是自私的,贪婪的,残暴的,孤僻的。它拒绝与雨林的其他成员交换皮肤与体液,拒绝与其他生命共存。它吸干了河流,污染了空气,杀死了西米椰棕和其他雨林中的Amai。然而,在第六章《油棕树的对位》中,赵家芳敏锐地捕捉到,马林德人对于油棕的评价并非静态与决绝。西米椰棕与油棕,这看似对立的两极,在原住民多物种的世界观中,呈现出了对位的张力,也就是Abu-Abu。在怨恨油棕的同时,马林德人也对它充满了好奇。对于他们来说,油棕是自私的,同时也是神秘的。一位马林德的教师说,现在油棕遍地都是,但它死死守护着自己的秘密。尤其是当一场植物病害席卷种植园的时候,大量油棕枯萎病死,马林德人对油棕树甚至产生了怜悯。一位年长的村民在去世之前的几天告诉赵家芳:“油棕树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不懂它的皮肤。”多物种世界观与对位法的认识论,让马林德人做出理解并联结油棕树的尝试。这种尝试在现代进步主义价值观与马林德人前现代生命世界的两极之间拨开了一小块协商的地带。
在结论部分,赵家芳强调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意在揭示当前多物种研究与后人类理论的局限。通过呈现比安河上游原住民社会中人类与植物的纠葛,赵家芳提请研究者们注意,在多物种研究中,植物并非总是受害者,而人类也并非总是行凶者。忽视这一事实将会限制我们去思考多物种互动中可能存在的暴力,导致对于多物种互动不加批判的赞同和另一种人类例外主义(认为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或者说是例外性的存在)。同时,马林德人的案例告诉我们,人类的类别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态的。马林德人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努力维护自己作为人类的尊严与边界。
棕榈油及其制品的全球流通让我们与马林德人的世界以千丝万缕的形式相连。
(责编:刘婕)
后人类主义
posthumanism
产生于21世纪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的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和思考。后人类主义思想继承尼采的“超人”哲学与福柯提出的“人之死”,可以视作后现代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与延伸。它所涵盖的议题广泛,包括反思传统人文主义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讨论人工智能和控制论下的超人类前景及伦理,以及跨越技术边界的人类本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