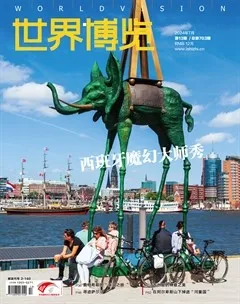妃子革命:末代皇帝溥仪离婚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仅仅数月时间,就风卷残云般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廷商定了《清室优待条件》,其中第一项确定了皇帝退位后尊号保留、银钱照顾、住处安排等事宜。
清朝灭亡后,1908年即位的溥仪(宣统帝)尽管大权丧失,荣光不再,但在紫禁城,溥仪仍是人人尊崇的小皇帝。1921年,溥仪16岁,到了婚配之时。
落魄的皇室
溥仪的生父载沣和其他王公大臣议定,要为溥仪选定皇后。消息传来,文绣的五叔华堪希望能够借此良机光耀门楣,重振宗族,就把文绣的照片送到内务府。文绣本是皇后人选,但经过反复博弈,文绣成了唯一的皇妃。被选为皇后的则是郭布罗·婉容。
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婉容一天与溥仪成婚,被册封为淑妃。毕竟都是不到18岁的少年,溥仪与婉容、文绣经常一起玩耍,如去景山游玩、学习骑自行车、学英语等。婉容贵为皇后,再加上她性格外向,天真活泼,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更为溥仪喜爱。婉容的一兄一弟分别娶了溥仪的两个妹妹,这让两家的关系更是亲上加亲。文绣秀外慧中,也知书达理,但终究还是无法与婉容相提并论。好景过后,文绣便觉内心苦闷,生活压抑。这时发生了著名的“逼宫事件”,为后来的诉讼离婚提供了可能。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总统曹锟。11月5日,冯玉祥部下鹿钟麟奉命将溥仪及其他皇室贵族驱逐出宫。清朝皇室正式离开了居住200多年的紫禁城。
出宫之后,溥仪先住在了醇王府,即父亲载沣的住处。由天子降为平民,溥仪极不情愿。他身边集结了郑孝胥、胡嗣瑗等一帮保皇派,密谋依靠内外势力,恢复清朝政权。在诸国之中,他们认为日本最可依赖。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护送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当天为农历二月二龙头节,选择这天出发,大概也有龙抬头、复大统的用意吧。
溥仪到达天津后,先入住于张园,婉容、文绣随后赶来会合。在张园居住了4年多,溥仪又迁至乾园。与张园一样,乾园也大有来头,曾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府邸。溥仪入住后,改名为静园,取“静以养吾浩然之气”之意(溥仪号浩然),“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如果说在紫禁城时只是心有嫌隙的话,那么到了天津,居住在静园这样一个地狭人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地方,文绣与溥仪、婉容的矛盾越发严重。溥仪仍旧偏爱婉容,物质上两人月银数额不均,感情上更让文绣倍感冷落。在内,溥仪与婉容住在二楼,文绣住在一楼的偏房,后来连就餐也不再同桌;在外,溥仪外出时经常携婉容为伴,忽视文绣。久而久之,溥仪身边的仆人也看不起文绣,大有轻慢嘲讽之意。
1924年1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前三条规定:“大清宣统帝从1924年10月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某个除夕夜,溥仪、婉容等人在楼上热舞蹈歌,其乐融融,文绣却独守空房,好不落寞。一时间悲从心来,万念俱灰,拿起剪刀就朝腹部刺去,希望以此结束生命。幸好有一太监及时发现并阻止,才不致悲剧发生。溥仪知道后非但没有好言安慰,反而语出讥讽,让人不要理她。
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曾赞赏过文绣的一篇文章《哀苑鹿》。讽刺的是,文中的句子却可作为文绣心绪的准确写照:“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于囿内不得其自行,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出也。”
逃走的妃子
在灰暗孤苦的日子里,文绣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妹妹文珊的陪伴。文珊的婚姻同样不幸福,丈夫身为八旗子弟,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姐妹互相倾诉,彼此安慰,让苦闷抑郁的情绪暂时有了缓解。
文珊把一个名为玉芬的女子引入了文绣的生活。玉芬为其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还是冯国璋的大儿子冯家遂的妻子。玉芬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独立,在丈夫外有小妾,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的时候,勇敢地选择了离婚。她告诉文绣,现在是中华民国,如今的溥仪只不过是民国的一个普通公民,不再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可以根据《中华民国民法典》请求离婚。
1931年8月25日,文珊禀告溥仪,说姐姐心情烦闷,希望可以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同意了,但要太监赵长庆跟着。文绣和文珊出静园后,指令司机前往天津国民饭店。到了国民饭店37号房间后,文绣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信件,让赵长庆带回去,跟溥仪说自己决定与他离婚,并且还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赵长庆听后惊骇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只得赶紧回去汇报。文绣准备得十分周全,她还聘请了李洪岳、张绍曾、张士骏这3位天津卫的大律师。
溥仪知道后亦大惊失色,赶紧派人前往国民饭店去接回文绣。但等着他们的只有3位律师告诉他们文绣女士不会再回静园,让溥仪考虑下她提出的条件。溥仪无计可施,只好听从郑孝胥、胡嗣瑗等人的建议,派出林綮、林廷琛2位律师出面谈判,希望能大事化小,不要闹上法庭。
8月28日,文绣以及双方律师在法租界的庞纳律师事务所正式展开谈判。文绣提出5个条件,并提醒道:“如不能照允,立即起诉,三日内务即答复。”为了给溥仪施加压力,文绣的律师29日就向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提起诉讼,法院也向溥仪下发了传票,告知他9月2日赴法院民事调解处进行调解。这让溥仪方律师很是气愤,责问对方为何一边调解一边起诉。这正是文绣方的策略,以诉促调,尽快达成圆满结果。
尽管溥仪方严格保密,这一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嫔妃向皇帝提出离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大事,简直闻所未闻。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有人套用当时流行的革命叙事,将文绣的举动视为“妃子革命”。这也是溥仪害怕出现的局面,因此逐渐失去耐心,想尽快达成协议。
10月22日,文绣、胡嗣瑗及双方律师于庞纳律师事务所正式签订协议:“(一)文绣自立此约之日起,即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二)清皇室主人于本件签字之日,给文绣一次终身生活费五万五千元(付款另有收据);(三)文绣于本件签字之日即将所有随身常用物件(另有清单)全部带走(付物时另有收据);(四)履行二、三两条件之后,文绣即归北平母家独身念书安度,绝不再向清皇室主人有任何要求;(五)脱离之后文绣不得有损害名誉之事,双方亦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之事;(六)文绣将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之申请撤回,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七)本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共缮四份,当事人各执一份,双方律师各执一份。”
至此沸沸扬扬的溥仪离婚案终于落下了帷幕,双方虽没有对簿公堂,但经过司法程序即法院民事调解处调解后,达成了庭外和解。事了之后,溥仪自觉颜面有失,遂写下“圣旨”:“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放归母家居住省愆。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思量一番后,删去了“放归母家居住省愆”,并不惜重金于第二日在北京、天津、上海报纸的显要位置刊出。这件事成了街谈巷议的趣闻。
本案并非溥仪唯一的离婚案。1957年,李玉琴向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对象即为溥仪。原来,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后,1943年将15岁的李玉琴纳入宫中,册封其为“福贵人”。日本战败后,溥仪被捕,从此两人十余年没有见过面,因此提出离婚。
女性的解放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女性意识得到了启蒙,曾有人统计过,《新青年》共7卷42期文章中,有35篇谈到了女性问题,包括女性的教育、自由恋爱、婚姻、贞操、解放等话题。
知识分子的倡导,报纸杂志的宣传,尤其是一些敢为人先的女性的实践,如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黄逸梵(张爱玲的母亲)等,大大解放了女性的思想,也让她们敢于冲破封建旧制的禁锢,对不幸的婚姻说“不”,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地方还掀起了离婚热潮,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
玉芬无疑也是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又将其灌输给文绣。文绣离婚后,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回到北京,恢复了傅玉芳这个名字,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军官刘振东结婚。1953年傅玉芳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终年44岁。
(责编:刘婕)

额尔德特·文绣,生于1909年12月,蒙古族人,字蕙心,号爱莲。她为额尔德特氏蒙古族之族裔,该族在满洲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其祖父辈曾官至吏部尚书,为朝野权臣。至父亲端恭时,家道已然中落,只能在内务府谋得一官半职。文绣母亲蒋氏为汉族人,文绣是长女,还有一妹妹文珊。父亲去世后,母亲便迁居至崇文门外的花市胡同,靠做些零活惨淡度日。1916年9月,文绣就读于北京私立敦本小学,并取学名傅玉芳。读书期间,文绣心思灵敏,聪慧好学,很得老师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