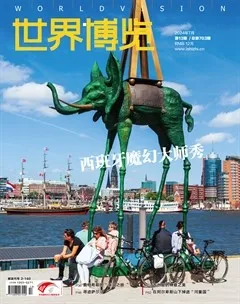寻迹萨尔浒

对萨尔浒之战的最初印象,则要追溯到小学,家里有一套中国通史连环画,一直以为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所著,但多年以后,仔细检索,才发现老先生只是为它题写了书名。当然,这不重要,通史也不重要,当时最痴迷的是在书上蒙一层几近透明的薄纸,照描绣像人物。印象尤深的是绰号“大刀”的明朝将领刘綎,横刀跃马,雄姿非凡。也是几年后认真读书才知道,就数这位在萨尔浒的结局最为惨烈。
抵达辽宁省抚顺市东郊的萨尔浒风景区,一眼望去,绿意盎然,没有一丝一毫古战场的影子。也不奇怪,史书上流血漂杵之地,现在大多碧水青山,再激烈的大战,对于广袤大地而言,或许只是擦破一点皮。当热心导游告知,萨尔浒古战场已经被大伙房水库淹没之时,不禁大失所望。平时还能远望城垣或山丘怀古,此刻只剩一池秋水。
不过,来都来了,追古抚今,观察一下山形地势,总归不虚此行。努尔哈赤(1559—1626)时代,女真人定都赫图阿拉(今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此地东南山高林密,唯有西北一隅地势较低,苏子河沿着沟川逶迤向下,直抵萨尔浒。战斗爆发之地,距离都城赫图阿拉大约75公里,其间多是崎岖山路,不利于八旗铁骑纵横驰骋。熟知用兵之道的努尔哈赤选择将前哨阵地前移,扼守门户,抢占地利。况且,萨尔浒水草丰美,足以喂养女真人数万匹战马,解除了后顾之忧。
面对女真人,明朝就没那么从容不迫了。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敲定平敌之策,大战一触即发。万历三大征后,明朝日渐疲敝,在辽东已是力不从心。没钱,政府就加征饷银,摊派到全国各地。没兵,就加紧抽调,浙江四川都要派人,蒙古叶赫部和朝鲜也不放过。层层加码、东拼西凑之下,杨镐手里终于攒出20万大军,对外号称47万,浩浩荡荡出发。按照作战方针,分进合击,四路会攻,矛头直指赫图阿拉。女真人御敌之法,正是那句: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6万女真骑兵将20万明军各个击破,一举逆转辽东局势。
少时读书,不求甚解,在看不到古战场的萨尔浒浅游一日,才特意关注明军因何溃败。当时初入职场,刚学会复盘总结,我煞有介事地归纳四路大军的致命弱点:急、怯、莽、猾,仔细想来,也有几分贴切。
西路军担纲主力,主将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这是一员不服老的勇将,镇守陕西多年,身经百余战,塞外人称“杜太师”。明军原定会师之日是农历三月初二,杜老将军急于抢夺头功,率军冒雪急进百里,孤军深入,提前三日到达战场。安营扎寨后,他不待友军消息,派1万人马抛下火器辎重渡河强袭,端掉女真两个营盘,总计杀死数十人。
上游的努尔哈赤反手毁坝放水,卷着寒意的春水倾灌而下,让明军折损千余士兵。午夜时分,决战打响,举着火把作战的明军,成了女真弓箭手和骑兵的活靶子。明军阵脚大乱,杜松死于混战之中。枪打出头鸟,冒进的杜松开了坏头,搭了性命,在朝堂之上也背了大锅,安在他头上的罪名是“先期竞进,抛弃火器,刚愎自用,背水而战”。
时间到了三月初二,只有一支军队谨遵将令,如期抵达战场,那就是马林麾下的北路军。这位马林,是位“将二代”,父亲马芳抗击蒙古几十年,《明史》称其“斩馘无算,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虎父无犬子,马林也是一表人才,性情刚正不阿,敢于反抗搜刮民脂民膏的税监,无惧触怒龙颜。只可惜千好万好,唯独领兵上阵不灵。未抵战场,马林就发现杜松的残兵,即那支被抛下的辎重部队。得知能征惯战的老将军已然殉国,马林未战先怯,但军令如山,又断然不敢后退。
他只能采取守势,把麾下一分为二,加上杜松残部,组成品字形,互为犄角,等待援军。乘胜追击的努尔哈赤,不给明军喘息之机,趁对方立足未稳,从山巅俯冲下来。马林的军队原本列阵迎敌,依次排出弓箭手、骑兵与枪炮营。然而,女真骑兵实在太快,明军来不及集结,就被冲散。以诗词书画闻名的马将军,没见过这阵势,心里一慌,带上几个亲兵落荒而逃。他逃得太急,连儿子都顾不上,二子战死阵前,挽回一些武将世家的颜面。至此,萨尔浒战事告一段落,两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努尔哈赤马不停蹄驰援赫图阿拉方向。
事后诸葛亮来说,努尔哈赤有赌的成分。从抚顺萨尔浒到明朝东路军逼近的本溪(今辽宁省本溪市)一线,如今驾车只需2小时,如果骑上跟战马速度相仿的电动小摩托,则至少需要8小时,这还得有现代公路加持。但女真人赌对了,明朝猛将刘綎进军迟缓,没能在萨尔浒激战之际直取守备薄弱的赫图阿拉。由于兵力尽在西线,努尔哈赤东路仅调拨数百人沿途砍树拦路,希望用这种原始战术阻挠敌人。
没承想,明军更不争气。刘綎本是一代名将,从缅甸到朝鲜、从云南到贵州,戎马半生,少有败绩。但兵马未动,东路军已是困难重重。刘綎帐下士兵抽调自川鄂闽浙,东北三月春寒料峭,避寒衣物寥寥,士气难免低落。他们还分到最差的军械,遭到前来助阵的朝鲜人在汇报里无情嘲笑:“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师为恃”。这要怪偏心的杨镐,他在朝鲜战场与刘綎结怨,借机公报私仇,配最烂的武器,分最远的路线。嘲讽明军的朝鲜人,自己也是拖油瓶,三天两天缺米下锅,还得靠刘綎派人救济。
更匪夷所思的是,一条乱枪打鸟的诡计,竟然变成扭转战局的奇谋。原来,努尔哈赤找了一个看起来还算机灵的明军俘虏,让他快马奔至刘綎营帐,谎报杜松稳扎营盘,专待东西夹攻敌人。这是个扰乱军心的损招,本来成功概率不大,毕竟萨尔浒战况惨烈,各路明军想必有所耳闻。吊诡的是,杜松马林之败,刘綎全然不知,还跟战俘约定以炮声为号,同步发兵。

一代名将,不知军情,不辨真伪,已经很要命了。听闻远方三声炮响,刘綎下令轻装疾进。明军在山地作战,一向是步步为营,以鹿角御敌。所谓鹿角,是把树枝或长枪绑在一起,挡住营帐或行阵侧翼,避免骑兵突袭。主将之莽,令东路军钻进女真人的埋伏圈。时机成熟,努尔哈赤从山岗俯冲,山谷里无处躲避的明军一触即溃。最后关头,刘綎展现猛将风范,双臂和脸颊皆遭重创,依旧大刀挥舞,砍翻几十人,力战而死。养子背上他的尸首,徒手杀敌,可惜未能突围。
四路大军折损三路,还在磨蹭的南路军李如柏,索性撤退。这位将门虎子,将“猾”演绎得淋漓尽致。父亲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兄长李如松入朝抗倭扬名,他自己跟随父兄征战,却混成官场老油条。坐拥辽东子弟兵,守着最易进军的路线,李如柏先是大摆宴席,与杜松把酒言欢,信誓旦旦助老将军抢下首功,后来杜松败亡不救,刘綎败亡也不救,只怕自家大军稍有闪失,以一己之私为萨尔浒彻底盖棺定论。不过,逃避可耻且无用,临阵脱逃的马林几个月后死于开原之战,不战而退的李如柏遭弹劾后畏罪自杀,纸上谈兵的杨镐在崇祯年间被翻了旧账,下狱处决。
回看萨尔浒之战,明朝兵多将广,但战略失当,前线指挥各有致命伤,难逃失败命运。努尔哈赤拥有地形和情报之利,但也在赌,赌刘綎进军慢,赌李如柏不敢战,难怪打开《满文老档》的记载,反复在说“这都是天助的事”。一个半世纪后,萨尔浒古战场迎来一位特殊客人,乾隆皇帝竖起一座长2米的青石碑,亲笔写道:“我大清亿万年丕基,实肇乎此。”这座石碑如今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算是这段历史最后的留痕。
(责编:南名俊岳)
萨尔浒之战书事碑

乾隆四十一年(1776)立于今抚顺大伙房一带的萨尔浒战场。灰白色石制。碑长240厘米、高178厘米、厚32厘米,碑座高80厘米。碑文为乾隆皇帝亲笔所作,全文记述萨尔浒之战的战事,以及清朝统治者对此战的评价。碑左侧面另外雕刻有嘉庆皇帝御笔七律诗一首。1993年国家鉴定委员会定其为国家级一级文物。
万历三大征

指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