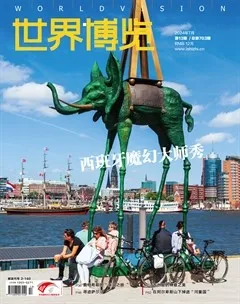探索神秘的“极北之城”

北极绒盛开的季节,我来到了挪威北极领地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朗伊尔城。风中摇曳的白色绒花让单调的苔原生动起来。一头头驯鹿正在吃草,白颊黑雁带着宝宝们在溪流边散步,朗伊尔城的年轻人喜欢在周末背上一杆来复枪、带上帐篷去野外度假……夏季的北极小镇,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在朗伊尔城,“北极熊”无处不在。除了极地博物馆,机场、超市门口,甚至酒店里都赫然矗立着北极熊标本,礼品店、皮货店里摆放着北极熊的皮毛,这些愈发激起外国游客想“遭遇”北极熊的愿望,然而当地人认为还是期待不要碰上的好。
当然,当地人必须学会邂逅北极熊时要怎样对付它。只要离开朗伊尔城,当地人都要带上枪。据说斯瓦尔巴大学的新生,入学第一周必须接受各种野外生存训练,包括射击、搭帐篷、驾驶和修理雪地摩托车,等等。自助旅行者需要明白,这里不是游乐场,而是条件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因此携带的装备要足以应付北极熊的威胁和极地气候的考验。
地球最北端的小城
坐标:北纬78度13分,东经15度37分
朗伊尔城距北极极点1300公里,是地球上人类最北端的定居点。为了对北极进行全方位的科研,各国科学家聚集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一大批极地科考站和研究所,朗伊尔城也逐步发展为全球最北的以极地研究闻名的城市。这座2000多人的市镇虽小,但设施完备,邮局、学校、托儿所、银行、医院、报社、酒店、商场、博物馆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街道上,遛狗的、跑步的、买菜的,生活似乎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的房屋多是简易房,鲜艳的外表与极地单调的自然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因为这里是冻土,所以管道都是架在空中的。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冒险家”乘船渡海前往斯瓦尔巴群岛,挪威人和俄国人作为探险先驱,先是捕鲸猎熊,后来渐渐转向开采煤、磷灰石、石棉等矿产资源。北极地区煤矿资源十分丰富,随着20世纪初美国矿主朗伊尔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跑到这个冰雪覆盖之地开掘煤矿。市镇附近的山坡上依旧可见一些煤矿旧址,废弃的矿车和采矿人的小屋就散落在那儿。镇子中心那座矿工雕像,不知被何人“点了睛”,本来沉重的历史纪念物顿时诙谐起来。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环保意识,肆意开采使北极晶莹的雪山变得“灰头土脸”。后来政府干预,环境才大有改善,7个煤矿现在已有6个处于停产状态。煤矿对当地生态环境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据说斯瓦尔巴群岛上空的一条轻污染云带,就是火力发电厂造成的。这座发电厂用本地产的优质煤来供应全岛的电力,据说是挪威目前唯一的火力发电厂。朗伊尔城出产的煤炭曾经温暖过整个挪威,而今这里的科学家正在为如何捕获和封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阻止全球变暖而努力。极地的生活,继续前行,只是以一种更文明和环保的方式。
如今,已远离开采业的小镇备受户外运动者和游客的青睐。每年的4月到10月间,从世界各地涌来的2万多名游客,不是登上邮轮开始海上旅行,便是背起帐篷加入野外探险的大军。
在登船之前还有大半天的时间,我叫了辆出租车,去稍远的山上转转。朗伊尔城郊外的一处山顶上用于科研的仪器中,据说有一个是中国研究机构架设的。车子向镇子外面驶去,人越来越少,动物越来越多。几头驯鹿正在不远处吃草。北极,并非寸草不生的荒野,虽然没有乔木、灌木,但有各种草本植物、苔藓和地衣。北极绒毛茸茸的白色小花铺成雪白的“绒毯”,绒球里包裹着种子。


路途中经过一个雪橇犬基地,因为是夏季,雪橇犬都被暂时关到栅栏里,见到有人经过便咆哮起来,这些需要大运动量的狗狗,在夏季的“失业期”有些焦躁不安。斯瓦尔巴群岛有包括朗伊尔城在内的5个居民点,冬季的时候,居民点相互间只能靠直升机或雪橇等交通工具来往,那时雪橇犬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坐着雪橇出城去,在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几条痕迹起起伏伏慢慢伸向远方,远处的雪山在低温下泛着蓝光,这才是北极的生活。
北极科考大本营
坐标:北纬78度55分,东经15度56分
登上极地邮轮航行两天后,我进入了更北的新奥勒松——北极科考大本营。新奥勒松位于斯皮茨卑尔根岛西北最大的峡湾——康斯峡湾的南部,此地有着巨大的北极苔原、积雪覆盖的群山,还有深入海洋的雄伟冰川,一片典型的极地风光。
新奥勒松昔日是一处煤矿开采地,苔原上星罗棋布着几十栋简易房屋。1962年的一起矿难终止了这里的采矿史,1964年,挪威政府在此设立卫星接收研究中心,成为第一个在此建北极站的国家。此后,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国纷至沓来,近几年,又增加了中国、美国、韩国、印度等国的考察站,新奥勒松俨然成为北极科考的大本营。



新奥勒松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体温计”,挪威政府将这里发展为专门的科学研究区域,禁止游客和其他人员在此过夜或长时间逗留,从而保持了较为完整的原始地貌,方便科学家对北极展开研究。盛夏,各种极地研究活动频繁展开,我看到,有科研人员正在湖边提取样本。游客需要特别注意:不可以随意触摸任何野外放置的科考设备,也不可以惊扰哺育期的鸟儿。新奥勒松也是鸟儿的家园,苔原上有不少鸟巢,尤以白颊黑雁和北极燕鸥最多,游客徒步时要特别注意。
鉴于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挪威政府在新奥勒松实施了近乎苛刻的环保措施:这里的垃圾分类已经达到25种之多,剩饭剩菜就地掩埋,其余垃圾都要运到挪威本土进行处理。新奥勒松不欢迎普通旅游者来访,游船可以在这里的港口停靠,但游客不得上岸过夜。挪威政府不允许各个站点自己开伙,统一由挪威的国有企业王湾公司——这家此前主持此地采矿工作的公司负责向各国考察站提供食宿等后勤保障,一来方便各国队员集中精力从事科考,二来也可以有效管理,避免环境污染。于是这座“大食堂”便成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交流的场所。
我找到中国北极黄河站所在的那栋二层小楼,门口有对石狮子的便是。2004年7月28日是北极黄河站诞生的日子,马上就要过20岁生日了!这是中国继南极长城站、南极中山站两站后的第三座极地科考站,中国也成为第八个在斯匹茨卑尔根群岛建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中国北极黄河站拥有全球极地科考中规模最大的空间物理观测点。
新奥勒松虽然没有常住居民,但邮局、酒吧、小卖部、码头、机场一应俱全。只是居民稀少,酒吧和小卖部都是定期开放的。对于游客来说,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在“地球最北”的商店淘纪念品,或是在“地球最北”的邮局寄出一张明信片。
现在的新奥勒松尽管从地理位置上与世隔绝,但它却以相当丰富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北极村”的居民们并不孤单,他们时刻向外界传送着关于极地的数据和信息,是这个美丽星球的一个缩影。
(责编:昭阳)
·北极绒·
北极绒在当地俗称“雪绒花”,像蒲公英,借助风力传播种子,7月底8月初正好是盛花期,与北极地区的其他显花植物一样,为了充分利用短暂的夏季,北极绒可以在两个月甚至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开花、结果的生命周期。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
虽然中国不是北冰洋地区的国家,但1925年生效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已经规定了中国进入北极的合法性,中国也是42个缔约国中的一员。该条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国民有权自由进入北极,并在遵守当地法律的条件下平等从事海洋、工业、矿业和商业等活动。北极不是免费的生态博物馆,厚厚的冰面之下,北极的宝藏总有一天会被发现,但保护环境与持续发展需要理性。在开发的同时,给后代留存一个纯净的北极,是今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