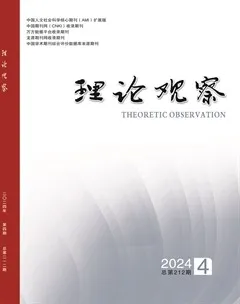民法典时代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体系衔接与适用标准
摘 要: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较早适用并逐渐扩展至其他侵权行为类型,彰显了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范引领价值。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包括惩罚、威慑以及充分救济三项内容。现行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范体系涵盖了《民法典》 《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在衔接适用时应结合产品类型、责任主体以及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妥善协调规范竞合问题。司法实践中为了合理发挥惩罚与威慑的作用,《民法典》第1207条中的“明知”应限缩性解释为“已经知道”,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性质;对于“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可参照身体伤残标准予以认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量定应当综合考虑责任主体的主观恶意程度、缺陷产品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以及衔接不同领域惩罚性赔偿规范之间的适用关系,实现过罚相当的法律效果。
关键词: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范竞合;数额量定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4 — 0109 — 06
我国《民法典》扩展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即从原来《侵权责任法》仅限于产品侵权扩展至包括知识产权侵权及生态环境侵权。作为侵权责任体系中较早规范惩罚性赔偿责任方式的适用领域,囿于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赔偿额度不易确定等争议颇多的难题,导致长期以来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引领价值。惩罚性赔偿在产品责任领域的制度效应需要立足于其基本功能,对其功能定位存在的理论分歧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在我国后民法典时代,有关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规则,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民法典》《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不同法律领域的规范体系,如何正确理解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需要厘清不同法律领域相关规范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系衔接以及规范竞合问题。此外,为了合理发挥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范功能,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与赔偿数额量定也需要进一步明晰适用标准。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我国《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在当前《产品质量法》新修订的契机下,对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上述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希望对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规则的理解与适用提供有益参考。
一、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定位
惩罚性赔偿,是指法律规定恶意的加害人给付受害人超过其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费用,以惩罚和威慑行为人将来实施类似不法行为的一种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作为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应的赔偿责任类型,是一种兼具惩罚、激励和威慑等功能的制度。[1]自20世纪中叶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率先在美国产品责任法等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并为不少国家产品责任立法所继受。
尽管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的性质,公法色彩较强,但其仍是一项私法制度,作为一种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适用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之所以在受害人的实际损害之外对侵权人苛加惩罚性赔偿,是因为侵权人实施加害行为时主观状态存在恶意,仅依靠补偿性损害赔偿并不能有效保护受害人,更难以遏制侵权行为人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在国外,有学者主张,惩罚性赔偿具有补偿、报应和遏制三项功能。[2]可以说,惩罚性赔偿是一种目的和功能兼具多样性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对原告个人和社会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就我国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而言,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包含赔偿、制裁和遏制三项功能。[3]也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是惩罚与威慑,而惩罚只是手段,威慑才是真正的目的。[4]针对上述理论上的分歧,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当主要包含三大基本功能,即惩罚功能、威慑功能以及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功能。
第一,在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其首要目的在于惩罚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不是填补因缺陷产品导致的损害。侵权人故意或恶意伤害他人,不仅违反了侵权法所规定的一般行为准则,而且还违反了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如果未能对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施以惩罚,将削弱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结构。惩罚性赔偿的首要功能正如在一般情况下惩罚的主要功能一样,是对压迫性、恶意性、欺诈性以及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形式侵权行为的惩戒,而非一般损害的填补或者侵权行为获得利益的返还。[5]如果仅让恶意生产或销售产品的主体承担一般的补偿性赔偿责任,则难以有效起到惩罚的效果以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针对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生产、经营产品的行为,只有加大处罚力度,才能真正彰显惩罚性赔偿的惩戒功能。
第二,在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赔偿还在于对其他不特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产生威慑作用。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惩罚性赔偿责任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增加经济上的额外负担,使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更高的代价,督促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6]对于侵权行为人而言,惩罚性赔偿追求的目标在于使得实施不法行为比避免不法行为更为昂贵,从而使其产生预防损害行为的动机。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通过利益消除的方式,使生产者和销售者考量违法成本,从而真正实现最优化的遏制机制。[7]
第三,在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赔偿能够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在恶意产品责任案件中,受害人往往遭受较为严重的人身健康损害,可能由此导致残疾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受害人的痛苦。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缺陷食品和药品致人损害等性质恶劣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产品责任案件,给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安全带来了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让恶意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补偿性的赔偿责任,既不足以惩戒责任人,也不足以抚慰受害人。因此,在产品责任中的补偿性赔偿之外,针对恶意的产品生产、销售行为苛以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预防恶性产品责任事件的发生,从而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更加充分、切实的保护。
二、民法典时代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规范体系及其适用关系
我国现行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规范体系涵盖了《民法典》《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如何在体系化的视角下正确理解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及其适用关系,则是当前理论与实践迫切需要厘清的问题。
(一)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现行规范体系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以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为基础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民法典》等不同法律领域的规范体系。如何正确理解我国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需厘清不同法律领域相关规范的内在体系关联及规范竞合问题。
1.消费领域的惩罚性赔偿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最初是在消费领域予以规范的,这集中体现在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该条首开先河确立了我国私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是以缔约上的欺诈为规制对象,该条文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在性质上是属于经营者构成违约而适用的惩罚性赔偿责任。[8]如果经营者在销售产品时存在欺诈情形,则买受人可以依据此条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但是由于赔偿数额是以商品价款的一倍为计算方法,并未考虑消费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可能会存在惩罚性赔偿金畸轻的问题。
2013年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对旧法第49条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完善,既有对旧法的重要修改,也有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创新的新增规定。从法律效果来看,惩罚性赔偿金数额从原来商品或服务价款的一倍增加到三倍,并规定了最低赔偿限额,既对违法经营者加大了惩罚力度,也有助于激励受害人积极维权。另外,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规定的第55条第2款首次将消费者“所受损失”确定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标准,并吸收了《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有关惩罚性赔偿的构造要素,标志着我国的惩罚性赔偿逐渐成熟化。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体系由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个部分构成。如果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缺陷产品时存在欺诈行为,并因缺陷产品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则应当分别适用该法第55条第1款规定的欺诈消费惩罚性赔偿及第55条第2款规定的严重侵权责任惩罚性赔偿,两种性质的责任承担并行不悖,可以同时适用。
2.违反食品安全义务的惩罚性赔偿
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对生产者、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义务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进行了规定,扩宽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领域。惩罚性赔偿不再局限于欺诈的情形,而是关注于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存在违反食品安全保障义务的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率先在食品领域大胆抛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欺诈要件,侧重于对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客观不法行为进行评价,可以说是弘扬了适度倾斜消费者的现代法治理念。[9]
《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所确立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对于生产者与销售者的主观归责标准存在差异,针对销售者适用的是具有主观故意的“明知”要件,而针对生产者则采取了更严厉的无过错要件,此种区别对待的立法规范值得商榷,也与惩罚性赔偿的基本法理不相符。从《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1款和第2款的内在逻辑关联来看,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是不以造成消费者的实际损害为前提的,其适用情形过于宽泛。此外,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量定,该条仍未摆脱以商品价款作为赔偿计算方法的窠臼。尽管赔偿数额从商品价款的一倍提到了十倍,但是仍可能面临由于商品价款较低而赔偿数额远低于消费者遭受的实际损失,从而使得惩罚性赔偿“威力不足”。[10]直到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在原《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基础上,将赔偿金数额修改规定为“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并设置了最低一千元的标准。”修改后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彰显出了对食品消费者的特别保护。当然,违反食品安全义务的惩罚性赔偿规范仅适用于食品类产品,并不能扩展适用于其他种类的产品缺陷致人损害责任。
3.《民法典》中恶意生产、销售产品的惩罚性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47条首次确立了适用于所有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该条同时也是惩罚性赔偿在整个侵权责任中的开创性规定。依据该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主观上存在故意为前提条件,并且将损害事实限制在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范围内,表明立法者认识到应当将惩罚性赔偿限制适用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行为性质恶劣的恶意产品侵权行为。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量定,该条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模糊性标准,实际上赋予了法官对于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现行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体系中,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其规范思想与构造方法对研究整体性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见微知著的意义。[11]长期以来作为我国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对惩罚性赔偿没有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此条款增加了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方式,衔接了其他法律中已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符合了时代的发展需求。尽管该条款作为一种提示性的规定,只有在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实际适用,但是毕竟为我国其他民商事法律构造和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了指引,规范意义可谓重大。《民法典》第1207条在《侵权责任法》第47条有关恶意生产、销售缺陷产品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范基础上,针对生产者、销售者违反产品跟踪观察义务并且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情形,增加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此外,《民法典》还将惩罚性赔偿责任延伸适用于产品责任类型之外的领域,分别针对恶意侵害知识产权、恶意损害生态环境的侵权行为新增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说,在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立法规范与司法实践基础上,我国惩罚性赔偿责任体系正在逐渐扩展其适用范围,以增强对相关重要民事权益的保护力度。
(二)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
在我国现行有关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范体系中,《民法典》第1207条、《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均有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这些规范之间在产品类型、主观要件、损害后果以及赔偿标准等方面不尽相同。如何妥善协调上述条文规范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无疑是当前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是有关产品欺诈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其与《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民法典》第1207条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范性质有所区别。对产品欺诈规制的着眼点在于其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损害后果是合同预期利益的损失,属于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而对产品责任规制的着眼点在于行为人存在主观恶意,损害后果是受害人的人身健康等固有利益遭受损害,属于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12]当两种责任同时存在时,各规范相互之间并不影响。受害人对此可以同时主张基于产品欺诈的惩罚性赔偿和基于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民法典》之间也会存在规范竞合的关系。当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严重损害后果时,关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三种规范可能会同时成立。相较于《民法典》第1207条的规定而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2款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标准有明确的可预见性,当出现规范竞合的情形时,后者更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2款与《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的规定相比,后者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明确规定了“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并且受害人对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适用标准具有选择可能性以及最低赔偿数额的保障激励。因此,后者对于受害人的救济更加有利,应当优先予以适用。
就《民法典》第120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可能会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竞合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交叉的领域属于责任竞合的规范,并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但笔者认为,《民法典》第120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这两种责任规范在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损害后果方面均有所不同。在主观要件方面,前者要求“明知”,后者仅对经营者规定了“明知”要件,但对于生产者并不要求“明知”的要件;在损害后果方面,前者要求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损害后果,后者甚至并不要求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13]由此可见,上述两种责任规范的构成要素不具有涵括关系,[14]不应当属于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实际上,《民法典》第120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之间也会存在交叉和重叠的关系,当经营者恶意销售存在的缺陷食品造成他人伤亡的严重损害后果时,上述两种规定构成请求权规范的竞合,受害人应当有权自由选择请求权的规范基础。
三、民法典时代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与数额量定
依据《民法典》第1207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须具有主观故意,并且客观上造成严重损害后果,而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量定也应当坚持罚过相当的原则,以合理发挥惩罚与威慑作用。
(一)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1.生产者、销售者须具有主观恶意
我国《民法典》第1207条要求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须以生产者、销售者主观上具有明知为前提。对于“明知”的理解,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严格性角度考虑,“明知”不应当扩张适用于应当知道的情形,而仅限于已经知道产品存在缺陷的情形。[15]也有观点认为,“明知”不仅包括确实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和推定知道;[16]甚至有观点认为,应当对“明知”作扩大化解释,不仅指故意还包括重大过失的情形,以更好预防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严重侵害公众人身健康行为的放任与漠视。
笔者认为,《民法典》第1207条关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旨在惩罚和威慑那些主观上具有恶意、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漠VJl/yqHrm16uniZzSqYFjA==视他人人身健康、具有道德上可非难性的生产者、销售者的行为。将“明知”限定为故意,能够实现惩罚性赔偿“精确打击”的规范目标,以最大效用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因此,应当对“明知”作限缩性解释,限于已经知道却仍然从事侵权行为,有“故意”甚至“恶意”之意,限缩性的“明知”应作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构成要件。如果包含重大过失在内的行为,则可能导致产品责任过度震慑的后果。
对于生产者、销售者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的举证责任,通常由受害人承担。在司法实践中,缺陷产品的受害人主张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往往囿于举证责任方面的困境而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如在“彭高通诉邬巍等产品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明知缺陷产品仍销售造成其健康损害,要求加倍赔偿,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项诉求不予支持。”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允许采用推定的方式来证明生产者、销售者主观上具有明知产品存在缺陷的故意。
2.客观上造成严重损害后果
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客观上要求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损害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207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客观要件是指“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具体而言,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后果包括:一是造成消费者、使用者死亡,即因为缺陷产品使受害人的生命权遭受侵害;二是造成消费者、使用者身体健康严重受损。这表明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并不是针对一般的侵权行为损害后果提供救济,而是针对遭受人身伤亡的严重损害后果进行救济,这也是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严格慎用的限制条件之一。
其中,缺陷产品对受害人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标准并不清晰,为了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及保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当对其进一步明确。首先,受害人的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必须是指客观上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后果,而不能仅是一种潜在的危险。[17]其次,关于受害人的健康严重损害的情况可以参照身体伤残的标准来认定。第三,受害人的健康严重损害不仅包括身体上的严重损害,而且还包括精神上的严重损害。如受害人因使用缺陷产品导致毁容,长期遭受精神痛苦,也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惩罚性赔偿金二者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因此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此两种诉讼赔偿请求。
(二)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
依据《民法典》第1207条的规定,在产品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确定标准过于模糊,如何量定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成为该制度在适用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由于该条文将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自由裁量权完全赋予法官,如果对其数额的量定因素不加以限制,将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惩罚性赔偿数额畸轻或者畸重的问题,进而导致滥用惩罚性赔偿或者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威慑功效。为了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妥当判定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应当对惩罚性赔偿金的考量因素进行明确,以适当增强数额量定的可预见性。
笔者认为,对于在产品责任中设置惩罚性赔偿最高限额的做法应当持慎重态度。如果对所有的恶意产品责任预先设定统一标准的最高数额,那么将可能导致生产商得以事先计算损害成本,并通过一些手段去除惩罚性赔偿可能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基于对成本—效益的计算后,实施恶意生产行为的企业在面对惩罚性赔偿规范时将更加肆无忌惮,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威慑功能至此将不复存在。[18]因此,不宜直接对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作出最高数额的限制。此外,主张惩罚性赔偿数额与补偿性赔偿数额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有助于防止惩罚性赔偿金过重的弊端。但是,确定惩罚性赔偿也不能仅仅单纯考虑实际损害后果,因为有时候可能存在生产者或销售者主观恶性较大但造成较小实际损害后果的情形,如果固守与补偿性损害后果之间的比例原则将难以起到惩罚性赔偿的威慑效果。
申言之,对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量定应当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实现惩罚数额的适当性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生产者、销售者的主观恶意程度。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当与侵权主体实施不法行为的主观恶意程度相当,其可非难性程度愈深,赔偿数额应当愈高。第二,缺陷产品导致的实际损害后果。赔偿数额应当与缺陷产品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维持适当的比例。具体的比例关系可以参照2013年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2款中的“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规定,该指引规定实质上是能够将《民法典》第1207条的规定在消费者保护领域予以具体化。[19]如果是食品类产品,则可以参照所受损失三倍的惩罚性赔偿的标准。第三,系统协调与其他类型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系。由于现行惩罚性赔偿体系包含了多个法律领域,针对侵权主体的同一行为,既可能存在私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也可能存在公法上的行政处罚或者罚金;即使在私法层面上,可能符合基于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同时也可能符合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为了避免惩罚过度,在确定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应当注重体系性思维,兼顾不同类型惩罚性赔偿的处罚情形,以合理发挥惩罚与威慑作用。
四、结语
伴随着民法典时代的来临,我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呈现逐渐扩张的态势,这也因此带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于不同侵权行为类型时遭遇的实施标准难题。我国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备惩罚、威慑以及充分保护消费者三项功能。《民法典》《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共同构成了现行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范体系,在衔接适用时应当依据产品类型、责任主体以及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妥善协调规范竞合问题。对于《民法典》第1207条的适用条件,在主观要件方面,应当对“明知”作限缩性解释,限于已经知道却仍然从事侵权行为,有“故意”甚至“恶意”之意;在客观损害方面,应当对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严重损害的后果进一步明确,对此可以参照身体伤残的标准来认定,以进一步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及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对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量定则是一项系统性的任务,应当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综合考量生产者、销售者的主观恶意程度、缺陷产品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以及系统协调与其他类型的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系。在《产品质量法》新修订的背景下,明确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有助于厘清不同法律之间的内在关联,促进法律体系的有机衔接。
〔参 考 文 献〕
[1]高志宏. 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二元体系与规范再造[J]. 比较法研究,2020(06):190.
[2]Bruce Chapman; Michael Trebilcock. Punitive Damages: Divergence in Search of a Rationale, Alabama Law Review, 1989(03):741.
[3]王利明. 惩罚性赔偿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0(04):115-116.
[4]高圣平.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与规则设计[J]. 法学家,2013(06):58.
[5]张新宝,李倩. 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J]. 清华法学,2009(04):6.
[6]Rober D. Cooter, Punitive Damages for Deterrence: When and How Much ? Alabama Law Review, 1989(03):1148.
[7] Hylton Keith N. Punitive Damages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Penalties,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998(02):421.
[8]杨立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J]. 清华法学,2010(03):9.
[9]刘俊海,徐海燕.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解释与创新[J]. 法律适用,2013(13):30.
[10]李响. 我国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规定之批判与完善[J]. 法商研究,2009(06):43.
[11]朱广新.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J]. 中国社会科学,2014(03):113.
[12]杨立新. 对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裁恶意产品侵权行为的探讨[J]. 中州学刊,2009(02):69-70.
[13]信春鹰.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392-394.
[14]税兵. 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J]. 法学,2015(04):103.
[15]冉克平. 产品责任理论与判例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82.
[16]张保红,唐明. 惩罚性赔偿条款“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之证明[J]. 人民司法,2016(01):89.
[17]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350.
[18]陈聪富. 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6.
[19]贾东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读[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282.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