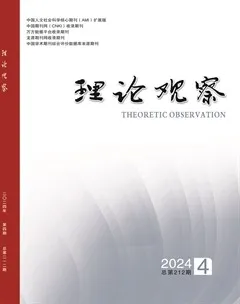北魏至清文化政策演变
摘 要:嵩阳书院发轫于北魏嵩阳寺,先后历经隋唐嵩阳观;北宋嵩阳书院;金元承天宫、嵩阳宫;明清嵩阳书院等阶段,成为三教荟萃之地,在书院史上具有独特之处。厘清嵩阳书院的发展脉落,可以发现其与北魏至清主流文化政策发展轨迹相一致,体现了北魏崇佛;隋唐、金元重道;明清尊儒的文化发展态势。
关键词:文化政策演变;嵩阳书院;儒释道
中图分类号:B222;B94;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4 — 0099 — 06
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指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异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孕育出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变迁以及自身文化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文化又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即所谓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因此,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政策演变可以窥探当时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差异,间接为溯源文化历史原貌提供佐助。
秦汉以降,儒释道三家的发展成为历代王朝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各王朝的儒释道发展态势是研究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内容。唐朝玄宗年间所设丽正、集贤书院虽冠书院之名但实为藏书、修书机构;后至唐末五代之际逐渐成为儒家讲经授业之地。宋人吕祖谦将嵩阳书院与岳麓、白鹿洞、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齐名,合为北宋天下四大书院。其中,嵩阳书院在历史上几经易名,北魏至清先后成为佛道儒三家势力寄寓之所,这也是其他三大书院所不具备的特征。因此,以嵩阳书院易名为视角,可以探析北魏至清时期主流文化政策的演变。
一、北魏至清嵩阳书院易名与发展过程
嵩阳书院的前身可追溯至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始建的嵩阳寺,佛寺香火绵延百二十年,至隋朝大业年间改为嵩阳观。李唐一朝,虽经过奉天宫、嵩阳观等阶段性变化,但是始终作为道教宫观而存在。五代之际,后唐进士庞式在嵩阳观聚众授课,后周改为太乙书院,开始具备书院讲经授业的职能。北宋时期更名为嵩阳书院,此阶段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经过统治者的授田、赐经,嵩阳书院赫然位于天下四大书院之列。金元两朝,先后易名承天宫、嵩阳宫等,教学活动停滞,此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叶。明嘉靖年间,在登封官员以及邑人的捐资援助之下,嵩阳书院得以恢复教学职能,直至清末学制改革之际。
(一)北魏:嵩阳寺
嵩阳书院的前身是肇建于北魏太和八年的嵩阳寺。现今仍保存的刊刻于东魏天平二年的《中岳嵩阳寺碑铭序》记载了嵩阳寺建立的始末:
有大德沙门生禅师……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永辞沸镬,拯拔群品,远离炎炉;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当中岳之要害,对众术之抠耳……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建造伽蓝,筑立塔殿,布置僧坊,略深梗概。王公卿士,咸发布向之心;凡厥庶民,并欣喜舍之志。②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生禅师建立嵩山建寺的原因是中岳地处要害,未有塔庙,应当创立神场,接引四方生灵,于是在北魏太和八年在嵩山肇建嵩阳寺。佛寺建立之后,北魏王公贵族、黎民众生纷至沓来,香火不绝。后来其弟子沙门统伦、艳二法师继续扩大嵩阳寺的规模,在原嵩阳寺的基础上又修建七级佛塔,“而七层之状,远望则迢亭巍峨,仰参天汉;近视则崔嵬俨嶷,旁魄绝望,自佛法光兴,未有斯壮也。禅师指麾,成之匪日。”①此时,嵩阳寺的建置已经趋于完善,僧徒多至数百人,名盛中原,香火鼎盛。
北魏后期,宣武帝亲情佞臣,诛杀大臣,导致兵连祸结,社会动乱,司空裴衍产生礼佛避世的心理,欲隐于嵩山,于是上书请辞:
衍欲辞朝命,请隐嵩高,乃上表曰:“小人愚怀,有愿闲养。伏见嵩岑极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游此岫……”诏曰:“知欲养疴中岳,练石嵩岭……既志往难裁,岂容有抑,便从来请。”②
裴衍,《魏书》有传,原是南齐官员,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北来魏国,上书隐于嵩阳寺。世宗末年,出山从政,后在征伐葛荣时军败战死,追赠司空。《中岳嵩阳寺碑铭序》中对其记载:“司空裴衍昔在齐都,钦承师德,愿归中国,为寺檀主。”③檀主即为施主,景日昣在《说嵩》中提及司空裴衍曾为寺主,这些都说明裴衍隐于嵩阳寺的十余载,促进了嵩阳寺的发展。
嵩阳寺自北魏太和始建,至隋朝大业年间改为嵩阳观,存在时间仅仅百二十年,但其影响弥远。嵩阳寺不仅为北魏以降嵩阳观、嵩阳书院、奉天宫等提供筑建旧址,而且亦是北魏佛法繁兴的典型代表。
(二)隋唐:嵩阳观
隋朝大业八年(612年),炀帝为求长生不老之道,下诏在嵩阳寺旧址之上营建嵩阳观。“初,嵩高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所资巨万”④,这是嵩阳观在史书中最早的记录。后,唐太史令李淳风之父李播“仕隋高唐尉,弃官为嵩阳观道士,号黄冠子,以论撰自见”⑤,李播因秩卑不得志,弃官为道士,修炼于嵩阳观。在隋炀帝的支持下,嵩阳观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并且为其日后在唐朝的繁兴发展奠定基础。
唐高宗、玄宗二朝,赖于皇权的渗入以及帝后的频繁游幸,嵩阳观的政治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大唐调露元年(679年),“高宗狩嵩岳,以车舆迎师正入嵩阳观问道,复送至逍遥谷”⑥;调露二年(680年)己未,高宗“幸嵩阳观及启母庙,并命立碑,又幸逍遥谷道士潘师正所居”⑦,可见唐代天子车马往复之频。调露二年,高宗下诏将嵩阳观闭为行宫,曰“奉天宫”。之后又在弘道元年(683年),携武后两次拜访隐居嵩山的上清茅山派宗师潘师正,均以奉天宫为行宫。睿宗年间,复“奉天宫”为“嵩阳观”,但无论是奉天宫还是嵩阳观,都具道教宫观之色彩。
玄宗崇仙重道,即位后四方访求永生之道,命人炼制金丹,以保长生不老。开元年间,玄宗下诏命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其炼制九转金丹,徐浩《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对其有详细的记载:
于是,考灵迹,求福庭,以为嵩阳观者,神岳之宅真,仙都之标胜,直中天晷景之正,记烈祖巡游之所……乃命道士孙太冲,亲承密诏。对授真诀……然后俾太乙启炉,陵阳传火,积炭于庑下。投药于鼎中……⑧
赖于嵩阳观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先皇对其之宠幸,玄宗对嵩阳观青睐有加,才令中使薛履信与孙太冲在此炼制金丹。玄宗在得到金丹之后,龙颜大悦,“资圣喜兮效神丹,神丹御兮福廷会。虹娩旗兮紫云盖,临万邦兮弥亿载”⑨,统治者的赞赏之态成为嵩阳观在唐朝昌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李唐前期,除皇家贵胄的中意之外,嵩阳观还成为文人墨客的游览胜地,诸如张说、白居易、储光曦等人都为此留下佳作。
李唐前期是嵩阳观名甲中原的阶段。玄宗之后,嵩阳观日渐衰颓,史书中并未从正面记载其衰落的原因,笔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推测一二。开元之后,安史之祸悄起,两京之地生灵涂炭,“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輥?輮?訛,各地道观都遭到不同程度烧坏,嵩阳观想必也因此衰落,不复当年盛况。
(三)北宋:嵩阳书院
唐末五代之际,社会动乱,官学遭到严重破坏,私学此消彼长,日渐勃兴,嵩阳观的职能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后唐清泰中,进士庞式于嵩阳观聚课”①,庞式与嵩阳观道士杨纳、南唐学者舒元在此讲经授业,使得嵩阳观初具教学职能。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改嵩阳观为太乙书院,这是嵩阳书院作为书院教育的开端。
北宋一朝是嵩阳书院发展的关键时期,至道二年(996年),太宗御赐“太室书院”匾额;景祐三年(1036年),仁宗下诏将“太室书院”易名为“嵩阳书院”。嵩阳书院的建置脉络在《玉海》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至道二年七月甲辰赐院额及印本九经书疏;祥符三年四月癸亥赐太室书院九经;景祐二年九月十五日己丑,西京河南府重修太室嵩阳书院,诏以嵩阳书院为额。②
在五代至宋几十载间,书院先后易名太乙、太室、嵩阳,盛极一时,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太宗、真宗、仁宗朝对书院多有赏赐和修葺,授田扩建、颁赐“九经子史”,设立校官学官,使得书院规模逐渐宏大。至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宋代“洛学”创始人程颐、程颢在此聚众讲学十余载,“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③,其学术活动吸引全国学者不远千里至嵩阳书院求学,嵩阳书院“崇堂讲遗文,宝楼藏赐书,赏田逾千亩,负笈者云趋”④,可谓名噪四方。
北宋中后期以后,政府开始重视官学的复兴,先后发起三次兴学运动,对嵩阳书院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次兴学运动以兴办公学为核心,抽调书院的学者,将官学与科举做官挂钩,剥夺书院的田亩资产,挤压私学发展空间,削弱了嵩阳书院的实力,书院呈现“师席久倚,生徒尽散落”⑤的惨状。虽有识之士致力恢复,但盛况不再。至靖康年间,整个京畿地区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各地书院教育逐渐沉寂,嵩阳书院的讲学教育也处于停滞状态。
(四)金元之际、明中叶之前:承天宫、嵩阳宫
金、元两朝以及明中前期,嵩阳书院的讲学活动处于低谷时期,空负北宋盛名。金人占领中原之后,南宋朝廷与金政权对中原地区展开频繁争夺,致使中原地区烽火连天,民不聊生。战争背景之下,身处中原腹地的嵩阳书院受到战火侵扰,学舍烧毁,学子流离。加之北方文人士子纷纷南下,依附于南方各地书院进行读书习业,嵩阳书院的教学活动更加陷入窘境。金代中前期虽有元好问、薛中正、高仲振、王汝梅、杜时升等名士在此讲学授业,但是书院教育的凋零以及社会的极度动荡使得嵩阳书院教学难以为继,最终在金世宗大定年间易名为承天宫,作为道教宫观形式存在。元朝时期,嵩阳书院的发展受到严格的控制,几乎废弛中断。元惠宗至正年间,嵩阳书院又易名为嵩阳宫,《敦请栖云真人住持嵩阳宫疏》载元代著名道士栖云真人修炼于此。
至明前中期,嵩阳书院的教学活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恢复。明朝诗人黄克晦在嘉靖年间写有《嵩阳宫三将军柏》一诗,诗曰:“惆怅茂陵无限树,荒丘残陇草菲菲。”⑥此时嵩阳书院还是以嵩阳宫为名,表明从金元以降,至少延续至明嘉靖初年,嵩阳书院主要是道教宫观形式存在,儒家所倡导的讲经授业之事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甚至呈现荒凉之象。
明代河南提学副使周梦旸在《嵩少游记》中记载:“嘉靖初,有知县侯泰者,饬为嵩阳书院,肖二程像于其中,不知何以竟澌灭,今祗颓垣耳”⑦,嘉靖初年,时登封知县侯泰在嵩阳书院旧址重建书院,恢复旧名,并且将二程肖像供奉其中,力图恢复嵩阳书院昔日盛况。但其又在文章中提及:“平旦,北出城,诣嵩阳宫。宫当嵩山之阳,翠屏如带”⑧,此时为明庚寅年,根据周梦旸的生平进行推测,应当为明万历十八年(1590),此时嵩阳宫依然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嵩阳宫、嵩阳书院之间呈现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嵩阳书院在金元以及明前中期的发展轨迹:道儒更替,儒学色彩下的书院功能虽有所恢复,但并没有得到稳定发展。
(五)明中叶之后、清: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的地位在明中后期有所提升,在地方官绅王尚絧等人的支持下成为官办县学,书院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嵩阳书院聚徒讲学的职能逐渐恢复,一时间书院文风大振、名士云集,书院成绩斐然。焦子春、崔应科等人在书院教育的熏陶之下,期取青紫,官至太仆寺少卿、湖广参议。明末,随着农民起义战火蔓及中原腹地,嵩阳书院“无半橼半瓦之存,即汉封将军三柏亦焚其一”①,又遭到严重毁坏。
清代,嵩阳书院在叶封等人的努力下得以重建。叶封任登封知县时,于“今年(康熙十三年)二月始,相度故基东南十许步,筑堂三楹,疱湢门阶以次而及,缭以周垣五十丈,并护二柏于内。”②清代的嵩阳书院在叶封为官之际得以重建,又祭祀宋代提举主管崇福宫程朱而下十四人,赋予嵩阳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祭祀功能,是嵩阳书院在清代的发轫阶段,开始带有儒学色彩。
叶封之后,逸庵先生耿介成为嵩阳书院在清代勃兴发展的关键人物。“叶封既解龟,其乡乡先生耿逸庵介复建堂三楹,迁二程朱子主持祀之,又作讲堂曰丽泽,旁列两斋曰敬义、曰博约,书舍若干区”③,耿介不仅扩大了嵩阳书院的建置规模,而且还做讲堂、聘学者,为士子讲学授课。在逸庵先生苦心经营之下,嵩阳书院的讲学功能也逐渐完备。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河南巡抚王日藻“眷言岳降之胜,拭目洛学之兴,慨然节损清俸,建藏书楼五楹”④,用俸禄捐建藏书楼,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十七日,藏书楼落成。从嵩阳书院藏书楼建置的目的来看,亦是为了阐扬洛学,复兴儒业。自藏书楼建置以来,藏书日趋丰富,诸如《册府元龟》《古唐诗归》等不胜枚举。至此,嵩阳书院集聚了书院所具备的祭祀、讲学和藏书三大基本职能。嵩阳书院由此声名大噪,“门庭孔峻,堂庑翼然。祭菜鼓箧有节也,讲习弦诵有所也,饔飧膏火有资也”⑤, 学士云集,群儒毕至,士子相交,谈经说道,盛况非常,颇有北宋遗风。
乾隆末年,嵩阳书院的发展呈现衰敝之势,《登封县志》载:“县官多购买所得,没有学识,聘请山长,不能辨识优劣,指导无方,主持乏人,学田渐为士绅霸占。”⑥此外,随着清末列强入侵,清廷政权的摇坠以及先进思想和教育的革新,嵩阳书院在清晚期的发展面临困境。清光绪年间,嵩阳书院竟沦落至“墙垣、房舍皆倾圮剥残殆尽”⑦的惨状,在乡绅耿建侯等人的捐资下历时三年才得以重新修缮,嵩阳书院昔日盛况已不复存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书院制度时,嵩阳书院仅有教职人员三人,学生三十九人,年支经费白银1037两。嵩阳书院在新式教育浪潮的裹挟之下,其传统的书院教育职能日渐消弭,最终被新式学堂所取缔。
二、北魏至清嵩阳书院易名的原因分析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的多次易名,反映了北魏至清不同历史阶段主流文化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大体呈现出北魏崇佛;隋唐、金元重道;北宋、明清尊儒的文化发展态势。再者,嵩阳书院位于具有“天地之中”之称的登封境内,是历代王朝权力中心辐射地带,会直接受到王朝政策的影响;儒、释 、道三教对嵩山所处要冲之地较为重视,三家势力在嵩山地区此消彼长,分化合流,这也为嵩阳书院形态更替提供条件。
(一)北魏崇佛的文化政策
嵩阳书院最初以寺为形,与北魏崇佛的文化政策紧密相关。首先,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崇盛。公元386年,拓跋珪建魏之后,认为“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周宇,招延僧众也”⑧,对寺院和僧侣礼遇有加。此后,除太武帝灭佛之外,北魏的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魏书·释老志》记载,至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⑨ 可见佛教在北魏的繁兴。另外,《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佛宇最盛时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寺的选址大多在京城和周边的嵩山地区。嵩阳寺建立之后,受到拓跋皇室的游幸,“时拓跋氏佞佛,孽后统内姬时命车驾”,?輥?輮?訛可见北魏对佛教之笃信。
其次,“魏、晋浮荡,儒教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輥?輯?訛,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儒学发展受到限制,士人困于时局,认为儒学不足以救世,所以儒学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停滞。再者,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道教的产生与发展,但是道教与佛教相比,其理论观念与宗教体制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尽管在魏晋时期“尚无、谈玄”之风盛行,但至南北朝时期,其影响则逊于佛教。
北魏后期,孝武帝西迁长安,高欢挟元善见迁都邺城,洛阳丧失京都地位。加之社会动荡,战乱纷起,僧尼北迁,洛阳以及周围地区的佛寺遭到严重毁坏,数量锐减,“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尽毁,庙塔丘墟……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① 佛教在北魏末期日渐式微,这为嵩阳寺日后的形态更替提供了条件。
(二)隋唐、金元之际、明中叶之前道教的辉煌发展
纵观李唐前期,尤其在高宗、武后、玄宗三朝,是嵩阳观发展的鼎盛时期。嵩阳观在隋唐时期的兴盛与道教的隆兴无疑有密切关系。李唐皇室奉老子为祖,尊道教为国教。虽武周一朝大兴佛法,但是仍下诏“佛道齐重”,所以道教发展并没有遭到严重制约。玄宗继位之后“尊崇圣祖,肃恭道教”②,唐朝道教的发展达到极盛时期,不仅给老子累加尊号,还在长安、洛阳设玄学博士,助长崇道之风滥行。隋唐之际,上清道茅山宗成为嵩山道教的主流。上清道宗师王知远曾派弟子潘师正在嵩山弘扬道教,潘师正在嵩山深居五十余年,高宗、武后多次驱车拜访,深得帝后的尊崇。玄宗时期,又有孙太冲修炼于嵩山,这些使得嵩山声誉远扬,俨然成为当时的道教活动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亦是书院的发端之际,但为何嵩阳寺后以道观为形并非以书院而立,是值得推究的。首先,一般认为开元年间设置的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但其设立的目的在于处理皇家政务,还不具备教育功能。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指出,玄宗之前民间就有书院的存在,如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创建的瀛洲书院丽正、集贤书院早了将近一百年。所以,通过书院发展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书院在唐朝中前期的发展有两条脉络:一是官府势力下创建的书院并未有后世书院所具有的藏书、祭祀、教学三大职责,只是冠有书院之名的行政机构;二是私人创建的书院虽已初具藏书、教育功用,但是在唐朝的数量较少,对唐代的教育发展影响有限。这种兴起于民间的办学模式,至少在玄宗一朝还未成气候。再者,唐朝国子学和太学教育发展良好,官学教育系统相对完善,士子求学并非难事,所以对私人创建的书院教育依赖不大。 所以,在上述因素之下,加之李唐重道的文化政策影响,将嵩阳寺改寺为观不足为奇。
金元之际、明中叶之前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皇统八年(1148年),金熙宗曾召见太一教主萧抱珍,表示对民间新兴道教承认和保护;大定七年(1167年),金世宗召见大道教祖刘德仁,赐其“东岳先生”号,表现出对民间新道教的鼓励提倡。③由此可见,金廷之初对于道教发展的支持,全真教亦在重道政策下借势发展。至元代,全真教在嵩山地区鼎盛发展。《大元嵩山崇福宫创建三清殿记》中载:“河南名郡也,居土地之中,而山水甲天下。其间深宫杰观,雄视一方者,率以嵩山崇福宫为称首”④,依嵩山而建的崇福宫是元代中部地区居于核心地位的全真教宫观。与崇福宫毗邻的嵩阳书院旧址,在全真教广泛传播的嵩山中,更名为道教宫观也是顺然之势。
明中叶之前,道教依然受到统治者的尊奉,相比之下,作为儒学交流场所的书院则受到统治者的严厉压制。明太祖曾言:“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⑤主张三教并立,承认道教的政治地位。至张居正掌政时,其认为书院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⑥,多次下令禁毁书院,嵩阳书院在此政策下实难得到有效发展,这也为嵩阳宫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
(三)北宋、明清尊儒的文教之风
嵩阳书院在北宋辉煌发展的原因有以下缘由:一是北宋官学发展颓滞,书院作为私学教育弥补官学发展不足;二是北宋统治者崇经术尊儒学,儒学在北宋发展蔚为大观,派系林立,需要场所进行学术交流 ,书院为其提供所需空间。
北宋初期,由于唐末五代以来社会长期动乱,政权更迭频繁,使得中央官学教育发展颓滞,州县之学难以普遍建置。此时,具有私学性质的书院开始勃兴,成为官学教育之外教育系统的重要补充部分。宋初,国子监内官员子弟不务正业,将其视为游寓之地,待到科举罢日之后,便各自散归,致使其“今学舍虽存,殊为湫隘;生徒至寡,仅至陵夷”,⑦可见官学衰敝。面对官学未兴、无处求学的窘境,有识之士“予惟前代庠序不能,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群居讲习之所。”①书院逐渐成为朝廷养士之所,为士人准备科举考试提供读书、备考的场地;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教学相比,更为切近科举考试的需要。
此外,北宋时期,统治者高度推崇儒家文化。仁宗曾曰:“朕纂临继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坠”,②统治者的待儒态度为宋初儒学的复兴奠定条件。嵩洛一带成为儒学活动中心之一,以二程、周敦颐为首的儒学巨擘游贯嵩山洛水之间。儒者常谈经论术于书院之中,将儒家经术与教学实践相结合。钱穆指出,“宋学兴起,既重在教育与师道,于是连带重要的书院和学校。书院在晚唐五代时已有,而大盛于宋代。”③旨在阐明宋学的兴起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因此,在书院林立的北宋时期,嵩阳书院在延续五代太乙书院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其讲经授业的职能,并且受到统治者的政策扶持,跻身四大书院之列。
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哲学,被当作科举考试的工具,以致“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④因此,以王阳明、湛若水等人为代表的儒学大家开始从批判程朱理学入手,以所谓的“心学”来重新构建儒学理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王、湛弟子及其后学建书院、开讲会,倡导各地,又将二者一起推向极致,形成南宋以来中国书院与学术再度辉煌的局面。⑤在此等因素的影响下,儒学重新构建的环境之下,明代的书院进入了复兴阶段,也为嵩阳书院恢复教学职责提供契机。
清初,嵩阳书院教学活动直至康熙年间才开始,虽经明末兵燓,但亦有政策原因。清初顺治帝下诏“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五行之徒,空谈废业”⑥,以高压政策限制书院发展, 以防危及统治。后政策稍宽,嵩阳书院才得以重新建置。窦克勤在《嵩阳书院记》中阐述了耿介兴建书院的宗旨:“耿太史逸庵先生倡道嵩阳,其学务以洛闽为宗旨,孔孟为要归,其教人务以主敬为根本”⑦,可以看出,清朝士人重建嵩阳书院的目的在于阐扬洛学之说,重振儒学之风,以士人崇儒心理推动书院重建。总之,嵩阳书院在北宋以及明清之际从事教学活动是儒学发展的结果。
三、 结语
以嵩阳书院易名为视角探析北魏至清文化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拮抗与冲突,使得秦汉以降的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元激荡的发展态势。文化所具有的排他性与整合性使得三教之间相互容纳调和,为三家荟萃嵩阳书院提供条件。嵩阳书院自北魏以佛寺形式肇建,历经隋唐道观、后周北宋书院、金元道观以及明清书院的多次嬗变,几易其名,历经兴衰,体现了佛道儒三家在历史上凭借统治者力量此消彼长的状态。与三教在不同王朝的兴衰有密切关联,总体上反映出北魏崇佛、隋唐金元重道、北宋明清尊儒的文教趋势。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