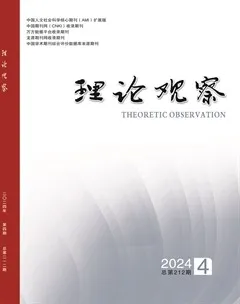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摘 要: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的生成存在理论、历史、现实层面的深刻逻辑。理论层面,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的论说为习近平“无我”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我将无我”作为“无我”-“我”-“无我”否定之否定程式中的高级转换阶段是马克思人的发展形态学说在21世纪的中国化表达;历史层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英雄群体的“舍我”精神为习近平“无我”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滋养,而“我将无我”是中国传统无我观的时代化表达;现实层面,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全球治理困境为习近平“无我”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现实的启示,而无我精神境界是对西方个人主义逻辑困境的根本性超越。
关键词:习近平;“无我”论述;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4 — 0005 — 05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式”乃相对于“西式”而言,“现代化”则相对于“传统”而言。社会现代化的本质即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则为中国式现代人的普遍生成。中国式现代人,既不同于传统共同体中的混沌“无我”式存在,亦不同于市民社会相对独立之“我”的原子式存在,而是一种生成于新时代的崭新的个人存在方式——觉醒“无我”式存在。这个崭新的“无我”概念由习近平在一次国际会晤中明确提出,当被问及担任大国主席的感想时习近平深情回应: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6]144。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指向我与人民、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本文拟就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作如下研究和阐述。
一、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人的发展形态学说为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理论基础。依据马克思人的发展形态学说,社会发展过程可划分为前资本主义“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后资本主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2]52,而人的发展呈现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与“自由个性”三种形态。“人的依赖”指古代个人对传统共同体的直接依附关系,这种形态同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依附共同体而生存的实际状况相适应,而作为共同体自然构成部分的个人表现出共同体主义的倾向,我以混沌“无我”的本我形式存在,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物的依赖”指近代市民社会市场主体间通过交换获取生活所需,商品作为承载生命可能的物态化劳动神秘获得普遍的统治权力,个人凭借商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自我,一切旧有的我的关系在市场冲击中烟消云散。以个人和共同体全方位发展为条件的“自由个性”摆脱了物对人身的全面宰制,扬弃了物对人心的深层异化,个人自觉融洽于物的关系以及隐没其中的人的关系,无限趋近于一种以觉醒“无我”方式充分实现自我的超我状态。由此可见,个人发展总体呈现出一个“无我”-“我”-“无我”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将“无我”-“我”-“无我”否定之否定的个人发展程式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图景之中,可以获得相对清楚的自我定位。以时间为纵轴,混沌“无我”表现为过去式,相对独立之“我”表现为现在式,而觉醒“无我”表现为将来式。以空间为横轴,个人发展形态具体表现为:传统的门第观念、熟人文化、依赖心理,以及制度设计的历史性缺位造成实际上贵贱有等、亲疏有分、强弱有别的阶层固化,“我”之意识尚未萌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商品成为个人存在的价值标识,对商品在数量与质量上不同程度的占有表明占有者不同的阶层归属,名酒佳人、华服美屋成为占有者高贵身份的标签与成功人生的明证,市场通过刺激与强化每个人的自我存续之心而变得生机勃发,“我”之意识普遍生成。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包括个人物质与精神能力的全方位发展,而且还涵盖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3]515;这种发展不是只有一部分人的充分发展,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3;这种发展是个人发展与共同体发展的高度统一,“我”之“无我”意识高度觉醒。
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人的发展形态学说的中国化表达。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形成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与“自由个性”三种形态并存的格局[9]29-35:一方面,从“人的依赖”走向“物的依赖”,从混沌“无我”走向“独立”之“我”;另一方面,从“物的依赖”走向“自由个性”,从“独立”之“我”走向觉醒“无我”。这种状况同中国由前市场经济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相适应:其一,新中国成立时社会经济千疮百孔,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尚未完全涤荡干净,因根深蒂固的惯性力量或显性或隐性残留;其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特定时期与特定范围之内仍以合理形式存在;其三,混沌“无我”之“我”对人的依赖与凭借商品交换从传统共同体中逐渐独立出来之“我”对物的依赖均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而彻底消失,但在社会主义的召唤与引导下,“我”之“无我”的自由个性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由此应运而生,这是个人与共同体互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成果的科学理论品格。
习近平关于“无我”概念趋向觉醒“无我”之意蕴。此“无我”并非完全排除“我”之本身,而是磨砺小我铸就大我,终至小我完全融洽于大我即“我”之“无我”的状态,“我”与“无我”的边界在个人自觉融洽于共同体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消失。“我”之“无我”高度觉醒,不同于尚未形成个人意识的混沌“无我”。混沌“无我”与觉醒“无我”反映了“无我”之“我”作为个体存在的不同成熟程度,反映了“我”之“无我”作为群体存在的不同发展阶段。混沌“无我”以“独立”之“我”为桥梁通往更高发展程度的觉醒“无我”。混沌“无我”、“独立”之“我”、觉醒“无我”三者不是前后相继的分别存在,而是共存于同一历史时空。对于共同体而言,其发展程度由构成共同体的个人之发展总状况所决定,或以“人的依赖”为主,或以“物的依赖”为主,或以“自由个性”为主;对于个人而言,其发展程度表现为不同形态不同占比的结合,或以混沌“无我”为主,或以“独立”之“我”为主,或以觉醒“无我”为主,有主有次缠绕式前进。
“无我”的提法极具中国传统哲学意味。《论语·子罕》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此“毋我”即“无我”。《庄子·逍遥游》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此“无己”即“无我”——人生至高状态的实现。佛家说,从因缘而起的假我,修行到自我,修心到真我,终至“无我”。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中国传统哲学构造出“我”之“无我”的理想人格,倡导以无我方式处置个人与共同体、我与他者的关系,他者指代外物、功名甚至自我的感觉与认知等。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人的发展形态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达。
二、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逻辑
毛泽东“舍我”精神为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历史滋养。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各种尝试,没有改变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找到救亡图存的可行路径。直至百余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舍生忘死,带领中国人民化被动为主动、从一盘散沙到万众一心,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舍生忘死”之“舍我”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对中国传统无我观的最本质表达,是特殊历史情境中个人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被动”指个人因客观形势被迫在生死之间作出抉择,“主动”指个人因主观信念而甘愿舍我。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反抗人类之不平等而牺牲了自己大部分亲人。正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涌现出无数像毛泽东一样的仁人志士,他们不忍苍生受苦而甘愿自己受苦,他们甘愿割舍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甘愿割舍自己挚爱的亲人,他们舍我护苍生,他们舍我守正道——正是因为他们的舍我牺牲,中华民族方可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舍我精神穿越历史时空的深情回应。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奔赴的方向一致——为苍生、为人民;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起点相同——不忍心、不负心。“为苍生、为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将共同体主义作为指导历史实践的方法论原则;“不忍心、不负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历史实践中锻造出胸怀天下的英雄品格和不忘来路的赤子初心。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二新年贺词中表示,“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7]65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绝对贫困造成绝对混乱——疾病蔓延、罪恶横行,而为了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持续努力,终于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无我为民,初心不改。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历史传承,这是中国革命红色血脉的世代赓续。
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是毛泽东“舍我”精神的时代化表达。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由图生存转换为谋发展。在革命图存阶段,无我的具体实现方式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毛泽东针对红军党内的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个人主义表现,提出用教育的方法予以纠正,批评不管集体、只顾个人的削弱组织战斗力的想法和做法[4]92-93;针对造成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表现,他提出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原则[5]360-361。各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表现程度不尽相同,实质却一样,即为了个体的、小团伙的特殊利益而无视总体利益,从个人的小我出发,从血缘、地缘等狭隘关系出发而不是从革命工作本身出发,不是从集体主义的大我出发,但由于救亡图存历史任务的危急性、紧迫性,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在改革图强阶段,无我的具体实现方式是磨砺小我铸就大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6]4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8]5-6。面对国内外的复杂考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当代中国青年将个人的小我融入人民的大我。无我不只作为一种组织原则被实施,而且作为一种人格目标被践行,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基本内核的时代化表达,“我将无我”开始成为一种愈加普遍的主动选择。
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对的个人主义,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其一,论域不同。个人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共有的意识形态,从经济、政治到道德、宗教,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由不同层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西方个人主义学说以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为载体被引介到中国,由于系统性水土不服而局促于主观精神领域,但它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尝试性适应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个人自由被整合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平等自由,个人主义由此导向社会主义。其二,意涵不同。个人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生活世界的深层逻辑,它被认为是个人的自我完成,是个人与社会相统一,是社会团结的实现而非社会团结的破坏;与此相对,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到《反对自由主义》,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对个人主义概念的使用基本指向其否定层面,即一切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思想与行为,个人主义被认为是庸俗而狭隘的利己主义,是群体的分化,是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其三,语境不同。西方个人主义产生并发展于资本主义对抗专制统治的斗争过程,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理解个人主义起源的历史凭借,后来的共识性界定基本没有超越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对个人主义的观点。由此可知,只有将个人主义问题结合具体情境进行考察,才能避免对个人主义批判的各种表面性与片面性,而反对个人主义与为人民服务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无我境界的一体两面。
三、习近平关于“无我”重要论述生成的现实逻辑
西方个人主义困境为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现实启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主导世界秩序的过程就是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石构筑整个上层建筑的过程。“个人”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产品,作为产品的“个人”运用了独特的制造工艺:自然个人、精神个人、经济个人、政治个人融为一体从而形成原子式个人——从尚未觉醒的混沌“无我”到权界分明的“独立”之我,从主观想象的个体性存在到立足现实的社会性存在,而自然个人以身体为边界,精神个人以自我为边界,经济个人以财产为边界,政治个人以权利为边界,这样拥有全方位界定的个人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任何价值附着其上。[10]5-13然而,这样的个人并非完美无缺,以个人理性为原动力、追求自我利益系统性最大化的个人主义存在无法克服的现实困境——集体非理性。
个人理性何以造成集体非理性?个人理性导向的结果不外乎四种:利己利人、利己损人、损己利人、损己损人。理性利己对自身、他人、共同体不产生任何作用的现实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故此不作考虑。个人主义的普遍利己是否自然导向普遍利他抑或社会进步?在总体财富有限而个人欲求无限的状况下,若要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只有以损害他人或共同体利益为代价,而所谓“利己利人”不过是对资本世界的一种臆想,“利己损人”才是符合资本逻辑的常态关系。“损己利人”乃在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中弱者自损以利强者,自利的动机招致自损的结果。“损己利人”与“利己损人”实为描述同一事物两个方面,二者均指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有人谋利成功就会有人谋利失败,而有的人在一场角逐中成功,则极有可能在另一场角逐中失败。然而,一方持续得利而另一方持续失利抑或一方持续得利而多方持续失利的关系不可持续,获利者必然遭遇失利者的对抗与反击,但谁人可以保证自己能够在这场无休止的资本游戏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费尽心力寻求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终将“损己损人”,它解释了人类几乎全部的悲剧性冲突,诸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文明冲突等。人们似乎从未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在自以为是的争战中得不偿失。个人越理性、越算计,则在集体非理性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西方个人主义从个人出发,个人优先于共同体,以个人与共同体先在二分的思维方式过滤一切经验与原则,由个人主义非历史性的方法论进而生成更为深层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而一旦个人主义成为思想与行为的方法,这就从逻辑层面排除了破解困境的可能性,集体非理性成为无可避免的宿命。与此相对,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以共同体利益为总原则,尝试在共同体的系统性活动中破解西方个人主义的现实困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乱象丛生。为了应对全球性治理困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从个别国家与地区的利益出发,不是从特殊民族与群体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全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出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百年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习近平关于“无我”的重要论述是对西方个人主义逻辑的根本性超越。相对西方个人主义而言,从共同体出发的无我导向的结果亦不外乎四种:利人利己、利人损己、损人利己、损人损己。此结果与个人主义导向貌似相同,实则迥然。“利人利己”指向个人自觉融洽于共同体的理想状态,而此状态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个人与共同体的发展程度;“利人损己”即舍己为人;“损人利己”乃客观结果与主观动机相背离——个人认知与行为能力相对欠缺的表现;“损人损己”就是通常所说的好心办坏事,好的动机造成坏的结果。倘若每个人均从共同体出发,那么,只要努力提高个人能力,社会总体进步就有可能;反之,倘若每个人均只考虑一己之利害,那么,纵使人人认知水平极高,行动本领极强,终究无法破解相互屠戮、各自为战的内卷困局。由此可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似乎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个人需求问题,而方法论的共同体主义似乎能够更加彻底地解决个人实现问题,从而确证一种更为优化的个人存在方式。
无我何以可能?不论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抑或精神层面,无我的生发存在其深刻的现实根源。一方面,个人为了自我保存而进行劳动生产,从依附传统共同体生存到社会化大分工系统中市场主体间通过商品交换获取生活所需而相互依存,自然个人通过经济合作完成社会化过程,想象的个人从天国降落凡尘而成为现实的个人。这样由自然、社会、精神不同层面需求构成的个人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不断拓展主体边界,个人之小我逐渐成长为共同体之大我。另一方面,个人为了自我延续而进行人口生产,毕竟现存个人的自然生命终归有限,而人口生产可以化个人的有限为共同体的无限,正是在化有限为无限的过程中,我之利己逐渐走向无我之利他,作为起初唯一的社会关系——夫妻柔情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爱——家庭由此生成。这种无我之爱存在一个普遍化、具体化的过程。所谓“普遍化”,一是主体的普遍化,每个人成为主动者、给予者;二是对象的普遍化,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在普遍化的过程中主体与对象合而为一,个人边界消隐。倘若个人发展程度高于共同体发展程度,个人要么自我降格,要么自我解构;倘若后者高于前者,个人要么自我升华,要么淘汰出局。所谓“具体化”,一是爱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爱有血有肉、有缺点的现实个人而非自我虚构的完美神像;二是具体地爱人,用现实的行动去爱人,而非停留在触不可及的想象空间。无我状态并非只存在于理念世界,而是可能并且需要具化为生活世界中的切实行动,并且已然开始具化为生活世界中的切实行动。由此可知,个人的自然、社会和精神需求只有以无我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而共同体只有以无我为原则才能获得真实的存在。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9]陈新夏.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人的发展[J].哲学研究,2014(08).
[10]赵汀阳.作为产品和作为方法的个人[J].江海学刊,2012(02).
〔责任编辑:秋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