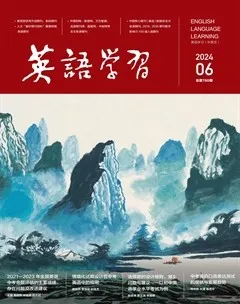《道格拉斯自述》中的时间叙事
引言
1845年出版的《道格拉斯自述》全称《弗烈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自述,由他本人亲自撰写》(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以下简称《自述》),是19世纪黑人废奴领袖道格拉斯的第一部自传,堪称奴隶叙事的典范。中文译者李文俊曾在此书译本中评述:“这本书,篇幅不大,却在美国历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1988:1)。本杰明·阿瑟·夸尔斯更是赞誉,在推动废除奴隶制的进程中,没有哪一本自传比道格拉斯的《自述》要更受欢迎和更具影响力,称《自述》为道格拉斯“赢得了跨越区域和种族的广大受众”(Douglass,1960:xix)。
早期对《自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影响、作家本人及他与白人废奴主义者关系的变化,20世纪中后期以后的研究则多转向对作品的文学性或文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探讨。从时间维度来看,研究者常常援引《自述》中奴隶“不知晓自己的出生年月也不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年龄”以及“长时间高强度的劳作常态”等时间叙事来佐证不同的主题,最终指向对奴隶制罪恶和残酷的揭露与批判。如亨利·路易斯·盖茨指出道格拉斯巧妙运用“自然”和“文化”、“循环”和“线性”、“黑夜”和“白天”、“野蛮”和“文明”等多组带有隐喻意义的二元对立,来刻画奴隶和奴隶主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存状态。这一系列的对比更是凸显了奴隶的悲惨境遇和奴隶制的压迫本质;其中,奴隶主拥有“线性时间”(linear time),而奴隶拥有“循环时间”(cyclical time)是盖茨特别强调的一组二元对立(Gates,1989a:90—92)。杰拉尔德·杰恩斯将种植园劳作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工厂劳作相类比,指出在奴役枷锁之下,奴隶对“劳作”和“休闲”、休闲”和“自由”等概念的区分和认知是扭曲的,论证了奴隶工作伦理既不是一种“新教工作伦理”,也不是“前工业或非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中家长制的工作伦理”(Jaynes,1991:98—112)。
以盖茨和杰恩斯为代表,研究者多从《自述》中单个时间侧面来论述不同的研究主题,而非从作品中多个层面时间叙事的呈现展开研究。基于以上阐释,本文从《自述》中时间叙事的三个方面切入,论证时间叙事如何成为再现奴隶生存状况、揭露奴隶制压迫本质的重要向度,以及道格拉斯如何运用时间叙事作为一条关键的叙述线索,借由时间标记,逐渐获得意识觉醒,最终实现自我解放。
时间意识的缺损与生命意识的受限
笔者从时间叙事切入,通过奴隶对自己年龄、出生日期的感知,对时间的划分与表达,对奴隶主赋予的所谓“自由时间”安排三方面展开分析,探究了身处奴役状态的奴隶对自我和周遭世界、事件的认知是被怎样的时间观所主导,以及在不平衡和被剥夺的时间认知和感知的背后所蕴含的主体意识、生命意识、社会性生活的剥夺。
1. 出生和年龄信息被剥夺
依照叙事惯例,传记作者通常会在自传作品开篇介绍自己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例如,富兰克林在初版于1791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不仅详细记叙了自己的出生信息,甚至追溯了父母和祖父母辈的出生情况。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自述》中,读者只能从“我出生在马里兰州塔波特县的特卡荷依”知晓道格拉斯的出生地;但就他的出生日期和年龄,道格拉斯却没有办法提供准确的信息——“我不知道自己精确的年龄,因为我没有见到过任何可靠的记载。绝大多数的奴隶都像马儿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龄”(道格拉斯,1988:8)。事实上,对自己出生和年龄缺乏认知在当时不是个例,而是奴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当被问及年龄和出生信息的时候,奴隶们顶多能语焉不详地说出大约是在“播种的时节、收获的时节、樱桃花开放的时节,是在春天,或是秋天”出生的(8)。“道格拉斯和跟他一样的大部分的奴隶一道,事关他们出生的这一关键信息被系统性地不被允许获知”(Gates,1989b:100),而这意味着整个族群的存在和身份不被承认。
“我能作的最精确的估计就是我不是二十七岁便是二十八岁”,这是道格拉斯在书写《自述》那年对自己年龄的大致推断,而这一推断源于他在1835年(已能够读书认字的时候)偶然听到主人说,他那时大约十七岁(道格拉斯,1988:8—9)。至于主人为什么会记得他的年龄,道格拉斯并没有陈述。但据研究者考证,当时大多数的奴隶主都有自己的财产账簿,里面会详细记载所有资产的信息和分类情况,前一页账簿或许还是对马匹的持有量、雄性或是雌性的记录;在同一本账簿的下一页可能就记录着奴隶的出生信息(Adjaye,1994:187)。由此可见,对奴隶主而言,知晓奴隶的出生日期和年龄,就像知晓他们马匹的雌雄和数量一样,只是一种对所有物属性和特征的标识。
作为生命的开始,出生是人生值得标记的重要事件。但在奴隶制下,奴隶主有意隐瞒了奴隶的出生日期及年龄,并且阻隔了他们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将他们的存在等同于动物,这是对奴隶存在的刻意弱化,对他们身份的蓄意剥夺。正如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所说:“奴隶出生的那一刻他就‘死’了,这里的‘死’说的是社会性的死亡,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参与社会生活”(Patterson,1982:46)。
2. 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的二元对立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2007)中提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对时间基本的经验感知,一种是古希腊的循环时间观,另一种是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奴隶用“播种时节”“樱桃花时节”来描述出生时间,在他们的认知中,“时间的概念是循环的,这与奴隶主线性的时间概念截然相反”(Gates,1989a:91)。与四季交替、作物时令相联系的循环时间观来源于奴隶暮暮朝朝、循环往复的劳作。与之相反,奴隶主线性主导的时间认知则与外界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观念相接轨。同一片种植园的天空下,截然不同的两种时间观的存在,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分野所在。
一个关于循环和线性时间观的基本共识是:在循环时间观主导的社会中,也存在线性的时间认知;同样地,线性时间观主导的社会中,也存在循环的时间认知(陈群志,2018)。然而,《自述》中种植园奴隶所持有的时间观却与上述共识相违背。奴隶主既拥有线性主导的时间观,也拥有四季轮回循环的时间意识,而奴隶对自身、周围事物和世界的线性时间的认知和感知却受到限制。后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其一生被奴役和驱使,对时间的体验是一个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过程。这种相对单一、受限的循环时间观体现的不是发展,而是重复。在理解奴隶生命历程中这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感之后,我们便能想象为什么莫里森作品《宠儿》中的塞丝在出逃失败后,为了让女儿摆脱没有终点的奴役,选择亲手杀掉女儿(Morrison,2000);也更能够明白为什么有的奴隶会有“放弃了一切对尘世的幻想,而寄希望于来生”的哀想(Jaynes,1991:107)。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不借助客观记号来划分、测算和表达时间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年份、月份、星期、日期、小时等时间序列,是一种社会制度,来源于社会生活,关系着个体和整个人类的实存(涂尔干,2011)。可见,小时、日期、月份、年份等表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形态下一种普遍的、约定俗成的,且相对客观的时间安排;社会成员通过使用这些时间概念来参与社会生活。《鲁滨孙漂流记》中有一个关键的情节,鲁滨孙虽漂流到荒岛,远离了社会性生活,但他有意识地运用时间概念去记录自己的生命历程,在木桩上刻下上岸的日期“1659年9月30日”,此后更是用长短不一的槽痕来记录每天、每周和每月时间的流逝(笛福,2014:71),这正是努力保持集体生活经验、维系自我身份和存在的表现。
《自述》中,在前半段的奴隶生涯中,道格拉斯和大部分奴隶一样,只拥有相对粗略的时间划分和表达标准。在回溯往事时,道格拉斯把七八岁离开种植园到巴尔的摩视为上苍的垂眷和最终能够逃离奴役的重要转折,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事件”(35)。然而对于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他却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信息:
我们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坐上船驶出迈尔斯河河口去巴尔的摩的。我只记得是星期几,因为当时我还不懂得一个月有多少天,也不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月。(道格拉斯,1988:34)
星期日是信教的奴隶主上教堂做礼拜的日子,也是奴隶一周中唯一能休息的时间。像道格拉斯一样的奴隶,对时间的表达仅仅限于这种粗略、循环的感知。道格拉斯不能运用更为精细的诸如年、月、日的标准去描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事实上,在对自己奴隶生涯的前半期的回顾中(在识字之前),他的叙述时间的表达和标记大多是约指的,时间线上也存在相互矛盾和混淆的地方。一方面,我们可以推测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和记忆的混乱;另一方面,自然是缺少线性的时间衡量和表达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回溯和标记往事的能力。与此同时,循环的时间观还进一步限制了奴隶对历史的感知(Adjaye,1994)。 线性的时间观赋予奴隶主以个人成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感知。而单一的循环时间意识却使得奴隶对自身成长过程和族群的集体记忆缺乏历史的认识和感知。
3. 具有欺骗性的“自由时间”安排
《自述》中奴隶主对奴隶时间的操控和剥夺,不仅体现在阻碍他们对自身年龄和出生日期的知晓,以及运用各种手段简化和限制他们对时间的认知,还体现在对奴隶工作、休闲以及“自由时间”认识的规训上。
对奴隶休闲的探究离不开对劳作的讨论,残暴至极的“黑奴驯师”科维驱使自己管辖的奴隶不分晴雨地劳动,“干活,干活,干活,这既是白天的命令,又是晚上的命令。最长的白天他都觉得短,最短的夜晚他也觉得长”(道格拉斯,1988:64)。然而,对奴隶时间的剥夺不仅体现在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劳作上,也在于他们不能自由选择休闲和劳作的时间。杰恩斯指出,在农业社会,季节、天气和作物决定了劳动的性质,但自由的农民在劳动强度和休闲劳动的切换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而事关奴隶的工作节奏和劳作休闲,如雨天是否要干活,却不取决于雨有多大、奴隶身体的状况或是他们的意愿,这完全由奴隶主的意志来决定(Jaynes,1991)。《自述》中,道格拉斯在高强度的劳作中体力严重不支,眩晕、手脚哆嗦,难以支撑,他请求休息片刻,而科维对这一请求置若罔闻,置之以一顿毒打,这就是一个佐证。
在谈及奴隶少之又少的休息,即每周安息日和每年圣诞节到新年的假日,道格拉斯认为这也并非是奴隶主仁慈或是良心发现,而是如“安全阀”和“避雷针”一样,是一种避免奴隶奋起反抗的安抚政策(道格拉斯,1988:74—75)。此外,奴隶主也不能一年到头地监管奴隶干活,他们自己也需要假日(Chua,1996)。进一步说,“这种假日是奴隶制全部的欺骗、谬误与不人道的一部分”,是对“受尽践踏的奴隶的最恶劣的欺骗”,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奴隶主们鼓励自己的奴隶从头到尾寻欢作乐,“不仅喜欢看到奴隶们自己酗酒,而且还采取种ed3e5e5a21672430a449d3308841d235种办法让他们喝醉”,然后再给他们的举动巧妙贴上自由的标签。其结果,首先是让奴隶主为“黑人天生就没有能力去承担作为自由人的责任”的论调找到辩护,为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提供诡辩;其次,“让奴隶只看到被歪曲了的自由,从而对自由感到厌恶”(道格拉斯,1988:74—75)。杰恩斯曾对此进行了形象的评述,对奴隶主而言,奴隶的劳动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在这种预设下,“劳动”和“休闲”、“休息”和“自由”的概念被异化和扭曲(Jaynes,1991:103—111)。换言之,奴隶可能认为相较于在科维的直接监视下随时可能挨鞭子,在场子里扬麦子和剥玉米是一种自由;就像在劳埃上校的大庄园工作而不是在田里劳作,或者周日可以休息、圣诞和新年假日可以酩酊大醉是自由一样。奴隶所认知和感知的“自由”和“休闲”,在自由人看来,却是无所不在的枷锁。
《自述》中道格拉斯还叙述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事件。在道格拉斯第一次逃亡计划破产之后,他被主人托马斯再次送回了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道格拉斯经过将近两年的学徒生涯,成为一名技术过硬的补船工,每周能够为主人赚取可观的收入。为了能积攒资金和相对自由地策划出逃,他向主人提出了“租赁自己时间”的请求,主人最终和道格拉斯达成协定,道格拉斯需每周定时上交租借时间的三块钱,而奴隶主不再为他提供住所和衣食。道格拉斯体会到此举既免除了主人照顾他的义务,又让主人依然能享受蓄奴的所有好处;而他不仅要承担自由人的责任,还不能享受到完整自由人的益处(道格拉斯,1988:100)。他深知这一安排的讽刺所在,自己辛勤付出的所得却要悉数交给主人,自己的时间却要出钱去向他人租赁,只因为主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道格拉斯曾亲历过两次易主,男女老少、已婚未婚的奴隶和马匹、牛群、猪猡列队排在一起,被估价、析产和分割;他也曾几番被主人租由其他奴隶主使用;更是多次耳闻和目睹奴隶被贩卖和转售的事件。这些事件连同时间租借一同向我们揭露:在奴隶制下,奴隶的生命成为可以切分、售卖、租赁、借用的商品。奴隶虽然拥有生命,却被奴隶主类同于牛马一样的动物,视为待价而沽的商品,成为帕特森说的“没有社会地位的人”(social nonperson)(Patterson,1982:5)。
透过道格拉斯三个层面的时间叙事,奴隶制的运作逻辑得以显现,其对奴隶尤其是心灵的荼毒更是得以凸显。通过阻止奴隶知晓出生和年龄信息,规训他们对时间的认知和感知,灌输有关“休息”和“自由”异化的认识,奴隶主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设置了阈限,进一步妨碍了奴隶对社会性生活的参与和对自我、族群存在和历史的感知。因此,奴隶虽然活着,但他们的生命意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剥夺。
时间的标识指向生命的标记
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和年龄,不能用确切的年、月、日来表达时间,这都限制了孩童时期的道格拉斯对自我身份和生命历程的感知和表达,给予了他深深的剥夺感,同时也成为激励他内心不断求索、试图寻找答案的动力。
1. 完整的时间意识的形成
道格拉斯在很小的时候,就为不能如白人孩子一样知晓自己的年龄而苦恼,“白人的孩子都讲得出他们几岁。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这个权利就应该被剥夺”(道格拉斯,1988:8)。如卢梭所言,“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卢梭,1982:9)。在压制和奴役下,道格拉斯不断求问自己的出生日期,挣脱奴役和走向自由的种子已然在他心底萌芽。
“奴隶,从定义上来说,在人类社会中所能拥有的社会地位被设置了一道阈限,正是阅读和写作,让道格拉斯得以跨越这个阈限”(Gates,1988:140)。在道格拉斯到达巴尔的摩,尤其是在他能够读书识字之后,他开始对时间拥有较为完整的认知,能够用更精确的日期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阅读不仅让道格拉斯对奴隶制和自身境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让道格拉斯逐渐掌握了更加完整的时间认知和表达。
“现在,我叙述到一个我的一生中可以提供日期的阶段了。一八三二年三月。”(道格拉斯,1988:53)他开始追溯自己过往的经历和所目睹的事件发生时自己大致的年龄,最为关键的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中重要节点发生的事件进行时间标注,在此过程中也逐渐获得了对自我和周遭经历更为清晰的历史感知。
2. 对生命历程的时间标记
“一八三二年三月”是道格拉斯从相对轻松自在的巴尔的摩回到圣迈克尔斯,成为种植园奴隶的日期,从这里开始到《自述》的结尾总共五十九页的篇幅中,道格拉斯对挣脱奴役走向解放的关键事件和重要时间的标识随处可见,有超过二十多处的记述。他记述主人托马斯加入卫理公会的日子,记述被主人租借给臭名昭著的科维的日子,记述奋起反抗的日子,最终虽没有改变被奴役的境遇,却在精神上获得自由。他还记述被转租借给弗里兰先生,与志同道合的奴隶伙伴一起度过的奴隶生涯中最快乐的一年;记述他和伙伴谋划出逃的时间节点,也记述出逃计划落空,他身陷囹圄,以及再次被送回巴尔的摩的日期。最为关键的是,他记下了成功出逃、身体获得解放的日子,当然还标记了结婚的日子。最后,是他开启演说家生涯、投身废奴运动的日子。
在众多时间标记中,有三个节点可谓在道格拉斯的自我解放之路上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一八三三年八月的一天”是道格拉斯宣称获得心灵解放的日子,“你们已经看到一个人怎样变成奴隶;你们将看到一个奴隶怎么变成了人”(道格拉斯,1988:67)。在这一天,道格拉斯奋起反抗科维。他曾经被驯服的身体、灵魂和精神复活了,“这次打架在我奴隶生活中是个转折点……我现在决定,不管形式上当奴隶的时间还有多久,我实际上做奴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道格拉斯,1988:73)。尽管在接下来的五年,道格拉斯依然身陷奴役枷锁之下,但他在心灵层面已经实现自我解放。而“一八三八年九月三日”则是他第二次出逃,成功抵达纽约,一生中最激动人心、实现身体实质解放的时刻(道格拉斯,1988:103)。这一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九年之后,道格拉斯在第二本自传《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中叙述道,“从心理体验来说,我只有九岁”(Douglass,1855:237),将逃脱奴役的“九月三日”视为获得重生的日子。而在十年后的同一天,他更是满怀感慨地给前主人托马斯写了一封公开信,纪念这一难忘的日期。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一日”则是道格拉斯参加楠塔基特废奴大会,站上演讲台,真正参与社会生活、投身公共事务的日子(道格拉斯,1988:112)。与前两次心灵解放和身体解放相对应,这一天则是道格拉斯开启人生新篇章,投身于为解放同胞、终结奴隶制而不懈奋斗的日子。
回顾《自述》,从孩童时期起,道格拉斯就意识到时间认知上的被剥夺,他渴望知晓生辰和年龄,主体意识已然萌发;巴尔的摩的岁月,在与同龄白人儿童的共处中,特别是能够读书之后,他对自身处境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虽没有逃跑的勇气,但想要逃脱奴役的想法逐渐生根;回到种植园后,在科维的鞭子下,身心饱受摧残,曾经拥有的主体意识褪去,他变得麻木和绝望,在海滩上呼喊,满腔愁闷无以发泄。而经由与科维的一战,他宣称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的到来。之后虽几经周折,第一次逃跑计划破产,被关进了监狱,但他再也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渴望。在二十一岁这年,他终于挣脱枷锁,获得身体解放。由此可见,时间意识的被剥夺是他奴隶生涯痛苦的经历,也是激发他深入了解奴隶制本质和自身处境的重要向度;时间标记见证了他思想的觉醒和争取自由的不懈探索,更是他艰难生命旅程回望的路标和指引。
正如丘吉尔所说,“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会看得越远”(Langworth,2011:576)。随着时间认知和感知的拓宽,道格拉斯获得了回溯过往、记录当下和预期未来的“自反性”。他逐渐看清小时候困惑不已的问题,也开始一步步记录里程碑式的成长,同时也积极规划未来,将“九月三日”定为再次争取自由的行动日。日期标记他的苦难和忍受,标记他的挣扎和反抗,标记他一步步挣脱枷锁走向自由。因此,时间意识的拓宽也意味着道格拉斯的生命意识逐渐完满。
结语
任何叙事作品和叙事现象都不是超时空的,《自述》中时间叙事再现了奴隶受奴役的生存现状和思维状况。通过分析奴隶在时间意识上被剥夺和规训的现象,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奴隶对自身、对世界、对历史禁锢和局限的感知,也明确了他们主体身份和生命意识的丧失。道格拉斯通过不懈的努力,跨越了奴隶主刻意为奴隶设置的阈限,逐渐获得了完整的时间意识。而时间的标记进一步助力他由身心受奴役的状态,一步步获得心灵和身体的解放,并使他参与社会生活,逐渐获得身份认同,最终拥有真实的自由。
参考文献
Adjaye, J. K. 1994. Time in the black experience [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Chua, J. 1996. Cliffs notes on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M].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Douglass, F. 1855. 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 [M].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Douglass, F. 1960.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 [M].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ates, H. L. 1988.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o-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tes, H. L. 1989a. Binary oppositions in chapter one of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 In H. L. Gates (ed.). Figures in black: Words, signs and the “racial” self (1st ed.) [C].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0—97.
Gates, H. L. 1989b. 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A]. In H. L. Gates (ed.). Figures in black: Words, signs and the “racial” self (1st ed.) [C].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8—124.
Langworth, R. 2011. Churchill by himself: The definitive collection of quotations [M].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Morrison, T. 2000. Belov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Jaynes, G. 1991. Plantation factories and the slave work ethic [A]. In C. L. Davis and H. L. Gates (eds.). The slave’s narrative [C].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12.
Patterson, O. 1982.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奥古斯丁. 2007. 上帝之城 [M]. 吴飞,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陈群志. 2018. 线性观与循环观:历史哲学中的两种时间观之争[J]. 社会科学文摘, (9): 79—81.
笛福. 2014. 鲁滨孙漂流记[M]. 唐荫荪,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道格拉斯. 1988. 道格拉斯自述[M]. 李文俊,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卢梭. 1982.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 2011.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 汲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朱雪丹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