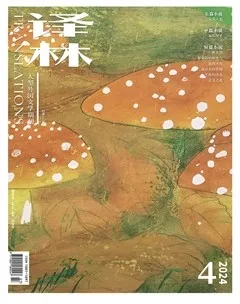雪地上的痕迹
伊娃·格林对天气变化异常敏感。此刻,她正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窗户玻璃,望着斯图雷帕肯公园里污脏枯黄的草坪和光秃秃的树木,蹙紧了眉头。
真是,前几天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呢,她懊恼地脱口而出。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她这话只能说给高高的护墙板听。凝神细听时,她能隐隐听到从双开门后面老板办公室里传出来的交谈声。她好奇里面的人在谈些什么。客人是半小时前来的,是一个瘦弱的女人,两眼含泪,面带忧色。在带她去见老板时,伊娃觉得以前似乎见过她——尖下巴,薄嘴唇,还有那绺搭在额头上毫无魅力可言的卷发。
不,伊娃相信她不是来谈离婚的。虽然担任区议会主席兼律师林德霍夫的秘书只有六周,但她已经见过很多前来咨询离婚的女人。这个女人脸上没有其他女人常见的愤恨或冷漠的表情,而是焦虑中透着果敢和坚毅。
伊娃看了一眼访客登记簿。她叫桑德夫人。桑德夫人?奇怪,名字听着也耳熟。难道曾在哪里听过或见过这个名字?
伊娃把登记簿推到一边,翻开账簿准备算几页账。12月的天黑得早,伊娃刚伸出手想开台灯,门开了,客人和律师脚跟脚走了出来。桑德夫人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声“再见”,走出了大门。律师站在地板上,若有所思地盯着紧闭的大门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着秘书叹了一口气。
“格林小姐,你认出她来了吗?”
伊娃点了点头,“但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
律师上前递给她一份报纸。是11月15日的报纸,头版有一条醒目的标题:出纳员荒地昏迷,9万克朗不翼而飞。
标题打开了伊娃的记忆之门。这起奇特的案子曾轰动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伊娃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过它的进展。出纳员叫桑德,伊娃正是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桑德夫人的照片。几天前桑德先生被拘捕了,妻子却坚信丈夫是无辜的,正想方设法为他脱罪。
伊娃看向老板。
“你接了这个案子?”
律师灰色的眼睛里满是忧虑。
“刑事案件风险很大,你很容易被某个盲点迷惑,陷进去就出不来了。”
“你觉得他是无辜的吗?”
律师耸了耸肩。
“我还没见过当事人,也没读过调查报告。妻子嘛,总愿意往好的方面想。”他长叹了一口气,“我答应明天回复她。”
律师转身,低着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走到门口时突然转过身来。
“如果你没什么特别的事,可以看看这个案子的卷宗,就在我办公室。”
趁着律师外出开会,伊娃读了桑德夫人带来的厚厚的审讯记录和调查文件,边读边在纸上草草地记下要点。
尼尔斯·桑德,37岁,在一家大型进口公司做出纳,所住别墅位于特朗松德,距离斯德哥尔摩市区约10公里。
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快到3点时,桑德离开工作岗位,前往位于布伦克贝格市场的哥德堡银行,准备把9万克朗存进公司账户。他没打算存完钱后再回公司,因为他已约好在3点15分去看牙医。他算过时间,不可能在下班之前赶回来。
桑德开的是自家的雪铁龙车,由于街上交通拥堵,没能及时赶到银行。等他到达时,银行已经关门了。
他本想回公司,把钱放进保险柜,但看了看表,发现这样做会错过和牙医的预约。他已被牙痛折磨了整整一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桑德去了位于城南的牙医诊所,医生给他做了根管治疗。4点半离开诊所时,他突然觉得膝盖酸软,头晕目眩。这种反应在以前看完牙医后也出现过。按照经验,喝一杯白兰地就会好。于是他去了一家餐馆,点了食物和7.5厘升白兰地。5点刚过,他离开了餐馆,开车朝城外驶去。来到南城区的斯坎斯图尔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按照桑德的说法,他对后面发生的事记得不太清楚了。车没开多久,他感觉脸发烫,眼前天旋地转,他不得不停住车,下来围着车走了几圈。之后他又上了车,朝特朗松德方向慢慢开去,间或停下来休息一下。雪下大了,很难看清路。
接下来他的记忆更加模糊了。他依稀记得到了特朗松德后,他把车停在一家报刊亭旁,不远处便是通往他家的支路。他记得自己买了份报纸,还抄了捷径——有一条贯穿荒地的小路,路的尽头就是他家。他模糊记得,他正走在小路上,有人在后面喊了声“你好”什么的,他转过身,太阳穴上挨了重重一击,顿时昏了过去。
桑德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雪地里。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装钱的公文包。公文包在他身旁,但里面的9万克朗不见了。他感到恶心,头痛欲裂,腿却动不了。他高声呼救,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对住在附近的夫妇,把他扶回了家,还第一时间给医生和警察打了电话。当时是7点,雪已经停了。
医生证实桑德的左太阳穴遭受过重击,并可能导致轻微的脑震荡。但在警方的询问下,医生承认,如果桑德不慎摔倒,头撞上石头或其他硬物,也可能造成这种伤害,这种伤害甚至可以是自己击打造成的。
警方勘查了现场。雪地上的痕迹表明桑德掉进了一条斜穿荒地的沟里,头正好撞在一块被雪覆盖的大石头上,雪上因此留下了一个椭圆形的深深印痕。由于刚下过雪,雪地上很容易辨认出他受那对夫妇救助的痕迹,以及他从位于主干道旁的报刊亭穿越荒地回家的足迹,同时,大家也能一眼看出从报刊亭到桑德出事的这段路上没有第二个人的足迹,这表明桑德是独自行走在荒地上的。而且,警方经过仔细检查,排除了有另一个人踩着桑德的脚印行走的可能性。
公文包里有一些纸和当天下午印发的《快报》,但没有钱。
桑德的车停在通往他家别墅的支路上,离主干道只有几米远,轻盈蓬松的积雪上留着一行脚印,从车上下来,通向40米开外的报刊亭,之后,这行脚印延伸到了荒地上。
这就是案件的大体情况。伊娃接着研读警方的审讯记录,不再做笔记,蓝色的大眼睛盯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快速移动着,偶尔会因奇怪的措辞或意外的结论而停顿几秒。她完全沉浸其中,当不经意间瞥到律师瘦削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不由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怎么样?”头发花白的律师问道。
伊娃把垂在额头上的一绺金发拂到脑后,坦言道:“我认为他是无辜的。”
律师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真的吗?”他探询地看着她。
伊娃继续道:“如果真的是桑德在回特朗松德的路上把钱藏在了什么地方,那他应该把整个事件安排得更巧妙一点。换作是我,我绝不会跑到一片积雪的荒地上,找个东西把自己敲昏过去半个小时。因为雪地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足迹,警方肯定会认为是我自导自演了这出戏。”她摇了摇头,“不,这太不可理喻了。”
律师轻声笑了笑。
“我想检察官没有怀疑他失去意识是装出来的,相反,他相信桑德确实掉进了沟里,脑袋撞上了一块石头。桑德当天晚上验了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
“我知道,”伊娃说,“不过,这不正好说明他是无辜的吗?如果是我想犯罪,我不可能让自己喝醉。”
律师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亲爱的格林小姐,很多罪犯在犯罪前都会多多少少喝点酒,不然他们没法干坏事。”
伊娃耸了耸浑圆的肩膀。
“你的意思是,桑德去餐馆喝酒,是想给自己壮胆?”
“警方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他在回家途中把钱藏起来了?”
律师点了点头。
“能藏钱的地方多着呢。”
律师又点了点头。
“然后桑德先生酒劲上来,掉进了沟里,头撞在石头上昏了过去?”
律师再次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警方的看法。”
伊娃噘起嘴,若有所思地看着律师。
“如果事情真如你想的那样,”她缓缓说道,“桑德先生假装回家后发现钱不见了,他会怎么向警方解释呢?”
律师解开外套纽扣。
“他也许会说钱是在餐馆被偷的,他是带着公文包进餐馆的。”
“那他为什么没有采用这种说辞呢?”伊娃穷追不舍。
律师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他肯定没想到他会掉进沟里昏过去。醒来后,他可能意识到这个意外正好可以用来说钱被劫走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全然忘了雪地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
“不只这个,他还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信誓旦旦地说,在把买来的报纸放进公文包时,钱还在里面。”
伊娃怀疑地摇了摇头。律师挂好外套,来到桌边拿起卷宗。
“我要仔细研读一下。”他朝她和蔼地点点头,进了自己的房间。
伊娃坐着没动,陷入沉思。案件存在着不合情理的蹊跷之处,就像背后有一只不知从哪里伸出来的手扭曲了真相。在阅读卷宗的过程中,她好几次有一种快触碰到真相的奇怪感觉,但离得还不够近,不能抓住真相。这让她有些恼怒。
伊娃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账本上,但没有成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甚至都没听到墙上的挂钟在5点和5点半时敲响的声音。她呆坐在那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正欲起身去找律师,门开了,律师腋下夹着卷宗走了出来。
“如果我是检察官,我也会逮捕他。”律师把卷宗放到伊娃的办公桌上,“这里面有太多否认不了的间接证据。”
他停下来,灰色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美丽的秘书,似乎期待着她质疑。但伊娃没有吭声,于是他继续说下去。
“他财务状况不太好,生活上也不太检点,追求享乐,狂喝滥饮。他还撒谎,自述在餐馆只喝了7.5厘升酒,实际上喝了12.5厘升。”
“我听说,喝7.5厘升开车没事,”伊娃平静地反驳,“但喝12.5厘升至少得坐一个月的牢。再说,”她补充道,“生活中循规蹈矩却犯罪的人多着呢。”
律师撇了撇嘴。
“还有其他加重嫌疑的细节。首先,他没有记下1000克朗面额纸币上的数字。公司有这样的规定,他以前都记了的,但这次没有。”
“人在匆忙之中,又受牙痛折磨时,忽略掉一些事很正常。”伊娃大胆地反驳。
律师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
“桑德通常会随身携带着银行夜间保险柜的钥匙,偏偏那天他把钥匙忘在了办公室。”
“我也经常把口红忘在家里。”伊娃说。
律师假装没听到。
“在接受警方的第一次询问时,桑德声称他把车停在报刊亭旁。当后来被告知汽车是在离报刊亭40米开外的支路上找到时,他立马改口,说有可能把车停在那里,然后走回到报刊亭。”
“我听说过这种事,有人在纽约参加狂欢派对,第二天在芝加哥酒醒后,对前晚派对上的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律师不为所动,继续道:“这些细节,再加上他财务状况不好,生活上对自己约束不严,完全证明了对他的拘捕是正确的。”
伊娃瞪大眼睛,脸涨得通红,不耐烦地敲打着桌面,“这么说,你相信桑德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把钱藏在从斯德哥尔摩到特朗松德的某个地方,等回家后装作发现钱不见了,然后声称可能是在餐馆被偷的。”她紧张地盯着他,“我理解得对吗?”
律师点点头,眼里放出光芒。
“在餐馆或别的什么合适的地方。”
“无所谓,钱在哪里被偷不重要,”她反驳道,“不过你和检察官肯定都认为他是个白痴吧。”
律师饶有兴致地看着秘书。
“怎么说?”
“就是说,桑德非常自信,觉得他说的他带着公文包到处走,却浑然不觉厚厚的九扎钞票什么时候不见了这种鬼话可以骗过你们。”
律师一时没有接话。伊娃正在担心,虽然一开始是老板鼓励她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她是不是有点太直言不讳了?但她很快看到律师惯常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如果哪天我有麻烦了,你一定要帮我辩护。”他用赞叹的语气道,“格林小姐,这个案子我们接了。”
“哟。”伊娃说,却莫名觉得膝盖发软。
公交车启动了,尾气喷到伊娃脸上。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她把雨衣裹紧了一点,怀着忐忑的心情独自一人踏上了黑黢黢的路。怎么说呢,一个人来到这么黑的地方可能是个愚蠢的举动,她对这个地方不熟,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寻找什么。她很好奇,如果律师知道了她凭着一时冲动,从环线路搭公交车来到特朗松德,摸黑寻找可以翻案——概率微乎其微——的线索,会说些什么。她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知道公交车回城的时间。
没走多久,她看到路的右边有光闪了一下,她朝发光的地方走去。之前的光点渐渐扩大成一片矩形,再走几步后,她看出那是一个报刊亭。还没走到跟前,她看到售卖窗口后面坐着个男人,正在埋首看书,只露出头发稀疏的脑袋。柜台上,在巧克力饼干和当月杂志中夹杂着一只旧烟灰缸,里面插着未熄灭的香烟。
这肯定就是桑德买报纸的报刊亭,伊娃想,那么支路和荒地又在哪里呢?她四下瞅了瞅,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条从主干道分叉出去的混凝土小路。那么荒地应该位于支路同侧,离报刊亭很近。她朝着小路同侧的方向走了一步,隐约看到路边茂密的针叶林有一道宽阔的缝隙。毫无疑问,她已经来到了三个星期前发生离奇案件的现场。
伊娃透过玻璃窗看着报刊亭里的男人。他仍在专注地看书,一点也没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她仔细思索了一番如何开口,正待上前,黑暗中一束闪烁的光引起了她的注意。
不,路上没有汽车或自行车,光是从林子里透出来的。也许来自附近一座房子?但紧接着她注意到了针叶林的缝隙,心里咯噔了一下,光来自那片荒地。
伊娃既惊讶又焦虑,匆匆离开报刊亭光照的范围,跑下短斜坡,停在一丛低矮的灌木旁。这里是荒地的边界,她隐隐能看到荒地向前延伸出去,形成一个长方形,两边是在风中沙沙作响的针叶树。
刚才还在闪的光已经灭了,荒地上漆黑一片,空无一人。难道是她看错了?不,她没看错,光再次亮起来,但瞬间又熄灭了。伊娃凝视着黑暗,惊讶中夹杂着恐惧。光离她出乎意料地近,似乎是从一片凹陷的地底下发出来的。
她站在原地不动,紧张地抱着一棵树,过了几秒钟,光又亮起来。她打了一个激灵,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有人正在桑德当初掉下去摔昏的沟里寻找东西。
伊娃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最终鼓起勇气,迈步朝亮光走去。荒地上积了水,靴子踩上去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她差点被一簇结实的草绊倒。
沟像一根黑线卧在荒地上,一直延伸进黑暗的树林。直到走得很近,她才辨认出那个打着手电筒的身影是个女人。女人把腰弯得很低,手电筒射出的锥形光束在泥泞的地上晃动着。突然,她挺直背,关掉了手电筒。
伊娃立刻停住脚,屏住了呼吸。难道是沟里的女人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接下来,手电筒的光束直直地照在她的脸上,刺得她睁不开眼。她本能地举起手臂往后退,像是要保护自己。
一个声音传来:“这不是律师的秘书小姐吗?”
伊娃放下手臂,手电筒的光束已经移开了,照在一圈黄草上。
“是的。”她惊讶地说道。
人影走上前来。
“我想……我在找……我知道我丈夫是无辜的……”
话说得很快,语气急促,语调飘忽,听着很不自然。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反射光,伊娃看到了桑德夫人一脸戒备的表情。
“我相信沟里有东西,”她继续道,“警察来时这里覆盖着雪,那个拿走了钱的人可能落了什么东西在这里……谁知道呢……”
伊娃回过神来。
“白天找不是更好吗?”她友善地建议道。
桑德夫人关了手电筒。
“白天!”她带着奇怪的表情,若有所思地重复道,“如果邻居们看到我白天在这里,又不知要说什么闲话了。”她眨了眨眼,“小姐,你住在这附近吗?”
“不,”伊娃说,“我坐车过来的,因为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她停顿了一下,“我相信你丈夫是无辜的。”
桑德夫人一下抓住她的手腕,声音突然有了活力。
“你真这么想?”
伊娃点点头。
“律师准备接下这个案子。”
桑德夫人紧紧握住她的手腕。
“啊!”
伊娃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变聪明了。
“我想你应该回家。请相信我们。如果警察知道了你摸黑来这里找东西,指不定会有什么误解。”
桑德夫人静静地站了片刻。
“也许你说得对,”她低声道,“我明天可以打电话给律师吗?”
“当然可以。”伊娃回答。
桑德夫人握了握伊娃的手,无比信任地道了声“晚安”,离开了。
伊娃带着些许好奇,目送着桑德夫人消失在夜色中。然后她若有所思地来到沟边,朝主干道的方向望去。这里离报刊亭估计有40米。荒地上隐约可见一条幽暗蜿蜒的小路。三个星期前,出纳员桑德就是带着装有钱的公文包踏上了这条小路——他从报刊亭出发,走到她现在所在的位置。他声称听到后面有人叫他,转过身来却挨了重重一击,失去了意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沟里,公文包里的钱不见了。但刚下过雪的地上只留有他自己的足迹,所以他的说辞没人相信,目前他因监守自盗公司的9万克朗销售款被拘押。
伊娃陷入了沉思。她一边思索一边顺着小路走回到报刊亭。头发稀疏的男人还在看书,柜台上摆放着杂志和巧克力饼干。她敲了敲玻璃窗,男人抬起头来,推开窗户。
“晚上好。”伊娃说。
“晚上好。”报刊亭老板道。男人30多岁,一张苍白的窄脸,淡蓝色的眼睛里充满着好奇。
伊娃趋向前,直截了当地问:“出纳员桑德就是在你这里买的报纸吧?”
伊娃捕捉到男人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
“是这里。”
她点点头,转头看着支路所在的方向。
“他是从那边过来的,对吧?”
男人警惕地看着她。
“你问这个干吗?”
伊娃犹豫了几秒钟。
“我姓格林,”她解释道,“是负责桑德案件的律师的雇员。”
“这样啊!”男人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你来这里,是想实地还原事发时的场景?”
听他的言语,还挺有文化的,伊娃想。她提高声音道:“对。”
男人半起身,指着支路道:“是的。桑德是从那条支路过来的,他先把车停在那里。”这个头发稀疏的男人打开了话匣子,“他跟往常一样买了份《快报》,然后从这里走到荒地,抄小路回家。这些我跟警察都说过了。”
“我知道,”伊娃说,“你看到他当时是带着公文包的,对吧?”
男人点了点头。
“他把报纸放进了公文包。”
“你有没有看到包里有钱?”伊娃问。
男人摇了摇头。
“警察也问了这个问题,但我真的没看到。他站得离窗口很近——就像你这样——他打开包的时候,包放在身子下面很低的位置。”
伊娃点点头。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公文包胀鼓鼓的?”
男人又摇了摇头。
“没有,真的。”他叹了口气,“太可惜了——我认识出纳员桑德有三年了。他是个好人,一直都是。当然,那天他是喝了点酒,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伊娃看着那张苍白瘦削的脸。
“那晚他有点喝醉了,是吧?”
男人点了点头。
“他是喝醉了,不但唱歌,还和我开玩笑呢。”
“他有没有说过他想走荒地上的小路?”伊娃问。
“他说了。”
“他有没有说过为什么不直接开车回家的理由?”
男人点了点头。
“当然说了,他说刚下过雪,支路太滑不好走,他最好步行回家,拿点灰撒在打滑的路面上。”
“他怎么知道支路路滑难走?”伊娃若有所思地问,“他才走到路口。”
“我没问。可能是凭经验吧,觉得刚下过雪的路难走。这种天气,路肯定滑。”干瘪的男人耸了耸肩,“mrrMXTObCmLehNk/va8p1Q==再说,他不是喝醉了吗?也许他想的是,把车停在路口,等醒了酒再开回家,毕竟支路很窄,弯道又多。”
“他一开始说车是停在这个报刊亭旁边的。”伊娃沉思道。
男人摇了摇头。
“他把车开了过去,停在支路和主干道交叉的路口。我认得他的雪铁龙车,他开过去时我还在想他是不是已经在城里买了《快报》。这种事以前有过。”
“那时是6点半?”
男人点了点头。
“我刚好在那之前看了下时间,之前的一个小时一个顾客也没有——主要是天气原因,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雪。”
“你还记得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吗?”伊娃随意地问了一句。
男人想了想。
“5点15分左右。刚开始下得不大,但随后就成了鹅毛大雪。”
“什么时候停的?”
男人皱了皱眉。
“就是桑德来这里买报纸的时候停的。”
伊娃打开手提包,拿出钱包。
“那么,在桑德来之前或之后,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或听到可疑的声音?”她问。
男人摇了摇头。
“我没看到人,也没听到什么声音。”他叼起一根烟,“我只注意到有一辆车经过这里。是辆卡车,从南边过来的。对了,那辆车跟桑德几乎是同时到达这里的,我觉得他俩好像在支路那边差点撞上。”
“我知道了。”伊娃点点头,掏出一克朗放在柜台上,买了份《晚报》。她把找的零钱放进钱包,再放回到手提包里。报刊亭老板好奇地看着她。
“你好像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说。
“确实,”她回答,“我知道是谁偷了公文包里的钱。”
最后这句话不是真的。她其实没有一点头绪。不过,45分钟后在环线路上下车时,伊娃自己都不知道,她离解开谜题又近了一步。
借着路灯灯光,伊娃查看了记在笔记本上的地址,然后朝北上了交通繁忙的哥特街,很快进入一条黑黢黢的小巷。不久,她走上灯光昏暗的楼梯,在一扇有点破旧的门前停下,按响了门铃。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开了门。
“安德松先生?”伊娃问道。
“是我。”男人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伊娃做了自我介绍,说明她来访的原因。男人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进来吧,屋里有些乱。”
伊娃进了房间,脏污的墙上贴着廉价的彩色印画,地板上有撕破的报纸。一个女人抱着婴儿穿过一扇门,消失不见了,两个玩玩具的小家伙抬起头来,用戒备的目光注视着她。
安德松请她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木凳上。
“啊,警察已经来过了。”他先开口。
“我知道,”伊娃点点头,“但我还是想再跑一趟,听你亲口说。”
“嗯。”他嘟囔道,似乎受宠若惊。
“11月14日傍晚你从特朗松德经过,对吧?”她问。
安德松点点头,视线飘忽不定,最后落到伊娃穿着尼龙丝袜的腿上。
“你确定是14日吗?”她继续问,把裙子往下拉了拉盖住膝盖。安德松把目光移开,看向上方。
“肯定。那是我最后一天开车去汉登。”
“汉登?”
他点点头。
“汉登离这里远得很,几个星期来,我都去那里运砾石。”
“你是什么时候经过特朗松德的?”伊娃问。
“6点半左右。”
“你当时看时间了吗?”
安德松摇了摇大脑袋。
“没有,但在那之前刚看过。那天我回城的时间有点晚,开到德瑞维肯湖的时候是6点25分,从那里到特朗松德只用了不到五分钟。”
“你在特朗松德遇到了一辆雪铁龙?”
他点点头。
“是的。就在那条通向树林的支路旁,离报刊亭不远。小姐,你知道吗,两辆车差点撞上,那个白痴没给出任何信号就变道!我不得不猛踩刹车,没翻车算我运气好。路本来就滑,加上刚下过雪,像溜冰场。我朝他大喊,要他小心点,然后继续赶路。说真的,我真想下车扇他一巴掌。他要么喝醉了,要么不会开车。”
伊娃把一绺垂下来弄得额头痒痒的卷发捋上去,问:“你看到雪铁龙在支路上继续往前开吗?”
“车在路口停下了,”他解释道,“我是从后视镜看到的。”
伊娃站起来,轻轻叹了口气。
“报刊亭还亮着灯吧?”她问。
他点点头。
“是的。”
“你注意到那里当时有顾客吗?”
“没有顾客。”
“你看到里面有人吗?”
安德松疑惑地看着伊娃,摇了摇头。
“我没注意这个,但应该有人,亭子里亮着灯呢。”
伊娃点了点头。
“应该是。”
伊娃朝安德松伸出一只手。
“还有一个小问题,安德松先生,6点半左右时雪还是下得那么大吗?”
“不,小多了。”
“谢谢提供信息。”伊娃道。
一刻钟后,伊娃找到了在11月14日星期五接待过桑德的餐馆女服务员,两人站在后厨的角落里聊了起来。伊娃没得到什么新信息。桑德是在4点半没过多久来餐馆的,他点了些东西吃,还喝了12.5厘升的酒。5点刚过他付了账单,但是不是立刻就走了她不知道。他有可能坐到5点半才走的,因为那个时候女服务员下班了,她注意到他之前坐的桌子旁没人了。对了,她也注意到了桑德来时带着个胀鼓鼓的公文包,他像保护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看管着包。
就桑德是何时离开餐馆的这个问题,餐馆的接待员也给不出一个更精确的时间,他对这位客人的印象非常模糊,觉得他是在5点到5点半之间离开的。
伊娃在哥特街上一边慢慢地朝环线路走去,一边思索着。看来,为桑德翻案的前景暗淡。他有可能真的是在5点半离开餐馆的。虽说这里距离特朗松德只有10公里左右,正常驾驶也就一刻钟,但如果司机喝醉了,肯定会开得很慢,而且还要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一下,所以花一个小时才到特朗松德也是有可能的。再说,如果他还需要把9万克朗藏在途中的某个地方,很可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就在她经过环线路和哥特街交叉路口的一个报摊时,她突然想起,桑德曾说过,他开车途经斯坎斯图尔(斯坎斯图尔就在环线路附近)时,天开始下雪。现在有个机会能确定他离开的时间。
伊娃来到报贩面前。你还记得今年下的第一场雪吗?记得,是在一个星期五傍晚。什么时候下的?5点过几分。报贩记得非常清楚——就在《快报》的车送来《增刊》时,天空飘起了雪花。他还对送报的人调侃道:“这场初雪你们报纸来不及报道了吧。”
伊娃站在报摊前,脑子里一团乱麻。她告诫自己放松,这样才能从乱麻中理出头绪。她仔细回想了一下,看来报贩的这个证词可以确定桑德是刚过5点——而不是5点半——就离开了斯德哥尔摩。这多出来的半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呢?对,这意味着桑德开车到特朗松德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这段距离通常最多用一刻钟。
就算他因为醉酒和下雪而开得小心翼翼,就算他时不时停下来清醒一下,就算他把钱藏在了途中某个地方,一个半小时的开车时间仍然太长了,令人难以置信。
突然,她脑中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惊人的想法,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联想,就好像在拼图游戏中找到了最关键的那张碎片,以此为中心,其他碎片一环扣一环,严丝合缝地拼贴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拼图。
伊娃走进电话亭,给气象局打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了报贩的话,没错,11月14日那天,斯德哥尔摩是在刚过5点开始下雪的。
伊娃走出电话亭时,已是8点55分。她急忙重返卡车司机安德松的家。9点整,她按响了门铃。人高马大的安德松开了门。
“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她气喘吁吁地说。
“好的。”安德松很吃惊。
“那天傍晚你开车经过特朗松德时,地上的积雪厚吗?”
“相当厚,15厘米左右吧。”
“雪地上有很多车辙印吗?”
他皱起饱经风霜的额头,缓缓地说道:“不,一条都没有,我敢保证。”
她激动地扑过去,在他胡子拉碴的脸上轻轻拍了两下。
“把外套穿上,跟我走,我们得去解救一个无辜的人。”她大声道,“快点,快点!”
一个多小时后,两辆警车和一辆私家车停在特朗松德的一栋小别墅前。车上下来了一帮着便装和制服的警察,一个胡子拉碴的卡车司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警察们分散开来,呈扇形包围了别墅。一个红头发的高级警官——此次行动的负责人——带着一小队人马穿过别墅没上锁的门,后面紧跟着卡车司机和金发女郎。狭窄的木楼梯在警察们脚底下嘎吱作响。一行人来到楼上,一扇门紧闭着,上了两道锁。
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扫来扫去,一名警察绊倒了。高级警官重重地敲着那扇紧锁的门。
“警察,快开门,不然就破门了!”
回答他的是沉默。
警官重复了一遍警告,房间里仍是沉默。
下一秒,随着一声巨响,门破了,警察们蜂拥而入。六道亮晃晃的手电筒光束齐齐照向角落里一个脸色苍白、头发稀疏的小个子男人,他面前放着几个装得半满的袋子。在枪口的威慑下,他不情愿地举起双臂,恶狠狠地看着高级警官从袋子里取出一沓沓的钞票。一名警察灵活而熟练地搜查了小偷的口袋,交给警官一个钱包,里面除了钞票,还有一本护照——上面是报刊亭老板的名字亚特·谢林——和一张去巴黎的机票。
“你至少五年后才有机会去巴黎了。”高级警官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地说道。
一名警察去到壁橱前看了一眼,拿着一只鞋子回来了。
“鞋码是42,”他说,“跟桑德的码数一样。”
谢林恶狠狠地盯着伊娃。
“当你戴着假睫毛站在报刊亭前时,我就该杀了你。”
“有点羞耻心吧!”伊娃愤怒地回击道。
律师早上喝咖啡时没有读那份让人吃惊的报告。9点03分,他来到办公室,想直接听秘书说说事情的整个经过。
“详细说说,”他说,“这可是非常难得的冒险经历。”
伊娃嫣然一笑。
“其实很简单,”她说,“事情是这样的:刚过5点桑德就开车离开了斯德哥尔摩,5点半左右他到达了特朗松德的那家报刊亭前。斯德哥尔摩刚过5点就开始下雪了,但特朗松德晚了大概一刻钟,所以当桑德到特朗松德时,路面上只有薄薄的一层雪。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桑德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神志不清——除酒精外,牙医给他注射的麻醉剂也有一定作用。在买报纸时,他无意中让报刊亭老板谢林看到了公文包里的钱。他摇摇晃晃地踏上了荒地上的小路,想等清醒后再回来取车,因为支路很窄,转弯又多,加上雪天路滑。
“谢林跟在他身后来到荒地,追上时,叫了一声,趁他转身,用扳手重重地击打在他太阳穴上。桑德倒下,掉进了沟里,谢林则把公文包里的钱洗劫一空。”
伊娃接过律师递来的一根烟,律师还为她擦燃了火柴。
“接下来就到了整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伊娃继续讲述,“之前只是零星地飘着雪花,而从这一刻起雪开始下得越来越大。谢林灵光一闪,想出个绝妙的主意。他继续待在沟里,在漫天大雪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期间基本不会有人来报刊亭——一方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另一方面是这个时间段没有公交车经过此地。再说,他从所站的位置也能看到路上的情况。
“6点半左右雪开始变小,地上的积雪已经很厚,完全覆盖了两人之前的足迹。谢林抖掉公文包和桑德身上的雪,在沟里的一块石头上按下印记,看起来就像是桑德把头撞在了石头上。
“很早以前谢林就注意到他和桑德穿同样码数的鞋,连鞋的款式都差不多。这时,他倒退着走回主干道,等回到报刊亭前,他大跨步来到雪铁龙停车的地方,上了车,把车朝支路开去,就在变道的时候,他遇到了卡车。他把车停在支路和主干道交叉的路口,下了车,沿着路边走回报刊亭,然后大跨步跳到门口,溜进了亭子。”伊娃叹了口气,“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律师抖了抖烟灰。
“确实是个绝妙的主意。”律师喃喃自语道,但紧接着提高声音,“为什么他不让车停在之前的位置?”
“就在他倒退着回来,往报刊亭走的时候,他听到了卡车过来的声音。这是个难得的绝佳机会,可以找到一个证人,证明雪铁龙是在6点半左右抵达特朗松德的。他还故意在卡车面前变道,以确保卡车司机印象深刻。当然,卡车有可能会在报刊亭旁停下,但他认为可能性很小,值得冒险。”
律师对伊娃的推理表示叹服。
“你是怎么调查清楚这一切的?”他问。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我调查出来的。”伊娃谦逊而老实地答道,“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案子里有一些不合情理的奇怪地方,但直到确定了桑德是5点刚过就离开了市区,我才厘清了事实真相。于是我想到,他确实可以在5点半之前——也就是雪下大之前——抵达特朗松德。然后自然而然地,我就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如果桑德这个时候在荒地上被人打劫,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劫匪一直等到雪停,再倒退着走回去,不管是警察也好,法官也好,都会认为那是桑德本人的足迹。”
律师点了点头。
“好在卡车司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他确认报刊亭外面的路上没有任何车辙印。”
“但在一个小时后,”伊娃说,“当警方勘查现场时,那条路上已经有很多公交车和其他车辆驶过的辙印,还有十余人在报刊亭前踩踏的脚印。”
伊娃从手提包里拿出小化妆镜,审视着眼睫毛。
“你看我的睫毛像是从超市买的假睫毛吗?”机智勇敢的女孩突然换了种俏皮的语气问道。
“当然不像,”律师语气坚定地说,“你的睫毛明显要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