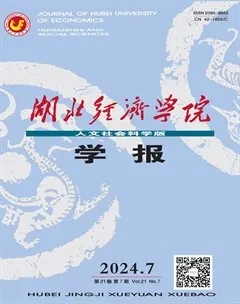NFT数字作品的首次销售原则适用分析
摘 要:在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面临许多困境。首先,在技术上能否能够在不产生新复制件的情况下使数字作品达到所有权转移的效果是一大难题;其次,在传统著作权法理论上,主流观点认为首次销售原则只应适用于有形载体的作品上,在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会使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冲突;最后,在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需要解决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NFT技术的出现使数字作品适用首次销售原则成为可能。第一,适用发行权的实质条件是交易作品的所有权转移,并不是交易作品的载体形式;第二,NFT交易模式与电子提单相类似,其能够达到使数字作品所有权转移的效果;第三,对于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利益冲突问题,可以采用补偿金制度以及发行权有限穷竭原则来进行平衡。
关键词:NFT交易;数字作品;发行权;首次销售原则
基金项目:烟台大学2023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NFT数字作品的首次销售原则适用分析”(GGIFYTU2303)
作者简介:王玉庆(1999-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烟台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能否适用首次销售原则一直极具争议,学界对此的讨论也从未停止。首次销售原则又称“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是指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经著作权人许可,或依法律规定,首次销售或赠与之后,著作权人就无权控制该原件或特定复制件所有权的再次转让[1]176。首次销售原则是著作权法对发行权的限制,故其依托于发行权而存在。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传统发行权的基础在于作品与有形载体的不可分性。在网络时代,数字作品的出现打破了作品与有形载体的不可分性,为了规制网络空间的数字作品传播,我国创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作品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商业模式,如电子书售卖平台,计算机软件售卖平台,音乐作品售卖平台等①。因数字作品的无形性,且困于技术的有限性,无法达到数字作品所有权转让的效果,所以网络交易平台大都以许可使用的形式进行交易②。买家在购买数字作品后不得二次销售。如此将会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不利于网络空间的二级市场发展。但是NFT技术的出现,或可将首次销售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成为可能。
NFT是“非同质权益凭证”(英文全称为:Non-Fungible Token)的简称,是依托于区块链技术,经过加密算法生成的记录在区块链上的一组元数据,该数据显示为存储特定数字文件的具体网址或者哈希值。数字文件可能存储在区块链上,也可能存储在其他外部服务器中,但是该NFT与该数字文件存在唯一且永恒不变的指向性。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去中心化以及不可篡改性,使得NFT之间不可替代,每一个NFT都是独一无二的。当NFT与区块链上的底层智能合约相关联,其便能记录每一个NFT的发行者,以及未来的每一次流转信息。当NFT指向的特定文件为数字作品时,这将使得该数字作品在网络空间上达到类似于物的被特定化的、唯一性的效果。但是发行权以及首次销售原则能否适用于网络空间仍需进一步的讨论。
二、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困境
(一)技术上的难题
在NFT技术出现以前,就有许多企业尝试在网络空间上开启数字商品的二级市场。如美国ReDigi网上二手音乐交易案③、德国Usedsoft网上二手软件交易案④、以及2019年Tom Kabinet 网络二手电子书交易案⑤等。欧盟法院也曾在先后两次判决中给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在美国ReDigi案中,美国法院认为在将音乐作品转售的过程中,其实质上是在新的介质上产生了新的复制件。虽然原来的复制件会被强制删除,但是这并不会构成对“新的复制件产生”的抗辩。在其他电脑中产生新的复制件的过程中,并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授权,其侵害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美国法院强调,并不是权利用尽原则不保护数字作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产生新的复制件,即如果将存储数字作品的载体一同转售,那么其就可以适用权利用尽原则。由此可知,在不产生新的复制件的前提下转移特定复制件,是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技术难题之一。NFT技术的出现或可解决这项难题,NFT本身是区块链上的一组元数据,NFT所代表的是其指向的数字作品的权益凭证。在第三方交易平台上,发行者与消费者所交易的是NFT权益凭证本身,整个交易过程不会产生新的数字作品复制件,NFT本身数量不会增加,甚至不会改变数字作品的存储位置。唯一改变的是智能合约上权益凭证所有人的记录情况。
在德国Usedsoft案中,欧盟法院认为,计算机软件公司收取用户销售金额应为软件所有权转让的销售行为,而不是许可使用行为,其授予用户的永久许可使用权限与所有权转让并无不同。计算机软件公司的销售行为是计算机软件的所有权转让,因此其适用首次销售原则。欧盟法院认为,在网络上发行软件行为与传统的有形载体的发行行为并无不同,只要构成所有权的转移,就可以适用首次销售原则。且法院认为只要用户在转售计算机软件时,将本地计算机上软件进行删除,其就不构成复制权侵权。由此可知,在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另一技术上的难题是:能否使数字商品在买卖过程中达到所有权的效果。对于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过程中能否达到所有权转移的效果,目前还存在争议。
(二)著作权法上的限制
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态度可以从“胖虎打疫苗案”中进行分析⑥。该案一审法院认为,目前我国发行权的适用条件为有形载体的作品原件或复印件的转移。依据数字作品本身的无形性,其无法适用发行权的相关规定。首次销售原则的适用基础为发行权,因此数字作品不能适用首次销售原则。这也是首次销售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最大的法律障碍。数字作品本身的数据属性,使其根本不会存在有形载体,因此有学者认为基于发行权而适用的首次销售原则在网络空间没有适用的基础。我国《著作权法》中对发行权的有关规定并没有明确说明其以有形载体为基础⑦,但是我国实务界以及理论界均倾向于认为发行权应以有形载体为基础。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的成员国,虽然WCT第六条关于发行权的规定中并未强调其必须适用于有形载体⑧,但是在议定声明中强调:“该条款中的用语‘复制品和‘原件和复制品,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所以主流观点认为我国作为WCT的成员国,观点应与WCT保持一致,遵守相应的规定[2]。在传统观点中,首次销售原则的成立基础与初衷是作品复制件与其有形载体的不可分割性[3],因此依据传统著作权法理论,数字作品没有适用发行权的条件,故无法适用首次销售原则。
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另一法律局限是:网络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⑨。在NFT数字作品的第三方交易平台上,除少数的盲盒销售模式以外,大部分数字作品都可以在该平台上进行浏览。交易平台所面向的消费者是不特定的公众,当消费者购买了一款NFT数字商品后,其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浏览或欣赏该NFT数字作品。由此可知,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过程中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畴。如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过程受发行权控制,则会导致在网络空间数字作品受到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叠保护问题,更有学者提出在网络空间适用发行权会导致信息网络传播权被架空[1]175。另一方面,如只是针对NFT数字作品的交易适用发行权,“而其他的数字作品交易(如视频网站提供电影、电视剧作品的付费下载)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会使专有权利的适用出现混乱,丧失统一标准,因此其不可取”[4]。
(三)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利益失衡
在2019年Tom Kabinet案中,欧盟法院提出电子书不同于计算机程序,电子书的转售不能适用发行权用尽原则。欧盟法院对于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存在看似两次自相矛盾的观点,或许我们可以从经济与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计算机软件与电子书的商业价值是不同的,计算机软件的商业价值在于其使用功能,而电子书的商业价值在于其本身的内容。通过传统的有形载体进行销售计算机软件的行为与消费者在网上下载计算机软件的行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并不会影响计算机软件本身的使用功能。相反,如果通过网上下载的计算机软件,不允许消费者进行转售,则“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特定主体的必要性”[5]。但是以数据为载体的电子书与存在有形载体的纸质书是不同的。书籍受保护的价值在于书籍本身的内容,而电子书的存在会使纸质书的市场大受打击,且电子书本身的数据性质,可以使其在阅读以及转售过程中达到无损性,其二级市场的开放将会使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受到较大损害[6]。因此,若要在网络空间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必须要解决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否则将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三、NFT数字作品适用首次销售原则正当性分析
(一)发行权及首次销售原则的立法背景及法理基础
首次销售原则是发行权衍生出来的,而发行权则跟复制权紧密相关。“在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产生之初,著作权人享有的主要就是复制权和表演权”[1]163。在1979年《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并没有规定作者享有发行权,而是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加入了发行权的规定。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作品与有形载体具有天然的不可分性,作者授权他人复制自己的作品,被授权人若想实现复制件的价值,必然会将其投向销售市场,所以作者授权复制权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发行的含义。但是复制权仅能规制非法复制行为,而对于他人非法销售经过合法授权的复制件行为却无法规制,因此立法者设立发行权旨在解决他人未经许可出售作品复制件的行为[7]。据此可知,发行权在某种意义上是复制权的补充规定。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权是:“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条文中的“原件或者复制件”是否就表达了是作品的有形载体的含义,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关于发行权的规定中也采用了“作品原件或复制品”的表达方式,而其在议定声明中又强调条款中的用语“原件和复制品”,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证明“原件和复制品”与“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并不天然等同。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关于发行权的规定并没有限制在作品的有形载体内。同理,美国《版权法》、英国《版权法》以及德国《著作权法》中对发行权的规定均采用了“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说法⑩,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为有形载体。上述针对WCT第6条的“外交官议定声明”不能代表所有条约国的看法,“它仅仅表明WCT通过之时,各国外交代表未能达成一致,而为达成WCT,各国代表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发行权限定于有形载体,这是欧盟委员会当时所代表的欧共体的立场”[8]。
在司法层面,从上述分析的几个案例中可知,美国法院以及欧盟法院在Usedsoft案中均没有以数字作品没有有形载体作为其不能适用发行权的理由。欧盟法院认为只要交易过程达到计算机软件所有权转让的效果,就可以看作是发行行为,可以适用首次销售原则。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第1款发行权的规定:“作者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作品原件或复制品的专有权。”我们可以把它表述成:作者有权以任何形式向公众转移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其所表达的发行权核心在于转移作品的所有权,而不在于作品的载体形式。作品的被保护价值亦在于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的载体,只是囿于当时年代的技术限制,作品与有形载体往往不可分离,所以才将发行权限制于有形载体之上,忽略了发行权的立法目的是使“著作权人得以控制侵权复制件的流通”[9]204,对于复制件是有形载体或是无形载体并不是重点。
首次销售原则是对发行权的权利限制,该原则最早是在1908年由美国联邦最高院Bobbs-Merrill Co. v. Straus案?创设。在该案中,被告Straus合法购得由原告拥有发行权的图书,并以低于原告所规定的图书价格将该图书进行了转售,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其发行权。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发行权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版权人复制和销售复制品的权利,而在发行权之外没有授予版权人控制复制件未来转售的权利,此种行为构成了对发行权的不当扩张,限制了合法复制件在市场上的自由流转。后美国版权法将首次销售原则纳入其立法体系并被世界各国接纳?。虽然我国对首次销售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承认将首次销售原则作为发行权的限制使用。首次销售原则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作品所有权人对作品所享有的物权上的处分权与作品的著作权人对作品所享有的发行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平衡消费者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前提是作品已经被发行权人合法的转移了该作品的所有权,即若数字作品可以适用发行权,那么其便有了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法律基础。
(二)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
如若在网络空间适用发行权,那么就需要厘清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法律适用上的界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著作财产权体系中的“传播权”,传播权控制的是以不转移作品所有权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使公众获得作品的行为[1]179。根据前文所述,发行权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控制的是转移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所有权的行为。因此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转移了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而不在于作品载体的有形或无形。网络发行行为不会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被架空,因其二者的管控范畴并不相同。著作权人在行使传播权时,主观想法是想传播其作品内容。著作权人的行为性质是授权许可他人观看或使用自己的作品,但是其并没有转移作品所有权的含义,更没有允许他人可以转售自己作品的含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受众在著作权人未加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以自主复制其所传播的作品,但是其并不必然能复制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本质并不是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而是一种可以使公众得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触作品的服务。在不违约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可以随时收回这种许可。而发行权是以转移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为目的,在买受者支付合理对价后,其便可以获得一份合法的作品复制件,并且可以拥有处置它的权利。因此发行权与信息网络权拥有本质上的不同,发行权适用于网络空间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重叠保护问题,更不会架空信息网络传播权。
(三)NFT数字作品的交易符合发行权的实质
数字作品本身就有作为知识产权客体被保护的独立价值,将数字作品与NFT进行唯一性指向连接的时候,其本质就是将该数字作品复制件进行特定化的过程。由于NFT本身所具有的“非同质性”“唯一性”,使得被特定化的数字作品复制件具备了类似物的独立性、特定性以及可支配性,这便与网络虚拟财产属性相契合[10]。“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事物,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既相对独立又具有排他性的资源”[11]。我国《民法典》第127条提及了网络虚拟财产应受保护的规定,?但是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并未说明。目前理论界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物权说”还是“债权说”具有较大争议。我国立法者曾在2016年5月《民法总则(草案)》第一次审议稿第102条规定:“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后又在2016年9月13日修改稿中,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财产权利保护,“在这两个立法的条文中,立法机关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物的属性,表达得十分清楚、明确”[12],也可以由此看出立法机关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的看法。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8条对债权的规定,债权是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可以看出,债权客体的本质是“行为”。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物,“是指凡是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财产”[13]27。网络虚拟财产的实质是数据代码,其本身独立于人身之外的客观存在,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并且具有财产属性,其符合物权客体的特征。因此,可以将网络虚拟财产看作是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虚拟物,将其作为物权保护。本文将采纳网络虚拟财产“物权说”观点,NFT数字作品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准物权属性,而NFT则是被特定化的数字作品所有权凭证。
NFT作为一种权利凭证,其与电子提单相类似。铸造人在铸造一个NFT时,首先要将数字作品上传至NFT交易平台,并且填写数字作品的相关信息,以及作品发行数量、交易价格信息等。在上传数字作品这一过程中,NFT交易平台会将该数字作品形成一个复制件存储到一个网络服务器中,随后会调用区块链上的底层智能合约启动NFT铸造程序,通过对铸造指令的自动执行,会在该区块链上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通证编码,后续将数字作品的相关信息形成一组元数据文件与该NFT进行绑定,至此便完成了一个NFT数字作品的铸造[14]。在铸造者与NFT交易平台之间存在一个类似代为保管合同的约定,NFT交易平台代为保管铸造者数字作品的复制件,同时NFT交易平台铸造一个NFT作为该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权益凭证放入铸造者在该平台上注册的账户内。其整个过程与托运人与承运人成立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制作电子提单作为货物收据以及权利凭证相类似。“提单是承运人识别货物占有人或所有人的凭据”[15],NFT相当于电子提单,NFT交易平台相当于承运人,NFT基于智能合约可以达成此功能。智能合约会记录该NFT数字作品的详细信息以及未来每一次的流转信息,其相当于在每一次交易过程中,帮助卖家通知NFT交易平台该数字作品的所有权进行了转移,NFT交易平台依据智能合约上的流转信息来确定该NFT数字作品的所有权人,并协助卖家将该NFT转移至买家的NFT交易平台的账户上。NFT交易平台起到了协助卖家履行合同义务的作用。电子提单是由承运人制作的,同样,NFT本身也是由NFT交易平台制作的,并不是所谓的“铸造者”制作的。“提单有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及权利凭证三大经济功能”[16],NFT也具有相似的功能。NFT可以作为NFT交易平台收到特定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收据,也代表了铸造者与NFT交易平台之间的代为保管合同证明,同时,NFT也是该数字作品的所有权凭证。电子提单流转过程中,其三大功能并未改变,只是权利人进行了改变。在NFT的交易过程中,随着NFT的流转,其本身的功能也随之流转,新的权利人依照NFT这一权利凭证,可以向NFT交易平台主张其是该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所有权人,并且NFT交易平台应对新的权利人继续履行代为保管合同。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数字作品复制件的存储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NFT的数据位置也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在智能合约上进行了所有权人的流转记录,NFT的管控账户由铸造者的账户变为了买受者的账户,此种交付形式与“指示交付”相类似。“指示交付又叫作返还请求权让与,是指在交易标的物被第三人占有的场合,出让人与受让人约定,出让人将其对占有人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受让人,由受让人向第三人行使,以代替现实交付的交付方式”[13]56。我国《民法典》第227条也对这种观念交付的形态进行了确认?。指示交付实质上是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转移,理论上NFT数字作品的所有权人具有请求NFT交易平台返还其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权利,但是目前来讲,此种行为不具有可行性,也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体物权中,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是为了实现该物的自身价值,而在网络空间中并不需要转移虚拟物的存储位置,也可以实现其价值。权利人请求返还数字作品的复制件可以理解为其要求将该数字作品的复制件由NFT交易平台的网络存储空间转移至自己的网络存储空间,此种转移行为并没有实际意义,数字作品在NFT交易平台的存储空间与在私人的存储空间并无不同,也不影响数字作品的自身价值,比如数字作品存储在NFT交易平台中依然可以实现其观赏价值、收藏价值以及使用价值。所以在网络空间中,返还原物请求权可以转换为权利人可以随时请求义务人配合其行使虚拟物权的权利。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NFT数字作品在NFT交易平台上的交易结果便是完成了该特定数字作品复制件的所有权转移,其符合发行权的实质要件,NFT数字作品存在适用发行权以及首次销售原则的基础。根据“实践先行”的策略,目前公众对于NFT交易性质普遍认为是其所指向的数字作品所有权的转移,而且对于NFT数字藏品,其本身收藏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对其转售的升值空间,二手市场的开放对于NFT数字藏品而言具有必要性。
四、NFT数字作品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具体制度设计
首次销售原则创设的目的便是通过让渡发行权人的利益,来使消费者的利益达到一定弥补。在纸质印刷时代,由于纸质本身的使用寿命有限,且二手作品通常不会有一手作品的观感,所以二手市场对于一手市场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数字作品不同,基于电子数据本身的无损性,以数据为载体的数字作品也天然具有无损性。二手的数字作品与一手的数字作品并无不同,不影响观感,也没有使用寿命年限。若无限制的开放数字作品的二手市场,会对发行权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进而打消创作者的积极性。这有违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影响作品的传播,阻碍社会的进步。法律作为社会制衡器,其应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进行调和,不应过分关注某一方或某一群体的利益。因此,若想数字作品的二手市场有长远发展,达到促进文化作品传播、鼓励作者创新的目的,就必须要通过相关制度来调节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目前的实践和理论中,主要有补偿金制度、设立追续权、数字发行权有限穷竭原则这几种形式来进行利益平衡,补偿金制度与追续权原理相似,因此我们主要对补偿金制度以及发行权有限穷竭原则进行讨论。
(一)补偿金制度
在实践中,目前允许转售的NFT交易平台会大都会通过契约的方式来约定在数字作品的每一次转售中给予权利人一定比例的版税,版税的比例是由铸造者在铸造NFT时自行写入智能合约内的,平台方一般不会固定版税,只是约定一个范围。如OpenSea交易平台约定权利人可以在0%-10%内约定版税。我国目前的NFT交易平台都不允许转售,在“胖虎打疫苗”案中,奇策公司旗下的涉案NFT交易平台允许发行权人在数字作品未来的每一次流转中收取卖家赚得差价的2.5%作为版税。约定的版税其实质是为著作权人设立了一个追续权。追续权这一制度起源于法国,其是指艺术家及其继承人就其艺术品原件的再次销售获取一定比例收益的权利。[17]其创设的原因在于艺术作品原件的稀缺性使其随着艺术家的名望的提升拥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艺术作品在未来的流转中获得的利益往往远大于其首次出售时的利益[18]。为了改变艺术家在著作权法上的不利地位,鼓励艺术家不断创作,创设了此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追续权,《伯尔尼公约》也对“追续权”作了相应规定?,但是目前我国对追续权的设立还存在一定争议。交易平台所规定的版税大都是针对数字藏品而言,权利人根据数字藏品未来转售的差价来收取版税。但是对于没有溢价转售的普通数字作品而言,或许可以参照补偿金制度对著作权人进行补偿。依照卖家平价或降价转售的价款,按照一定比例来收取补偿金对著作权人进行补偿。而且不管是“版税”还是“补偿金”都可以依据NFT的智能合约在作品时交易自动执行,其可以避免现实中作品流转对象不明,无法行使追续权等问题。
(二)发行权有限穷竭原则
对于数字发行权有限穷竭理论,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法律应赋予著作权人在一定次数内控制其数字作品转售的权限。著作权人在一定次数内对数字作品的转售拥有许可权,并且可以基于转售价格收取一定比例的转让费,在该数字作品的转售次数达到上限之后,著作权人将失去这种“许可权”以及“收费权”,该数字作品的转售将不再与著作权人相关[19]。另一种理论认为,法律应对数字作品的可供阅读设备数量进行底线规定,并且允许权利人对其剩余阅读设备数量进行转售,在次数范围内亦可以转售数字作品,当该次数用完之后,该数字作品的转售权利仍回到著作权人手中,以此来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20]。前者是将利益平衡倾向于公众,后者将利益平衡倾向于著作权人,但两者对于数字发行权的限制与实体中首次销售原则对于发行权的限制相差较大。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世界可以达到与现实世界相映射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实体数字作品的性质映射到网络世界。NFT使数字作品达到了与有形载体作品相类似的特定性、唯一性以及不可篡改性,那么我们也可以把有形载体作品的易磨损性、使用寿命有限性映射到数字作品中。实际上,IBM公司于2011年提交了一项专利申请,该专利可以通过系统设置外部温度、老化速度、作品载体的种类等参数使数字文件作品像普通的纸张或者照片一样逐渐老化[21]。就算不使用这样的技术,也可以根据相对应的实体作品的使用寿命来限制数字作品的转售次数,在达到相应次数后该数字作品将不再被允许转售,其所有权将永久归于最后一位买家。
五、结语
“法律是推陈出新、不断繁衍的社会行为规范,不会也不应紧随某些生活元素的变动而随意改变,也不会对日新月异的新鲜事物熟视无睹,将传统法律与新生事物之间作出一致性解释,或许才是恰当的出路”[22]。发行权形成于印刷时代,但不能因此说明他不适用于数字时代,只要能够对法律进行合理解释,并且有技术作为支撑,那么发行权适用于现实世界与适用于网络世界并无不同。现实世界所具有的问题,网络世界也同样具有,首次销售原则可以解决现实世界中著作权与物权的冲突问题,便也可以用它来解决网络世界中著作权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诚然,目前的NFT交易平台以及相关技术和规则还不成熟,如果草率的将首次销售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这也正是我们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在任何时代,著作权法的目标都是为了作品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在数字时代,我们应探索在法律的指引下,利用更好的技术来使文化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使数字经济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
注 释:
① 如亚马逊Kindle商店售卖电子书、苹果App Store中付费下载软件、QQ音乐平台售卖电子专辑等。
② 如苹果App Store中的服务条款显示:“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获得免费或付费内容,二者均成为‘交易。每一笔交易授予您一项仅使用内容的许可。”
③ Capitol Recs., LLC v. ReDigi Inc., 910 F.3d 649 (2d Cir. 2018).
④ UsedSoft GmbH v. Oracle International Corp,2012.
⑤ Nederlands Uitgeversverbond & Groep Algemene Uitgevers v.Tom Kabinet Internet BV and others Case 263/18,2019.
⑥ 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 0192 民初 1008 号民事判决书。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六)项规定:“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⑧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CT)》第6条发行权规定:(1) 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作品原件或复制品的专有权。(2) 对于在作品的原件或复制品经作者授权被首次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之后适用本条第(1)款中权利的用尽所依据的条件(如有此种条件),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影响缔约各方确定该条件的自由。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⑩ 美国《版权法》第106条规定:“发行指以销售或其他转让所有权的方式,或者以出租或出借的方,向公众分发作品的复制件或录音制品。”英国《版权法》第18条规定:“对于任何类型的作品,向公众公开发行作品复制件均是版权所禁止的行为。”德国《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发行权指公开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或者使之流通的权利。”参见《十二国著作权法》翻译组译:《十二国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页,第577页,第150页。
11 Bobbs-Merrill Co. v. Straus, 210 U.S. 339, 350 (1908).
12 美国《版权法》第109条a款规定:本法之下合法制作或经版权人许可制作的作品复制件的所有人,可以不经过版权人许可,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分其所有的作品复制件。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十二)项。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5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7条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17 《伯尔尼公约》第十四条之三规定:“(1)对于艺术作品原作和作家与作曲家的手稿,作者或作者死后由国家法律所授权的人或机构 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作者第一次转让作品之后对作品进行的任何出售中分享利益;(2)只有在作者本国法律承认这种保护的情况下,才可在本同盟的成员国内要求上款所规定的 保护,而且保护的程度应限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所允许的程度;(3)分享利益之方式和比例由各国法律确定。”
参考文献:
[1]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11.
[2] 王江桥.NFT交易模式下的著作权保护及平台责任[J].财经法学,2022(5):70-80.
[3] PERZANOWSKI, A., & SCHULTZ, J. Legislating digital exhaustion[J].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2014,29(3):1535-1558.
[4] 王迁.论NFT数字作品交易的法律定性[J].东方法学,2023(1):18-35.
[5] 郑万青,高金强.电子书版权保护的欧美经验——兼论我国电子书版权保护体系的构建[J].知识产权,2017(12):92-97.
[6] 孙那.论数字作品发行权用尽原则的最新发展——以Tom Kabinet案为研究对象[J].出版发行研究,2021(1):55-62.
[7] 谢宜璋.论数字网络空间中发行权用尽原则的突破与适用——兼评我国NFT作品侵权第一案[J].新闻界,2022(9):66-74+96.
[8] 何怀文.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3(5):150-159.
[9]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10] 高郦梅.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解释路径[J].清华法学,2021,15(3):179-193.
[11] 林旭霞.虚拟财产权性质论[J].中国法学,2009(1):88-98.
[12] 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及重要价值[J].东方法学,2017,57(3):64-72.
[13] 杨立新.物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14] 林妍池.论NFT数字藏品交易中发行权的扩张——基于对“NFT第一案”的反思[J].科技与出版,2023(5):115-124.
[15] 郭鹏.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权利证券化——以电子提单为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6(4):66-70.
[16] 陈芳.电子提单制度构建基础问题研究[J].求索,2013(2):176-179.
[17] 李雨峰.论追续权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中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32(1):126-136.
[18] 张惠彬,张麒.NFT艺术品:数字艺术新形态及著作权规则因应[J].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2(3):42-50.
[19] 何炼红,邓欣欣.数字作品转售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兼论数字发行权有限用尽原则的确立[J].法商研究,2014,31(5):22-29.
[20] 武光太.试论电子图书数字首次销售原则的构建[J].中国出版,2013(13):47-49.
[2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Aging File System:US20110282838[P].2011-11-17.
[22] 叶林.无纸化证券的权利结构[J].社会科学,2009(3):89-9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