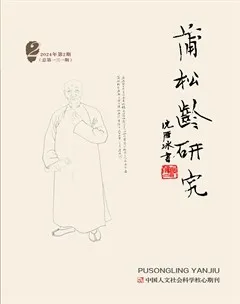折衷叙事:聊斋俚曲中的升仙幻想
收稿日期:2023-11-29
作者简介:赵佩汶(2000- ),女,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
摘要:在通常推崇大团圆世俗理想的聊斋俚曲十五种中,《蓬莱宴》与《寒森曲》却以主人公升仙而离家作结。《蓬莱宴》的言语、情节和结构都存在矛盾,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摇摆不定,暗合蒲松龄在现实中的遭际与挣扎,升仙结局是在现实与理想之外另辟的“蹊径”。《寒森曲》的主人公商三官突破性别限制的奇举被高度赞赏,但也需要承受父权社会的规训,其升仙归宿是折衷叙事的结果。不同于常见的“元结局”,聊斋俚曲中的升仙幻想既是无奈的妥协,又是能够酝酿出高层次“个性”的“积极幻想”。原本限定在“劝世”模套下的俚曲,也得以承载更为复杂的意蕴。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俚曲;《蓬莱宴》;《寒森曲》;积极幻想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志码:A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1640-1715)“以山东淄川地区流行的俗曲小调填入新词而写成的通俗说唱作品的总称” [1]5208,共有十五种。如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所述,聊斋俚曲是蒲松龄怀以“救世婆心”所作,“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 [2]3439蒲松龄自己亦在《慈悲曲》中道出劝善目的,“唱着解闷闲玩,情真词切韵缠绵,恶煞的人也伤情动念。” [3]103因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劝世道理成为俚曲故事的底层逻辑。在主人公得“善报”的结局中,登科荣仕与阖家欢乐这两项世俗理想被普遍落实 ① 。然而,《蓬莱宴》与《寒森曲》两曲,一方面着力宣扬儒家道德与追求,而另一方面,善良主人公的行动却以升仙、离家作结。“唱白相间,散韵交织”的文本内部潜藏矛盾,从中或可透视出蒲松龄在劝世与抒怀之间的折衷幽绪。
既有的聊斋俚曲研究,大致可分为音乐学、语言学、文学、非遗传承四种方向。其中文学领域的研究,或是综合论述聊斋俚曲的创作背景、思路、版本、艺术性等,或是对某一篇目进行溯源与阐析,或是以特定视角归纳分析其中的文化思想意蕴。对于聊斋俚曲中的升仙走向及其中蕴结的复杂态度,学界还未有聚焦。本文试解析聊斋俚曲中具备特殊性的升仙幻想,期望补充一种更为全面理解俚曲的视角。
一、《蓬莱宴》:梦破后的升仙“蹊径”
据刘艳玲考证,《蓬莱宴》是以唐代裴铏《传奇》中的《文箫》一篇为本事的再创作 [4]。《文箫》讲述仙女吴彩鸾与穷书生文箫仙凡遇合,二人有前世神仙情缘,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谪为民妻一纪”。为补家用,彩鸾日抄一书鬻钱,此事逐渐为人所知,二人便搬往郡举村中教儿童读书,最后双双骑虎而去。
在《文箫》的基础上,《蓬莱宴》对情节的重要改动如下:王母见彩鸾动凡心,为施予磨炼而有意撮合二人。彩鸾与文箫恩爱有加,生下儿子韵哥,文箫为求取功名去长安参加科举,才高却落第,归途中吕洞宾将其度脱,彩鸾在家望夫不归,一日忽然彻悟,重新修行成仙。二人在蓬莱宴上短暂相会,又各归仙列。后来彩鸾偷来人间探视韵哥,被王母罚在人世三年,再次升仙后,韵哥中了状元。可知,《蓬莱宴》新编了升仙、离家的结局,增添了科举相关的桥段,将彩鸾嫁与文箫的性质由谪罚改为历练。这些改动的部分更能集中体现蒲松龄对前在文本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旨向。
《蓬莱宴》对科举、爱情与家庭的态度有所矛盾。对于科举,俚曲一方面进行了辛辣的揭露与讽刺。文箫想去应试,彩鸾道“一字不通瞎试官”,“上下都是些好奸贪;若是做了官,才吃不的安稳饭”。 [3]381文箫原是“玉皇面前管书的童子”,十七岁便成了“名士”,却落了第,俚曲中解释为试官贪污。但另一方面,俚曲结尾却提及“韵哥中了状元”,最末诗曰:“夫妻俱得长生乐,又见娇儿中状元。” [3]398“长生乐”与“中状元”并举,都有引人艳羡的意味。结语诗具有为全文定性的作用,俚曲对科举成功的推崇便也格外明显。
对于爱情与家庭,一方面,俚曲以超脱、恒久的仙域映衬其易碎与虚幻。易碎在于,明明彩鸾更喜相守,文箫却以怜妻操劳与求取功名双重动机而离家应试,落第后又觉羞于面妻。吕洞宾带有离间意味地对文箫说彩鸾“限期将满”,“你不舍他,只怕他舍了你” [3]385,又请文箫饮入三杯道酒,之后文箫便转而“一心要出家,妻子全不恋” [3]386。虚幻在于,当彩鸾重回天上,发现蓬莱宴甚至还未散,因而发出慨叹:“回头真是一场梦,可笑离合与悲欢,劳劳攘攘真扯淡。” [3]395
但另一方面,俚曲始终都有将爱情与家庭置于成仙之上的表述,极言其珍贵与幸福:“朝朝每日受孤单,今宵才晓得夫妇乐”,“早知人间这样欢,要做神仙真是错。” [3]376另外还以四百多字的笔墨描绘了彩鸾文箫恩爱美好的夫妻日常,兼及“这样自在,比那神仙还强”“这时节把那富贵神仙一切忘” [3]380-381的评点。之后文箫被吕洞宾度脱,诗曰“佳人才子两相欢,何苦抛家去求仙” [3]388。彩鸾最后还忘不了“儿女缘”,偷偷下凡探望韵哥,进一步表现出对家庭的难舍难分。
除了以上言语、情节层面的矛盾,俚曲在结构上也没有呈现出世俗故事通常具备的对称和圆满。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从100个俄罗斯神奇故事中抽象出相对稳定且作为故事“基本组成成分”的“功能”——“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5]18他在俄国故事中,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34-2005)在北美印第安人故事中,李扬在中国民间故事中,都发现了“缺乏—缺乏消除”这组举足轻重的“核心功能对”。邓迪斯还将该组“核心功能对”提升至民间故事的普遍规律:
大量的民间故事是从不平衡性(disequilibrium)向平衡性(equilibrium)发展的。根据这一观点,不平衡性——一种令人惧怕的、如果可能的话应力求避免的状况——可以看成是一种过剩或者缺乏的状态,不平衡性可以用一些东西过多或另一些东西过少来表述……民间故事即是怎样去掉剩余的东西和如何结束缺乏状况这种关系的简单组合。[6]162
以上形态结构理论虽是从民间故事中提炼,却也可被用于剖析聊斋俚曲这样情节与主题都与民间故事具有一定亲缘性的文人作品。
文箫表面上因体谅妻子而惭愧,缺乏对家庭的贡献;但实际上他自认有“满腹好文章”却未能变现,真正所缺乏的是富贵功名。彩鸾乐于“饮酒赋诗”的清闲生活,瞧不上中举这种“草头之霜”,曾对文箫多加劝阻,但文箫还是不顾妻子的真正诉求,离家应试。后来文箫落第,未能满足缺乏,此时吕洞宾这股“外力”便来哄诱性地度脱他,于是文箫抛却一切失意与牵挂,跟着师傅去修仙。既求不得富贵功名,便转而以忘却富贵功名、取得更高层次之解脱的方式来试图弥补缺失。可以看出,俚曲对缺失采取了逃避的态度,缺失被掩藏,却也被遗留下来。
而彩鸾,须引入普罗普的“回合”概念进行分析,“回合”是“始于反角的恶行或主角的欠缺,最后以婚礼或缺乏消除等告终” [6]5,即一个“缺乏——缺乏消除”的过程,一个故事可由一个或多个回合构成,回合与回合之间有连续、穿插、分总等多种组构关系。彩鸾的经历是一个大回合包含一个小回合。在小回合中,彩鸾缺乏爱情,凭借王母撮合的外力与自身的努力——抄书以补家用,她与文箫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缺乏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段满足是乌托邦式的,“上无公婆,下无子女,直睡到日上三竿,娘子才起来梳头” [3]376,二人不受世俗琐事烦扰,且彩鸾可以使用仙力以维持虽不富裕却也清雅的生活。当乌托邦遭遇现实问题,儿子出生而操劳增多,丈夫又抑郁不平而去应试并失踪,彩鸾就又回到缺乏的状态,长年望夫不归而终日愁闷,直到重新打坐修仙。与文箫类似,俚曲也是悬置了彩鸾的缺失,只是以升仙作为权宜性的安慰。在大回合中,彩鸾缺乏的是仙识定力,王母看出她思凡,便故意使她经受磨炼——“那妮子不安分,教他受受”。 [3]390小回合便是磨炼的具体过程,这场人间试炼使彩鸾幡然悔悟:“我今受人间苦,才知天上甚快活” [3]394,因此仙识定力加强,缺失在很大程度上被填补。但她之后又偷下凡去看望韵哥,说明她依然对人事心存流连,缺失也并未圆满。
可以看出,不同于其它以大团圆为结局的俚曲作品,在《蓬莱宴》中,蒲松龄并非直接落实世俗理想,而是先承认了现实的困阻——科举黑暗、人心不足,又为了使俚曲不至于“沦为”悲剧,便以回避的策略构拟了升仙幻想。理想遭现实冲撞之后并未坍毁,而是乘想象之力升至蓬莱。然而,升仙长生虽在幻想等级体系中高于凡世纠缠,但俚曲无论是在言语、情节还是结构层面,都含有对人间情感的趋向,这就暗示着升仙叙事根底里的无奈。
结合蒲松龄的人生经历,或有助于对俚曲之矛盾挣扎报以“同情之理解”。蒲松龄一生久试不第但仍孜孜于科举,从十九岁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开始,一直考到六十多岁,屡败屡战。在《试后示篪、笏、筠》一诗中,他明言科场黑暗、希望渺茫——“今日泮中芹,论价如市贾”,“文字即擅场,半犹听天数”,但又继续勉励儿子们投身科举——“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 [2]1804蒲松龄对科举有着堪称顽固的执念,中举是其经年累月的迫切愿望,所以他常常将科举成功设为幸福结局的必要指标。但同时,他心间也横亘着摧折自己的险恶现实,因此对理想的实现并不完全乐观。这种症结需要合适的机会宣泄出来,于是他有可能将自身遭际投射到文箫身上,幻想出解脱之道。
蒲松龄与发妻刘孺人同甘共苦五十六年,对她感念至深。但刘孺人操劳寡言,不通风雅,跟蒲松龄的精神沟通相对欠缺。在婚姻之外,蒲松龄曾长达十几年追慕迷恋歌妓出身、富有才情的顾青霞。蒲松龄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爱情理想,但他笔下兼具持家与才情的吴彩鸾形象却可谓“双美合一”,该角色的设定还映照出现实人物的影子。比如,在蒲松龄落第后,刘孺人曾劝他:“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2]3398这与彩鸾对文箫的规劝如出一辙。顾青霞能歌善舞,彩鸾也会“舞霓裳”;顾青霞“书法欧阳画似钩”,彩鸾之字也“真不在钟王下”;顾青霞“佳人韵癖爱文章,日日诗成唤玉郎” [7]336,彩鸾亦衷爱赋诗。既然蒲松龄摹绘了彩鸾这样足以承托其爱情理想的女子,为何彩鸾与含有蒲松龄自我投射意味的文箫之间的爱情还是不得善果?首先,文箫的自责、自卑是蒲松龄心理的真实写照,对于刘孺人,有《语内》一诗为证:“少岁嫁衣无纨袴,暮年挑菜供盘飧。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 [2]1888对于顾青霞,蒲松龄魂牵梦萦却无能为力。或许是由于彩鸾与真实人物的高度重合,蒲松龄更易因联想而被扯回困窘的现实,对彩鸾的美好便觉自惭形秽,俚曲中也正是文箫因心理不平衡而导致爱情破灭。另外,据考证,《蓬莱宴》约作于1689年之后 [8]42,而顾青霞于1688年病逝,蒲松龄曾写下《伤顾青霞》悼念她:“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7]338顾青霞离世,蒲松龄寄托在她身上的浪漫情思也随之消殒,或许这种爱情幻灭的情绪也被注入《蓬莱宴》的创作当中。
切身的打击多少令人对理想的命题心存芥蒂,蒲松龄的现实遭遇或也成为他建构理想世界的情感阻碍。虽然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出于劝世目的而作,通常需要科举顺利、家庭美满的世俗理想结局以施教化,但其个人所积压的抑郁心绪有时亦需要出口。也正是因为劝世的目的,蒲松龄不能在俚曲中悲愤大骂,只能回避失落而引向超脱的升仙幻想。因此,《蓬莱宴》所呈现的并非不假思索的世俗美梦,而是“美梦落空”之后又另辟蓬莱这样虚幻归处的历程。这场“清醒梦”的走向反映出蒲松龄历经大半生磨难之后的出世倾向,但其言语却又时刻倾诉着他对世俗理想的向往。
二、《寒森曲》:规训之内的性别突破
《寒森曲》糅合改编了《聊斋志异》中《商三官》与《席方平》两篇故事,大致讲述善人商员外被地主赵恶虎打死,赵恶虎贿赂官府而糊涂结案。商员外的小女商三官扮作清唱艺人杀死赵恶虎,砍下其头颅,随后自戕。赵恶虎死后又在阴司使贿,员外和三官无力应对,二儿子商礼便绝食以赴阴曹为父鸣冤。阎王贪贿,商礼受尽折磨,终于得遇二郎神。二郎神处罚了一干恶徒,使商员外、商礼复生为人,商礼名登甲榜,选为刑厅,执法严明,后官至尚书。商三官升为神仙,封孝义夫人,香火旺盛。
该俚曲中升仙幻想的承载角色为商三官 ① ,一方面,她为父报仇,贞洁观强烈,恪守儒家人伦秩序;另一方面,她最终选择成神而非回归人世家庭,这似乎又与儒家观念相悖。文中三官自述不愿还阳的理由为:“女子不守闺中教,拿着口刀去杀人,嫁丈夫也着人难信。到如今成了话柄,怎见那远近乡邻?” [3]329这便勾连出文中两组关于人物价值评判的矛盾,其一是“闺中教”与报仇,其二是“人人听说肯称赞” [3]303与“乡邻话柄”。第一组矛盾,三官乔装色诱,手刃父仇,这样有损“贞洁”,且过于刚烈,违背了传统女性评价标准的“闺中教”;但也正是因为三官突破了性别的限制,她的行动才被视为卓尔不群。第一回开头便有曲词:“报仇难得痛快,尤奇在二八红颜。快刀终日绣裙掩,杀人时秋波不转。” [3]273如若三官为男性,为父报仇,便只是相对常见的孝子英雄;但她是“二八红颜”,其出格壮举在古人的视野里相当鲜有,女性的娇柔与斩仇的血腥相叠合,显出秾丽奇绝之色。俚曲对三官多有“全胜人间男子汉”“真正胜似男子汉”之类的赞词,在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之下,将女性抬至一般男性之上,是蒲松龄崇扬三官冲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显证。除了独自复仇核心行动所体现出的机智果敢,俚曲还在其它一些桥段中强调了三官的不同凡响。例如,当商员外的两个儿子背着伤痕累累的父亲回到家,年方十六的三官“跑进来把柳眉直竖,便说:‘二位哥怎么不杀了赵恶虎,提他那头来?” [3]276其过人胆识在初次登场时便展现得淋漓尽致,后面她的所作所为也证明这并非撒气的空话。再如,当一屋子人都守着商员外哭时,三官说:“或是服药,或是打官司,哭歇子当了什么?” [3]276这些描述都体现出三官别具慧眼,蒲松龄对该角色的欣赏也溢于言表。
第二组矛盾,合情合理的称赞和带有贬抑意味的“话柄”如何能在乡邻口中并存?三官对父家甚为忠笃,除复仇牺牲之外,她还在父丧期间“气咂咂”地拒绝了原定的求亲,在阴间为父向二哥托梦求助,成神之后差遣小神“憨头郎”救父于海难,最后在父亲去世时前去迎接,对父亲的敬爱贯穿全曲。在对父亲如此孝顺的情况下,三官对“话柄”的自述,恐怕并非她倾向成神而不愿归家的推托之辞,而确是很可能存在的情况。归根结底,父权社会中,人们的称赞针对的是三官对父家的维护,在对父家最高利益的服务过程中,女性的逾矩才可暂且搁置不论。然而,这种逾矩终究还是与父权社会有所龃龉,三官“抛头露面”的色诱与杀人的刚峻,都有悖父权的规训。当被兄长问起杀死赵恶虎的过程时,三官红脸道:“那个话不好学,到而今还害嚣,为父亲竟把廉耻抖。” [3]322“廉耻”是父权用以制约女性的思想枷锁,其地位低于父亲,却高于女性,还以关乎父家的名声的由头向女性施压。三官在父丧期间对嫁人不屑一顾,在父亲的困难解决之后才注意到出嫁问题,还提到“嫁丈夫也着人难信”,根本上是以父家为重,还有对使父家蒙羞的担忧。若三官重返世俗生活,当以父家为核心的风波平息后,女性的逾矩部分将很可能被筛取、清算,女性自己或陷于流言蜚语缠身的窘境之中。
从以上两组矛盾可以看出,一方面,蒲松龄对商三官突破性别限制的智慧与刚勇报以由衷的赞叹,但另一方面,蒲松龄身处父权社会当中,难免被父权观念所影响,也深知大众会从父权角度对俚曲进行审视,所以他无法撇开三官壮举中对父权的悖逆成分。他对此的规训常常借三官自己之口说出,将三官塑造成既勇毅又知礼的完美形象。从结构层面来看,三官最初缺失某种公道,当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讨回公道之后,却又陷入新一轮的缺失——缺失自洽的处境。按照当时的一般观念,女性的“善报”应当是复生团圆、婚姻美满、儿子中举,但有违“贞洁”与“温顺”的三官却难以在人间收获此种世俗理想。蒲松龄大概不愿三官死,也不宜使之复生,于是只能为其开辟一条升仙的路径,这样既跳脱出凡俗规矩,又能彰明奖赏的意味。所以,三官之升仙,也是蒲松龄无法克服现实阻力,不得不另辟蹊径而构思出的美好幻想,是一种试图弥补三官之缺失的折衷叙事策略。而三官虽然在生活方面离家,心中却依然关怀父亲,正如彩鸾记挂韵哥那样,如此一来,人间事还是始终牵制着看似超脱的幻想。
对三官升仙结局背后复杂态度的厘清,也为理解俚曲中的其它问题开拓了思路。为何上天入地受尽酷刑为父伸冤、为最终全家获胜作出关键贡献的商礼,未能像三官一样被封神?或许是因为商礼可以毫无阻碍地在人世获得理想的“善报”,享尽荣华与功名,便不必将其安置到欠缺实感的天上去了。为何三官在俚曲的前半部分尽显英雄气概,复仇所向披靡,后半部分却自认“女人难争辩” [3]304,束手无策?这种人设的割裂,或许缘于蒲松龄平衡俚曲中男女力量的叙事倾向。商三官不同于其它篇目中囿于家庭琐事的女性,对于男性主导的普世价值观而言有些过于刚强了,而蒲松龄又希望俚曲传遍大街小巷,感发世人,所以便需要再选取一个伟大的男性角色来拼合成曲。在第一个回合中,“人世缺乏公道—手刃仇敌彰显公道”,商三官是主人公;而第二个回合“阴间缺乏公道—告至天神讨回公道”,则是商礼的主场,三官不能在此处行使那类属于主人公的重要“功能”,相较于第一个回合,其力量便显得大大削弱。
其实,即便是在第一个回合,三官也是处于受限状态,她只能女扮男装、自下而上地复仇,行动范围较为狭小。但成神以后,她不仅能以女性神的形象正面世人,还掌管众神,在神仙界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仕途通达”。可见,升仙幻想虽是蒲松龄的无奈之举,含有某种压抑的情绪,但也确实巧妙地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了超然的解放,显示出一般篇目所不具备的开放性。
三、个性的浮现:升仙之于“元结局”
施爱东通过对中国传统戏曲、民间故事乃至世界民间文学现象的考察,提出“元结局”的普遍规律:
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初始条件和欲望目的之间的虚拟语言游戏。……游戏最终必将指向同一个欲望目的,那就是标志世俗幸福的婚姻、家庭、财富和地位,我们将这种标志世俗幸福的大团圆游戏终点统称为“元结局”。[9]76
只要主人公是“正能量的负载者”,故事讲述人和听众就会共同赋予其“元结局”。聊斋俚曲是底层文人的劝世之作,平易通俗,正面主人公通常都获得了“元结局”的归宿。但《蓬莱宴》和《寒森曲》的结局,虽然看似有类似于“元结局”的“外包装”,如前者结尾诗曰:“夫妻俱得长生乐,又见娇儿中状元。” [3]398后者则借二郎神之口夸赞成仙的好处:“二郎爷夸又夸,这个话实不差,不必定把丈夫嫁。奏上元穹高上帝,封号重重福禄加,父兄何必心牵挂?只受那千年香火,胜强似一世荣华。” [3]329但本质上彩鸾、文箫、三官都因升仙、离家而未能通往世俗的圆满。俚曲或许也尝试给出某种解释,即点出三个角色原本就是神仙,彩鸾是西王母座下的仙女,文箫是玉帝的书童,三官“原是一仙娥” [3]329,那么,按照“尘归尘,土归土”的道理,他们升仙是水到渠成之事。但除了彩鸾,对文箫与三官神仙身份的说明都是一笔带过,他们更接近人而非仙。即便是仙,也可以拥有“元结局”,如在《聊斋志异》的《神女》《织成》《嫦娥》等篇目中,主人公最后都在凡间过上了团圆的生活——可见蒲松龄并不必然坚持人仙应当相隔。但在世俗性更强的两篇俚曲中,蒲松龄却反而没有将“终点”设置为“标志世俗幸福的大团圆”。
这种反常现象或许是因为,某些作者无法回避的现实因素阻碍了“欲望目的”的达成。人们想象欲望的满足,是从现实成分多、实现可能性高的情景开始,而当这两个条件不充分时,世俗理想便无法取信于人,于是只能进一步寄托到明显虚构而不必被诘问真实性的幻想中去。这一步夹杂着万般无奈,与其说是在继续尝试满足欲望,毋宁说是一种妥协的安慰。
不过,虽然此类幻想是失落之后的折衷之举,但也是姑且摒除了现实的斥力,为作者与受众提供了腾空至超然之域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篇俚曲中的升仙幻想属于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从精神分析实践中所归纳的“积极幻想(Active Phantasy)”:
在这条汇集的溪流中,主体的意识人格和无意识人格都汇聚成了一个共同的相互统一的产品。这样的幻想可以说是对人的个性化的统一体的最高表现形式;甚至可以说通过它对人的统一体的完美表达而创造出了个性。[10]364
“个性化”意味着从集体规范中脱离和分化出来,因此“是一种意识领域的延伸,使意识的心理生命变得极为丰富” [10]381。蒲松龄的升仙幻想同时容纳了“意识”——对现实之黑暗、隔阂、规训的透视,和“无意识”——对“快乐”的本能追求,具象化为科举、爱情、对智勇双全女性的欣赏,并将两方面编织成俚曲这种熔人生经验、深彻体悟与闲情意趣为一炉的“统一体”,从而区别于其它众多因循套路的作品,“个性化”也就浮现出来。通过对原本冲突的双方的调和,蒲松龄“意识的心理生命”大大丰富,他以蕴藉着复杂心理经验的通俗作品为载体,向世人传递着经过延展的、更为广阔的“意识领域”。
结语
《蓬莱宴》和《寒森曲》的主人公反常地未能抵达登科荣仕或阖家欢乐的世俗理想,而是隐入升仙的幻想。两篇文本内部俱含矛盾,折射出蒲松龄在凡心与超脱之间的摇摆态度。在这思想的摇摆历程中,现实的阻碍横亘在通往人世理想的路途之中,作者便最终写就理想落空而以幻想补偿的“清醒梦”。相较于常见的“元结局”,升仙幻想既是无奈的妥协,又是能够酝酿出高层次“个性”的“积极幻想”。蒲松龄在面向大众的俚曲中,亦多少捎带与大众口味可能并不契合的个人心绪,复杂的创作动力相互作用,使作品形成一种愈加令人沉思并与人共振的张力。失落之后何以归依?升仙的幻想,正演绎出一种自我调适的生命哲学。
参考文献:
[1]马良春,李福田.中国文学大辞典 第七卷[K].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2]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清]蒲松龄.聊斋俚曲集[M].蒲先明,整理;邹宗良,校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4]刘艳玲.聊斋俚曲《蓬莱宴》本事考论[J].蒲松龄研究,2014,(2).
[5][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6]李杨.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焦伟.蒲松龄诗词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17.
[8]刘秀荣,刘婷婷.聊斋俚曲论纲[M].济南:齐鲁书社,2016.
[9]施爱东.大团圆何以成为元结局[J].民族艺术,2021,(3).
[10][瑞士]荣格.心理类型[M].吴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A Study on the Fantasy of Becoming Immortals in Liaozhai Liqu
Zhao Pei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fifteen Liaozhai Liqu that usually promote the secular ideal of reunion,Penglai Yan and Hansen Qu end with the protagonist ascending to immortality and leaving home. The language,plot,and structure of Penglai Yan all have contradictions,fluctuating between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world,which coincides with Pu Songling's experiences and struggles in reality. The ending of becoming immortals is another path opened up beyond reality and ideals. The protagonist Shang Sanguan's remarkable breakthrough in gender restrictions in Hansen Qu is highly praised,but it is also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patriarchal society,the ending of becoming an immortal is the result of a compromise narrative. Unlike the common happy reunion,the fantasy of becoming immortals in Liaozhai Liqu is not only a helpless compromise,but also a kind of Active Phantasy that can brew high-level Personality. The Liqu that were originally limited to the edification can also carry more complex connotations.
Key words: Pu Songling;Liaozhai Liqu;Penglai Yan;Hansen Qu;Phantasy Active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