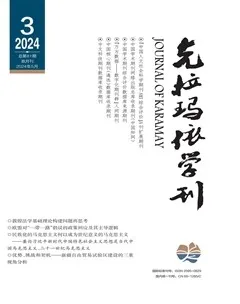敦煌法律故事之功能及类型举隅
摘 要: 敦煌法律故事属于敦煌法学研究的范畴,是敦煌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法律故事具有实际上的宪法、行政法、基本法功能,是中国古典法律“大、小传统”互动中“大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地区人们法律情感维系、法律意识凝聚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古典法律宪章中取得法律效果“情理法”统一“中庸”平衡境界之表征,还是良法善治、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敦煌法律故事包括但不限于敦煌契约类、婚姻家庭类、继承类、土地纠纷类法律故事。敦煌法学领域中“敦煌法律故事”理应成为形成“中华大国学”理念及中华“文化自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法学研究理应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的法律经验事实及理论积淀,针对转型中国产生的中国法律问题进行认知与解释。中国法律的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充分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敦煌法律故事是展现中国法律主体性的重要载体。敦煌法学中所蕴含的伦理正义,是中华法系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 敦煌法律故事;敦煌法学;敦煌学;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4.03.04
著名敦煌学大家姜亮夫先生指出:“敦煌保存着儒、释、道三家最重要的典籍……从整个中华文化来看,敦煌替我们保存了我们文化里边的。”[1]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所涉内容异常广泛、无限丰富,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献两大方面,涉及民族、民俗、宗教、艺术、历史、考古、地理、经济、法律、语言文学等众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资料原始性、“书籍写本性”[2]、图画直观性、学科交叉性等特点。
“敦煌法学是研究我国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石窟艺术与出土法律文献及其他资料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敦煌法律现象、法制状况、法律生活、法律关系、法律过程与变迁及其规律的学问,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蕴含、严谨的结构和鲜明的特征。由此也构成了敦煌法学的基本学理体系。”[3]按照现有敦煌学的学科分类,其中并未涵纳敦煌法学,敦煌法学也并非敦煌学的二级学科。
西北师范大学王勇教授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策划主持的“敦煌法学:学科证成与案例展示专题”中,系统梳理了“敦煌法学”这一重要学术研究范式的流变。该“主持人语”指出:“敦煌法学”这一新型交叉学科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在刘俊文、胡留元等先贤学者提出“敦煌法制文书”“敦煌法制文化”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学、文献学、法学等相关学科充分发展的产物。2007年,兰州大学法学院王斐弘教授在其专著《敦煌法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敦煌法学”这一概念,并且将敦煌法学视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2020年,甘肃省法学会敦煌法学研究会在兰州正式成立,李功国先生当选为研究会会长。2021年,历经数十年积累、三年艰苦写作,李功国先生主编的《敦煌法学文稿》及其姊妹篇《敦煌古代法律制度略论》两部著作顺利出版。至此,敦煌法学基本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学术团队及研究平台搭建工作初步完成。[4]
敦煌法律故事显然属于敦煌法学研究的范畴,是敦煌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敦煌法律故事”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故事”是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概念,在王朝日常律令执行、行政施为和政治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故事具有“法律分析、政治解释和文化构建”[5]三种功能,甚至有的法律故事还有“疗愈作用”[6]。恩格斯曾对民间故事作过高度评价:“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7]在法律未产生以前,民间故事尤其是与法律相关的故事,还承担着维持秩序、规范行为的法律功能。[8]
(一)实际上的“大宪章”
敦煌法律故事具有实际上的宪法、行政法、基本法功能,是中国古典法律“大、小传统”①互动中“大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对宋代法律故事进行研究后指出,宋代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故事”具有多重属性,“详练故事”与“力行故事”是对君臣的高度政治褒奖,熟练掌握与遵行“故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素养。皇帝和官僚集团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会检校与参详故事,从故事中寻找施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故事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宪法、行政法意义。进言之,宋代故事不仅表现一系列单项制度规范,更是一种政治话语和思维方式,其内涵宽泛、功用多重,具有较强的理论张力。故事不仅是法律规范与政治制度,甚至可以称为一套“话语体系”,且其背后折射出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留意。[9]其实,何止宋代,历史上很多法律故事,譬如“狄仁杰断案”“包公断案”“海瑞断案”“于成龙断案”等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清官情结”“青天老爷”意识。包括敦煌法律故事在内的古典法律故事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古典法律“大宪章”的作用。非但如此,当今大家司空见惯的“今日说法”“社会与法”“庭审现场”等电视及新媒体栏目,实际上依然有此功能,只不过弱化了其“报应神圣性”功能而已。
(二)法律意识凝聚的载体
敦煌法律故事实际上还是法律情感维系、法律意识凝聚的重要载体。法律情感是人们对法律本质和法律现象所持态度的心理体验;它是依据现实的法律制度能否符合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而产生的喜好或者厌恶的心理态度;[10]它既可表现为对法的关切、喜爱、信赖、依恋和寄托,也可表现为对法的漠不关心、厌恶、怀疑。[1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12]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等。[12]按照一般法理学的解释,法律意识可按不同的标准作不同的分类。从意识主体的角度我们可将法律意识划分为个人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其中,个人法律意识是指具体的个人对法律现象的思想、看法、意见和情绪,它是个人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经历的反映。群体法律意识是指家庭、阶级、民族、政党等不同的社会集合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敦煌地区的人们作为社会群体,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意识。敦煌法律故事是当地人们法律情感维系、法律意识凝聚的载体。
(三)治理效果“情理法”统一的表征
敦煌法律故事还是我国古典法律宪章中取得法律效果“情理法”统一“中庸”平衡境界之表征。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13]及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4]中,无一例外地认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礼俗秩序是法律秩序的源生秩序。自上而下的官方王权系统和自下而上的民间礼俗系统,形成制衡,互相掣肘。在这种动态平衡中,官方与民间、“民情”与“王法”、公法与私法、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等,这些看似对立矛盾的不同法律情势,在敦煌法律故事的言说中得到统一。
(四)良法善治、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
敦煌法律故事还是良法善治、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法律秩序的最终目的是良法善治、民淳俗美,形成美好的“法俗”②。传统中国,儒释道的有形公共文化空间非常多,几乎每个县邑城镇都有自己的儒释道祖神佛及地方城隍庙等神鬼公共建筑系统。国家法的惩戒方式及标准渗入民间神鬼系统的善恶报应观念中,两者双向互动,内外交错,掣肘平衡。有的善恶报应系统,譬如佛教或者城隍系统所宣扬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惩罚方式不仅祸及自身,且及子孙后代,乃至万世。神道设教,其意绝非现代科学语境中的“迷信”,而是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在这种双向互动的文化系统中,国家法的惩戒及标准与民间善恶因果报应之间相互影响,动态平衡,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最终形成古典中国2 000多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15]。这种双向互动,通过“敦煌法律故事”善恶报应的载体,支撑着民众心中最朴素的正义观念,从而形成卢梭最伟大的法律格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16]
二、敦煌契约类法律故事举隅
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契约文书中,以汉文契约文书最多,其研究成果颇丰。据学者最新介绍,敦煌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有 316件。这些汉文契约文书的年代,最早为前秦、最晚为元代,主要集中在唐五代至宋初,其时间跨度之久、地理范围之广,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史,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契约文书的历史背景,再现契约文书背后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态。这些关于契约文书的学术成果大大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也为深入研究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学科注入了新的血液。[17]
以“S. 466广顺叁年(953)十月廿二日莫高乡百姓龙祐定兄弟出典地契”[18]为例:
广顺叁年岁次癸丑十月廿二日立契,莫高乡百姓龙章祐、弟祐定,伏缘家内窘阙,无物用度,今将父祖口分地两畦子,共贰亩中半,质典与连畔人押衙罗思朝。断作地价,其日见过麦壹拾伍硕。字(自)今已(以)后,物无利头,地无雇价,其地佃种,限肆年内不许地主收赎。若于年限满日,便仰地主办还本麦者,便仰地主收地。两共对面平章为定,更不许休悔。如若先悔者,罚青麦拾驮,充入不悔人。恐后无信,故勒此契,用为后凭。
地主弟龙祐定(押) 地主兄龙章祐(押)
质典地人押衙罗思朝 知见父押衙罗安进(押) 知见人法律福海 知
人们常说我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但这些史籍大多经过古代史官和士人之过滤和筛选,而敦煌契约则是当时民众直接使用的文书,具有原生性,是反映当时社会和经济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历史、书写历史的原始依据”[2],对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民俗、文化、政治、经济等情况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广顺”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年号,“广顺叁年”具体是指公元953年。“出典”是典型的法律行为,在传统社会一般是指土地出典。法律上是说,承典人支付土地典价而占有、使用出典人的土地,出典人于典期届满时,返还典价赎回土地或者不回赎而丧失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广顺叁年十月廿二日,事主龙章佑兄弟,因家中遭遇困难,将自己的贰亩中半田地质典于与自己田地相连的押衙罗思朝。“押衙”,是唐宋五代时管理仪仗侍卫的小武吏。这份文书显示:自今以后,“物无利头,地无雇价”,并且“肆年内不许地主收赎”。 这是土地出典形式的明显特征,它的基本意思是:出典人为获得典价而不必向典买人支付利息;典买人则有权对典物进行使用或支配收益而不付租金。如果谁先反悔,就要“罚青麦拾驮(duò)”, 给不反悔的那个人。最后通过书面方式签订这份文书,“恐后无信,故勒此契,用为后凭”。契约最后的“知见人”就是见证人,如果以后立约双方发生争执,“知见人”就是证人。这表明,这份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文书,是书证。虽然敦煌地处中原王朝的边远地区,但从这份典型的非常直观的书证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典田契约在五代典田方式的流行”[19]。
又以“乙酉年(925)敦煌邓子受雇契”[20]为例:
乙酉年二月十二日,乾元寺僧宝香为少人力,遂雇百姓邓仵子捌个月,每月断作雇价麦粟壹驮,内麦地叁亩,粟地肆亩,其地折柒个月(二),余残月取勿(物)。春依(衣)长袖一并,襕裤一腰,皮鞋一量(两)。从人雇已后,便须逐月逐日驱驱入作,不得抛却作功,如若忙月抛一日□三,勒勿(物)五斗;闲月抛一日,勒勿(物)壹斗。子手内所把陇具一勿(物)已上,忽然路上违(遗)失,畔上睡卧,明明不与主人失却,一仰雇人衹(支)当。如若有病患者,许五日将理,余日算价。节下休乡原例宽闲。如若当□□□水□□□□他人庄舍苗子□□,官罚羊来,一仰当六(?)人祗(支)当,一定己后,更不许休悔。如[先]悔者,罚麦五硕,充入不悔之人。空无人信,两共对面[平]章,故立私契,用为后凭。售(受)雇人邓仵子(押)口承人兄邓清子(押)见人。
这是一份敦煌归义军时期农业领域的雇佣契约法制文书。该文书明确记载了雇佣关系产生的原因,如“家中欠少人力、家中阙(缺)少人力”等。但仅从雇主的角度记载了雇佣契约签订的原因,雇工签订劳动契约的原因没有做出具体的文字记载。不过,从这一时期农业领域雇佣契约文书记载的整体内容分析,不难得出雇工签订雇佣契约的原因,即由于家庭贫困,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或者偿还债务等原因。
在雇价以及支付方式等方面也突破了以往的规定,出现了除银钱以外的其他物品作为酬劳,如粮食、衣物、鞋子等,雇价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满足雇工签订雇佣劳动契约的初衷。
该文书还对雇佣期内劳作的时间作了详细规定,如在农忙月抛工一日,以五斗粮食相抵;在农闲月抛工一日,以一斗粮食相抵;在雇佣期间出现生病等情况的,可以休假五日;超出五日的则算为抛工,以上述方式进行折抵,而且契约中明确规定逢年过节,可以归乡休息。
契文中还记载了劳动工具管理的规定,如“具一勿(物)已上,忽然路上违(遗)失,畔上睡卧,明明不与主人失却,一仰雇,人衹(支)当”[21],即雇工应当对劳动工具承担管理义务,遗失或者被盗的,雇工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如果因雇工劳作不当,给他人造成损害或者被官府罚没的,由雇工承担全部责任。[22]并且在契约文书末尾签字画押的规定发生了变化。
由是观之,从契约文书记载的内容来看,契约条款清晰、内容完备,归义军时期敦煌农业领域雇佣契约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三、敦煌婚姻家庭类法律故事举隅
在莫高窟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中,至今尚保存着38副婚嫁图,另有榆林窟的3副。其中,敦煌莫高窟360窟、148窟、85窟,榆林窟38窟、25窟等石窟壁画更是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中古时期的婚嫁习俗,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对这些资料的解读,除了谭蝉雪先生《敦煌婚姻文化》[23]一书有短短1 000字左右的解读外,学术界对敦煌婚姻文化所显示的深厚的学术意蕴的诠释和解读是相对匮乏的。
目前,对敦煌婚姻家庭类法律故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出土文献“放妻书”上,散见于金眉《唐代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制度初论——兼与西方法比较》[24]、崔兰琴《唐以降传统法定离婚制度探究》[25]、冯卓慧《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帛书、敦煌文献及律令所见》[26]、王斐弘《敦煌法论》[27]、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28]、李功国《敦煌莫高窟法律文献和法律故事》[29]、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30]等专著中,及范学君《唐五代敦煌婚姻浅议——以敦煌文书为中心的探讨》[31]、陈得胜《敦煌出土放妻书研究》[32]等硕士学位论文及系列期刊论文上,其核心观点是敦煌“放妻书”反映了唐代社会中的离婚自由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而对于其他内容则鲜有研究。
以俄藏(Дx.11038-3)“放妻书”(Дx.11038-3)[33]为例:
谨立放妻书一道窃闻夫妇义重,如手足似难分;恩爱情心,同唇齿如不别。况且夫妇念同牢之乐,恰似鸳鸯双飞,并胜花颜,共坐两得之美。□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夫妇相菿(草到)(对),今则两自不和,似将难活,眅(目反)(反)目生嫌,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遂会六亲、以俱一别。相隔之后,(愿)妻娘子谏选髙(繁体高)官之至,弄影(寝)前,美呈琴瑟合(韵),(解)怨舍结,再莫相谈,千万永辝(台辛)(辞),布施欢喜,其两家并惣(物心)(总),意欲分别,惣(物心)不耳三年衣粮,自后更不许再来互相搅乱。自今己后,更不许相为(违)。忽若论烈(列)夫妇之义者,便任将凭官断,则之(知)皂帛(白)。
该“放妻书”正文开篇,均陈述夫妻之间因缘而产生的美满婚姻以及婚后相爱的状态。从内容上看,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都是因缘所致,显然是受了当时佛教的影响,说明当时佛教在敦煌地区及唐代的巨大影响。紧接着,文书从婚后所生冲突及对双方家庭产生的消极影响展开描述,主要原因是“缘分不睦”,只能分离。离婚理由则大致分为:因家族不睦(《宋开宝十年放妻书》等);因贫困而感情不合(《留盈放妻书》等);缘分已尽或“不相安谐”(《放妻书样文》斯0343背等);夫妇双方不孝不悌(《夫妻相别书文样》等)[34]。
当然,“放妻书”中对离婚理由的描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对比唐朝法定离婚原因“七出”“ 义绝”及“和离”,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文书契约中所描述的离婚原因,并非上述三个法律原因之一。只是民间一种流行的离婚契约。“遂会六亲、以俱一别”。如今夫妻缘分已尽,“六亲”皆可作证。《唐律疏议》规定了“七弃三不出”[35],并规定了离婚证人制度。在“放妻书”上,证人亦要签名或押手印。可见,“放妻书”是当时敦煌地区所流行的离婚文书范本。
“放妻书”虽只在敦煌发现,但并非只反映敦煌地区的婚俗,而是整个唐宋时期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反映,[36]它既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又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
当然,有学者研究指出,敦煌还有“掠夺婚”的史实材料。在敦煌藏文写卷P.T.1083号中就明确记载:“沙洲户女子每为吐蕃、孙波(部落)及个别尚论③以婚配之名,抄掠而去,(实则)多沦为奴婢。”[37]这证明,大约在公元795年或807年间,④吐蕃社会确实存在掠夺婚。在举世闻名的敦煌汉简中,我们依然能发现当时因战争俘虏而导致的掠夺婚状况。据《敦煌汉简》载:“东叶捷翖候故焉耆候虏尔妻即鄯善女,今共奴已与鄯善不合,则中国之大利也。”[38]上述材料可证明,敦煌地区除了唐宋流行的一夫一妻多妾这种婚姻形态外,还存在“掠夺婚”的可能性。
四、敦煌继承类法律故事举隅
据学者统计,敦煌有关家庭遗产分配、纠纷的卷子,总算起来,大约有二十多件。这些卷子,对于我们研究唐宋时期家庭发展的状况、儒家文化对家庭的影响、当时家庭遗产分配的法规、民间不成文的习俗,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39]总体而言,从敦煌继承类文书中可见,唐代遗嘱继承受法定继承均分观念的影响,同时也重视立嘱者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通过重要知见人的见证,以保障立嘱的权威性。在财产分割方法上,遗嘱析产比较灵活,已形成成熟的方法,无须官方介入,反映出唐代民间处理家庭事务的自主性及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张力。[40]
以“唐景福二年(893年)押牙索大力状”[41]为例:
押衙索大力右大力故师姑在日,家女满子有女三人,二女诸处嫁,残小女一,近故尚书借与张史君娘子。其师姑亡化,万事并在大力,别人都不关心,万物被人使用,至甚受屈。伏望将军仁恩照察,特乞判命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
景福二年二月日押衙索大力 灵府状
该文书是典型的继承遗产纠纷,内容是押衙索大力要求分得师姑遗产的牒状,从文书“右大力故师姑在日,家女满子有女三人,二女诸处嫁,残小女一”的表述可知,索大力师姑的家庭成员状况是有女三人,二女已出嫁,幼女残小,在财产继承上,因二女已出嫁,因而小女是理所应当的继承人。又据“其师姑亡化,万事并在大力,别人都不关心,万物被人使用,至甚受屈”可知,索大力是实际上处理师姑后事的人,所以其主张继承师姑的部分财产,但师姑财产却被人使用,索大力并未取得丝毫收益,因而以诉者身份向官府诉求。该案后无判词,所以具体到索大力是否获得财产补偿不得而知。但可以断言的是,在这一时期,为老者赡养并处理后事的非亲人员是有继承老者财产的权利的。
又以“S.2199《唐咸通六年(865年)尼灵惠遗书”[42]为例:
尼灵惠唯书咸通六年十月廿三日,尼灵惠忽染疾病,日日渐加,恐身无常,遂告诸亲,一一分析,不是昏沉之语,并是醒之言。灵惠只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留与侄女潘娘,更无房资。灵惠迁变之日,一仰潘娘葬送营办,已后更不许诸亲恡护。恐后无凭,并对诸亲,遂作唯书押署为验。
该文书是相关僧尼的继承案例,从中可以获知三条信息:一是,奴婢可以被看作财物进行继承;二是,僧尼的两世性,在神界的精神无尘和在俗界的物质相附,也就是说僧尼可以在宗教之外有其独立的物质财产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处理;三是,遗书的效力最高性,在被继承人订立遗嘱后,其财产的分割应完全按照遗书进行,继承人地位的获得也是由遗书所赋予的,并不因亲疏远近而有所限制。
再以“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荣清牒稿”[41]为例:
牒 荣清不幸薄福,父母并亡,债负深广,艰苦非常。食无脱粟,衣罄皮毡,昼则饮水为飱(歹食),夜则寒吟彻晓。数年牧羊未息,便充手力。父业不可不承。(后略)
该文书后缺,具体诉状和判决结果不详,但从前文可知,应为承父产牒状。文书有“父母并亡,债负深广”和“父业不可不承”的表述,即可知道,在子承父业的情形下,其父所负的债务也要一并由子来偿。这一继承原则虽不符合债的相对性原理,但在我国古代诚信立家的价值传统下,却是最基本的债之继承原则。
五、结语
敦煌法律故事属于敦煌法学研究的范畴,是敦煌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法律故事具有实际上的宪法、行政法、基本法的功能,是中国古典法律“大、小传统” 互动中“大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地区人们法律情感维系、法律意识凝聚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古典法律宪章中取得法律效果“情理法”统一“中庸”平衡境界之表征,还是良法善治、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敦煌法律故事包括但不限于敦煌契约类、婚姻家庭类、继承类、土地纠纷类法律故事。
中国法学研究理应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的法律经验事实及理论积淀,针对转型期中国产生的中国法律问题进行认知与解释。其关注焦点主要是“转型期中国”产生的“中国法律问题”而非“西方”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律的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充分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敦煌法学领域中的“敦煌法律故事”理应成为形成“中华大国学”[43]理念及中华“文化自觉”⑤“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4]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法律故事是展现中国法律主体性的重要载体,敦煌法学中所蕴含的伦理正义是中华法系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笔者愿与同行一起,为我国的敦煌法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致谢:辽宁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刘秀文、邹炳楠、
陈弘泽、丛新爽、陈冬梅、夏郡鸿同学在资料搜集上有贡献。
注释:
①芝加哥大学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参见Rbbert Redfield. “Vincenzo Petrullo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New Series,1957,59(2).pp.352-353。
②中国古代在国家(礼法)与社会(俗)之间建立了合理的联系,创制了“俗—礼—法”之间渐次递进的社会制度模型,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兼具风俗性法学和理性法学的特点。参见杜文忠:《论中国古代法律的“法俗”特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39-147页。
③官职,唐代吐蕃的一个职官系统名称。参见林冠群:《吐蕃中央职官考疑——〈新唐书·吐蕃传〉误载举隅》,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9年,第80本第1分,第43-76页。
④据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推测,该卷日期为公元795年或807年间。参见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⑤“文化自觉”作为一个正式名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参见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407页。
参考文献:
[1]姜亮夫.敦煌学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36.
[2]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等.谈谈敦煌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1-3.
[3]李功国.加强敦煌法学研究 讲好敦煌故事[N].民主与法制时报,2021-11-25(01).
[4]王勇.“敦煌法学:学科证成与案例展示专题”主持人语[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3(1):27.
[5]何玉红.法律分析·政治解释·文化构建—— “故事”研究的三种路向[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6):130、130-138
[6]白雨,李静.叙事实践:文学艺术作品中法律故事的疗愈作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1):226-236.
[7]转引自谈士杰.史诗《格萨尔》与藏族民间故事[J].青海社会科学,1993(1):67.
[8]李春斌.藏族婚姻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92-93.
[9]喻平.论宋代法律体系中的“故事”//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37辑)[C].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222-237.
[10]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0.
[11]李春斌.藏族大学生法律意识实证研究——基于478份问卷的调查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74-78.
[12]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19.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5]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
[17]韩树伟.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J].吐鲁番学研究,2023(2):128-139.
[18]郝春文.敦煌遗书[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50.
[19]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J].历史研究,2011(6):103.
[20][日]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城.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M].东京:东洋文库,1980:123 .转引自王凯平.敦煌、吐鲁番雇佣契约文书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18.
[21][日]石滨纯太郎.西域文化研究[M].东京:西域文化研究会,1962:123.转引自王凯平:敦煌、吐鲁番雇佣契约文书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19.
[22]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汉语言词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43-448.
[23]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24]金眉.唐代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制度初论——兼与西方法比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5]崔兰琴.唐以降传统法定离婚制度探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9.
[26]冯卓慧.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帛书、敦煌文献及律令所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7]王斐弘.敦煌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8]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9]李功国.敦煌莫高窟法律文献和法律故事[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
[30]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31]范学君.唐五代敦煌婚姻浅议——以敦煌文书为中心的探讨[D].南京师范大学,2007.
[32]陈得胜.敦煌出土放妻书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2015.
[33]乜小红.对俄藏敦煌放妻书的研究[J].敦煌研究,2008(3):68-69.
[34]刘文锁.敦煌“放妻书”研究 [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2-57.
[35]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8.
[36]胡翠霞.敦煌《放妻书》研究综述[J].丝绸之路,2011(8):16-17.
[37]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42.
[3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223.
[30]齐陈骏.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件敦煌遗书[J].敦煌学辑刊,1994(2):51-60.
[40]林生海.唐代家产继承研究:以杏雨书屋藏羽53号敦煌文书为例//卜宪群主编.中国区域文化研究(2023年辑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54-70.
[41]唐耕耦主编.敦煌法制文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451、448.
[42]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中心,1986:153.
[43]张炯.“序”//班贡帕巴·鲁珠.尸语故事[M].李朝群,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序”1.
[4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