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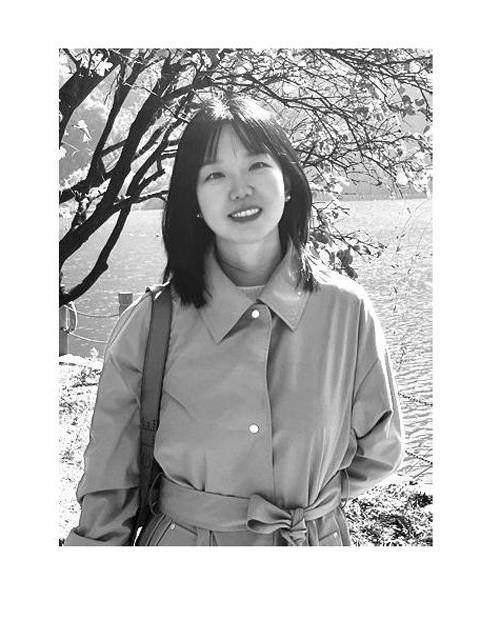
王扬灵,现居西安。作品见于《美文》《延河》《莽原》等刊,出版《理想主义罗曼史》《大唐女史薛涛传》《美人食梦》等长篇小说。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李商隐《天涯》
1
送走种春兰,外面纷纷扬扬下起了雪。琼花,我想。种春兰的灵魂顺着殡仪馆的盐白色烟囱杳杳飞升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南京博物馆有一面南朝墓室拼镶砖画,画中就是条美妙的游龙。雌雄难辨,仙气飞扬,不像在砖壁上,倒像在虚空中。
心中要有何等的虚静,才能在泥土上画出这样的龙,然后在橘红的火焰中烧制它。我当即就羡慕那无名的南朝工匠了。至少在泥胚和火炉前,他一定是物我两忘,如在云中。
其实我把脉看诊时,也有同样感受。
指尖轻稳地搭上病患的手腕,一缕表面上来自人体,实际却来自神秘虚空的脉动便风声一般传进我体内。我能把握最微小的变幻,如同在乱山中把握一只昆虫翅膀的忽闪。看病于我是最愉快的事,从我第一次搭上别人的脉搏我便知道了。
最后一次搭上种春兰的脉搏时,我不禁忡然变色。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我看向她,她回我以疲倦又略带讽刺地一笑。
一个月后,种春兰从鹤川县卫生学校废弃的水塔上飞身一跃,跳进月亮。
2
1983?1984?1984。1984年,我和种春兰在鹤川县卫生学校中医班做同学。
在那个场景中,我首先看见了我自己。我的形象不太清楚,白而软,朦胧模糊。相比之下,鹅黄窗格和碧绿水杉却丝丝鲜明,辉映着清淡的、毛边的,那个时代的阳光。我感到安心,因为坐着别人就看不到我天生的跛脚。只看上半身,我还是很清秀的。片刻后,男女同学像一股色彩杂乱的小小洪流涌入。教室里嘈杂起来。
接着,一个女孩推开薄薄的木门,环视周围。随着她的目光,嘈杂像一群麻雀般飞走消失了。余下的一两声,仿佛梦呓。后来我明白,种春兰是为舞台而生的,舞台由她随身携带。因此她不像迟到,倒像登台亮相。
当时种春兰才十八岁,已在县剧团唱过两年戏。而我是二十八岁。二十七八,青春尾巴,人们开玩笑似的说。好在班上不止我一个年龄大。虽然中高考制度早已恢复,但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上学的不少。我的原因是我的家庭。
我父亲曾跟随部队辗转在秦岭深处。即将解放时,一次小规模战斗,他肺部受了重伤,被就近安置于鹤川县委。新中国成立,我的母亲,一个鹤川县药材铺家的娇弱胆小的女儿,生下哥哥和我便早早谢世。该上山下乡时,哥哥去了。几十年后,在那片遥远的黄土地上,他以清水头乡中心小学校长的身份退休。父亲的老和病由我承担了。他肺病复发去世后,我才真正走出那个院子。
那个院子,我的记忆的画布上尽是些阴翳的琐碎片段:蓝盈盈的月亮。父亲绵长的咳嗽。县委大院灰蓝砖砌的镂空花墙。灶台上断续的青烟。枇杷叶毛茸茸的背面。
枇杷叶熬水,清肺止咳。枇杷花开在初冬,冷天冷地里,忽然碰来一阵绒绒粉末似的香。因为父亲的病,我们灶台上常年熬着这些花花叶叶。枇杷树,春天不怎么鲜嫩,冬天也不枯凋。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喜欢这种树。
父亲心情好时,饮着枇杷花与红糖熬成的糖浆,我们谈诗。主要是中国古诗词,也有普希金、阿赫玛托娃等俄罗斯诗人。父亲最爱杜甫。心情不好时,父亲从头到脚地挑剔我。头发太长,像个戏子;头发太短,像只刺猬;平着脸,丧气;笑时大牙外露,野气;娇娇弱弱,没一点浩然之气!狂怒时他骂:“你以为你是什么资产阶级小姐?一只寄生虫!”
父亲,他的坏肺吞吃了他的远大志向。他痛苦地享受着漫长的高级津贴。“寄生虫”,他骂。
随即他回转过来,讨好地,亲切地,和我讨论杜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叫我去书房拿他的剑。
说媒的妇女来了两次,父亲说:“我没意见,我尊重她自己的意见。”但其实他有很多意见,从灰蓝的地砖间生出来,虬曲树根一般。“女人结婚都是受罪。磨掉一层皮,一层肉,一层骨头,变成另一个形状,另一个人。你要是结婚……得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断定:“你的心是这样,你的脚又是那样。你必得受大罪。”
我默默出门,一脚高一脚低地到县委档案室上班。二十五岁那年,父亲帮我安排了那个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是个沉默寡言的独腿老头,每年八月一日,把一张红色的光荣证放进胸前口袋。那就是他唯一的语言。不知为何,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安慰。
我学习了枇杷树和独腿人的沉默,加上跛脚,再也没有媒人上门。然后,我又学会了隐身,就是在人群中默想:我不存在。久而久之,我真的不存在了。几乎没有人和我来往。
父亲去世了。我脱去父亲的衣裳,那是我这一生唯一见过的异性身躯,至今记忆犹新。干瘪,灰黄,充满怨念和遗憾。那时候,一股花香味的风忽然破开灰蓝框的大玻璃窗,向我吹来。我透明了。我的头发、我的脚,我飞起来了。
一脚高一脚低地,我走去辞掉档案室的工作。我坐进中医班雪白的教室,伸手搭上种春兰浑圆白嫩的手腕。那一瞬,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我抬起眼,种春兰对我粲然一笑。
3
种春兰的笑是完美的,就像她的手、她的脚、她的头发、她的脉搏一样完美。现在回想,我把她在很高的地方供奉起来了。说个可笑的体验,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要用一下厕所。之后,我按照父亲留下的习惯进厕所去点根香。进去当然是臭的,但我竟然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那时我尊爱她就到那种程度。
所以她对我哭的时候我很吃惊。“学校哪哪都不如剧团好,”她擦着眼泪,怀念以前唱完戏后,妆都不卸,在后台团团坐着吃夜宵。煮鸡蛋、烤玉米、花干……纸皮馄饨最香,汤里点了虾皮、香菜和小磨香油。艺人有艺人的规则,心里尊卑分明,外面无论大小,大家在一起就是笑。不像中医班,人人在背后议论她,弄得她很孤独。有的女生还试着她的性子欺负她,那种欺负是让人心里知道嘴里却没法说出来的。她心情不好,成绩也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来学中医呢?”我问。
“唱戏唱不了一辈子。我想念书,想当干部,当——‘知识分子。”种春兰说。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不是好书?好演员,一样是知识分子。未必只有医生、教师是知识分子?”说完我脸通红了。那时我不会说话,觉得这种程度就算跟人吵架。但我的确对当时人人想当“知识分子干部”的风气嗤之以鼻。我觉得,大多数人就像群羊一样,根本不管道路,只会跟着潮流跑。就像班里那些同学,一毕业就再不会碰书本,将来个个都是庸医。
种春兰的黑眼珠比一般人大,在台上飞个眼,角角落落都能照顾到。她定定看了我一会,忽然说:“姐,我以后能不能来你家看书?我看见好多书。我是乡下孩子,家里连一张纸都没得。”
种春兰的家,山脚下一院黄泥房,屋檐下堆着许多烂鞋帮子。离房子不远有一道河,她父亲过到河对面和一个寡妇过日子后,就不再返来河这岸。种春兰一被剧团选上,她的母亲也就跟个做小生意的安徽人走了。我想象,那黄泥房就渐渐潦草在水声和细雨里。
种春兰站在我父亲方正的书房中央满脸惊羡:“这么多书,都能把我埋了!”
那些书当然不舍得把种春兰埋了,反而做成阶梯,送她走上去。就像她希望的那样,成为干部,成为“知识分子”。
她在那间书房里读了汤显祖,莎士比亚,福楼拜。有一阵她每天都很紧张,因为《包法利夫人》。吃饭睡觉,她都操心着艾玛的命运。终于看完那晚,她面色灰白,直直躺在我的小床上,眼泪从眼角滴进两鬓。
我左手握着右手,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
她自己缓了一会,睁开眼喃喃地说:“这是一本教科书。”
“什么?”
“教育我不要太浪漫。”
4
那句话怎么说?“人类从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然也不会从文艺作品中吸取教训。
中医班结业,我被留在县卫校附属医院。工作两年,我拿到函授本科,随即脱产去北京读研究生,种春兰牡丹一样的圆脸又滴下两行清泪:“那咱俩就分开了。”
种春兰那时仍稚气未脱。毕业时,她本可以和我一样留在县卫校附属医院,因为这样的美人,任何单位都稀缺。单位总有用女主持人、女歌手、跳舞女郎的时候。但她却不肯去院办,一定要和我一样去临床科室。临床科室已经满了。结果她被分配到极偏远的卫生院,每个月搭顺车才能进县城来看我。没多久,她就被当地一个乡痞缠住。每天晚上,那人在她窗下丢小石头,使她不能睡觉。卫生院里又只有她和另一个中年女赤脚医生。我们商量又商量,权衡又权衡,最终还是匆匆找到我父亲的老战友,调出档案让她回了县剧团。
种春兰痛哭一场,说“白上了学”。不过,一两年间她就成为当家花旦,天天送戏到工厂,到部队,到田间。逢到年节,在鹤川县大剧院开专场。介绍对象的人太多,一下台她就躲,不回剧团宿舍,回我家。
那阵子她光彩照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古董书桌,送给我。南洋檀,桌斗挂着铜片锁。她怕钢笔尖划花桌面,又裁了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压着她自己的剧照:狐仙胡秀英。
“狐仙怎么能结婚?你看我们团的吕红霞,一结婚就生孩子,生完回来,腰这么粗,脸这么大,台上光一打,哎呦呦!”种春兰鼻子皱起,像花瓣刚醒时的褶皱。
“再说,女人一那个就不美了。”她很做作地说。
我不喜欢这种做作,就把头低了。
她连忙软软抱住我的胳膊给我戴高帽:“我要以你为榜样,冰清玉洁一辈子,好好干一番事业。”
那时,我人生最后一次难得的相亲刚告失败。对方是个火电厂职员,面目我早记不清,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介绍人说对方很恼怒。我并没说什么令人恼怒的话,因为从见面到在河堤上散步,我几乎一言不发。他自己介绍了他的家庭,他的工作,每当我不发声,他就自己补充上他的家庭或工作的缺点。然后我继续一言不发,他就脸色铁青地走了。河堤上的柳丝飘拂,河水活活地流动,我顿时也觉得自己活了。预感到我将永远结不了婚,我竟然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见我一言不发,种春兰以为伤到了我,忙一脸认真地说:“没事!你不老,不信你看。”她把我推到穿衣柜上嵌的、描着白色梅花的镜子前。那时我快三十五岁,长相平庸,白而平淡,但仍像个少女。
就在种春兰如此做作、如此坚定地表示要献身舞台后,她怀孕了。
我伸手搭上她的脉搏。在我的俯视下,那张牡丹脸缩小了,皱巴巴的。
我仍记得我当时的感觉——诧异,忧愁,恶心,嫉妒。种春兰的血液浩渺、有力、毫不知耻地在我指下波动。
种春兰看我表情,皱起眉毛哭了,哭得满脸通红。
渐渐的,她的血液的波动却使我平静下来。“士与女,殷其盈矣”——阴阳平衡,多么正常,何况是如此美丽的种春兰。我不该像那些庸俗的人一样。那些同事,永远和我隔着一层膜,头凑在一起嘁嘁喳喳,我一走近就悄悄了。
5
种春兰第一次结婚,孩子父亲是《刘海砍樵》里的刘海,狐仙胡秀英的爱人。婚后种春兰丰腴起来,脸上生出一种骄傲愉快的神情,好像她怀揣的不是个孩子,而是个光荣证。刘海很爱她,两人每天黄昏在丹凤河边散步,他像对太后一样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她。
我去北京,种春兰和他一起送我到县城汽车站。她刚掉出两滴眼泪,就被他嬉皮笑脸地逗没了。我第一次离开县城,就去那么远的地方,车一发动,种春兰就消失了。
在北京那三年,我只用念书,却急遽地衰老了。我头上长出很多白发。可笑的是,这白发倒成了什么明证,每到实习,病人都格外地对我的医术表示信任。
那段时间我自己的身体却并不好,经常觉得疲倦。北京的空气也不好,车太多,人太多。因为无法适应,我干脆把自己关在校园里,每天就是宿舍——食堂——教室——湖边——宿舍。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持最基本的精力和内心的平静。
秋窗风雨夜,我忍不住给种春兰写信。有时候写得太长。她很少回信,即使回也是只言片语,简短单调,说孩子出生后又忙又累。后来信多起来,她丢下孩子回了剧团,便有时间在部队,在工厂,在田间,在后台给我回信。她的语气又活泼起来。后来又有一阵没有信。在我等的有些担心时,她的信才来了,信里杂七杂八扯了许多,最末问:“你记不记得包法利夫人?”
研究生毕业,我拒绝留京的种种好处,兀自回了鹤川。院领导马上给我评了主任医师。看着我的白发,人们对我又尊重又同情。在夸赞我的医术后,他们往往要小声加一句:“她是个可怜人”。我假装没有听见。但那话像一匹黑纱披下来,披在我头顶。
我想念种春兰。
种春兰在我回鹤川一周后才来找我,这让我真有些伤心。甚至,我暗自哭过一次。但当我见到她,我就立刻原谅了她。她也变了。她变得那么——那么美丽,冶艳,眼波流动,那么动人和迷茫。
包法利夫人,种春兰是在恋爱了。
那是个很庸俗的故事,说不定当时每个县城都有一套。我不知道种春兰为什么要和与我年纪相仿的领导谈恋爱,总不能就因为他是领导。早晨去丹江河边锻炼时,我发现卫校附属医院附近竟然开了间歌舞厅,那些大腿肥白的外地女人,清晨才从舞厅的厚门帘里出来,张开口红斑驳的嘴唇打着呵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真的是喧嚣而骚动的。
据种春兰说,这位领导是个知识分子。她深陷其中,我不置可否,事后我想也许我应该劝说点什么,当然,我劝说大概也没有用。而且,我始终是个不会说话的人。
事情就顺着每个县城的套路,或者说人间的规律走下去了,一点也没有意外和侥幸,或不得了的惊喜。领导回了家,人称艳福不浅,种春兰离了婚,被人骂是破鞋。但当时县城还有个离婚的女人,就是那歌舞厅的女老板。她和某个局的局长在办公室,局长老婆像董永一样抱走了他们的衣裳,使得局长不得不半裸着伸出窗外,叫下属去北新街给他买一身西装。穿上新西装的局长一定要离婚,老婆反而后悔了,又跪下求丈夫。这局长倒不依不饶,立逼着离了婚。女老板立刻给他买了一辆桑塔纳,两人在县城招摇过市。
我不知道种春兰作何感想。那段时间她是混乱、疯狂和崩溃的。我小心翼翼地陪伴着她,像感受脉搏一样感受她潮汐般起伏的心情。她经常会忽然哭起来,然后擦擦脸打开门走出去,回来脸上便变得冷静。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去找了领导,或者前夫刘海。消沉了一阵之后,她忽然又疯狂起来,天天去跟刘海及刘海的妈打仗,争着管那个孩子。她扁起身子立起头发,似乎非要变成个良母。结果仍是失败了。孩子像小大人样跟她说,妈妈不要天天来了,闲了来看看我就行了。
种春兰灰白着脸在我的小床上躺下了。
也许因为回了鹤川,也许因为不再孤独,我的健康却渐渐恢复。我到静泉山上采撷商芝,不厌其烦地做复杂的药膳,不管种春兰伸不伸筷子。我绕着枇杷树种了许多金色的菊花,秋来借点夕阳,花丛像火焰在跳动。
种春兰终于休完病假回剧团上班,却不见她再去部队,田间,工厂。晚饭间我问起来,她咀嚼着很随意似的说,来了新花旦,很年轻,不用她去了。
抱歉,那对我来说却是一段适意的日子。种春兰好像在开至荼蘼时领悟了春晖的温暖可贵,变得温柔敦厚,知礼感恩。在家里,她开始洗衣、做饭、刷马桶;出去买菜,她能立着听卖菜的扯半小时闲篇。晚上我们坐在书房里燃一支香,相对而坐,我读论文,她读古今中外的小说剧本。有时候她读着又哭起来。
春天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晚上,种春兰拿出一叠绿格子稿纸,说要写个剧本。我看到她手边放着《茶花女》,就开玩笑地说:“写个茶花女的故事。”
她却摇一摇头:“那不适合国内,更不适合鹤川。”
写到秋天,她给我看。故事讲一个女医生,悬壶济世,孜孜不倦,万般委屈,挽救了许多生命,却被病人误解,又失去丈夫孩子的欢心。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她获得了病人、丈夫、孩子的爱和认可,她自己却积劳成疾。最后一幕,她穿着雪白的病服,在鲜花和众人的簇拥下满怀希望地望着观众席说:“春天,我看见春天来了!”
就像一切合时、合世的故事,这剧本立意略显庸俗,但不乏精彩华章、动人乐句,可以说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从中取得一些东西。
接下来许多晚上,我听种春兰清唱了全本,我们一起打磨,修改,她很尊重我的意见。
春节时剧作一上演,就获得广泛好评。县里很重视,上报到省城演了三天,场场爆满。又上报到北京。一年后,种春兰获得了文华奖。
6
我们平滑紧密如两匹叠在一起的绸缎的日子结束了。她变成点状,时不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但更多是空白。经过很久的适应,我才重新形成自我的铁律,就像在北京时。饮食,工作,锻炼,休息,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和内容。在不惑之年,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顺滑之境,像笔直铁轨上的列车。专注凝神中,我创造性地解决了几个疑难杂症,发表重要论文,受邀到省城中医药大学举办讲座。
种春兰是那么明亮、美丽,看上去异常年轻。鹤川已经放不下她。她和省剧团的一个离异男导演一起停薪留职,在省城创办了春兰剧院。半年后,他们结了婚。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孩儿是个小春兰,出生三个月就被他们找关系丢进托儿所。托儿所营养丰富,管理严格,不到三岁,她就能自己管理大小便,脸上时常露出牡丹花般使人心醉的笑容。她是个人见人爱的甜心。
我一直很念着她。我忽然想起她七八岁时暑假来鹤川,在枇杷树下的样子。当时我和种春兰坐在窗里,我正听她给我诉说。种春兰说得很投入,我听得很认真。她说戏曲是如何式微,靠戏票赚钱变得多难。她现在反倒喜欢去田间表演,似乎那些贫穷、衰老的农民眼睛里,还能看到真实的对美的赞叹和对人物的爱。而她的丈夫已渐渐放下艺术,成了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他们在省城最好的商业区买下一栋三层漂亮小楼,挂牌“春兰艺术馆”。“你就在这里带两个学生唱,”丈夫这样要求她。艺术馆往来无白丁,先是鹤川商会的汇聚点,然后省城各路名流也常来举办“沙龙”。年节时,商人们出资让她在省大剧院唱华丽专场,一级配乐,戏服全部苏州定制,剧票大多不卖,给各机关国企赠送。
“唱了一辈子戏,竟然觉得倦了。”种春兰说。那天她穿着一身宽大雪白的丝绸长裙,像玻璃罩中的希腊贵妇人。我给她倒上青烟袅袅的茶汤,看向窗外。就是那刻,我看见那小女孩罕见地收起了鲜花般的笑容,小小的脸上显出一种老成的平淡。后来她一路念寄宿学校,直到十六岁去加拿大,再也没有回来。
这段婚姻在种春兰四十岁时,一个年轻女人挺着肚子来找她而画上句点。
7
种春兰应该是最后一代色艺双绝的戏曲名伶。她带的最优秀的学生,转行做了电影演员。她回到鹤川,我和她度过了她生命最后的几年。我很后悔,没有推掉没完没了的会议、讲座,多和她相伴。其实我们都很忙,不知怎么,这个时代所有人都疯狂地很忙。她被封为鹤川文化馆馆长,继续创作了两部戏。演了几场,拿几个奖。她发现戏曲已经是这个模式后,对创作也意兴阑珊。
追求她的男人始终有,但没有她合意的。我感觉到,她更喜欢和我避居在这栋老旧的灰蓝色小楼中。
抱歉,她的生命逐渐沉寂的日子,依旧是我的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候。那些被鸟鸣唤起的清凉早晨,洗手间白瓷砖地面上她的微卷的长发,润肤霜、洗发水、沐浴露混合的香气,她曼声清唱的嗓音。那些帘幔低垂的夜晚,我们闲聊白日发生的小事,一起看看最新的电视,评价好歹,然后相对读书。我的睡眠很好,我的嘴角有了不易觉察的温和笑意。我以为我早已拥抱孤独这株雪白的大树,但种春兰却给我开出了温柔的花朵。
种春兰已经弥散在天空中。种春兰消失了,我真切地感到一阵失衡,一阵衰竭。我下意识地微微抬高右手,去摸左腕。在即将摸上那一刻,我却松口气把两手撒开了。
手轻轻摇荡着,灰蓝的窗隙钻进一小阵微湿的冷风。窗外,枇杷树正在开花。我的手指不自觉地微微颤动,像在把脉,给那花间吹来的风。
责任编辑 李知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