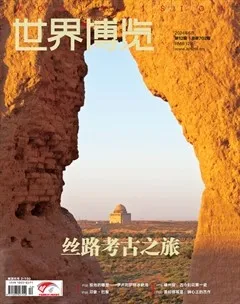生生不息:以己之身丈量天地


斯科特先生是我学习空手道的教练,他曾在日本受过顶级空手道训练,并在爱尔兰开办了欧美最有影响力的空手道联盟。该空手道联盟每年有教练团访问日本,所以今年我就跟着他,和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挪威和丹麦的教练们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日本武艺观摩之旅。
行动即思想
观摩和体验过4种不同空手道流派的训练,外加一次剑道训练和另外两整天的拳法训练(一种糅合了合气道、柔道、空手道和中国功夫的训练方式)之后,我意识到这些外观上非常不同的武学技艺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任何一种流派都要求练习者能够用身体感知空间和距离,在下意识和无意识中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在与对手产生合适距离的时候出击或格挡。如果练习者有足够的内核力量和肌肉记忆把身体能量最大程度投射到具体使用的技术中,保持重心平稳,收放自如,那么具体使用哪一种流派的哪一种身体姿态或具体技艺,甚至有没有武器在手上,都是完全不重要的。
用身体感知运动和移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它跳过了抽象化和知识性的智识与反思过程(大部分被认为是需要由语言进行的),可以说行动就是思想本身。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梅洛-庞蒂大概是第一位在现象学思想中极大强调“前语言性”或“非语言性”的身体认知过程的现象学家。一如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学从历史研究中抽离出来,把语言本身看作符号来认识和讨论,梅洛-庞蒂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几代欧美符号学家们也致力于把运动和移动本身看作价值中立的符号来研究它们自身产生的认知过程和意义。
再仔细想想,大部分我们熟悉的艺术形式,比如音乐和舞蹈,又和我上面提到的武艺有何不同呢?一次即兴的音乐演奏或舞蹈,没有事先的编舞也没有乐谱,思想在运动中成型又即刻消逝,最后没有什么会留下来用于反思和重复。音乐和舞蹈是镌刻在手上和身体上的诗,每一次移动就是书写诗行本身,却没有语法和句法。这是皮尔斯符号学中的永远处于动态而不会凝固成任何具体意义的象征符号,也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阐述的记忆的本质:一种绝对的运动状态。
身体的本能认知
加州大学的符号人类学教授萨莉·内斯把这些思考带入了她对人与景观互动的研究,深入思考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交流与互动方式,甚至是生命和非生命形式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带出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包括语言和交流的本质,何为身体的认知以及这种“前语言”或“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如何反映了更大程度的文化或文明形成过程。
内斯教授的田野调查大部分是在加州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完成。这个国家公园建于1864年,占地3000多平方公里,拥有壮观的瀑布、幽深的峡谷、高耸的巨型红杉和作为全世界攀岩者心中圣地的巨型花岗岩山峰。其中近 2700米高的山峰半圆丘(Half Dome)和世界上最大的单一花岗岩酋长岩(El Capitan)每年都会吸引全球顶尖的攀岩高手前来。约塞米蒂的访客大多会进行远足、露营或攀岩活动,在内斯教授看来,这是观察人类以身体运动探索空间与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交流过程的绝佳机会。
约塞米蒂的访客们在主动思考如何进行一次野外活动和怎样运用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对一切都有预想和解释:要一天走完多少公里,要看瀑布感受震撼,要到峡谷露营感受世外桃源般的宁静,要用怎样的路线爬上半圆丘,要用怎样的技术收紧大腿或小腿哪一处的肌肉绕过酋长岩凸出的几处裸岩……然而一旦运动开始,身体与自然环境开始接触,主动思考往往让位于即时的本能反应。即便是个人的单独运动,也会受到日晒和空气湿度、地面粗糙度、障碍、运动过程中与其他物种或特殊地形遭遇等情况的影响。攀岩时,需要面对的偏离预想的情况就更多了。这些时候,我们会更有机会观察到身体本能的应对。当人摔倒或在某处滑倒,本来人要置身其上的地面或岩石忽然就会变成施动者扑面而来,身体则会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收缩和规避伤害。陌生的风景和地貌成了人需要小心翼翼“谈判”的对象。意外遇到熊,要跑吗?要躲到岩石后面或树上?要几个人一起发出很大声音把它吓跑?等等,熊在做什么?是要去抓鱼,还是幼崽走丢了在找?这时候,不仅身体会本能地做出一切预料之外的移动和动作,而且可能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彻底改变环境和整个景观的张力,而且对整个旅程和这个地方的诠释都会和最初的想象发生很大的偏差。攀岩者的身体与重力需要协商的情况更是无时无处不在。我们最终会从这些漫长的野外活动中,发现事实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事情:只要在运动和移动之中,我们的身体本身就会做出自己的思考,那是一种经过思辨的主动选择与即时的无意识反射的组合。而这些行动和反应本身,最终会影响和改变世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思考。
永恒变动的象征意义
内斯教授在分析她的田野调查材料的时候,邀请我们重新思考何为象征符号。当我们认为一个东西代表了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就是在为那个东西赋予象征意义。然而任何一种事物的象征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永远处于动态,不停变化的。永不停息地主动与无意识地做出新诠释,本就是人置身于世界与时间中的常态。柏格森告诉我们,灵性的思考与物质世界本无既定分野,身体在运动和活动中对外界做出反应的模式就是记忆的本质,所以我们的记忆包含了自身的历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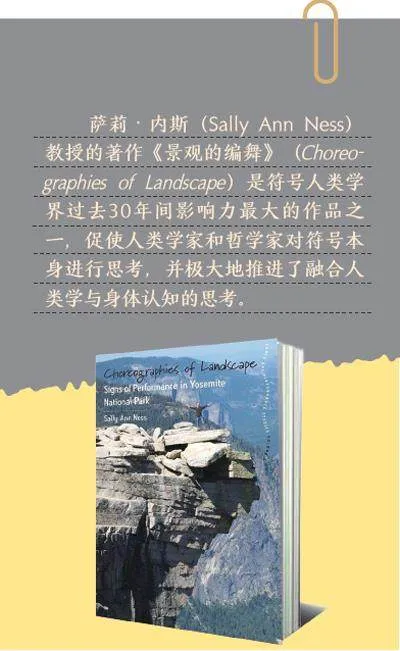
如果把语言看作交流的模式,而且把“前语言”或“非语言”的互动和交流也包含在内,就会发现所有空间和景观都充满了语言。蝙蝠发出的辐射波得到了树的回应,从而改变了飞行的路径。土壤中的细菌和真菌群落此消彼长之际,发生了对养分和氧气的不同需求,这些信息投射到植物根部,促使不同植物物种做出争夺地面空间或共同生长的不同反应。农民看到狼,拿着枪追出农舍,狼是要逃跑,还是把农夫引走,好让自己的同伙偷袭牲口?人与狼各自的决策以及一切意料中或意外发生的事情都被远处被忽略的狼崽看在眼里,产生了数种可能的交流模式与结果,这不是自然发生的教育与学习吗?移步到北极圈,无论在西伯利亚还是加拿大北部,人与雪橇狗或狩猎狗当真磨合出了一套包含了不同声调与特殊音素的可观察的语言(更接近对语言的一般定义),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思考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语言人类学家们和符号人类学家们在思考语言的边界的时候,不时会希望溯洄远古,那时在同一空间中产生互动的所有物种自然会形成各种下意识和无意识的交流方式,它们的总和大概就是语言的前身。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起内斯教授对象征符号的研究?语言和音乐作为最抽象的象征符号,其意义和对其的诠释亦是动态和永远不停地变化的。人类学家们对各种文明的神话情有独钟,认为它们是有意识的历史书写出现之前对文明和文化起源的最好记录。仔细看看各个文明的起源神话,难道许多不是在重现那个各个物种无差别共处的文明起源之时,那个诗意的语言遍布天地的属于所有物种的记忆?


回到文章最初写到的刚过去的日本之行,当我向我的教练说起,各个流派的空手道甚至不同武学的技法好像是共通的。他说:武学意味着很多东西,但首要意味着一种联系和连接,联系身体的各个部分,连接身体与所处的无时无刻不在被对手改变的空间。描述这种联系和连接为某种特定的技艺永远会失败,因为它是永远处于动态中的,你的身体是不停流动的。你能看到的,只是某个特定模式被干扰的那一刻身体做出的反应。我告诉他,作为学者,我相信我们仍然应该不停地尝试去描述和思考,没有答案的研究才是最好的研究。一如贝克特的戏剧中我最喜欢的台词:我们会再失败,更好地失败。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