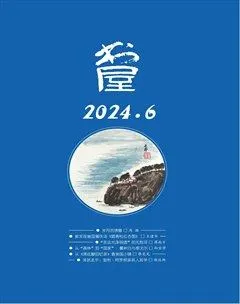湘女情深
年初与友人聊起拙著《我与名人没有约》,在众多名人中,独独谈到杨静远。想起她当年曾写信给我,于是从私人文件的“故纸堆”中,找出她的信和资料,再三读之,一时感慨颇深。
杨静远女士是中国社科院编审,与我父亲同庚,但我们从未谋面。我在湖南图书馆工作时,曾写信给她。她是著名翻译家,从《彼德·潘》到《杨柳风》,译著颇丰,广受欢迎,而且是勃朗特姐妹研究专家。在她的个人小传结尾处,我写道,“我视她若圣女”,而她在来信中却说:“对惠赠雅号‘孔雀公主十分感谢!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哩!”
杨静远出身名门,父母皆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她念大学时天赋极髙,且门门成绩优异;又喜欢钢琴,常在家中自弹自唱,让同在一校的堂姐钦羡不已。后来,父母为她安排负笈美欧深造,但她却“先顺后反”,留学结束后选择了回国,为获得新生的祖国服务,且自降薪酬。且在那改变自己命运的转换过程中,写下了收录在《写给恋人》一书中的多封书信。
可惜,我此前从未拜读过她半世纪后才结集出版的此书,但却从朱正等人的评论中,感觉其分量很重,并为自己能得到她的亲笔信而感到荣幸和珍惜。她的信还让我联想起在那十年中,我与隔山隔水、相恋相望的女友往来的几百封信,这些信保存至今,亦可见证湘女的情深且专一。
杨静远与成幼殊是表姊妹,二人爱国之心如一,但她比成幼殊更天真、更理想主义,此后的际遇也迥然有别。成幼殊是成家儿女中,引导其弟成思危矢志报国的领路人,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而杨静远在自己异常艰难的二十多年中,与亲戚失联,生死两茫茫。
我在重读她的来信后,亦翻阅了自己旧著中写杨安祥的《湘女多犟》,发现了她们那群沾亲带故的湘女群体的一个共性——秀外慧中。在看似文静、柔弱的外表下,她们都有一颗坚韧的赤子之心。即便是在他乡异国漂泊最久的杨安祥,晚年亦和她的亡夫一样,哪怕白发人送黑发人,仍无悔于落叶归根。
杨静远在《写给恋人·尾声》中写道:
1979年是个大转折。……我又调到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实现了我和文学的黄昏恋。更想不到,到1987年告老离职时……荣获“革命老干部”的称号,享受了离休干部的殊遇。
其实“右派”也罢,革命干部也罢,我只是一个有点天真几分傻气时常迷惘至老也不成熟但不失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
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问:你在1948年放弃留在海外做一名华裔学者的机会,不顾一切奔回来,却落得半生坎坷,不后悔吗?
答:不后悔。
问:假如时光倒流,再给你一次抉择的机会,你怎样做?
答:还是回来。
文末附上杨静远来信全文,为尊重故,将部分文字隐去。
崔述伟先生:
您好!
收到惠赠《我与名人没有约》,很感兴趣,尤其书中涉及我的几位近亲和我本人,对惠赠雅号“孔雀公主”十分感谢!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哩!第149页有两处小差误:①“在武汉大学任……副教授”,实际上是“自请降为讲师”。②被分配至“中央编译局”,应是“出版总署编译局”。都是小问题。关于成之凡,我不知道你对她的看法是否有共同之处。奇则奇矣,但与乃(其)妹的温和敦厚、谦和质朴相比,天差地别。不说别的,既信奉道教,就应清静无为。但她在政坛和物质虚荣的追求上却完全背道而驰,不是很奇怪吗?听说湖南方面对她期望很大,盛情款待,希望她对家乡作一点贡献,最后却大所失望,而她也不再露面了……
我因老伴于年初病故,现已迁居我儿子家,新址为……。祝
新年好!
杨静远
2005-2-28
去年曾寄上拙作《让庐日记》,想已收到?
附上《新京报》报道一篇,被逼上门谈的。
另,信笺上面空白处,提及资中筠姐妹,亦录于此:
尊著中没有收入资中筠、妹资华筠(舞蹈家)姐妹,很可惜。资(中筠)是精通中、英、法文的真正学者,曾任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她父亲资XX(耀华)老也是湖南耆宿。
本栏目责编:刘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