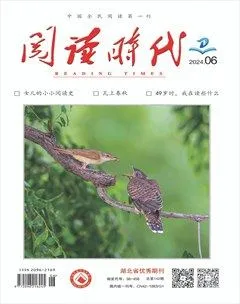纸窗 纱窗 蠡壳窗
朱秀坤
窗外,瘦竹五六竿;室内,紫砚压书案。隔开也即连通内外的是一扇木格花窗,窗纸雪白,小院清幽,抬头可见天光云影,开卷便是经史子集。夜间用功,随意一瞄,三两枝青竹落在窗纸上,轻轻摇曳,珊珊可爱。一时兴起,饱蘸浓墨,悬腕临摹,就是一幅疏密有致的墨竹图。这是我在郑板桥故居小书斋看到的一扇纸窗,板桥云“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想必先生在小书斋内,月月画,年年描,日间挥写夜间思,画到生时是熟时,终是画成了一代大家,画出了枝叶关情的“板桥竹”。
古时,“窗棂糊亮白纸裁”是寻常事,清词大家纳兰性德爱惜梅花的孤寒,便写“怜伊大冷,添个纸窗疏竹影”,让纸窗和竹影庇护梅花以温暖。宋代王禹偁的一句“白纸糊窗堪听雪,红炉著火别藏春”,则让人身临其境般感知到诗意与温馨。
这样的纸窗如今不多见了,小学时候我却是见过一位美术老师爱将宣纸贴在窗户玻璃上,画的尽是水墨小品,折枝兰、篱下菊、没骨牡丹,或者雪中梅、霜天竹、出水荷花之类,也算是纸窗吧。倒是种类繁多的木格花窗还能在古典建筑中看到,如象征吉祥的如意纹、寓意长寿的龟背纹、鱼跃龙门的鱼鳞纹、满堂平安的海棠纹、招财进宝的轱辘钱纹、满腹诗书的冰裂纹、富贵不断头的回字纹……在游览苏州拙政园、沧浪亭或者扬州何园、个园的轩榭楼馆时,时不时就会遇到,但没有窗户纸,一律镶上了玻璃。

倒是古装片中常有。烛影摇红的纸窗前,映出一个云髻高挽的丽人,走向案前苦读的公子,是一幅红袖添香伴读图。或者是月黑风高杀人夜,蒙面人以舌尖舔破窗纸,吹入迷香,烟雾中一见主人昏倒,立即入室盗走传世珍宝。更为惊悚的,一柄短剑插进喉管,一声惨叫,三滴血喷射到窗纸上,沥沥滴落……
曾经,那些极具审美与艺术价值的木格花窗间,总要糊上窗纸的,麻布纸、竹篾纸或白棉纸、粉连纸,讲究的人家会使用上等宣纸,挡风、保暖,透光但不透明。条件稍好一点的,也会在纸上涂一层桐油,防水防潮,润泽又结实。帝王家的窗户纸则相当考究,明代宣德年间,专门开发出一种丈六大纸“露皇宣”,洁白柔韧,最初就用来给皇家糊窗户糊墙壁。因此如影视片中以口水沾湿窗纸,是不大可能的,用手指去捅破倒是实情,毕竟是纸,没那么牢固。
钟鸣鼎食的贵族用罗纱当窗纸,质地更加结实,且采光、通透度更好。《红楼梦》中贾母见黛玉住的潇湘馆窗上绿纱旧了,且与院内翠竹配色不美,马上要求换成“霞影纱”。书中说:“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可不是这个?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明儿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听听,皇帝专用的府纱也比不上霞影纱,贾府就用来糊窗户,难怪刘姥姥口里不住地念佛,说:“我们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贾母马上答应:“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时,都拿出来,送这刘亲家两匹。”如此口大气粗,足可见贾府的豪阔奢侈。
明清时期苏州东山、西山一带,还有一种“蠡壳窗”,如清代黄景仁诗云“鱼鳞云断天凝黛,蠡壳窗稀月逗梭”。将贝壳磨得薄亮后也叫“明瓦”,镶嵌在窗棂上即是。因工艺繁琐,全靠手工,只有富户才能使用。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园林的窗户要“俱钉明瓦,或以纸糊”,可见明瓦的格调高雅,现在拙政园的见山楼还保留着蠡壳窗。清代中叶后出现玻璃,明瓦就消失了。
记得我在晋北大同当兵时,附近的古镇上,快过年了,人们还会在木格窗棂上糊窗户纸,糊得雪亮一片,然后贴上大红的窗花,都是吉庆有余、喜上眉梢、五福临门或者满堂富贵之类的主题,一派喜庆与祥瑞之气马上就出来了。真想哪天再回一次晋北,选一老屋、纸窗,与战友二三,喝茶聊天,闲话军旅,以慰相思。
(源自《联谊报》,王世全荐稿)
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