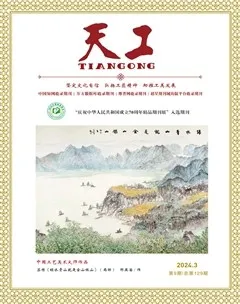超越东西之间

[摘 要]“马”题材是常玉在动物类创作中使用最多的主题,他在创作过程中将这一形象进行了象征化处理,即在彼时动荡的历史背景下,立足于中国文化身份进行形而上的现代性转换,同时在不断转化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常玉;马;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4)9-0060-03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谭涵.超越东西之间:关于常玉“马”主题中审美现代性的建构[J].天工,2024(9):60-62.
一、常玉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形成
根据《顺庆府志》记载,常玉的父亲常书坊是当地的画师,尤其擅长画马和狮子,在常玉好友庞薰琹的回忆录中写道:“常玉之前画中国花鸟画同样画得非常好,依稀记得他告诉我,其父亲是一位画家,并且常玉还藏有其父亲的画作。”①此外,常玉的“一笔式”画法和古雅清灵的画面受到师傅赵熙的影响。
常玉“马”主题画面中的平面感塑造,受到西方现代艺术和东方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常玉在少年时期居住的四川顺庆府一带流行“川北皮影戏”,又称“川北渭南影子”,人物造型较高且头帽相连,胳膊较长,均为侧脸示人,这与常玉创作的“马”形象一致;第二,常玉在1918—1919年去日本短暂学习,这也促进了常玉之后艺术风格的形成。
在留法期间所经历的两个与中国相关的大型展览,以及日本艺术界强调对本民族艺术振兴的理念,对常玉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本民族文化身份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个展览是1924年林风眠和吴大羽等人所建立的“霍普斯会”与留法艺术团队“美术工学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第一场中国美术展览会。《东方杂志》对这次大会做了特别报道,报道题目为“旅欧华人第一次举行中国美术展览大会之盛况”。另一个展览是1925年4月法国巴黎世博会所推出的“国际现代装饰与工业艺术博览会”,这里的艺术创作强调的是一种“新装饰艺术”的风格,即在形式上采用几何纹样和异域风格的图样,将具体形象简化,在材料上则将现代工业技术和材料融入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强调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庞薰琹认为这次展览是“巴黎正举办的十二年一次的博览盛会”。这两次展览虽然在与常玉有关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是身处于现代艺术的集合地巴黎蒙马特地区的常玉,对影响极大的展览颇为关注,从同时期留法的朋友那里也可以听到相关的信息。
二、常玉关于“审美现代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在深入探究常玉在留学期间是如何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浪潮影响之前,我们首先对“审美现代性”一词进行解释。“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中的“现代性”(modernity)区别于“现代化”(modernize),前者虽然是伴随后者产生的概念,但其指文化转换的内涵,侧重于精神层面。后者则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过程,侧重于物质、科学技术或制度等方面。审美现代性包括感性和超感性两个层面。在感性层面上的现代性体现为浓厚的感情色彩、大众化的日常生活、商品化、媒介化以及流行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感性层面中大众化审美现代性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即它既以自然的人性来抵制理性主义,也加深了人的感性异化的程度。而超感性层面包括超世俗性、反叛性、精英化意识以及非理性态度。常玉在“马”主题创作中既突出了对民族传统的继承性,也包含审美现代性的感性和超感性两个层面的内容,达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增强了作品的经典性。
常玉关于“审美现代性”的知识建构与其在大茅屋艺术学院的求学经历、“巴黎画派”以及其所生活的蒙马特地区的艺术风向和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相关。常玉在学院学习时处在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极强的创作空间中,吴冠中将其表述为一种“业余性的美术学院”,即突破传统和框架式的创作,强调非正统性和突破性。从常玉的创作实践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他受到巴黎画派的莫迪里阿尼和具有超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夏加尔、米罗等人“自动书写”的创作理念的影响。《巴黎画派的历史与时代》中提到,巴黎画派是由20世纪20年代巴黎的蒙巴纳斯地区聚集的大量具有现代主义创造理念的艺术家发展起来的,巴黎画派的艺术家相互鼓励、启发。常玉对于画面线条的塑造既具有中国文人绘画的金石之气和极强的书法线条感,也具有莫迪里阿尼般的清晰简洁、抽象般的线条形式感,尤其要注意的是,两者都注重通过弧线勾勒人物或是动物的外轮廓,使形象更加优美和圆润,并且蕴含某种内敛的情感。从具体形象的塑造来说,常玉塑造的马的形象和女性人体与莫迪里阿尼一样,都表现为拉长变形的人体比例以及对臀部的夸大处理。此外,常玉在描绘“马”形象时,总是将主体形象塑造成单眼示人状,这与米罗的主体形象塑造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莫迪里阿尼将自己对“单眼主体形象”的看法融入舒尔瓦日肖像画中,他认为这一形象的形成是由于“舒尔瓦日总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另一只眼睛看自己”。从更深刻的层面来说,“单眼形象”表达了这类艺术家虽处于现实中但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愿望。
对于常玉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可以根据其好友的记述来分析。如吴冠中说在巴黎访问友人时所见到的常玉不拘礼节,并且尤其关注生活态度问题,给人一种居无定所的浪子印象①。陈炎锋则在书中提到“常玉的生活丰富多彩,对朋友和善”②。常玉的这种行事作风既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的“游戏”的志趣有关,也与当时常玉所生活的蒙巴纳斯地区有关,还受到法国的“疯狂年代”大环境影响,基于此,他创造了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艺术作品。
三、常玉“马”主题中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现代性转型
常玉在创作“马”系列作品时,审美现代性突出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显性层面,包括画面的平面装饰性和对主体形象的变形和夸张。二是隐性层面,包括在此画作系列中“裸女”形象的隐匿与在场,以及通过象征性的手段来强调个人的处境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平面装饰性是指通过大块的平涂色彩,弱化三维空间,使画面趋于扁平化的艺术处理效果,画面空间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被切断。常玉“马”主题中对于主体形象的变形和夸张,一方面是源于常玉对摄影术的兴趣。据陈炎锋所说,常玉在旅居柏林的两年里,对摄影术产生了浓厚兴趣③,这一时期摄影术在多项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巴黎画派的曼·雷发明的“自动成像”技术,摄影师安德烈·柯蒂斯发明的具有凹凸镜效果的技术等。另一方面,常玉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将他创作的“马”形象与弗朗茨·马尔克的“马”形象进行对比,发现常玉与马尔克塑造的“马”形象存在共同点:一是采用单眼或是侧面面向观众的角度进行展现,并且对马的臀部进行了夸张和局部特写;二是将马脸进行简化,并将马融入整体画面中,即用单一的大块面色彩来概括这一主体形象。

从隐性层面来说,常玉用象征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同时表现画面中“裸女”形象的在场性。常玉曾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对人体奥秘的好奇,对人体美的欣赏已经成为他的生理需求。在常玉的画室中经常堆满了对人体和人像的速写和素描作品。通过比较常玉的“裸女”画像和“马”形象,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以下特征:单眼示人的概括类主体形象,常玉所塑造的主体形象与朱耷所塑造的动物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具备某种荒谬怪诞感。常玉的“马”形象在行为姿态上都进行了拟人化处理,并且常玉在离婚前后塑造的“马匹”形象也有不同。在“粉红色时期”创作的作品中,整个画面被浪漫的、粉红色的主色调填满,无论是单个还是两个马匹形象,都具有女性化的姿势、粉红的身体以及女性的柔美之感,有别于1940年以后的“黑色时期”弱化主体形象、强化旷远背景的创作。此外,在《毡上双马》与《斑点双马》中,可以明显看到两匹马之间的互动性不断消失,只保持单独的站立姿态。常玉之所以通过“马匹”形象来塑造“裸女”的在场性,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早期家庭教育的缘故,包括父亲常书坊擅长画马和老师赵熙的教导等,并且在常玉的房间中摆放着几个马的雕像,这可能与父亲去世或者与妻子离婚后的个人情感有关。二是常玉妻子的姓名“Ma”可以翻译为“马素”,两人在 1931 年结束了婚姻关系,常玉在离婚后为马素创作了《戴绿手套的侍女》等作品,并且在双面画《白马、黑马》与《豹》(见图1)中,常玉在画面左下方题字:“这幅画经过了两个时代方成,起画在一九三十年代,黑马画成,白马未成,完成在一九四五年。这个时代,我恋爱一个少妇,因她而成此画,这幅画已属于她,后因绝离,此画仍为此——玉记。”由此可知,常玉对妻子充满浓厚的感情和深切的怀念。三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就有女性与“马”相互映衬的具体运用,美女与骏马并置的传统程式源于西楚霸王项羽。《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雅,常骑之。”在常玉的相关创作中,这种处理方法源于中国文人画中“风景即人体”的思想。常玉作品中“裸女”在场的审美现代性意义,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艺术环境中,都可以作为传统和反传统的象征符号。
此外,常玉的“马”形象也可以被看成某种自喻或自我象征,将常玉的《禾穗双马》(见图2)和另一幅作品《孤独的象》(见图3)联系起来。在这两幅作品中,常玉将动物形象置于一片虚无的荒漠之中,并且给观众一种动物在漂浮着的无所依靠之感,画面中的主体形象与“粉红色时期”创作的动物形象具有明显差别,主体被其他景色包围,让位于宏观的场面,并且形象更加概括,成为纯粹的剪影式的表达,同时画面以大地色调为主,更增添一种沉思而非欢快之感,作为主体的动物形象在看不到尽头的荒芜大地中前行,就像晚年的常玉在寄给达昂的信件中说的一样,他将自身比喻为身处“荒漠苍茫的大地上奔走的孤独小象”①,这与他晚年的生活处境相关。从社会的大背景来说,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巴黎被德军占领,艺术市场趋于萧条,常玉对于画商、画廊采取“不配合”的态度,从而错过了许多机会,并最终失去赞助人。他一边依靠朋友赚一些外快,如卖画或出版菜谱类的书籍,一边通过在中国式仿古的家具厂制作器物来谋生。常玉在1955年寄给罗勃·弗兰克的信件中写道:“在经历了一生的艺术创作后,我现在终于懂得怎样绘画了。”可能是受到在中国式家具厂制作器物的影响,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常玉以更抽象、简化和流畅的书法线条进行勾画,并且通过赭石与黑色的对比或金黄等颜色的平涂来增强装饰感。晚年的常玉就像画作中的动物形象一样处于无依无靠的境地。虽然常玉在20世纪30年代(有认为是1938年)因长兄去世,回国奔丧分得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但在返回巴黎后他过着入不敷出的逍遥日子,长此以往,经济条件快速变差。另外,家人的陆续离世、友人的陆续回国以及与妻子的感情破裂,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推广“乒乓网球”的失败和20世纪40年代去美国举办画展的失败等,进一步加重了常玉的“异乡人”之感。
四、小结
通过对法国彼时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相关社会事件的研究,对常玉与“巴黎画派”“大茅屋学院”“天狗会”关系的梳理,以及常玉后期家庭变故等内容的探究,对常玉在艺术创作中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进行详尽、深入的探讨,同时探究在“马”系列创作中,常玉如何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最后将研究放置在整个中国艺术史发展脉络中,阐述常玉的艺术创作为中国艺术发展提供了启示和指导。
注释:①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83页。
注释:① 何艳屏:《吴冠中画韵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455页。
② ③ 陈炎锋:《华裔美术选集(1):常玉》,艺术家出版社,1955。
注释:① 陈炎锋:《华裔美术选集(1):常玉》,艺术家出版社,1995,第41页。
——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