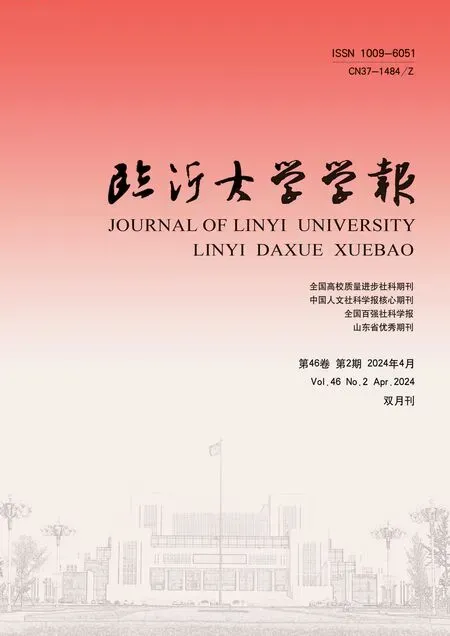共通与共谋:论语派杂志的生成逻辑
李茜烨
(中山大学 中文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00)
在关于论语派的既有研究中,论者多将目光聚焦在对其性灵幽默的小品文和隐士色彩/名士姿态的讨论上,有从前对其身份的消极否定,也有后来从文化、政治等维度的客观分析,后者打开了论语派的研究视野。黄开发、杨剑龙、吕若涵、裴春芳、郭晓鸿等学者对于论语派的文化思维、小品文文学观念、政治身份等问题的探讨已十分透彻。本文关注的话题为:在20 世纪30 年代上海的都市氛围中,论语派的三本杂志《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是一次文学、政治与商业出版的共谋。它们既在小品文的问题上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和政治性,又利用一定的出版发行策略,使该派成员可以发声,并召唤了一批认同者和参与者,最终聚合成了媒介共通体。由于他者的在场,论语派在文学史意义上自由主义的文学和政治意味得到更大凸显;又由于商业和杂志的参与,论语派才不仅是一个以抒发自我见解为目的的文人团体,还是一个有着经济动力和庞大读者群的媒介共通体。
一、自我定位与他者刺激
冷成金在《隐士与解脱》中认为,无论是道隐、心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壶天之隐,但凡真正的隐士,都与他们在政治中理想的溃灭和退隐的无奈心态有着紧密关系。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灵,又有着无声的反抗和用世的热烈,他们不一定个性独异、潇洒风流,也不一定放浪形骸,山水自然、日常生活、书斋笔墨是他们唯一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张立伟在《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中则认为隐士有忤世与避世之分,而忤世才是隐士精神传统中最耀眼的底色。在古代,无论是一般的士人,还是隐士,他们都将对“道”的信仰作为一种超越的精神,并用以解决世间的问题。正是这样一种超越的精神才能使士人对社会有着反思和批判,也更能向内探求自己的修养和心灵,才能在压迫和困顿之中依然眼光注视着现实。而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救世”“经世”的传统意识成为他们大部分人思维中的重要一脉,他们更从中国古代有气节的士人身上吸取了敢说敢言的谏诤精神,而这种精神又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混合发酵,有了争取言论自由、思想宽容的意义。当他们遭遇挤压和思想文化的规约,则有一部分转向了隐士传统,他们不是在闲适清雅中自视甚高、淡忘现实,而是在夹缝与矛盾中苦恼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论语派是具有一些“隐士”色彩的。他们的这种自我定位不是堕入了阿Q 式的“精神胜利法”,而是一种孔子隐逸体系中指向现世关怀的精神传统,一种庄子隐逸体系中指向人格独立的思想意义。
在论语派的三本主要杂志中,《论语》承担了写作幽默文章与进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任务。论语派在《论语》第一期的《缘起》中就声明:“我们无心隐居,迫成隐士。”[1]1这则《缘起》已经将论语派的整体色彩表现得非常显著,他们愿做无立场、无党派的所谓“隐士”,也的确在其刊物的各类编辑后记、室语、发刊词和创作实践中高举着性灵、幽默、闲适的大旗。林语堂在《论语》第一期的文章《图书评论多幽默》中声明:“一年间发刊洋洋六十万言劝人缄默,少谈国事。”[2]可是,细读下来,读者会发现《论语》上的文章并不见得全都缄默,反倒是含着不少激愤与锋芒,多与国事相关。“我们是反对儒家仁义之谈,而偏近韩非法治。”[3]论语派对于社会的回应是积极的、及时的,当年《论语》编辑之一的林达祖回忆道:“实事求是来说,《论语》也像一般报纸一样,凡国家社会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论语》报道不敢后于人,发抒意见也不敢后于人。”[4]其幽默文章与各类批评并存是有其幕后动因的,他们说“故日世道衰,多幽默”[5],鲁迅虽然不欣赏《论语》的幽默,但也赞扬过:“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6]可见《论语》在30 年代逼仄的环境之下,主动承担了知识人独立思考和批判反思的角色。
面对后来进一步收紧的言论空间和恶化的社会形势,那些未免有些直露的文字让论语派意识到:“况且骂急了人,骂出祸来,论语也就寿终正寝了。”[7]《人间世》和《宇宙风》创刊后则更多地担当了性灵闲适小品文的文学性任务。论语派希望这两本杂志能创作和刊登的文章是“做人须近情,做文亦须近情。小者须含有意思,合乎‘深入浅出’‘由近及远’之义,由小小题目,谈入人生精义,或写出魂灵深处”[8]。论语派对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品文的要求是切实的,并非消极的,更不是逃避的,不是故作闲适潇洒的飘飘然之态,而是认为其中含着真正文学的因子,是指向生命的健全、书写生活的本相的。论语派认为,篇篇高呼的文章是不切近人生的,一本正经的态度也让人生惧,“谓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句老话,便能叫人化消极为积极,变中国人民如一盘散沙之现象,吾尤不信”[9],空洞的喊叫不过只是虚伪的培养皿,因此,他们认为能解决这一虚浮高调的办法便在于文章的近情与清新,包含着学问、思考、宽恕和自我。《人间世》和《宇宙风》上真正能实现他们这种呼吁的小品文并没有逃世的态度,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是真诚切实的,尤能在普通的生活细节中启人思、予人感,透露的是对实在生活、世道人心的关怀,对读者趣味有热切的引导。他们把人暂时从紧张的政治和战争中拉回到日常生活,恢复了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感知。
《论语》杂志幽默文章与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并存,《人间世》《宇宙风》对表现日常生活的性灵小品文的提倡与创作,这些问题已被研究者们讨论较多,其杂志背后的隐士/名士身份、自由主义文人心态也有过论及,但是,以上提及的这些特性仅是主体态度的自我展露,对于论语派以杂志为阵地形成共通体是不够的。按照让-吕克·南希对于共通体凝聚的关键释义,“他者的在场并不构成为了限制‘我的’激情释放而设立的边界:相反,唯有向他者展露,才释放我的激情”[10],论语派杂志以上共通性的自我展露,必须通过他者且将自我外展在他人面前,其共通体才能真正被凝聚,或者也可以说,他者的刺激使得论语派在文学史意义上自由主义文人的立场和身份得以确立和凸显。因此,笔者想要关注的是论语派三本杂志具体的生成语境,以及它们在外展共通性时的运作。对于论语派而言,所谓的“他者”主要是左翼文人团体和官方势力。
在论语派同人对于《论语》创刊过程的回忆中,他们都提到《论语》只是一帮好友多次聚会以后商量出的一个自说自话的园地,大家凑钱出资,甚至只想过办到第六期即停刊。“那时已经是夏天了,许多朋友晚上到邵家闲谈,时方热天,一面纳凉一面闲话,大家提出要出一本杂志来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11]178至于《论语》所提倡的幽默也是在一次偶然的长谈中得出的关于写作的想法:“在一次偶然的长谈中,他们(引者注:林语堂和邵洵美)都主张提倡‘幽默’(humor)和清议,认为世事无常,应该一笑置之。于是引出了《论语》半月刊的编辑和发行。”[12]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论语派的发起者们最初虽然秉持自由发声之理念,但是旨在解自己之无聊、发自己之牢骚,并未想过把自己与哪方面对立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论语社同人”,成为《论语》的创造者。经过之前学者的考证,论语社“社员里面,有发起人,有股东,有实际投资人,有具名与不具名的编辑,有长期撰稿人,有经理”[13]。章克标回忆当时出资办刊的具体数额“乃定大家拿出钱来自办,共预备一千元,先收五百元试出六期,所以当时市上有论语只出六期即行停刊的谣言……这时语堂和洵美是大股东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14]。因此,在《论语》最初发起的时候,论语派并不是一个文艺性质的团体,而且政治意味也没有后来那么明显,他们在秉持自说自话原则的基础上有着明显而浓厚的商业色彩。
至于后来引起左翼文人大肆批评的《人间世》之闲适小品,林语堂在1934 年的《再与陶亢德书》中提到,《人间世》以闲适小品为主是因为他在《论语》的来稿中发现了许多无法被幽默文章涵盖的优质闲适小品文,考虑到这些文章缺少合适的发表园地,遂决定创办《人间世》专刊闲适小品。不过,林语堂在后来的自传里进一步透露了创办《人间世》的内因:“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后来又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15]295而章克标回忆说:“至于说林语堂和邵洵美后来发生矛盾,是为了争夺《论语》的主权,似乎没有这件明确的事情,只是在编辑费与稿费上有了意见。后来林语堂就另外去编辑了一份更为出色的《人间世》半月刊,《论语》就由邵洵美及另外请人帮助来出下去了。”[16]无论真相到底是林邵因为争夺《论语》主权而产生了矛盾,还是编辑费和稿费等问题,都向读者揭示出《人间世》及后来《宇宙风》创刊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因素,而《再与陶亢德书》中所提到的《人间世》作为闲适小品专刊之事,则是林语堂与《论语》股东在经济问题发生之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从《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的创刊出发,我们发现论语派三大刊物的创办原因其实较为单纯,且一开始对经济因素有较大的考量,而后来给文学史留下的所谓夹缝中的自由主义文人印象和具有政治意味的隐士/名士色彩,则是在他者的刺激下才得以进一步形成的。
在《人间世》创办之前,《论语》虽也因幽默而被批评过,但尚未与左翼文人形成对峙之势。鲁迅在《“论语一年”》等文章中对《论语》半月刊的评价只是针对幽默文章本身提出批评,1933 年陈子展评价《论语》时的观点是“不过幽默而已,倒没有什么”[17],可见,此时《论语》虽然遭到质疑和反对,但并未上升到立场和政治身份的层面。而《人间世》创刊后,尤其是以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事件为导火索,外界对论语派便群起而攻之了:
林编《人间世》时,即申明此系纯粹小品文月刊,迨出版一期,即遭自由谈,中华日报及其他刊物之物议,以为在此时期,不应出版此种“玩物丧志”之物,林即分别应战,不料后来阵线扩大,攻击者愈聚愈多,林几有应付不暇之状……[18]
《申报·自由谈》对论语派、《人间世》、林语堂的批评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批评闲适之于玩物丧志、小品文之于“有闲阶级”、论语派之于名士。左翼文人还创办了《太白》等刊物与论语派杂志形成对峙之势,提倡战斗的小品文,且认为论语派有凭借小品文垄断文坛的想法,“自从《人间世》创刊后,主编者以为小品文当以自我为中心,闲适为格调。于是违反这两个条例的短文章,就仿佛变做弃婴,给拼绝于小品圈外了”[19]。在左翼文人的围攻之下,林语堂等人不得不发出回应,著名的《方巾气研究》《周作人诗读法》等文应运而生。由于他者对论语派杂志的评判,以及论语派的回应,其杂志的定位和色彩才愈发清晰。鲁迅在1934年5 月致林语堂的信中说道:
窃谓反对之辈,其别有三。一者别有用意,如登龙君,在此可弗道;二者颇具热心,如《自由谈》上屡用怪名之某君,实即《泥沙杂拾》之作者,虽时有冷语,而殊无恶意;三则先生之所谓“杭育杭育派”,亦非必意在稿费,因环境之异,而思想感觉,遂彼此不同。[20]
“因环境之异,而思想感觉,遂彼此不同”乃鲁迅较为客观的判断,所谓“思想感觉”并非指一般的精神意志,而是带有立场上的分歧,至于林语堂口中的“杭育杭育派”则更是直指左翼文人。
在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通过追溯晚明公安派形成言志文学观以后,林语堂在1932 年《论语》第七期上发表的《新旧文学》第一次呼应了周作人,从周作人的观点中为论语派散文找到了晚明性灵小品的立足点,“此数人作品之共通点,在于发挥性灵二字,与现代文学之注重个人之观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独特,且类多主张不模仿古人,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21]181。后来又有著名的《论文》在《论语》第十五期发表,主旨仍在回应周作人、提倡晚明性灵小品。然而,此时林语堂对于周作人的言志文学更多的是停留在散文写作层面,尤其是晚明性灵小品的认同上。只是,后来为了应对左翼文人的批评,林语堂才在提倡晚明小品文和支持周作人言志文学观的基础上有了关于当时文坛“道学气”“方巾气”过重的论断,把锋芒指向功利主义的文学工具论。虽然在《方巾气研究》中林语堂开篇就说,“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21]168,但如此明确的立场分歧,尤其是针对左翼文人而提出方巾气、道学气,是在此刻才正式提出来的。在一开始,无论是论语社同人还是林语堂本人,从未想到一个自说自话、用于赚钱的杂志会发展到如此对峙、论争之势。
官方对论语派杂志的批评一方面是认为其幽默闲适消磨民族意志,另一方面是针对林语堂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一事,以及林语堂与鲁迅等左翼文人的交往进行批判。《论语派的解剖》(治选,《社会新闻》,1934 年,第7 卷第18 期)、《林语堂替谁说话》(读者,《时代日报》,1936 年1 月7 日)、《声讨鲁迅林语堂之流》(刘公,《金钢钻》,1934 年7 月31 日)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曹聚仁回忆当年文坛时说:“林语堂提倡幽默,《论语》中文字,还是讽刺性质为多。即林氏的半月《论语》,也是批评时事,词句非常尖刻,大不为官僚绅士所容,因此,各地禁止《论语》销售,也和禁止《语丝》相同。”[22]为了应付左右夹击,论语派杂志才不得不更加鲜明地举起自己具有隐士/名士色彩的旗帜,强调言论自由宽容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性灵、闲适、幽默和小品文的声调,把共通性外展到他者面前。在他者的刺激下,此时的论语派杂志已经从最初的论语社同人刊物演变成了真正具有政治意味的媒介共通体,并通过一定的编辑和发行策略对其特性进行不断地加强,维护共通体的自主性。
二、寻唤认同者的编辑策略
杂志媒介对于论语派而言是最主要的载体,通过具有商业性质的印刷媒介的召唤,使得平时很难沟通的人们以杂志为中介变得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了,共通体也在这种方式中得到进一步凝聚。论语派杂志畅销并获得了较多的认同者,与其具有独特性和参与性的编辑策略不无关系。这里主要谈到论语派杂志寻唤认同者的两种编辑策略:一是在杂志封面上下功夫,以醒目而有深意的封面文字吸引认同者;一是设置专号与征文活动,这一方式使得读者对于共通体有了较高的参与度。
现代大众媒体赋予了论语派更多得以抒发自我想法的“曲径”,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可能性形成相互回应且具有公共性质的共通体。写文章固然可以达到独抒性灵或委婉讽刺的效果,但商业出版物的封面亦可大做文章。过去少有学者会关注论语派杂志的封面文字,而实际上,杂志的封面很可能是读者阅读的出发点,它具有特殊而醒目的召唤功能,并且给予读者杂志风格和内容的暗示。
《论语》和《宇宙风》的封面上曾出现过不少文言摘引,笔者对封面的文字进行逐一整理后发现,这些文言摘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塑造了他们闲适幽默的隐士外表;一类则别有幽怀,透出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意味。
“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23],“李笠翁曰:午睡之乐,倍于黄昏。三时皆所不宜,而独宜于长夏”[24],这等文字充溢着闲情逸致,向读者暗示了杂志内容的性灵幽默。他们在封面上醒目地宣扬着这种飘逸潇洒的生活状态,一方面有助于轻松地通过书报审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作一猜想:或许不少批判者即是被封面文字所“迷惑”,在未细读杂志内容前就已下了定论,这也难怪论语派会遭遇“名士气”或是消沉民族意志的评价。
不过,分量更重且召唤知我者的,其实还是那些别有幽怀的摘引。比如以下几则:
颜氏学记曰:莱阳沈迅上封事曰:“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惭且恸也。——《书明刘户部墓表后》[25]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6]
郑板桥曰:国将亡,必多忌,躬行桀纣、必日驾尧舜而轶汤武。宋自绍兴以来,主和议,增岁币,送尊号,处卑朝,拥有民膏,戮大将,无恶不作,无陋不为。——《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27]
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28]
封面上类似的引文有多则,此仅举四例。不难发现,这些摘引与外祸、亡国、懒政、苛政、内乱、民怨等有关,每一条都指向了当时的大环境。第一例中的“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惭且恸也”,道出了论语派的心理活动,面对黑暗暴戾之局面,为明哲保身又不能明言,欲反思、批判而不得,在故作闲适中生存着、焦虑着,内心既惭愧又悲痛。第二例是《诗经·大雅·荡》的节录,这是《诗经》中有名的怨刺暴君、反映天下无纲无纪的诗歌,此处摘引的意义自不必多言。后二则的“国将亡”“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等语也与《论语》杂志中各色幽默的亡国救国兴国论(《救国难歌》(老舍,第六期)、《发起救国道场意见书》(章克标,第十八期)、《理发救国论》(老向,第四十一期)等遥相呼应。
《宇宙风》第二十九期的封面引用的是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里那段著名的论断:
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29]
这段摘引的目的大概仍是反对文学作为宣传的武器,表明《宇宙风》革除文章“道学气”做有益于社会现实、民族文化的杂志的宗旨。所以,封面上的摘引也就有不少直指世道人心之批评的内容:
一切刓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朱文公政训》[30]
这段话也被林语堂在《中国人之聪明》一文中引用过,指向的是中国人“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特点,普通人“刓方为圆,随俗苟且”,在位者“曲直在前,只不理会”,从而导致举国浑浑噩噩、暗无天日。论语派用朱熹的这段话作为封面来讽刺此种社会现象,在进行社会批评的同时也把自己同这一类人划开,他们虽然有看似闲适幽默的姿态,但绝不是与世沉浮、不辨是非之人。
周作人在《闭户读书论》中说:“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31]《论语》摘引古书做封面文字与周作人读古书、做“文抄公”的态度有些相似,他们缄默地沉入故纸堆,又从中寻出安慰,寻出可以对话的对象,把未曾言明的、不便直言的话通过摘引的方式表达出来。封面间的文字形成互文的效果,若是认同者必能解其中真味。而将其置于封面,何等醒目,看似不曾说过什么,又似说了许多。论语派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与逼仄的言论环境做起了“游戏”,把苦笑传达给了认同者,醒目的封面却平安地度过了审查与危机,不能不说是对“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环境的一大“幽默”。
论语派凭借杂志封面丰富了自我表达,扩展了言论方式,也召唤了大批的认同者,又通过专号和征文活动很好地利用了杂志制造出来的公共交流空间,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不仅使刊物销量大增,也在与读者频繁的互动中通过语言和媒介构建了共通体,使他们对大众的召唤得到回应,从而收获了更多的认同者,巩固了杂志的共通性。他们通过专号征文把对真实人生、实在生活的关怀传递给了大众。他们对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深谙其味的:“譬如今之妇女刊物除了打倒拥护之外,还有什么贴切人生有趣味有意思的议论记述?中国的杂志如果永远高谈阔论下去,中国的杂志无论怎样送赠品大减价也总只有没落,没落,一百个没落。”[32]
《论语》上举办过各种主题的征文专号活动,将“周年纪念号”“复刊号”也计算在内,共出过22 期,其中有的征文活动还是有一定奖金的。通过这些征文启事中对文章的要求,可以读出论语派一贯坚持的真诚、近情、切实的小品文写作原则,杜绝高呼空喊,以清新自然的风格为主。透过这些活动可以看出,论语派在尝试落实其文学观念和审美风格方面的努力,在这种大众征文的活动中,他们对文学是积极的、介入的态度,致力于迎合和引导读者的阅读和写作趣味。第二十五期公布《论语》周年纪念征文悬赏名单后,又发起了以“低能校长”“无脑县长”为主题的征文。第五十二期发出的以“现代教育”为话题的悬赏征文,要求“老老实实正正经经把现代教育的内幕实写。或能谈到现代教育之根本方式制度及原理上之刺谬矛盾不合实际者,尤为上乘”[33],且规定奖金第一名五十元,第二名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第六十九期发布了《农民生活专号征文启事》,其中说:“然而纸上谈兵,文人通病;‘经济恐慌’,我闻已熟,‘农村破产’,此调常谈;要在有感而发,勿作纸上吟哦。”[34]陶亢德在本期《编辑后记》中关于此次征文作了说明:“农民之苦,人尽皆知,不劳空喊,能把农民的真生实活实在细腻生动的写出来,农民的苦乐自然活跃纸上。不至使人如觉隔靴搔痒。”[35]从征文的效果来看,成绩也是达到甚至超过预期的,第六十一、六十二期的“现代教育专号”上所刊文章均以关注当下与普通人最为相关的教育问题为主,也涉及了对教育理论的介绍和探讨。第七十三期的农民生活特辑里多用写实的态度谈当地农村的特色民俗、风景、家庭生活、劳动生活等,文章笔法闲适、浅白、幽默,让读者看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状态。在这些文章里没有高呼、没有口号,只有苦乐相伴的真实农民生活。这一系列活动不仅实践和传递了论语派的文学理念,也在读者中形成了一定的认同圈,使论语派的公共交流空间得以扩展,进一步扩大了共通体的规模。
正如林语堂自道的那样:“退而优孟衣冠,打诨笑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胡求,强颜欢笑,泄我悲酸。”[36]在商业出版的运作下,论语派虽是相对于话语中心的边缘人,却没有丝毫边缘意识的自卑和沦落,反而借助商业和媒介不断寻唤知我者,也得到了可观的回应,他们自己的立场被更多人所理解,对言论空间的争取与守护也更具有传播性。
三、商业出版与杂志自主性的维持、偏离
作为媒介共通体,论语派杂志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来维持自己的商业营运和共通性。在出版策略中所有促成自主性的因素里,共通体内部、知我者以及同行的推荐与评价机制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就《论语》来说,每年的九月十六日都要推出“周年纪念号”,上面不仅有相应的周年纪念号征文和悬赏,而且还登出不少论语派内外评价《论语》的诗文,我们在其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其杂志共通性的不断重申,也可以窥探共通体维持自主性的过程。在第二十五期的“周年纪念号”上,打头的是林语堂的一首《论语周年秋兴有感》,在序文中他说:
晨起,欲为《论语》周年作卷首语,而秋风萧杀,令人悲恻。偶吟“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下不治可奈何”之句,以附篇首,而愈写愈凄凉……幽默之泪,就诗中求之可也。[37]2
此处可见隐士般退避的无奈和苍凉的心境,而正文部分“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下不治可奈何?愿把满腹辛酸泪,化作秋蝉唱秋歌”[37]2,分明是欲入世而不得、欲有所为而无法的悲痛,和孔子的“道隐”相差无几了。全诗再往下读皆是一番酸苦之言,唯有最后一节“春满庭前觉太和,儿孙堂下笑呵呵,田陌行人齐上坡,池中花动知鱼过,秧里凤吹见田螺”[37]2,方可见出一些潇洒情态来。在这一期上,老舍做《贺论语周岁》:“论语已周岁,国犹未全亡,苍天实惠我,放胆做流氓!”[38]18《论语》在世道日衰之中幽默背后的悲苦心酸之态已跃然纸上。
在第四十九期的“两周年纪念号”上,“同志小影”专栏展示了老舍、老向、邵洵美、全增瑕、俞平伯、丰子恺、姚颖、郁达夫、何容、海戈、江寄萍、钱仁康、阿符、大华烈士等人的近照,这一行为可以说是一次论语派成员的团体亮相,亦是一次来自“官方”的身份认同。第七十三期的“三周年纪念特大号”上,海戈发表《记“三”》评价《论语》三年来的成绩:“故论语三年来,曾不左派,而也常反对右派;曾捧要人,而也常痛骂要人。”[39]这不仅是普通的共通体内部的评价,更是一种知我者言,与二十五期“周年纪念号”林语堂的《论语周年秋兴有感》以及《论语》的共通性是分不开的。
共通体内部评价不只有《论语》“周年纪念号”上的一系列举动,他们对于自己刊物上的小品文也有不少评价,这些评价多见于《宇宙风》。“知堂先生的《明末的兵与虏》,告诉我们‘殷鉴不远’。莫石先生的《唐人与支那人》这篇日本通讯,使我们痛感自己的不肖,该怎样发奋有为……《保证人》是何容先生的幽默作,读这种文章,能够从微笑中领悟出社会上的合理处”[40],“木石先生的春在东京,告诉我异国的春景。姚颖女士的文章擅于夹叙夹议,风趣天然,隽永耐味”[41]。虽然以上那些文章的作者并不一定全是论语派成员,而编辑当然赋予内在逻辑以优先性,以杂志的文学观念内在地分析作者来稿,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些评价里看到“痛感自己的不肖”“社会上的合理处”“辛苦艰难”“启人生趣”“怡情养性”等能体现出论语派杂志价值观的词汇。
1934 年5 月,林语堂还为论语派的作家们出版了《论语文选》,据张泽贤《中国现代文学散文版本闻见录》的收集,此套丛书有《老舍幽默诗文集》(老舍)、《论语文选》(郁达夫)、《庶务日记》(老向)、《幽默解》(邵洵美)、《我的话》(林语堂)、《蒙尘集》(海戈)、《幽默诗文集》(老舍)、《说幽默》(邵洵美)八种。“论语丛书”的作者(编选者)均为论语派成员。根据章克标的回忆:“《论语》应读者要求,还特别发行了合订本以半年十二期合订为硬面精装的一册,只售一元。”[11]179这都是他们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经典化的方式。
这些共通体内部的自我评价,充分展示了论语派的精神内核,体现了共通体内互为知己的关系和共通体自主运作的能力。除此以外,论语派刊物的爱好者、拥护者也自觉地对这一共通体的自主性起到了维护作用,他们理解了论语派的文章,认同论语派无奈之下的幽默,欣赏杂志的性灵小品,他们进入共通体的逻辑之中,又从外部对共通体进行阐释。“生于可以愤慨之世,当然不能无愤慨之情,所以论语诸公之言外流露愤慨,乃人情之常,正足以见诸君子之‘人气滃然’。”[42]“我爱论语诚如论语社同人戒条所说:不主张公道,只说老实的私见。当今天下主张公道的人已是太多,而肯以老实的私见公于人者,实在太少;见那鬼鬼祟祟的英雄的叫卖,真使我们堕入五里雾中。”[43]爱护《论语》的读者都在论语派的文章里读出了他们纸背的意味——除了性灵幽默闲适外,还有苍凉与悲怆、无奈与愤懑,也有真诚与真实。读者的理解和拥护使得论语派杂志的共通性在批判声中更进一步得以确立,具备了一定的抵挡外部质疑和打压的自主性。
论语派长于微言大义的姚颖谈到读者对自己的评价时说:“责备我最厉害的,是一般以革命自负的朋友,他们怪我不去谈民族复兴与二次世界大战莫索里尼希特勒,而谈烟的作用主席购物夏日的南京,他们说我清谈误国,并引晋朝的先例作证……但是爱我护我的,又屡屡对我树起大拇指,他们以为中国过去太为礼教所束缚了。”[44]读者对于姚颖评价的两极分化或许也能映射出世人对论语派的态度,革命的一派责其太消极、太幽默,而知我者却是百般爱护,赞其说话的勇气与痛快。
当然,除共通体内部、知我者以及同行的推荐与评价机制这一具有优先地位的自主倾向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 三本杂志的经济独立是其维持自主性不可或缺的因素。1930 年代的上海,文学与商业之间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合谋关系,商业和经济资本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操纵着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论语》第一期的《缘起》就声明过:“钱是由我们同人中一位高门鼎贵的友人来的。我们但知他豪爽,至于他这钱那里来的,我们怎知道?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来这钱要看读者出的,读者这钱那里来的,我们更不敢穷究了。”[1]2-3而他们的确通过刊物获得了足够的经济资本,林语堂晚年回忆道:“我创办的《论语》这个中国第一个提倡幽默的半月刊,很容易便成了大学生最欢迎的刊物。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对我说:‘我若有要在公告栏内公布的事,只须要登在你的论语里就可以了。’”[15]295陶亢德在《宇宙风》办刊一年时说:“实际上宇宙风已出了二十四期,刊载了五百余篇百五十万字的文章,百多幅漫画,有四千多的长期定户,一万五千的零购读者。”[45]而且《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本刊物还实行了捆绑销售策略,在《宇宙风》上可以见到这样的字样:“论语、人间世定户直接向本社定阅,全年优待九折。”[46]这均能见出论语派刊物销量之广,其意义不只在于让销售方赚得许多经济利益,更在于使得这个共通体获得了自主运作的雄厚的经济支撑。
不过,商业的运作虽然给论语派杂志带来了经济独立,却又使共通体产生偏离自主性的消极方面。沈从文评论当时的上海文坛时说:“或与商业技术合流,按照需要,交换阿谀,标榜通道,企图市场独占。”[47]而就文体来说,小品文的写作和售卖似乎容易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仅由于篇幅短小、内容简单而较之长篇小说和专著更容易产出,也因为对于上海读者而言,在光怪陆离的工业社会里生活更需要性灵文字使他们的闲暇时光得到娱乐和放松。于是,论语派的刊物也就有了不得不迎合读者趣味的倾向,《论语》的“雨花”“卡吞”等栏目是专说笑话的,而刊登的文章也有不少堕入了单纯说笑或是无意义的生活琐事的尴尬,并未见出任何深意来。这些向商业投其所好的行为,使得论语派的杂志多了一些轻浮和浮躁,本应该出自内心的真诚却为经济利益所操纵,部分地遮蔽了那些曲折沉着的议论、讽刺和切实真情的散文,甚至让人察觉到他们所认同的隐士身份有一些故作姿态的嫌疑。所以鲁迅便评价:“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噉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48]鲁迅认为他们的隐士生活和创作当然是有挣扎意味的,只是在现实生存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更加装饰了隐士的招牌。更何况,刊物的运转较之一般的图书更是文学、资本与商业的共谋。所以,商业的运作虽然保证了论语派的自主性,令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本维持自己的内在逻辑而不向三十年代的政治话语屈服,却又促使他们走向了自主性的反面,使其在《论语》第一期《缘起》上所标榜的“隐士”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商业竞卖的名片。
在报刊经济维度的考量下,论语派杂志即成了言论理想和消费文化的合一。《论语》第一期《缘起》的说辞,使人可以足够相信他们有办一贡献于社会国家的刊物的志向。不过,林语堂的确是一位长于“写书赚钱”的有着商业头脑的作家,“性灵幽默”和“言论自由”的旗帜也难掩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前面分析过的《人间世》和《宇宙风》创刊的直接原因更是显现出他对经济因素的考虑。论语派杂志不仅显示着其同人的文学和政治观念,也是商业和消费文化与前两者的合谋。
结语
论语派杂志的共通性是在自我定位和他者刺激之下才得以完整地形成。就自身定位而言,《论语》承担了论语派写作幽默文章与进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任务,二者的并存源于1930 年代的逼仄环境,尤其是源于此时上海严厉的出版物审查制度;而《人间世》和《宇宙风》则更多地倾向于提倡和刊登性灵闲适小品文。由于左翼文人团体的质疑和官方的批评,论语派杂志才从最初以自说自话为目的和有着明确经济因素考量的刊物,转变成了进一步以性灵幽默文学观为根基,并指向功利主义文学工具论的阵地。而作为媒介共通体,论语派杂志实是一场文学观念、政治身份与商业出版的共谋。论语派杂志利用杂志封面、专号与征文活动、读者与同行评价机制等一系列的编辑、发行的策略来形成庞大的认同群体,维持他们共通体的运行,并巧妙地规避了当时上海对出版物的严格管制。此举既使他们小品文的创作理念传播性更强,也达到了他们对社会、历史、文化部分讽刺与批判的目的。在商业出版过程中,论语派杂志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维持共通体的自主运营,然而,消费文化也使论语派杂志不可避免地为了销量而产生了媚俗倾向,从而部分地消解了其小品文的文学性和杂志的批判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