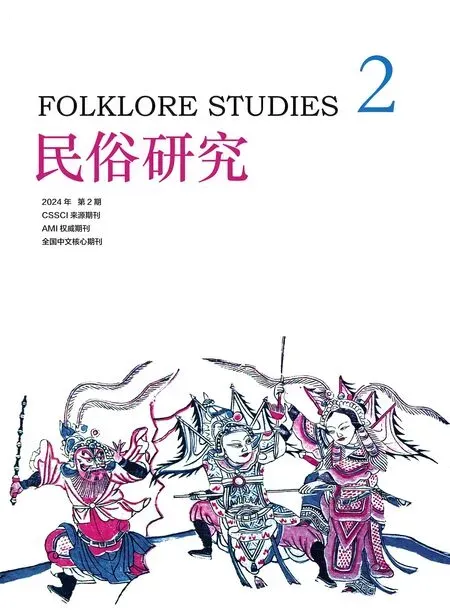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夏小正》岁首星象考
刘宗迪 宋 亚
今本《夏小正》为《大戴礼记》一篇,但《夏小正》原本是独立成编的,至汉代经师整理古书,才被编入《大戴礼记》中。《夏小正》详细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气象、农事、天象,记述物候尤其不厌其详,面面俱到,涉及草木、鸟兽、虫鱼数十种动植物的物候现象,显然是一篇基于实际观察经验,旨在根据物候判断农业时令的农事历,其中记载了数个星象,但其关于星象的记述还缺乏像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那样一个完整的十二月昏、旦中星和二十八宿体系,这些星象记载表明当时还仅仅关注对几颗明星的观察,显然是源于民间的实用观星经验,而不是出于专业天文学家的系统观察和推算,表明《夏小正》尚处于从原始的物候历向成熟的天文历的过渡阶段。《夏小正》文字朴实而简古,记事参差而翔实,物候、星象等知识全为实用而不求完备,不是像《十二月纪》那样的纂集旧籍成文、依托五行为说、行文追求整齐,当成书甚早,其中应保存了华夏先民非常古老的时间知识,对于研究上古天文、历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夏小正》的历法问题,因为其书以“夏”为题,言其为夏代之书,而《礼记·礼运》有言:“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云:“得夏四时之书,其书存者有《小正》。”(1)朱彬:《礼记训纂》卷九,中华书局,1998年,第334页。是郑玄认为《夏小正》即孔子从杞国所得的“夏时”,即夏代时令之书。《史记·夏本纪》太史公赞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2)司马迁:《史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89页。是司马迁即以《夏小正》为孔子所得夏代之书。司马迁为天文学世家,其祖先为周室太史,“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5页。,必明于天学历数之掌故,以《夏小正》为孔子所得夏代之书,当为先秦天官相传之说。《夏小正》既然题为夏书,而《礼记》《史记》又言之凿凿,故古代学者均深信《夏小正》为夏代文献,其所述历法为夏代历法,亦即夏历,即沿袭至今的以孟春之月为岁首的夏历之前身。
近世以来,学者有了历史发展的观念,认识到夏代文字尚不存在,遑论夏代文献,像《夏小正》这种体制完备的农事历文献不可能出现于夏代。《夏小正》既非夏代之书,则以《夏小正》历法为夏历之说也就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加之历史上有所谓“三正说”,即夏、殷、周三代历法各不相同,夏历以孟春之月(即夏历正月)为岁首,殷历以季冬之月(即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周历以仲冬之月(即夏历十一月)为岁首,因此,20世纪以来,围绕着《夏小正》所用历法问题,不同的学者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定论。诸家所论归纳为三种观点:夏纬瑛、杨宽、何幼琦等认为《夏小正》所用历法为夏历,以孟春之月为正月(4)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73页;杨宽:《月令考》,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3-510页;何幼琦:《〈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张汝舟、张闻玉、蒋南华等认为《夏小正》所用历法为殷历,以季冬之月为正月(5)张汝舟:《〈(夏)小正〉校释》,《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1期;张闻玉:《〈夏小正〉之天文观》,《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蒋南华:《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而陈久金、刘尧汉、卢央等受彝族历法的启发,鉴于《夏小正》所记星象和物候不乏与夏历星象和节气龃龉之处,因此提出《夏小正》所用历法为十月太阳历,即分一年为十月、每月为36天、余5天为过年日的纯阳历。(6)李白:《〈大戴礼·夏小正〉所用历法考证》,《钦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陈久金等认为《夏小正》其书原本只分为十个月,华夏上古时期曾有过一个使用十月太阳历的阶段,后来行用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十月太阳历湮灭不闻,后人将《夏小正》分为十二个月,导致被重新划分后的星象、物候记事与夏历的实际情况不合。(7)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第4期;刘尧汉、陈久金、卢央:《彝夏太阳历五千年——从彝族十月太阳历看〈夏小正〉原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238页。十月太阳历说令人耳目一新,轰动一时,影响甚大,被很多学者视为卓识。但十月太阳历说毕竟与夏历传统大相径庭,且古代文献中难以觅见十月太阳历的线索,《夏小正》文本本身也不乏与此说相悖的证据,故尚难以为定论。
人类的各项制度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到成熟、由粗疏到精确的发展历程,纪时制度也不例外,历史上大致经过了物候历、星象历、推步历三个阶段。由于物候变化与天气变化、农事条件关系最为密切,且花开花落、鸟兽迁徙之类物候现象容易引人关注,最初使用的肯定是物候历,根据草木、鸟兽、虫鱼的变化、迁徙、叫声等判断农时,《夏小正》中记载最丰富的就是各种物候现象。但是,物候受地域、气候的影响,缺乏普适性、准确性,而满天星斗为普天之下所共睹,日月轮回、斗转星移较之物候能更准确地确定时间,因此,先民们一旦认识到星空运行的规律,肯定会用星象纪时,于是物候历就被星象历替代,《夏小正》于记载各月物候之外,还记载了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八月“辰则伏”、九月“内火”、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一系列重要星象(8)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28、29、33、35、37、39-46页。,可见当时已经有了丰富的星象观察经验,表明《夏小正》实为物候历向星象历的过渡时期的产物。《夏小正》只记载了正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九个月的星象,缺二月、十一月、十二月的星象,而且只提到鞠、参、斗、昴、南门、大火、织女和银河等几种最引人注目的星象,未见后来《十二月纪》中那种系统的十二个月昏、旦中星和二十八宿的记载,说明当时对于星象的观察还处于仅观察有限的几颗亮星的阶段,尚没有建立二十八宿坐标系,更没有对日月运行规律的细致观察。二十八宿作为日月运行的天文坐标系,日月运行周期和方位的准确观察,是历法推算、建立精确的推步历的基础,这必须在长期天文观察、积累大量观察数据并且掌握了日月运行规律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夏小正》反映的历法水平距离推步历还有很大差距。
既然《夏小正》还不是推步历,那时候的天文学还不具备精确观测和推算的能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制定历日,不可能精确地确定每一个年度周期、每一个月份的起止,不可能精确地计算某个特定年度周期的天数,甚至不可能预先根据对日月运行的推算精确地确定每年的第一天是哪一天、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哪一天,而只能根据对日、月、星辰位置的随时的观察临时判定。既然《夏小正》的历法不是推步历,那么,所有关于它所用历法究竟是夏正还是殷正的争论都是无的放矢。因为没有成熟的推步历,也就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岁首日期,岁首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不居,而不会固定于孟春之月(夏正)或季冬之月(殷正),所以争论《夏小正》所用究竟是夏正还是殷正就是没有意义的。至于十月太阳历说,彝族历史上是否使用过十月太阳历,姑且置而不论,《夏小正》这部物候历的存在,就足以推翻存在十月太阳历的可能性。因为十月太阳历纯粹以太阳运行为制定时日的依据,以36个天为一个月(太阳出没36次),以10个月为一年,剩下的5天放在最后为过年日。如果真有这种历法的话,只要确定了某天为推算时日的起点(相当于历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可以简单地推算未来的每一个日期,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每一个农事周期,而根本不需要再费心去观察那么多物候、星象,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夏小正》这样的物候历。(9)古埃及历法就是纯太阳历,一年12个月,每月30天,每年加岁余5天,一年共365天,以天狼星偕日升、尼罗河涨水之日为岁首,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87页。纯阳历的观测、推算十分简单,用来决定农时也十分准确、方便。但是,大多古代民族(巴比伦、印度、波斯、中国)却没有使用阳历,而宁愿使用麻烦的阴阳合历,阿拉伯人甚至使用与太阳无关的纯阴历,原因何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历法不仅为农时服务,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供日常生活记日期。月相一天一个样,用来标志日期直观且方便,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月相记日的习惯和朔望月制度。既要明农时,又要记日期,于是各民族就自然使用阴阳合历了。
夏历和殷历之别主要在其正月不同,夏历以孟春之月为正月,殷历以季冬之月为正月,故关于《夏小正》是夏历还是殷历的争论,无非是关于《夏小正》正月或岁首在何月的争论,既然《夏小正》所反映的天文学水平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推算、确定每一年的岁首所在,那么争论其为夏正还是殷正就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讨论《夏小正》是夏正还是殷正虽然没有意义,但《夏小正》的岁首问题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所有历法,不管是多么原始的历法,其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新年的起点,即使是一个需要每年重新观察确定的起点。只有确立了起点,才能从这个起点开始依次对接下来的月、日进行命名、编码,不管这种命名、编码是根据物候、星象确定,还是天文推算的结果。岁首就是时序的起点,是任何纪时制度都必须首先确立的坐标原点。《左传·文公元年》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510-511页。“履端于始”就是确定纪时的起点,有了起点,才能按部就班地筹划接下来一年的时序(“序则不愆”)。
历法上的岁首,作为一年开始的一天,也就是节日意义上的新年,或曰元旦,中国传统夏历是以距离立春节气最近的朔日为元旦。正因为夏历元旦根据立春节气确定,所以民国初年改历后,将夏历元旦改称为春节,也算名副其实。那么,在没有成熟的基于天文推算而确立的夏历之前,自然也就无法准确确定立春节气(甚至还没有立春的概念),自然更谈不上确定与立春相邻的朔日。华夏先民是在什么时候过年,是如何确定一年的起点即岁首的呢?《夏小正》既然是现存最早的华夏岁时文献,其中记载了好几个重要的星象观察信息,是否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依据星象决定岁首的能力呢?
一、“初昏参中”与《夏小正》岁首
如前所述,历法的发展,是先有物候历,继之以星象历,然后才有推步历。原始的物候历阶段,先民们是根据物候纪时,也只能根据物候确定新年,将某种物候现象的出现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比如草原民族在青草返青时过年,渔猎民族在马哈鱼的洄游时过年,农耕民族在某种农作物收获的时候过年。“年”字的甲骨文象征禾穗低垂的样子,表明从事农耕的华夏先民可能曾经以农作物的丰收为新年的标志。由于物候历受地域、气候的影响,缺乏普适性和恒定性,随着文明的进步,物候历必然被天文历所代替。早期的天文观测还十分疏阔,缺乏对日月运行周期的精确观察和推算技术,故必须依靠对日、月、星象的即时观测,并结合对物候的观察,确定特定的时日,此时的天文历还只能称为星象历。《夏小正》详细记载了众多物候和九个月的星象,就已经具备了物候历的性质。由于新年岁首是历法周期中最重要的时间点,先民们一旦认识到星象与时间的关系,肯定会用某个特定星象作为新年岁首的标志,从而将这一星象作为岁首星。众所周知,由于尼罗河洪水与埃及人的农业活动息息相关,尼罗河洪水的到来预示着播种季节的到来,因此古埃及人最早即以尼罗河洪水的到来作为新年的标志,后来,埃及人发现每当尼罗河洪水到来时节的拂晓,天狼星就会随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于是,埃及人就用天狼星作为新年的标志,天狼星就成了埃及人的岁首星。那么,华夏民族最早的岁首星是什么星象呢?就笔者所知,华夏原始星象历岁首星的问题在学界还从来没有被提出过。实际上,《夏小正》中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华夏先民一度以参星作为新年到来标志,参宿就是华夏先民的岁首星。
《夏小正》云:
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畼。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献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1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24-30页。按:今本《夏小正》文本经、传相混,今只录其经文。
这段文字的内容可以分为物候、农事、气象、星象四类:启蛰(冬眠的动物苏醒了)、雁北乡(大雁从南方回到北方)、雉震呴(野鸡开始鸣叫了)、鱼陟负冰(河冰消融,鱼浮上水面)、囿有见韭(菜园子里长出了新韭)、寒日涤冻涂(早春的太阳融化了冻土)、田鼠出(田鼠钻出了洞穴)、獭献鱼(水獭趁机大量捕鱼)、鹰则为鸠(鹰隼消失不见,斑鸠飞回来了)、柳稊(柳树长出了嫩芽)、梅杏杝桃则华(梅树、杏树、山桃纷纷开花)、缇缟(莎草长出来了)、鸡桴粥(母鸡开始抱窝),是为物候;农纬厥耒(农民修整农具)、初岁祭耒始用畼(农民使用农具前要进行祭祀)、农率均田(农民开始平整土地)、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农民趁积雪刚刚融化先耕种公田)、采芸(采集芸蒿),是为农事;时有俊风(该月经常刮起浩荡的春风),是为气象;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则是星象。参指参宿三星,“初昏参中”,谓参宿在正月的黄昏见于正南方夜空;斗柄指北斗七星中的摇光、开阳、玉衡三星构成的勺柄,“斗柄悬在下”指正月黄昏时分斗柄指向下方,即北方;鞠也是星名,古代天文记载中罕见鞠星之名,鞠星究指何星,学者众说纷纭,先后被指为鞠星的有虚、臼、天钱、天钩、匏瓜、禄、北落师门、危、室等(12)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皆无确据,唯清人王筠《夏小正正义》云:“窃亿鞠星盖老人星也,是星近南极,秋分之曙见于丙,春分之夕见于丁,一岁仅再见。”(13)王筠:《夏小正正义》,清光绪五年王懿荣辑刻《天壤阁丛书》本。老人星是整个夜空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颗亮星,位于参宿的左下方,每年春天,当参宿升上南方夜空,过几天之后,老人星也随之升起。但是,由于老人星纬度甚低,位置偏南,在中原地区平时很难见到老人星,每年只有在春分前后的黄昏和秋分前后的拂晓,老人星升上南中天最高点,才能出现在靠近正南方地平线的地方。因为老人星一年之中分别在春分和秋分前后出现两次,故《夏小正传》云:“鞠则见者,岁再见尔。”(14)关于老人星的天文学问题及其在古代岁时制度中的作用,详见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67-1381页。
《夏小正》正月记事,将“鞠则见”与“初昏参中”同列为正月星象,足以证明参宿就是《夏小正》的岁首星。
《夏小正》正月条记载了三个黄昏星象,即“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这三个星象中,只有“初昏参中”和“斗柄悬在下”有可能同时发生,即当参宿在黄昏时分升上南方夜空的时候,眺望北方夜空,正好看到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下方(北方)。至于“鞠则见”,则肯定无法与“初昏参中”和“斗柄悬在下”两者同时发生。如上所述,鞠星(老人星)位置偏南,纬度甚低,只有在每年的春分前后的黄昏、秋分前后的拂晓才能见于南方地平线上方,其可见时间很短,升起后不过几天就重新隐没于地平线下而不可见,故古人依据对老人星的观察判断春、秋分的日期。依据天文软件回溯,可知在上古时期,老人星在参宿以东,与参宿之间的赤经相差约30°,也就是说,老人星要在参宿初昏南中天约一个月之后才能升上南中天的最高点而被看到(周天赤经360°,恒星每天西行约1°),这意味着,“鞠则见”只能发生于“初昏参中”一个月之后。既然“初昏参中”与“鞠则见”的星象相差一个月,那么,要使这两个星象出现在同一个月里,只有当“初昏参中”出现于月初、“鞠则见”出现于月末才有可能。这意味着,“初昏参中”实为正月的月首标志,正月月首也就是岁首,因此,“初昏参中”也就是《夏小正》的岁首星象。
综上所述,《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鞠则见”两条星象记载表明,《夏小正》时代的华夏先民是将“初昏参中”作为岁首星象,即以黄昏时分升上正南方夜空的参宿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
阴阳合历的岁首不能单纯依靠恒星位置确定,还必须考虑月相。《夏小正》分一年为十二个月,表明它是依据月相纪月,《夏小正》当依据对太阳、恒星和月相的综合观察而判断每一个月的起止,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传统的夏历是以月亮与太阳合宿之日为月首,此时月亮处在地球与太阳之间,太阳在月亮背面,故月亮不可见,是为朔日,但朔日无法观察,只能靠推算确定,而新月初生容易观察,故早期历法很自然以新月初生之日为月首,古书称为“朏”,“朏”即月出之义。常玉芝先生《殷商历法研究》指出,商代历法就是以新月初生为月首的。(15)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24-340页。《夏小正》所反映的天文观察尚很原始,也当以新月初生为月首。这意味着,《夏小正》岁首或元旦,是综合“初昏参中”和新月初生而确定,每年春天到来之际,先民们看到黄昏时参星即将升上南方夜空时,就知道新的一个年度周期即将开始了,此时他们将期待下一个新月初生的日子,并将这一天定为新年的第一天。
由于春天“鞠则见”星象只能发生于春分的黄昏,二十四节气中较春分早30天的是雨水节气,两者之间还夹着一个惊蛰节气,这意味着《夏小正》的正月可能包含了三个节气,其天数肯定不会少于30天,这是因为《夏小正》时尚无完善的节气制度和推步历法,每个月的天数可能还有很大的变化,需要随时依据星象、物候和月相的观察而确定,因此还无法形成后来的一个月含两个节气的纪月法(当时还没有二十四节气制度)。(16)常玉芝先生指出商代历法有30天、31天的大月,小月则可能少于29天,甚至只有25天,并且会出现最多达3个连大月、3个连小月的情况,说明商代历法的月长还极不稳定。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夏小正》“鞠则见”与“初昏参中”同为正月星象的记载表明,《夏小正》时代是以相当于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节前后的日期为一年的开端,而并非像后来的夏历,以雨水之前的节气立春为正月节,也就是说,《夏小正》岁首较之后来通行的夏历元旦大概迟半个月,那时候的人们比现在晚半个月过年。“囿有见韭”“杏、杝桃则华”“农率均田”之类的物候和农事记载也表明《夏小正》的时序较迟,现在新韭初见、桃杏开花要到农历二月才有可能,农民也要出了正月、到二月才开始春耕。
现行二十四节气制度中,雨水在前,惊蛰在后,沿袭的是《淮南子·天文训》中的二十四节气的顺序,《淮南子·天文训》是最早全面罗列出二十四节气名称的文献。但在古代还有另一种二十四节气顺序,即《汉书·律历志》中的记载,惊蛰在前,雨水在后。《律历志》所据为刘歆三统历,但刘歆把惊蛰放在雨水之前,却并非自作主张,而是由《礼记·月令》而来。《礼记·月令》虽然没有像《淮南子·天文训》那样明确地列出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但它对十二个月物候的记述中,已经蕴含了二十四气体系的雏形:如孟春之月,“蛰虫始振”,“孟春”已含立春之义,而“蛰虫始振”则相当于惊蛰节气;仲春之月,“始雨水”,相当于雨水节气,“日夜分”即春分;孟夏之月,“小暑至”即小暑节气,“日长至”即夏至。按照《月令》的物候顺序,惊蛰在雨水之前。刘歆重视《月令》,故其三统历依据《月令》体系对《淮南子》的二十四节气秩序做出调整。实际上,《月令》以“蛰虫始振”为孟春物候,正是沿袭自《夏小正》,后者正月物候的第一条、亦即全年物候的第一条,就是“启蛰”。这意味着,华夏先民用“初昏参中”作为岁首星标志新年的时间之前,在单纯的物候历阶段,可能是以冬眠动物的启蛰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的。众生启蛰,万物复苏,预示着冬去春归,用启蛰作为新年开始的标志可谓顺理成章。启蛰是动物物候,以启蛰为新年到来的标志,很可能源于更为古老的渔猎采集时代。《夏小正》正月物候中,“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田鼠出”“獭献鱼”“鹰则为鸠”“鸡桴粥”都与动物活动有关,足见当时的人们对于动物的生态行为之熟稔。“启”正含有开启、开始之义,寓意新一年的门户从此敞开了。
但是,《月令》的惊蛰物候跟《夏小正》的惊蛰物候只是形式上的对应关系,在时间上却无法对应起来。《月令》和《夏小正》的惊蛰尽管都在正月,但在阳历的时序上,《月令》的正月却并非《夏小正》的正月,故《月令》的惊蛰也不是《夏小正》的启蛰。《月令》的春分在二月,《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夜分”是也。春分在二月,则正月当以立春为节气、惊蛰为中气,是《月令》的惊蛰当在正月下半月。“鞠则见”的星象记载表明《夏小正》的一月含有春分,《夏小正》正月既然含有春分,而春分的日期是不变的,则其正月初当在二十四节气的雨水和惊蛰之间,是《夏小正》的惊蛰当在正月的上半月,可见《月令》的岁首较之《夏小正》在节气上提前了半个月。正因为《月令》是以立春之月为岁首,所以才能称一月为孟春之月,《月令》已经开启了后来夏历以立春定岁首的先河。
综上所述,《夏小正》中,“初昏参中”与“鞠则见”两者同见于一月,由于鞠星只有在春分前后的黄昏可见,又由于上古时期参宿与鞠星的赤经相差约30°,因此“初昏参中”与“鞠则见”两个星象之间相差约30天,这意味着,《夏小正》以含有春分之月为正月,而以参宿黄昏南中天为正月到来的标志,即以参宿为岁首星,以参宿在黄昏时分升上正南方夜空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遥想《夏小正》时代,每当明亮的参宿三星升上黄昏的正南方夜空时,浩荡的东风送来春天回归的气息,冬天的积雪开始消融,冻土开始融化,大雁北翔,雉鸡啼鸣,河里的冰化开了,鱼从水底浮上水面,水獭趁机大肆捕鱼,菜园里长出了青青新韭,草木开始萌动,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动物们蠢蠢欲动,田鼠钻出了洞穴,山上的杏花、桃花含苞欲放,万物复苏,大地回春,种种迹象都表明,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农民们应该收拾农具准备新一年的劳作了。当此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时节,群星灿烂的猎户座升上正南方,在整个早春的夜晚都辉耀在南方夜空,因此,古人就以“初昏参中”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南方夜空中明亮的参宿就成了华夏民族的岁首星。
二、夏主参星、商主大火的传说与夏商岁首制度
《夏小正》以“夏”为名,古代学者因此相信其为夏代遗文,认为其所记载的是夏代的物候和天象。夏代尚无文字,《夏小正》当然不可能是夏人所著。实际上,鞠星的记载就足以表明它不可能出自夏代。如上所述,鞠星(老人星)纬度甚低,在中原地区很难看到,每年只有在春分前后几天的黄昏、秋分前后几天的拂晓才能见于正南方的地平线之上。由于岁差和天球章动的缘故,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一直经历着微小的变化,老人星在上古时期的纬度较之现在更低,因此更难见到。计算表明,如果以黄河下游的泰山为观察点,老人星在商周之际的公元前1000年之前即使升上最高点,其赤纬仍在地平线下,因此无法看到,直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老人星运行的最高点才逐渐升上地平线以上,才可以被中原地区的观察者看见。(17)刘牛:《公元前2000年-公元元年间老人星可见性计算报告(摘要)》,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378-1381页。由此可见,《夏小正》不可能成书于夏代。然而,《夏小正》不是出自夏代,却并不妨碍它为夏人后裔所作,反映了夏人的岁时传统和时间制度。众所周知,夏代虽亡,但夏人犹在,史载周武王灭商,封夏人后裔于杞国。《礼记·礼运》载孔子之言云:“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18)朱彬:《礼记训纂》卷九,中华书局,1998年,第334页。《史记·夏本纪》太史公赞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19)司马迁:《史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89页。是以《夏小正》即孔子在杞国得到的夏时之书。夏代人不能著书,但夏人的后裔杞国人却能著书,将夏人父老世代积累、口耳相传的岁时知识、星象知识和物候知识付诸文字。杞国直到春秋时期犹存,且距曲阜甚近(20)杞国为夏后,《史记·陈杞世家》云:“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1583页。该杞国在雍丘(即今河南杞县),后迁于缘陵(今山东安丘县北)。《春秋》《左传》屡见关于杞的记载,杞、鲁来往尤为频繁,前人均认为是由雍丘迁缘陵之杞国。但是,王恩田先生指出,若以《春秋》《左传》所记之杞均指同一杞国,则其中很多记载难以说通。王恩田先生通过对新泰出土杞国铜器的研究,结合甲骨文、商周金文资料,证明春秋时期新泰有杞国,详见《从考古材料看楚灭杞国》《新泰杞国铜器与商代杞国》(王恩田:《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45-253页、261-267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国侵占杞国的土地,杞国诉于晋国,晋国迫使鲁国归还杞田,鲁人以成邑与之。成邑即郕,位于鲁国东北境,可见杞国必定在鲁国东北,而曲阜东北即为今新泰县,可见被鲁人视为“夏肄”“夏余”的杞国当位于新泰一带,详见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96-497页。,周游列国、信而好古的孔子当然有可能在杞国得到记载夏人岁时传统的文献,其书尽管不可能成书于夏代,却可能保存了夏代的文化记忆,以“初昏参中”为正月星象标志、以参宿为岁首星的传统可能就是源自夏代。
说到这里,很自然会联想到那个著名的夏主参星、商主大火的传说。《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2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217-1218页。《左传·襄公九年》也说:“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963-964页。这一传说众所周知。那么,夏主参星、商主大火究为何义?《左传·襄公九年》之言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学者多留意“祀大火”,认为夏主参星、商主大火就是指商人负责祭祀大火星、夏人负责祭祀参星,而往往忽视了“火纪时”一语。其实,“火纪时”才是商主大火的要义所在,同理,夏主参星的要义也是“参纪时”。何谓“纪时”?所谓火纪时或参纪时,即以大火或参宿为根据制定时序。制定时序最关键的一点是时序起点的确定,即岁首的确定,上引《左传·文公元年》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履端于始”即确定岁首,夏人以“初昏参中”为岁首,就是“履端于始”,也就是“参纪时”。
既然所谓夏主参星是以“初昏参中”作为岁首的标志,而《左传》将商主大火与夏主参星相提并论,那么,商主大火当意味着商人是以“初昏火中”作为岁首的标志,即商人当是以大火星在黄昏南中天之月作为正月。上引《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尚书·尧典》亦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2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第18-19页。二者均以大火昏中作为仲夏五月的星象,则“商主大火”而“火纪时”的说法可能意味着商人历法是以仲夏五月为正月,以“初昏大火中”为岁首星象。
古书中并无关于商代岁首的明确记载,所谓“三正”之说,即夏正以孟春、商正以季冬、周正以仲冬之说,只是战国之际学者的虚构,并非史实。殷墟卜辞中载有大量关于商王占卜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时日干支和气象物候,因此自从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学家就致力于对商代历法的研究和重建,并对商代岁首提出种种假说。常正光认为殷以夏历四月为正月,温少峰、袁庭栋认为殷以夏历三月为岁首,郑慧生认为殷以夏历六月为岁首,张培瑜、孟世凯认为殷历岁首尚不固定,可能出现在夏历的七月、八月、九月,王晖认为殷以夏历五月为岁首。(24)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84-385页。常玉芝先生《殷商历法研究》广泛搜罗甲骨文献,连累排比,对商代历法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透彻的研究和系统的重建。关于商代岁首,常著通过对卜辞中气象卜辞、农事卜辞的研究,得出与王晖相同的结论,认为商代历法的岁末与岁首的交替在夏天,商代历法的岁首一月是播种黍子、收获小麦的时节,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尤能证明商代历法以五月为岁首的证据是一片连续记录了两个月甲子日名的记事刻辞,即《甲骨文合集》24440,该片刻辞首句为“月一正曰食麦”,接着刻甲子、乙丑、丙寅直到癸巳30个干支日名,30个日名后的一句为“二月父”,接着刻甲午、乙未、丙申直到癸亥30个干支日名,整版文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六十甲子日名表。(25)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该版甲骨文中的“月一正曰食麦”“二月父”意谓正月名为食麦,二月名为父,“食麦”和“父”分别为正月、二月的月名,“父”何义不得其详,但“食麦”之义甚明,“月一正曰食麦”,当指以一月为正月、一月开始食用小麦,则一月当是小麦收割的月份。《月令》云:“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26)朱彬:《礼记训纂》卷六,中华书局,1996年,第243页。以四月为小麦收获之月,则五月自可食麦。《左传·隐公三年》载:“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2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27页。可见春秋时期四月即可收麦。《管子·轻重乙》云:“令以九月种麦,日至而获。”(28)颜昌峣:《管子校释》卷二十四,岳麓书社,1996年,第610页。《轻重己》云:“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29)颜昌峣:《管子校释》卷二十四,岳麓书社,1996年,第640页。均以夏至前后为麦熟时节,夏至在夏历五月。可见上古小麦收获当在四五月之际。古人每当收获,都要首先用新获之物献神祭祖,《礼记·王制》云:“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30)朱彬:《礼记训纂》卷五,中华书局,1996年,第188页。夏天新麦初收,故以麦献神。五月既为新麦收获之月,则卜辞所谓一月食麦当即仲夏五月,可证商代历法以仲夏之月即夏历的五月为岁首。上引《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黄昏,大火星正好升上正南方夜空,可见商人确实是以大火昏中作为岁首标志,此即商主大火,“祀大火而火纪时”的本来意思。殷墟出土如下一片卜辞:
己巳卜,争[贞]:火,今一月其雨。
火,今一月其雨。(乙)
火,今一[月]不其雨。(甲)(《甲骨文合集》12488甲乙)(31)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401页。
占卜当下的一月会不会下雨。常玉芝先生认为该辞中的一月即殷历一月,亦即夏历五月,其中的“火”,即指大火星。(32)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401页。在古代宇宙观中,大火星属于东方苍龙的一部分,《山海经·大荒经》的记载表明,商代当已将包含大火星在内的东方列宿想象为天上的神龙,并根据龙星的方位判断季节,龙星处南方时正值夏季,夏季是多雨季节,故古人将龙星视为雨神。(33)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0-205页。该版卜辞因火而占卜一月是否会下雨,当即反映了此种观念,其“火”当即指苍龙之心大火星。
商主大火以火纪时,意指商人是以“初昏大火中”为岁首星象、以大火昏中的夏历五月为正月的纪时习俗,这一点反过来可以佐证夏主参星当是意指夏人以“初昏参中”为岁首星象、以参星昏中的月份为正月的纪时习俗。与古埃及天文学注重对偕日升星象的观察不同,华夏古代天文学注重对黄昏南中天星象的观测,这是因为中国地处北半球,居所坐北朝南,因此对南方的夜空更为熟悉和关注。
《左传·昭公元年》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3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218页。,至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唐,《定公四年》称其地为“夏虚”,可见唐之所在原为夏人所居。《诗经·唐风》所录即为唐地歌谣,亦即夏人遗风,其中《绸缪》是一篇歌吟男女于三星之下邂逅相遇的情诗,诗云: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35)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毛诗传笺》卷六,中华书局,2018年,第151-152页。
毛传认为三星即参星。该诗三章皆借三星起兴,据“三星在天”“三星在隅”,难以判断三星的具体方位,但“三星在户”一语足以说明,诗中男女是邂逅相遇于三星南中天的时候,门户朝南,正对参星,则诗人所见参星必在正南方夜空。人约黄昏后,“三星在户”当即指“初昏参中”的星象。夏人以“初昏参中”为岁首星象,在参星昏中的时候过新年,这对邂逅相遇的恋人大概就是在新年庆典上相遇的。《夏小正》只记物候和星象,而不及岁时庆典活动,《唐风·绸缪》则向我们透露了夏人在三星高照时分举行新年庆典的消息。
正因为元旦是新时间的开端,新年是人间最盛大、欢乐的节日,而参星被华夏先民作为新年元旦到来的标志,因此,明亮的参宿在华夏民族文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尽管由于岁差的缘故,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加上历法制度改易,参星早已不复在岁首的黄昏升起于正南方,但世世代代的人们仍执着地把参星作为岁首的标志,后世学者仍将“昏参中”书写于岁时书的开端。
《月令》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36)朱彬:《礼记训纂》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第214页。,以“昏参中”作为岁首星象。但《月令》出自战国晚期,彼时星象与《夏小正》星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况且《月令》以春分之月为二月,则当以立春之月为正月,其岁首较之《夏小正》岁首提前约半个月,故彼时根本不可能出现“初昏参中”的星象。只是由于以参星为岁首星的文化记忆早已深入人心,故《月令》仍坚持以“昏参中”作为正月星象,书写于时令的开端,其用意当主要不在于这一星象的纪时意义,而是在于其象征意义。(37)《月令》是基于战国秦汉之际流行的五行说而用不同来源的物候、天文、农事、仪式、灾异等方面的内容熔炼而成,其中的天文、物候内容并非源于成书时的实际观察,而是抄自其他现成的文献。孟春之月“昏参中”也非源于实测。不过,当时天文学尚十分疏阔,对于“昏”的时刻也无严格界定,在《月令》的岁首,即《夏小正》岁首半个月之前,尽管并不会出现“初昏参中”的星象,初昏之时参星还尚在东南方夜空,但在太阳落山的初昏一个小时后,参宿就会升上南中天,此时仍大致算得上是昏参中,故《月令》不称“初昏参中”而称“昏参中”,大体上还可以成立。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时则训》全盘沿袭了《月令》的星象和物候内容,其星象记载与当时的实测星象相去更远。
三、结 语
时至今日,已去《夏小正》成书的西周时期3000多年,距离夏代则更达4000余年,由于岁差的缘故,当今的星空图景与夏代、西周的星空图景相比早已移步改位、面目改易,加上历法变革,现在春节的日期也并非《夏小正》的岁首,因此,《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的星空图景不可能在今天的春节复现。现在每年除夕,当太阳在西方降落的时候,参宿才刚刚在东南方升起不久,要到夜间九十点钟,参宿三星才升上南中天。不过,除夕之夜的九十点钟,正是神州大地千家万户煮饺子、吃汤圆、燃放烟花爆竹、出门迎神、祭拜天地群神的时候。每当此时,尤其在夜空晴朗的乡村,欢度大年夜的人们仰望星空,满天群星中首先映入眼帘的肯定是南方夜空明亮的参宿三星。三星高照,年复一年俯瞰着幸福欢乐的人间,守护着即将开启的新岁月的门户。因此,老百姓仍将参宿视为新年到来的标志,“参门正南,家家拜年”“三星在南,家家过年”“三星高照,新年来到”之类的谚语仍在乡间口耳流传。(38)孙媛媛、刘宗迪、吴蕴豪、张超:《山东地区民间星座知识调查》,《民间文化论坛》2023年第4期。诸如此类的谚语,既反映了民众对于除夕之夜三星高照这一美丽星象的亲切体察,也保存了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岁时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