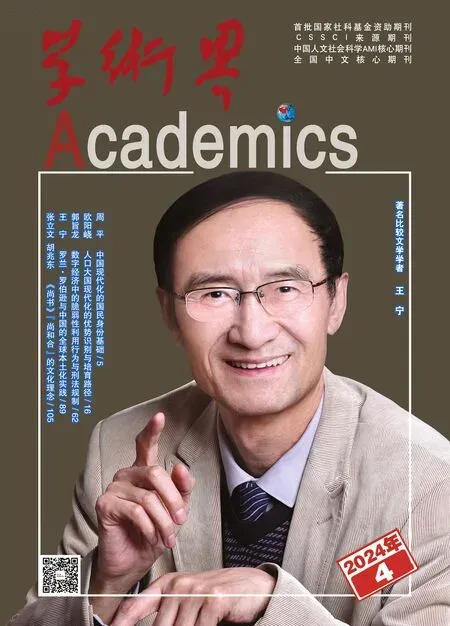论“非遗”的三个面向
彭兆荣
(1.福建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2;2.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引 言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第二十二条明确提出: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1〕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以农为本”的农耕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简称“非遗”)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党中央在“龙年”伊始就关注“三农”,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重要位置,以配合乡村振兴战略。如何遵照中共中央新的精神,描绘好“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线路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考验我们能否做到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二、面向民众:“非遗”之当下
我们所说的保护和传承“非遗”包含着以下几个含义:第一,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对文化遗产价值保护的体现。第二,是在联合国遗产事业推进中,体现中国作为大国的历史责任。第三,是中华文明在延续过程中的历史需求。第四,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代实施的重大工程。第五,是传统的乡土文化“活态传承”的机制。总之,“非遗”既然是全球化背景下遗产事业的中国实践,就需要在遵行“国际规则”中体现“中国经验”。这也是我们在当下确立“非遗”发展战略的目标和定位。
就国际规则而论,“非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遗产分类上的一种类型和规定。从联合国遗产分类的谱系可知,1972年颁布的《世界遗产公约》只是粗略地将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2〕专家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对遗产的“二分法”过于宽泛,很多类型无法容纳。由于受到美国“物质遗产”(physical heritage)概念的影响,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设了一个“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机构。后来又受到日本遗产保持法的一些概念和“有形遗产/无形遗产”(tangible heritage/intangible heritage)分类的影响,联合国于1992年正式将原来的“物质/非物质”分类表述改为“有形/无形”。我国在翻译上出于译名和使用上的连续性,仍沿用“物质/非物质”的语用概念。
事实上,对于“非遗”的概念和范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了在定义和使用上的变化外,也经历了一个学科参与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民俗学在强调民间、突出民俗、反映民意方面,体现了“非遗”的重要特点。比如在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及其他艺术。〔3〕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29届会议上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虑到“人类口头”本就属于“非遗”中的内容、形态和形式,便删去了“人类口头”的概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4〕“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式成为官方用语和操作概念,它具体包括以下五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等。
不言而喻,任何文化遗产都是前辈遗留下来的文化“财产”,同时,任何“财产”并非一成不变,会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价值变化”,人类文化遗产也不例外。我们可以藉此追问:人类遗产早已经有之,何以在近五十年陡然“升温”?其实,人类并非在今天才突然从遗产的“老照片”中认清其价值,提高保护遗产的历史“使命感”;与其说当今的“遗产热”是人类认识上的提高,毋宁说是历史在现代语境下的需求(包括商业需求),促使遗产事业的生成。难怪有学者称今天的世界遗产事业为“后现代主义遗产”(post-modernist heritage)中的“产业化生产模式”:一方面,“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商业,这使得在过去曾经出现过、发生过(对遗产的破坏性事件和行为)的社会风气有可能回潮。”〔5〕另一方面,在遗产事业中,人类也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以回顾的目光、保护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文化遗产事业既是“文化的延续”,也是“文化的制造”。
众所周知,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性类型,“非遗”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活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因为它是“活态历史”(living history)的演绎和演义。对于“活态历史”,我们自然也要对其进行符合特殊语境的“灵活解释”(living interpretation),〔6〕以确认和理解其表演和展示性的情境,以及它们与地方、民众和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非遗”与地方文化、乡土民俗结合在一起,呈现了“遗产的差异”(heritage with a difference),〔7〕就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饮食一样。
从遗产的角度看,只要是文化遗产,包括“非遗”,就与特定群体中的亲属关系,特别是继嗣制度存在着密切关系。英文中的遗产(heritage)与继嗣(heritance)同源。具体地说,遗产是根据既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财产和权利,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1.遗留财产。指下辈继承从上辈留下的财产。2.继承原则。指一种经由历史形成的继承方式。比如在父系制社会里,一般形成由父系制血统为线索的男性继承原则。3.责任义务。指继承者在获得继承权的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换言之,遗产就是一种继承关系。同理,“非遗”作为一种活态遗产,也就包含着一种独特的遗产—继承—责任机制。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我国古代称自己的国家为“社稷”,今天称为“乡土中国”,〔8〕都旨在表明“农”的特点。乡土社会是一个与“土地捆绑”的社会,家庭—家族—家园互为一体,其中宗族作为传承纽带成为关键因素。我国村落,特别是汉族村落,最有代表性的模式是以宗族为纽带的延续和传承。具体而言,随着宗族人口数量的扩张,在原乡的土地资源不足以供养的情况下,宗族分支便自然发生。而当一个分支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村落时,开创者就成为“开基祖”,村落大多以宗族姓氏为村名。这既是我国传统村落最有代表性的模式,也是我国“非遗”发生和传承的原生形态。
从人类学的视野看,宗族的繁衍在乡土社会形成了特定的代际关系,即“世系”(lineage)。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传宗接代的重要性往往用宗教和伦理的词汇表达出来。传宗接代用当地的话说就是‘香火’绵续,即不断有人继续祀奉祖先。”〔9〕特定的乡土性“非遗”,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宗族和宗族联盟创造出来和传承下来的,也符合“家”的特定属性:“宗法”。宗法有两个脉向:纵向上(历时)是通过同一宗族脉络传承和扩大,形成了一个以宗族历史为背景的特级制度,〔10〕同时也是“家族”的根本依据,“族这个单位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成员资格是家”;〔11〕横向上(共时)表现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宗族内部和宗族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所建立的联系。所以,在汉族传统村落里都有宗祠。人人都有祖宗,家家都有族谱。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最能够反映乡土社会文化的正是“非遗”。
概而言之,我国正在积极推动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方面是适应全球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国实践以体现“中国特色”。同时,配合乡村振兴战略,用“非遗”这一文化纽带将民众、民意、民情、民风、民俗串连起来。
三、面向乡土:“非遗”之历时
任何遗产都是从过去遗留或传承下来的,但是“非遗”与诸如“文物”“遗址”等不同,它属于保持生命“活力”的遗产。如果遗产是指“过去的历史”或“历史的过去”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情境中的价值体现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对待祖先传下来的还“活着”的遗产,既是考验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考察我们在“传统的发明”〔12〕方面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非遗”除了具有“活态”特性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地方性”特点。严格地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类遗产可以不依托地方而存在,只是“非遗”的地方性特点更加凸显。我国的长城也是文化遗产,也有“坐落”于某个特定地方的特性,但全世界人民并不会刻意地去强调长城的地方性,而是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标志。“非遗”则不同。我们以“南音”为例。“南音”属于闽南(福建南部操闽南语方言)特殊的地缘文化。虽然“南音”在历史的形成中也融合了大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比如古代的宫廷乐种)却并不突出。南音使用的工尺谱也有别于其他中国戏曲音乐的工尺谱。此外,南音中不仅包含了北方丝绸之路交流所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迹与痕迹(比如“横抱琵琶”),还有从我国西南地区传过去的文化因子,泉州南音所供奉的“始祖”孟昶即为后蜀国君。南音历史性地汇聚了不同历史、不同区域多元文化的因子,最终在晋江流域,特别是在泉州形成雏形,后又通过泉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传播到世界各地。2006年,南音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由是可知,“非遗”具有三大特点:历史—地方—活态。所以,我们今天将保护传统文化与地方性特色联系在一起,聚合于“非遗”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性质而言,“地方”是一个公认的被赋予文化意义的特定空间。然而,“地方”并不仅仅是简单为某一群体提供地理上的栖居空间,其具有文化特征,也构成与其他地方社会发生互动的完整形态。因此,对“地方”的理解不能只注意地方民众当下的生活形态,还必须将其与历史性地缘结合在一起。特别在今天,地方与地缘性认同已经成为全球化解释的根据。〔13〕可以这么说,地方是文化生成的土壤,是文化展演的舞台,也是文化存续的依据,没有地方文化,“非遗”就失去了生成的土壤。而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文化不是别的,正是乡土文化。
接下来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非遗”之地方性特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诚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表述的,地方是乡土社会的基层单位,是“面对面的社群”,是“生于斯死于斯”之所,是民众的生存之本和“人性之神”。〔14〕这些特点都映射到乡土文化汇聚的“非遗”之中,成为特定人群共同体的特殊情感:是那些“我们可以看得见”(we can see)的依据,是“土地之上”(above the soil)的文化和历史景观。人们通过“看得见”(visible)的遗产与“看不见”(invisible)的情感联接起牢固的关系纽带。〔15〕因此,尊重“非遗”中乡土社会的主体价值也就成了遗产战略的根本。然而,由于我国传统的政治地理观决定了“家国天下/一点四方”的独特体制,国家与地方的“二元关系”在权力格局中有时会产生历史性的失衡,因此,凸显乡土社会的“非遗”也是一种新的价值平衡。特别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如何将两种权力——费先生所总结的“同意权力/横暴权力”(民间权力与官方权力)〔16〕平衡好也是考验我们对待“非遗”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逻辑性地,通过保护“非遗”来体现地方遗产保护的力度具有两个方面的认知价值:首先,任何遗产都有其“地方性”,它指遗产发生和传承的具体地理空间和文化场域。地方民众会将这些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非其他人的“财产”。主观上他们不仅为之感到骄傲,客观上他们也会通过某一个遗产确定地方人群共同体的“文化指纹”。其次,文化遗产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今天,都存在一种“再地化”(re-localization)现象。这很正常,那种将特定的文化遗产“固然化”的认识是偏颇的。文化的“再地化”一方面反映在历史的演进中其内容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客观性);另一方面,遗产的地方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需要被重新解释和认识(主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赋予“非遗”特殊的价值,也是一种新的“再地化”现象。
就文化遗产的归属性而言,“地方性”和“非遗”是相互表征的。与“故乡”一样,“地方性”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地理上的、认知上的、情感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相应的空间性,空间性包含了四层意思:第一层是依据人的居住形态所形成的空间;第二层是根据我们的意向、我们关注的中心对象形成的观察空间,它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的;第三层是由文化结构和我们的观念而形成的存在空间,这是一个充满社会意义的空间;第四层是认知空间,即我们如何抽象地构筑空间关系的模式。〔17〕也就是,“非遗”所依存的地方性空间包含着地理的空间性、历史的客观性、文化的认同性和认知的主观性。
当文化遗产与地方建立起历史的关系纽带时,一种历史的责任形制便呈现出来: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对某一个地方进行文化保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它涉及五个相互依存的不同层次:1.历史记忆。地方性“非遗”都是特定的地方群体从他们的先辈那儿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具有强烈的历史记忆因素。2.文化认同。文化遗产事实上属于一种价值认同。认同具有两种根本的品质诉求:原属性和选择性。具体地说,遗产被特定群体所选择,在遗产中也必然包含着体现其根源、根本的原属性品质;同时,遗产在不同语境中被作为“工具”加以突出和强调,以换取那个情境中的利益。3.发展变迁。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特定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遗”都一直发生着变迁,既包括来自特定文化形态的内部变化的动力,也包括来自外部影响的力量。4.政策导向。我国当下的“非遗”事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所以政策导向也像晴雨计一样。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所看到的文化遗产之所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某种意义上说也粘贴着这一历史时段深深的政治印记。5.方式方法。遗产不仅具有形态上的特殊性,还具有物质构造上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一方面源自创造“产品”(比如某种手工艺)时的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也包含在后来继承者所使用的保持性方法和手段中。而这一切都不能与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相分离。因此我们要格外强调的是,从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的角度看待文化遗产以及遗产资源,需要对地方知识和系统有深入的了解,这不仅对遗产的保护至关重要,而且对遗产的规划、管理及其适用性和适度性都不可缺少。〔18〕
概而言之,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乡土社会成了基本和基础的社会结构。作为呈现、表述乡土社会文化的形式、形态,“非遗”也就成了标志、标识。因此,要认识乡土社会的历史,地方性“非遗”既是一个入口,也是一个路径。
四、面向品牌:“非遗”之未来
“非遗”可以成为“品牌”或“招牌”,而二者当中,我们更希望能够发挥主动性、自觉性、创造性将特定的“非遗”设计成为一个“品牌”,通过当今“品牌时代”将传统的地方性文化遗产宣传出去、传承下去,而不仅仅只是为了个体、团体利益和短时段需求打出“招牌”。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品牌强国”系列节目正是试图突出“品牌价值”,强调在今天这个“品牌时代”如何通过“品牌力量”来推动国家的发展。那么,“非遗”能否成为一种新型的品牌,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呢?窃以为,可以。其中的逻辑关系很清晰:既然“遗产”指先辈传承下来的“财产”,说明其有价值;既然有“价值”,就可以和可能“增值”。不讳言,今天我们不少地方都通过“非遗品牌”去做资产增值的事情。
毫无疑义,我国传统的活态性“非遗”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无形资产、无形品牌。比如四川的“非遗”——“变脸”。变脸是川剧表演艺术中的一种特技,虽然川剧变脸属于国家机密,但并不妨碍其“非遗”的品牌价值。只是我们今天总体上还未达到自觉地将“非遗”作为品牌进行创新设计,也没有形成合力(政府、地方、产业)。这正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工作,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什么类型的“非遗”可以改造、创新成为品牌,从而既能对其保护和传承,又能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发挥推动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进行深入的调研、专业的评估、创新的设计和协力的推动。
当今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被形象地表述为“地球村”。全球化的社会属性是移动性(mobility),而大众旅游即是移动社会的典型表征:一方面全球化移动性表现为“人的移动”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大众旅游也带动了社会的全方位移动和变化,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19〕其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全景式移动”,包括以下五种移动图景:族群的图景(ethnoscape),技术的图景(technoscape),财金的图景(finanscape),观念的图景(ideoscape)和媒体的图景(mediascape)。〔20〕这一全景式的移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我国当代的旅游现象堪称全球最为活跃的全景式移动现象。
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表现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安居乐业是传统价值,“父母在,不远游”成了乡土社会的生活景象,也是农业伦理之“人与土地的捆绑”关系的直观体现。因此,今天的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的挑战,同时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应对方式。随着大量游客的到来,传统的“非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再生产”效应。笔者认为,与其被动地应对大量游客到来造成对传统“非遗”的侵蚀,不如自觉地、主动地将传统的“非遗”品牌化,既自信地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又智慧地将这些“活态遗产”转化为旅游品牌。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首要任务是保证那些“非遗”创造和传承主体的权利和权力。
人类遗产与现代旅游活动从根本上说无法分开。换言之,文化遗产,特别是“非遗”已经成为当今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人类重要的遗产景观和景点都成为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和媒介,也导致各类遗产的“再表述”(re-presentation)现象。〔21〕这很正常,传统的“非遗”是地方民众自己创造出来和传承下来的,以往与其他群体几乎不发生关系。然而,大众旅游的到来,促使、迫使“非遗”从原来面对相对单一的群体变为面对四面八方的外来游客。旅游作为一种消费会制造和强化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倾向。在当今的旅游活动中,各类遗产已经成为一个无形的品牌,成为游客进行“旅游攻略”的重要内容。遗产因此也增加了全新的展示内容,形成了现代社会再生产的“旧遗产—新品牌”。杰米森将这种“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归纳为:“旅行活动涉及诸如视觉和表演艺术,遗产的建造,以及区域、景观、特殊的生活方式、价值、传统和事件等”更大范围和更新范畴。〔22〕
“非遗”作为创新性品牌在“遗产旅游”活动中具有重要价值,但在游客对传统“非遗”的分享过程中也存在着使遗产价值产生区隔和分裂的因素,毕竟游客与东道主对遗产及其实践价值的认知存在着差异。对游客而言,到遗产地旅游是“客位性”的,而东道主则属于“主位性”的。所以,在“非遗”品牌的建构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游客与东道主的“客位—主位”互动关系。具体地说,我们既要将传统的“非遗本色”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又要考虑到四面八方游客的欣赏、参与、品味等实际需求。对于游客来说,到某一个遗产地旅游属于“观光”“体验”活动,而对于家园遗产的地方民众来说,“非遗”成为他们的“展示”和“再创造”活动。比如,近期在贵州兴起的“村BA”,既将民族村寨的文化特色呈现出来,又让它超越某一个具体的村落而成为一个游客与东道主共同参与的活动。某种意义上说,缘起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的“村BA”就具有“非遗”品牌的价值和特点。
现代社会的再生产需求提高了“非遗”的消费性。世界著名旅游人类学家格拉本教授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撰写了一本名为《学会消费:什么是遗产与何时成为传统?》的著作。〔23〕“消费”与其说是行为,还不如说是观念性认知。他归纳出遗产的三种类型:(1)人们继承的由祖上传下来的祖产;(2)由特殊的身份认同所获得和赢得的财产;(3)通过交换或者其他形式得到,并被特定人群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三种类型的遗产都与亲属关系、姻亲关系的基本类型相联系,具有明确的情感纽带,不可任意消费。〔24〕但在我国当代大众旅游中,就发生过一些由于对特殊遗产的“过度消费”而伤害东道主情感的事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利益驱使所致。
今天,在旅游目的地(对游客而言)和具体“家园”地方空间(对东道主而言)的关系中,“非遗”经常扮演着一个“文化导游”的角色。比如泼水节是傣族的特殊节日,泼水节的寓意是将水作为美好的祝福送给对方,一个人被泼的水越多,得到的祝福也就越多。西双版纳傣族园就专门为游客设计了“天天泼水节”,今天甚至已经演变到了这样的情形:到西双版纳旅游,不去体验泼水节,那旅游就有“不完整感”。泼水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云南傣族文化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
概而言之,当今已是全球性“遗产事业”与“旅游产业”并置的时代,“非遗”作为品牌、成为品牌也已成为一种趋势,无论是保护遗产的方面,还是旅游消费方面,都是如此。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遗品牌”的打造任务。
五、结 语
2024年龙年伊始,从相关部门的信息、数据来看,文化体验已成为人们旅游活动中的重头戏。其中又以两种文化类型为主要代表:传统的古典、经典文化和地方乡土性“非遗”活动。体验“非遗”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展现民俗、民情、民风、民意的体验式、沉浸式、参与式旅游,无论是观赏舞龙舞狮、逛庙会、体验地方文化,还是感受地方风俗、品尝地方饮食,皆属“非遗”范畴。
今天,将某一个文化遗产(包括“非遗”)打造为品牌、名片的模式已成为世界范式。以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Cote d’Azur)地区的城镇为例:戛纳(Cannes)国际电影节、尼斯国际狂欢节(Carnaval de Nice)、芒通(Menton)柠檬节(Fête du citron)、摩纳哥(Monaco)国际马戏节、普罗旺斯(Provence)薰衣草活动等都是依托当地文化遗产而闻名世界。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非遗”的期待和需求也在增大。如何将“非遗”作为一个品牌来保护(面对当下)、来传承(面对过去)、来推动(面对未来)是我国“非遗”工程新的任务,将“非遗”打造成一张地方名片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