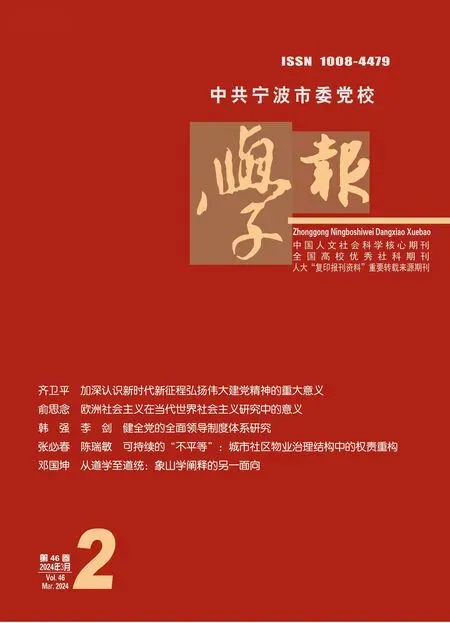从道学至道统:象山学阐释的另一面向
邓国坤
从道学至道统:象山学阐释的另一面向
邓国坤
(贵州大学 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象山学曾被阐释为道学、心学与禅学等。在明代中期之后,象山多被称为心学;但在明代中期之前,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与禅学。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认同和拥护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而是承认了道学称谓,且多次谈及道学、理学与道统。在象山后学的努力下,宋代官方承认象山学的“道学”与“道统”名位。在会同朱陆的主调下,元代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肯定象山学的道统地位,刘埙、刘仁本等甚至称其为集孔孟之学之大成的“道学之宗”。明代前期进一步会同朱陆,许多学者认为象山学是“圣贤之学”“圣学正传”。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名位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其兼具“心学”身份,象山学成为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
陆九渊;道学;理学;心学;道统
象山学被普遍地称为“心学”,是明代中期之后的事情。在南宋至明代前期,象山学的阐释主要有心学、理学与禅学三种。三者之中,心学阐释属于少数派①,因为在明代中期以前的阐释中,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理学、禅学。象山学被称为禅学的历史已经有所研究[1],但是象山学被称为道学的历史却较少被关注,所以具有继续研究的空间与价值。陆九渊承认了道学的称谓,却从没有自称心学;象山学拥护者积极争取“道学”之名,并且将其列入“道统”序列;最终陆九渊以道学名位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2]。
重视心学阐释而忽视道学阐释,实在是象山学阐释研究的莫大缺失,更是对象山学史的巨大遮蔽。如能真实地还原这一段历史,则对我们全面梳理象山学史,重新考察象山学的学术性质有巨大的帮助。此外,象山学的道学阐释研究有助于解决某些学术争议:例如象山学是“心学”还是“道学”,朱、陆、王三者关系等问题。因此,学界不妨暂且悬搁象山学的心学阐释定性,以开放、客观、包容的心态来探讨象山学的阐释问题,并且实事求是地呈现象山学的道学阐释。
一、以道学阐释象山学
道学是一个所指较广的概念,或是一种学问②,或是一种治学工夫③,是一种宗派或团体④,或是一种道统⑤。不同的学者使用它时,可能意指某一类内涵,或者使用其多类内涵。但在宋明时期,道学(或理学)乃是儒家正统之代名词,也是宋明儒者学说的荣誉称号。例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等都被普遍地称作道学。更为重要的是,道学或理学乃是为位列道统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宋明时期,大多儒者都会重视道学的使用,为自己或他人争取“道学”之名,进而最终得以位列“道统”。在宋元时期,程朱之学逐渐被视为道学,程朱本人也被视为道统传人。象山学派与道学、道统有所关联,却未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在宋元时期,象山学被称为心学,诸如“本心之学”“传心之学”等,但是这些阐释仍属少数派。事实上,程朱之学在宋元时期更多地被称为心学[3]。与此同时,以朱子学派为主的学者称呼象山学为禅学。心学与禅学的阐释几乎伴随了象山学的八百多年历史。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道学阐释一直被用于称呼象山学,这种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拥护和支持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
在现有文献中,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也没有提出“心学”一词,而是承认了“道学”的名号,且多次提及道学与理学。在《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中,陆象山引用他人之口,提出了其兄陆九龄思想学术的“道学”名号,“其与先生启有云:‘文辞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风,道学造微,得子思孟轲之旨’,推尊盖如此”[4]313。在《象山语录》中,象山与李伯敏谈如何为“道学”,“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此风一长,岂不可惧?”[4]437在《与朱元晦》中,象山与朱子谈论主张道学的考官,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近者省场检防试卷官,以主张道学,其去取与蒋正言违异。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计,但风旨如此,而隐忧者少,重为朝廷惜耳”[4]94。
除了“道学”以外,陆九渊曾提及与推崇“理学”,因为道学与理学是异名同义。陆象山提出:“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4]14陆九渊高度颂扬宋朝的理学,并认为其能够接续道统,可见陆九渊是非常认可“理学”这一用法的。相比之下,道学与理学常被象山所使用,而心学则是陆九渊所未曾提及的话语。
更值得重视的是,象山曾以道学家的身份回应对道学的攻击,并且认为自身的道学无可攻击。陆九渊分析了社会上攻击程朱道学的话语,例如“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与之为敌,哓哓滕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4]440—441。此是陆九渊对于一般道学“有名无实”的指责。而对于自身的“道学”称谓,陆九渊提出“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道学如陆某,无可攻者。’又如学中诸公,义均骨肉,盖某初无胜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个敬信处”[4]440—441。陆九渊引用他人评价其为“道学”之话语,且似有自得之色。因为他颇为自豪地引用了攻击“道学”最为猛烈的程士南的话语“道学如陆某,无可攻者”,此语乃是陆九渊默认“道学”称谓的最佳例证。通过象山抨击他人道学,以及对自身道学的自得分析,象山应当认同道学称谓,并且具有自身的道学标准。
与道学相关,象山也关注“道”与“道统”,因为“道”乃是道学的核心内涵,“道统”乃是道学的外延。关于道统,象山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态度。在当时,程朱之学基本被奉为道学之楷模和典型,但陆象山对程朱的学问也有所评论。对朱子之学,象山首先是肯定的,如赞扬朱子清理诏狱,建立社仓,并且与朱子谋求得君行道,共举义利之辨。在学问上,朱陆虽然有多次争辩,但两者并非无相同之处,例如两者都承认太极是万化根本,都拥护道学和理学,甚至象山与朱子的工夫之争曾有一度缓和与认可,如“观省加细,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4]306。对程朱在道统的地位,陆象山也是有所赞扬的,例如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之专,践行之笃”[4]13,“朱元晦泰山乔岳”[4]414。陆象山认为程朱等人的研究、讲授、实践道都达到了汉唐所没有的新高度,因此说“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4]436。陆九渊对理、道的论述,远多于对心的论述,然而在心学阐释史的掩盖下,陆九渊关于道、理的话语逐渐被关于心的话语所遮蔽。
由于象山自身学问的关系,象山对于程朱之学及其道统地位有些微词。象山认为,程朱虽传续孔孟,却未能达到曾子、子思、孟子的高度,“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4]436对朱子也有批评,“踹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4]27,甚至公开宣称朱元晦“见道不明”[4]419,“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4]414。如此一来,陆氏的批评立马就引发了巨大争议,自然也引起朱熹弟子的强烈不满,此举甚至引起了朱陆两派后学关于“道统”的讨论。
当朱子后学在强调朱子为道统正宗的同时,象山后学也在推崇象山的道学名位。陆九渊去世以后,象山后学以“道学”与“理学”称呼象山之学,实质上是为了让象山位列“道统”。例如袁燮在《题彭君筑象山室》提出,“义理之学,乾道、淳熙间讲切尤精,一时硕学,为后宗师者,班班可睹矣!而切近端的,平正明白,惟象山先生为然”[5]卷八。陈来先生指出,南宋时所谓“义理之学”也指理学[6]8。而袁燮指出义理之学在乾道、淳熙年间出了许多大师,而“切近端的平正明白”的唯有象山。言下之意,陆九渊之学不但是理学,而且是其中相当出色的一种。更重要的是,袁燮强调陆九渊为孟子后一人,远超程朱等人,此似乎暗示陆九渊越过程朱等人接续孔孟之道统。
在象山后学的努力下,宋代官方开始承认象山学的儒学地位,也以“理学”称之。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炜在嘉定十年(1217年)奉旨撰《议谥》,承认了陆子继承孟子之学,“自轲既末,逮今千有五百余年。学者询口耳之末,昧性之天真,凡轲之所以诏来世者卒负于空言。有能尊信其者,修明其学,反求诸己,私淑诸人,如监丞陆公者,其能自拔于流俗,而有功于名教者与?”然后直接称呼其学为“理学”,“公生而颖悟,器识绝人,与季兄复斋讲贯‘理学’,号江西二陆。”[4]385—386此乃官方承认象山学的“理学”(道学)地位的标志。
元代在调和朱、陆的主调下,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大多推崇象山学,肯定其儒学地位。刘埙与陈苑、赵偕等皆是元代象山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崇尚象山学,并认为陆九渊承接“道统”。刘埙认为陆九渊乃是孔孟道统之集大成者,“自尧舜而累传而达孔孟,自孟氏失传而俟夫宋儒,故有周程二张濡其原,而周则成始也;有朱张吕陆承其流,而陆则成终者也。脉理贯通,心境融辙,殆天地重开而河洛复泗也,道之统绪,撂见是矣”[7]361。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埙的道统话语中,陆九渊乃是宋儒发展之终极人物,也是集孔孟之学之大成者。所以,象山的地位似乎比程朱等人更为重要,此话语可谓对象山学道统地位的进一步构建。刘仁本甚至称象山为“道学之宗”,他赋诗曰:“春满花香竹影间,慈湖水长绿潺湲。庙廷独祀杨夫子,道学还宗陆象山”[8]卷六。以象山为道学之宗主,乃是对象山道学的正统性乃至宗主性的认可,这自然是推举象山学的又一高扬之作。相比宋朝,象山学在元代儒者的地位要尊崇一些,因为元代儒者不但以道学称呼象山,而且开始重视象山学在道统上的地位。
在宋元时期,象山学被称为“道学”与“理学”,甚至被列入道统之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虽然陆九渊被称为道学与理学的次数不如程朱之学多,但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因为这起码表明,道学阐释是宋元时期象山学阐释的一个重要观点。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学界中,均有部分学者对象山学的道学阐释与道统地位做出一定程度的肯定。尤其是元朝,由于会同朱陆的缘故,朱陆后学以调和朱陆为主,称呼象山学为异端邪说的话语较少出现,反而使象山学的道学地位得到较大的提升。
二、由道学而道统
明代初期延续了元人的学风,进一步会同朱陆。究其原因,明代陆氏学脉并未中断,明初浙东传杨简之学者甚众,诸如桂彦良、乌春风、向朴、刘安、颜鲸等人,均为杨简之世嫡[9]。据文献记载,“今江东西间,往往不乏其人。世虽欲舎之,而终不能使之不传者”[10]卷五。换而言之,明代初期江西一带仍旧有尊崇象山学者生生不息。此外,程朱之学虽为官学,但也存在支离僵化等问题,因此,官方对其并非毫无责难。例如朱元璋与儒臣讲说《论语》一书时,不时对朱熹所作的《集注》提出怀疑、排击、发难,甚至称朱熹为“宋家迂阔老儒”,在科举范本中也尚未全部采用宋儒之说,更遑论朱子之说[11]。
明代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另辟蹊径,试图探求与融合别的思想资源,例如象山学。明代前期关于调和朱陆的话语很多,可以分作多种类型。其一是,承认朱陆有所不同,却都属于儒者范围,所以应该兼顾两者,而不应相互对立。最早如苏伯衡(1329年—1392年)指出:“文公以道问学为主,文安以尊徳性为主。夫道问学、尊徳性二者如之何其可偏废也。”[12]421其二,有些学者认为,朱陆乃是早异晚同。如程敏政认为朱陆兼有“道问学”与“尊德性”,乃早异晚同,两者同尊德性,也同道问学[13]733。其三,有些学者只论朱陆之同,力消朱陆之异,或者是大同小异。如刘文卿认为朱陆皆归于尊德性一路,后人也应在此处会同朱陆[14]卷二百二十一。此外,有些学者指出朱陆异同之论,主要是因为后学之原因。如张宇初(1359年—1410年)指出,朱陆之辨乃是后人遵循旧习、求奇之过[15]448。
在会同朱陆的学风下,象山学的道学地位越加提升,逐渐受到朝野的推崇,这导致象山学与程朱之学等明代正统思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明初官方修书如《五经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书》编有《象山陆氏九渊》,此外朝廷一直在修缮陆九渊的祭祠与书院。而在民间,象山著作大量、多次刊行。明代中期刊行了多种版本,“最早版本为陆时寿刊本,后有陆和刊本、李茂元刊本、荆门本、金溪本、何迁本等十种版本以上”[16]。当时甚至出现了一股“右象山,表慈湖”的浪潮[17]卷二十二。例如在正德末年,湛若水在西樵山读书时,“闻海内士夫,群然崇尚象山”[18]卷七。又如明代开国功臣、文臣之首宋濓较为推崇象山,他在《金溪孔子庙学碑》中指出,象山学博大圆融,光辉明亮,照耀后世[19]卷十六,且能够昌明为学界所忽视的“心”,与入其门者共同践行大道[17]卷二十八。
鉴于象山学在明代前期的声望与影响,象山学被公认“道学”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时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有称呼象山学为道学的话语,例如明初著名学者解缙(1369年—1415年)认为陆九渊乃是江西道学之首,“江西道学之士,自陆夫子务以力行为先”[20]卷七。在陆九渊的影响下,江西学者以雕琢词章为耻辱,“思如文安公之道学修明”[18]卷七。值得注意的是,解缙的“道学”内涵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与儒家经典精义相联。因为解缙对道学的定义极为严格,如“六经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为道学之本也。”[18]卷九大力推举象山学为道学者,还有吴宽(1435年—1504年)等人。吴宽在《题朱、陆二先生遗墨后》提出:“朱、陆二先生道学之妙,皆杰出于百世之下者也”[21]卷五十三。王廷相(1474—1544年)在《浚川集》提出:“宋晦庵朱子、象山陆子皆以道学倡鸣于时”[22]卷三十,进而指出朱陆先异而后同,皆是圣人之学。又如郑岳(1468年—1539年)称“其(艾轩)与朱、吕,陆象山,俱以道学倡东南”[23]卷十三。从上述明代著名学者以道学称呼象山学的话语中,可知象山学的道学名位已经得到了明代学人的较大认同。
伴随着道学阐释说的流行,象山学在儒家道统的名位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与加强。许多明代前期的学人都曾论及陆九渊与道统的关系,如宋濓认为象山学能够得到圣人的真传,“远探圣髓”[17]别集卷二。又如归有光认为,象山学乃是“圣贤之学”,乃是得道之学,遥契亚圣孟子[24]别集卷二,并且强调象山学之“全体大用”,皆“不谬于圣人”[22]别集卷二。又如何乔新(1427年—1502年)直接将陆象山作为圣人之学之传人,与周程张朱等一并列入“道统”[25]卷二。薛应旂(1500年—1575年)称呼象山学为“圣学正传”[26]卷十三。胡直(1517年—1585年)将象山与明道并称,认为他们“得尧舜孔子以来之学脉”,他甚至公开宣称,除了孟子,能够发扬昌明孔子学问的学者只有程灏与陆九渊[27]卷二十。以“圣学正传”称呼陆象山,其实就是以“道学”称呼陆象山,因为在明人看来,所谓“圣学”其实就是“道学”。但在某些时候,圣学也可指“心学”[28],因为两者一物二名,其实就是指包括尧、舜、禹、孔、孟等圣贤的学问。
在上述话语中,不难看出象山学在明代学人中地位较为崇高,并被列入道统序列。然而,呼声最为强烈的当属柯维骐(1497年—1574年)。在《答吴克复论宋史柬》中,他赞成吴克复认为陆象山该进入“道学传”,“吕东莱、林艾轩、真西山、胡文定、陆象山宜入道学,不可与孙复、杨万里、陈傅良、范冲、朱震、郑夹漈同列”[13]卷一百七十四。此是明人为陆九渊抱不平的翻案文章代表。《宋史》之“道学传”乃是道统的象征,主要记载周、张、程、朱一脉,而主张陆九渊进入“道学传”的话语表明,象山学进入道统已经得到多数人赞成,此实乃象山学地位的再一次提升。
象山学在明代中期以前的阐释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因为其将对今人理解象山学有新的启发。象山学在明代为学人所肯定与推崇,乃是其道学阐释以及道统地位的确立,而非由阳明学派所推举的“心学”方才出现。象山学在明代中期以前被列入道统,要远远早于王阳明、牟宗三等人的道统说,其含义也与牟宗三等人的心学道统说不太一致。在明代道统上,象山学可与程朱之学并立,而无牟氏正统与别传之分,这可谓重探朱陆关系之新材料与依据,足为今人所重视。
三、由道统而从祀孔庙
上文已述,明代已有象山进“道学传”的呼声,然而历史已经不能改写,陆九渊没能进入“道学传”。明代能够给予象山的官方最高荣誉是“从祀孔庙”,因为礼仪乃是“国家对社会价值的认定和肯定程度的有意识表示”[29],更重要的是,“孔庙是道统的形式化”[30]109。当某人能够从祀孔庙,一般意味着某人之学乃属于孔孟宗派,能够接续儒家道统,而且在当时有强大的思想或政治功绩。在明代,上述情况就是从祀孔庙的核心标准。当陆九渊已经被明人称为“道学”,以及位列“道统”,因此获得“从祀孔庙”乃是合乎情理的。
当然,从祀孔庙不仅仅是一件思想事件,更是一件政治事件,因为它关乎国家的思想、教化,乃至礼仪名分。因此,陆九渊从祀孔庙乃是多方角逐与考量的结果,其最终成功也自然包含多种原因。除了学术因素之外,例如明代前期会同朱陆风气的盛行,政治因素也不可忽视。例如大礼仪事件中,推崇象山学的阳明学者备受重用,以及明代前期江西士大夫担任要职者甚多等等,这些政治因素都有助于陆九渊从祀孔庙[2]。
在明代中期,程朱理学仍然被奉为思想正统。因此在从祀孔庙上,明代与宋元时期一样,以“道学”(理学)作为从祀孔庙的基本条件与参考标准。就算是被今人视为“心学”的王阳明也是以“道学”的名义从祀。如明神宗曰:“皇祖世宗尝称王守仁有用道学,并陈献章、胡居仁俱祀孔庙”[31]。作为明代最高统治者,代表明代官方意识形态,其认定王阳明的从祀标准乃是“道学”,此极具代表意义。当然,由于道学与理学名异实同,明代从祀标准也可称为理学。如方大镇提出:“先帝尊崇理学,以尚书薛瑄从祀孔庙。我皇上复采廷臣议,以新建伯王守仁、捡讨陈献章、布衣胡居仁三人并从。夫理学者,国之所宝也”[32]卷三十六。明代如薛瑄、陈白沙,皆因“理学”从祀。如唐顺之《故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奏议》曰:“然自瑄以前,儒者犹汩于辞章事功之习,而未有能卓然于道德性命之归者也。而瑄实倡之矣。……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传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实倡之矣。是则瑄其我朝理学之一辟也”[33]文集卷一。从上述话语可见,“道学”或“理学”乃是明代从祀孔庙的必要条件。而根据陆九渊在明代的阐释史,陆九渊能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身份得到了朝野的广泛认同。
在薛侃《正祀典以敦化理疏》中,与陆九渊一同申请从祀孔庙的陈白沙就是根据“理学”的名位[34]164—169。其中,薛侃首先点明了“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宗中才之主,亦惟始终崇尚濂洛之学,遂得庙号曰理”[34]164—169。同时,他在此文为陈白沙请求从祀孔庙的时候,也是用“理学”的名义,“当代文行、名节、忠勤之士固多,而潜心理学者数人而已。然究其所造,又皆未免以人性为仁义,其于所谓‘一以贯之’之旨则时有出入,而未或有自得也。惟翰林院检讨陈献章博而能约,不离人伦日用,而有鸢飞鱼跃之机,虽无著述,观其答人论学数书,已启圣学之扃钥矣”[34]164—169。虽然,陈白沙在此次从祀中未能被准予,然而其“理学”色彩已经为人所重视。
明代中期乃是理学向心学过渡的时期,而陆九渊从祀孔庙则可谓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陆九渊以“道学”或“理学”之地位从祀孔庙,同时又开创了“心学”从祀的先河。因为阳明学派的薛侃在《正祀典以敦化理疏》称呼象山学为心学,“自孟子没而心学晦,至宋周敦颐、程灏追寻其绪,九渊继之,心学复明。故所至,从游云集,惟乡曲老长,俯首听诲,当时吕祖谦、张栻莫不敬服”[34]164—169。因此,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乃是集“道学”“理学”与“心学”一身的人物。在明代,象山思想学术色彩是复杂多样的,承担了明代学术转向的重要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心学”在明代中期乃是涵义复杂的概念,可以指向程朱之学,也可指向阳明学、象山学等,乃至其他思想学术。以心学专指陆王之学乃是明末以后的事情[35],在明代中期心学仍是儒学的公共话语和阐释称谓。在明代前期,“心学”与“理学”乃是一理殊名而已,如杨升庵提出,“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已”[36]卷七十五。又如张东提出,“心学与理学,体用相须,初非贰致”[37]卷五。因此心学也多指程朱之学,如程敏政曰“心学所渐,悉本伊洛”[12]522。明代前期之“心学”与“道学”(理学),两者一物二名,并非对立之概念,共同指向整个儒家思想正统,此在日本学者荒木见悟的论著中已有所阐述[26]。
道学与心学的这一层关系非常值得今人注意,也是重新认识象山学的关键话语。因为这些话语表明,道学与心学均可涵盖于象山学,皆被用以称呼象山学。例如薛侃称呼白沙学为理学,称呼象山学为心学,应非偶然为之。盖因明代中期,心学与理学、道学乃是一物异名,因此薛侃的上疏中既用理学也用心学,而毫无违和,当时的朝廷和士大夫也同意了薛侃的请求。
阳明学派以“心学”称呼象山学或许存在多重原因。一是,阳明学派延续明代重视“心”的思想潮流,以及象山学自身带有的“心”之色彩。因此阳明学派主张之“象山心学”不过是彰显与重构了象山学中的某一思想而已。二是,阳明推崇象山学为“心学”,同时阳明学派也以“心学”自居。阳明学派此举应当是要将“心学”列入明代思想正统之中,并且要掌握心学的解释权与话语权,最终将“儒家心学”转化为“陆王心学”或“阳明心学”。因为心学在明代已经流行,但主要称呼程朱之学的称谓,并非陆王心学的专称。然而要完成上述目的,必须借助象山学的道学称谓和道统地位。如果象山学没有道学称谓与道统地位,绝不可能在道学向心学转化时发挥如此重要之作用,因此,象山学乃是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
由于上述原因,象山学是程朱后学与阳明学派均予以推崇和抢夺的思想资源,因此受到明代朝野的共同推崇。当陆九渊从祀孔庙后,象山学在明代中期达到了道学称谓的最高峰。如陈明水所言,象山已经与周、程并列。他在《答乐必弘》提出:“象山之道,近已少明,圣天子从祀之文庙,则固与周程并矣......象山(书)院额,晦翁手笔也。互相尊信,亦与晦翁无嫌”[38]卷一。从祀之后,象山学的地位是非常巩固的。中明霍韬欲罢黜陆九渊,却受到皇帝的否决与呵斥,如“霍韬又欲黜司马光、陆九渊、吕怀,欲将道统正传皆进之庙堂,系于四配下。至是,礼部集议以请。上曰:‘司马光、陆九渊从享与四配等位次,俱历代秩祀。又经我太祖钦定,俱照旧,不许妄议”[39]卷八十五。晚明唐伯元因反对王守仁及陆九渊的从祀孔庙,因而被贬,如“疏末又欲斥两庑之陆九渊,而进宋之周、张、朱、二程于十哲之末。则举朝皆骇怪。九渊为世宗所褒,与欧阳修并祀,安得擅议废退?其仅得薄谴者幸耳”[40]卷十四。从上可见,虽然有某些士大夫请求罢黜陆九渊的从祀地位,却无不以失败告终,且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驳斥与处罚,可见陆九渊道学与道统地位之巩固。
四、结论
在南宋至明代前期,象山学被阐释为道学、心学与禅学。但在南宋至明代前期,心学阐释属于少数派,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理学、禅学。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认同和拥护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而是承认了道学的名号,而且多次谈及道学、理学与道统。在象山后学努力下,宋代官方承认象山学的理学与道统名位。在调和朱、陆的主调下,元代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肯定象山学的道统地位,刘埙、刘仁本等认为陆九渊乃是孔孟道统之集大成者,甚至是“道学之宗”。明代前期进一步会同朱陆,受到朝野的推崇。许多学者认为象山学“远探圣髓”,是“圣贤之学”“圣学正传”。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身份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其“心学”身份,成为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
历史上的象山学阐释是多元且演变的,心学阐释不应遮蔽其道学阐释,实事求是地还原象山学的道学阐释历程,有助于学界更好地理解象山学的本来面目,也可为梳理象山学述提供坚实的基础。通过对象山学的道学阐释史考察,可以得出以下重要信息:象山学与朱子学曾被同称道学,一同位列道统;心学在明末之前并非专指陆王之学,而指向朱、陆之学;在阳明学之前,象山学本与朱子学亲近,后来却与阳明学并称;象山学乃是明代道学向心学演变的关键学术。以上信息对当下重新梳理朱、陆、王三者关系,乃至重构宋明理学史均有重要借鉴意义,也是当下继续推进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① 详见周炽成《陆九渊之冤:陆学在宋代非心学》,广东社会科学,2014(5);邓国坤、周炽成《陆九渊学说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15(2)。
② 参见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社会科学战线,1982(3)。
③ 参见《大学》之“如切如磋,道学也”。
④ 参见《宋史·道学传》,专指某一类型的学者,与普通儒者概念不同。
⑤ 参见邵海根《性道、道统与政统——“道学”的三重维度》,湖北社会科学,2021(10)。
[1] 邓国坤, 戴黍. 禅与非禅: 象山学争议考[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3).
[2] 邓国坤. 陆九渊从祀孔庙之因果考证——兼陆王关系新探[J]. 学术探索, 2018(11).
[3] 冯国栋. 道统、功夫与学派之间——“心学”义再研[J]. 哲学研究, 2013(7).
[4]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 袁燮. 絜斋集·卷八,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
[6] 陈来. 宋明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7] 刘埙. 水云村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1195册, 2014.
[8] 刘仁本. 羽庭集·卷六, 清乾隆翰林院钞本.
[9] 陈宝良. 明初“心学”钩沉[J]. 明史研究, 2007年, 第10辑.
[10] 胡翰. 胡仲子集. 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4册)[M]. 沈乃文主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13.
[11] 陈奇. 明朝前期的陆学潜流[J]. 毕节师专学报, 1994(1).
[12] 苏伯衡. 苏平仲文集, 永康胡氏退补斋刻民国间补刻金华丛书本.
[13] 程敏政. 篁墩文集, 明正德二年刻本何歆程刻本.
[14] 黄宗羲. 明文海, 清涵芬楼刻本.
[15] 张宇初. 岘泉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1236册, 2014.
[16] 邓国坤. 历代《象山先生全集》版本演变考论[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17] 孙奇逢辑. 理学宗传, 清康熙六年刻本.
[18]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 清康熙二十黄楷刻本.
[19] 宋濂. 宋学士文集, 清光绪七年至同治八年永康胡氏退补斋刻民国间补刻金华丛书本.
[20] 解缙. 文毅集, 清乾隆三十二年吉水解氏敦仁堂刻本.
[21] 吴宽. 匏翁集, 明正德三年奭刻本.
[22] 王廷相. 王氏家藏集, 明嘉靖杨时荐刻清顺治十二年修补本.
[23] 郑岳. 郑山斋集, 明郑象贤刻清郑炫补刻本.
[24] 归有光. 震川集, 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5] 何乔新. 椒邱文集, 明嘉靖元年广昌知县余罃刻本.
[26] 薛应旂. 薛方山集, 明嘉靖刻本.
[27] 胡直. 衡庐精舍藏稿, 明万历十二年郭子章刻二十三年庄诚补刻本.
[28] 荒木见悟, 李凤全. 心学与理学[J]. 复旦学报, 1998(5).
[29] 朱鸿林. 国家与礼仪: 元明二代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5).
[30] 黄进兴. 优入圣域: 权力、信仰与正当性[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31] 谈迁. 国权·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 清钞本.
[32] 吴亮. 万历疏钞, 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33] 唐顺之. 荆川集, 明嘉靖三十四年安如石刻本金陵书林重修本.
[34] 薛侃. 薛侃集[M]. 陈椰编校, 钱明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5] 邓国坤, 周炽成. 陆九渊学说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2015(2).
[36] 杨慎. 升庵集, 明杨有仁辑刻本.
[37] 张瀚. 明疏议辑略, 明嘉靖三十年大名府刻本.
[38] 陈明水. 明水陈先生文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七二, 1997.
[39] 俞汝楫, 编. 礼部志, 稿. 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 沈德符. 万历野获, 编. 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B244.8
A
1008-4479(2024)02-0111-08
2023-06-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象山学阐释演变史”(21CZX033);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项目“20世纪以来海外象山心学编译与研究”(20GZGX30);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宋元明哲学史课程改革研究”(2022C003)
邓国坤(1989—),男,广东广州人,哲学博士,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与海外汉学。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