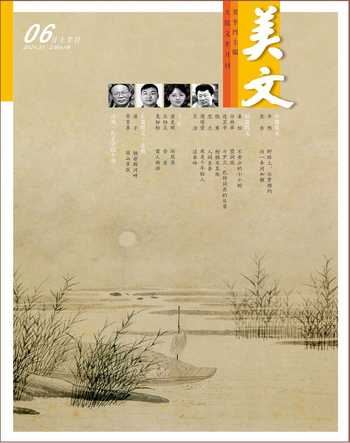我是个年轻人
周靖萱
我工作的地方只和王府井步行街隔了一条马路,很近,但是我不常过去。最近的三年我们都发生了许多转变,我不去是为了逃避一个在心里转了几万遍的念头——我是个年轻人,不过也没什么意义。
第一次把眼前的景色对应上“天地”这个词的时候,我十六岁。学校放暑假,住在川藏的某座山上,头上是天,脚下是云,我想那时我是曾短暂拥有过天地的。能够想象到的最绿的绿、最蓝的蓝、最黑的黑、最白的白……所有最纯粹的颜色都是我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那是草、是苍穹、是夜、是太阳……成群的牦牛疯跑,有时我抚摸它们,有时我骑它们,有时我怕它们,有时我也享用它们,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你爱一样生物与你杀掉它们仿佛没什么冲突。我不谨记自己作为人的高尚。
我采花,将萤火虫捉起来,在高海拔的地方我度过了冷冽的夏天,雪也会下,我带着小喇嘛们边躲雪边讲故事,喝用泥水煮出来的面汤,拿刺骨的雪水给他们洗衣服,跑到山腰上的小卖部买零食给他们吃。他们终日地缠着我,像普通的孩子们一样,会趁着铲雪的时候打雪仗,把泥巴偷偷藏进我的鞋子里。我有时候也被气得拿铲子揍他们,用不讲新故事威胁他们,但是也有很温馨的时刻。他们从树下撿到了小鸟给我,我们一起拿煮不熟的米饭喂它。三四岁的小喇嘛长得漂亮极了,眼睛大大的,红彤彤的小脸和嘴巴,很远地看到我就跑着扑上来。我抱着他们,一个个吻便落到我脸上,我也不拿他们当佛,总是觉得承担太多的膜拜对年幼的他们来说,还过于辛苦。
十八岁的时候身边有了一群朋友,我不敬畏任何东西,勇气和混账在我心里同时滋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年少的人畏首畏尾,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人,只有青春在我们的眼睛里荡漾。我可以去电影院看十几次同样的电影,彻夜不眠再睡过整个白天,凌晨三点我们到处找吃的,在便利店肆意扫荡,在四点的大街上我们骑车,大声地唱歌,撞见打群架的小团伙,边吹口哨边溜得飞快。柳树的叶子扫过我的头顶,我感到风在我脸上滑过,快乐像洪水一样涌向我,我被它一下子冲走,大脑里空白一片,只记得一个词,那是——自由……
我听很多古怪的音乐,买一些用不上的小玩意儿,敷着深褐色的面膜去上课。什么理论我通通听不进去,我只想到诗歌、舞蹈,想到话剧和夜场。我总在写作,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女生宿舍成天吵架,但是也马上和好,明明刚才还面红耳赤的两拨人,转头又可以坐在一个屋子里,吐槽渣男、嗑瓜子、哭哭、哄哄,找一个空教室放映《回家的诱惑》,跟着主题曲一起大唱特唱。那几年我还常常喝多,清醒的时候很少,做很多丢脸的事儿。听说我酒品差得很,还坐到同学家的健身单车上,声称要骑走。他们跑过来扶我,我又折腾,手里的烟一歪,烫了我一个疤,在胸口。事实上我不吸烟的,那种味道让我闻着头疼。
再回到家的时候,我将要二十岁了,在王府井的胡同里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助理,写的东西统统都不过。在某一次下雨的时候我坐在满是白炽灯的格子间里,看着电脑发愣。我突然在想自己是否真的拥有才华?我对写作产生了困惑,对于已经认知到的一切也同时不确定了起来。偶尔闲下来我总是埋进厨房,做饭、烘焙、腌泡菜、熬果酱……我急需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来证明过去。我爱过的,怎么会没有爱过我呢?与写作一同抛弃我的,还有爱情。
即便我的脸青春犹在,性格也还算热闹有趣,可是我那时喜欢的人是不中意我的。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人性本贱,总是对得不到的东西格外偏爱,所以才会喜欢上不喜欢我的人。只是慢慢的我才明白,我只是还不能接受,人生不能事事如意的真相。浪漫是我生命的主旋律,对于下班时偶尔会碰到的乞丐大叔,我心里都充满了愉快,甚至会期待每天的见面,期待那一瞬间的微笑和点头。我看不见他的狼狈,误以为我们是在分享这个美好的未来。我下意识地不愿理解——我不理解他的卑微、他的无奈。我不愿去明白,我们之所以相遇是因为他必须乞求生存。
我还不到二十二岁,不过也快了,我仍想停留在原地。可是我一定要走。那么我就不走到那条街上去,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是吗?他们也会走到那些山上去吗?会在杨柳依依的春天盛放?我还要继续长大吗?或者要走向老去了?是不是每一个问题的后面都会配有答案?我把剩余的,那些鲜活的心跳都换成了问号,希望有一天……希望有一天……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