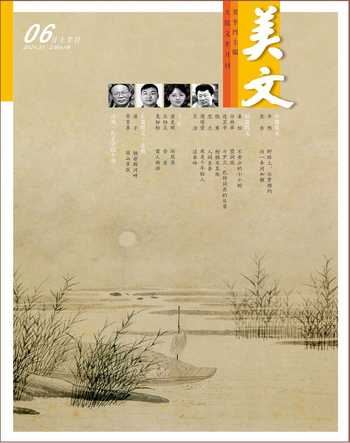南卡罗莱纳的灰松鼠
杨蒙
杨 蒙 本科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专业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方向为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
自然文学创作,必须走进自然、观察自然、聆听自然、感受自然。回想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和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等作品,其引人之处正是将深刻的思想和美学表达融合在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中,且由观察引发出人类心灵与自然的碰撞。这也是自然文学明显区别于生态文学等相关文学类型的特点之一,即自然文学不仅在于唤起人们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和对环境危机的关注,还在于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并打开通往更深层次精神和灵性体验的门户。美国自然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已经带动了生态批评和自然文学的“动物转向”。今天,我就写写南卡罗莱纳非常常见的小动物灰松鼠吧。
一
初到南卡,我對随处可见的小松鼠感到很不适。只要出门,不论是街道上、草丛里,还是矮墙上和花坛中,小松鼠几乎占据了所有地盘。你稍不留神,小松鼠就会从你头顶的树杈间飞速穿过,当你转过头想一探究竟时,只剩下摇摇晃晃的树枝和飘散的落叶。每次走在街上,我都会做好远离小松鼠的准备,但是防不胜防,因为小松鼠会随时随地出现在你的视线里,甚至还会和你四目相对。每当孩子们距离小松鼠半米远时,他们都会兴奋地尖叫,然后悄悄地靠近,试图去触摸一下它的身体。而我则会赶快喊叫他们回来,再把视线从小松鼠所在的区域移开。从心理学上讲,孩子们很容易受我的行为影响,即通过“学习行为”如观察他人(父母或同伴)的恐惧反应来学习恐惧。因此,为了避免给孩子们造成恐惧感,我每次看到小松鼠时都会稍稍侧过身去,以减少小松鼠带给我的紧张情绪。直到小松鼠离开,孩子们也逐渐从惊喜的神色中平复,我才会带他们继续前行。后来因为小松鼠出现频次较高,加上孩子们热爱动物的天性,很快他们就牢牢记住了小松鼠的英文叫法“Squirrel”,这也是孩子们落地美国后学会的第一个关于动物的英文单词。我也不禁感慨:“果然大自然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此之后,每当孩子们看见小松鼠,他们就不停地喊着“Squirrel”……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当孩子们用英文喊出小松鼠的名字时,我竟没有一丝紧张感。哪怕当我反应过来脚边就有一只小松鼠时,我也不再会惊恐地跳起来或者叫出声。一方面小松鼠的英文叫法减少了我对“鼠”字的恐惧,另一方面孩子们对小松鼠的喜欢以及小松鼠的灵动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
圣诞节假期中的南卡罗莱纳大学校园格外安静,除了寥寥行人和狗狗在校园中漫步,就是我和硕硕(女儿)、果果(儿子)坐在松树下看小松鼠了。这里最常见的小松鼠种类主要是东部灰松鼠(Sciurus carolinensis)。除此之外,还有红松鼠(Sciurus vulgaris)、福克斯松鼠(Sciurus niger)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过灰松鼠。东部灰松鼠体长约40到50厘米(包括尾巴),当它们的尾巴竖立起来时,身体大约有30厘米。它们的毛色通常是灰色,腹部毛色较浅,主要为白色或淡灰色。它们的大尾巴以灰色为主,尾巴四周成白色。当太阳光打在小松鼠身上时,尾巴周围就形成一圈明亮的光晕,瞬间它们就成为一只只自带光环的小精灵。它们的尾巴既是保持平衡的工具,也可以用来与人沟通。我们发现当小松鼠想要无限接近人类时,它们会先左右摇晃着尾巴慢慢走来,等足够靠近时,它们会马上把尾巴竖起来,成平滑的S形。然后瞪大双眼看着你,两只拇指大小的耳朵也会直立起来,就像我们观察它们一样注视着我们。有几次,孩子们就这样和小松鼠四目相对,有的小松鼠还会坐在对面,听着孩子们和它们对话。他们之间的距离大概不到半米,就是这半米的距离足以让两者建立信任并相互讲述自己的故事。孩子们好像还发现了规律,每次他们想跨越这半米距离再离小松鼠近一些时,小松鼠立马就会离开。从此,他们就默契地保持着这半米距离的对话。在这里,小松鼠是最不怕人的,它们随时可以从你脚边溜走,或者站在路边望着你。而你有时路过向它们打个招呼,它们也不会被吓跑。我曾经多次问果果:“小松鼠能听懂你讲话吗?”他坚定地回答:“能啊!”“那你能听懂小松鼠说话吗?”果果好像觉得这是个无需回答的问题,然后竟有些不耐烦地答道:“当然能啊!”如果你接着问他们谈论了什么,果果会绘声绘色地讲出一大串对话。对于大人而言,这好像是孩子编的故事。但对于孩子们而言,他们和小松鼠就像朋友一样,有着心与心的沟通。我们还发现小松鼠的前肢(即手)通常有四个指头,而后肢(即脚)有五个趾头。它们的爪子非常锐利,很适合它们在树木之间跳跃和在地面上快速移动。此外,小松鼠的前肢虽然相对较短,但非常灵活,甚至可以看到它们前肢肌肉形成的优美线条。硕硕每次都要和小松鼠比赛剥榛子,她会挑选一个外表干净且无裂痕的榛子,然后用脚踩一下,当力度不当时,榛子立马就变成了泥。多数情况下硕硕都无法赶超小松鼠,因为在小松鼠吃完榛子并丢弃果壳时,硕硕还在细致地剥着榛果外面的棕色薄膜。即便如此,她每次都很享受这个“失败”的过程。从南卡大学马蹄铁(Horseshoe)的草坪向远处望去,觅食的小松鼠和奔跑的小松鼠共同构成一张大自然的乐谱,就着微凉的风,欢快地演奏着。
之所以这里松鼠众多,主要得益于南卡适宜的生态环境、温和的气候以及城市与自然环境共存的理念。小松鼠不仅喜欢吃坚果,如橡子、核桃、栗子、榛子、松子等,也喜欢吃各种果实,包括苹果、梨、桃、樱桃、浆果(如草莓、蓝莓)等,因为果实可以为它们提供额外的水分和营养。某些小松鼠还会吃花朵,以及某些树木的嫩枝和树皮,这些可以作为它们饮食的补充。而南卡罗莱纳州拥有丰富的森林和自然资源,包括广阔的松树林、硬木林和其他类型的自然栖息地。这些环境为松鼠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场所。另外,这里气候温和,冬季相对较暖,这就意味着松鼠可以全年活动,繁殖周期较长。当然,温和的气候也代表食物资源全年丰富,有利于松鼠的生存和繁衍。在许多南卡罗莱纳州的城市和乡村地区,人类居住区与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公园、后院、街道绿化带等人工环境为松鼠提供了额外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地。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如未吃完的食物残渣等,也可能吸引松鼠。但是在这里,几乎没有人主动投喂小松鼠。硕硕最开始向小松鼠投喂花生,小松鼠根本不理会。后来我建议她观察一下周围人的活动,看看是否有人投喂小松鼠。后来她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人投喂任何动物,不管是小松鼠还是小鸟。那时她也明白了什么叫尊重其他生命的选择和生活习性。因此,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互不干涉就成为一种无言的约定。
在我的印象中,小松鼠是住在树洞里的。而且在南卡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满各种树洞的大树。但是有一次雨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小松鼠和小鸟一样,也会在树干上筑巢。那天,我们看到一只小松鼠嘴巴里咬着一堆干树叶,然后快速地爬上树干,钻进一个酷似鸟巢的窝。刚开始我们以为小松鼠在帮助小鸟筑巢,后来直到窝里又钻出一只小松鼠,且发出快速连续的“吱吱”声,我们才确认那是一个松鼠窝(也称为“巢”或“栖巢”)。松鼠窝比鸟巢大,由树枝和树叶构成。与鸟巢不同的是,松鼠窝看不到泥土的痕迹,而且巢的位置更为多样,包括树枝、地面、岩石缝隙,甚至人造结构。后来,我们抬头看到巢穴时,不会再下意识地把那窝当成鸟巢。
我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如此勇敢地观察鼠类,甚至去发现它们的可爱与灵动。或许这就是自然的神奇之处,在无形之中将我们彼此连接,以最自然的方式消除我内心的恐惧并治愈恐惧带来的心灵创伤。
二
毕竟在以前我是极力避免说鼠、听鼠、见鼠,更别说靠近鼠和观察鼠了,因为我有非常严重的“恐鼠症”。
相信很多人对抑郁症和恐高症并不陌生,但是对恐鼠症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毕竟连很多小朋友都不会害怕的小动物却让我这个大人望而生畏。这种恐惧像是基因里自带的,只要我一接触“鼠”类的字眼,浑身上下立马会紧张起来。就像初中时代一次严重的“翻车”,就是由一只小老鼠造成的。那天中午,我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刚过十字路口,飞速的车轮就从一片模糊干瘪的东西上压过,而游离于车轮外的是一条细长的尾巴。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刚刚的碾压画面,且飞速修复着那张支离破碎的小尸体。大脑“成像”的刹那,我意识到那是一只被太阳晒干的老鼠尸体。顿时我的双腿一软,双手同时失去了知觉。随着车轮失控,我的身体和自行车重重地倒在地上。胳膊肘和小腿外侧擦破了皮,血液很快渗出。这时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老大爷路过,连忙询问我是否需要上医院。他看着我煞白的脸,以为我是因中暑而倒地的。直到听到老大爷大声抱怨这炎热的天气,我才慢慢回过神来。但是面对此情此景,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告诉老大爷自己是被一只小老鼠而且是干瘪的小老鼠尸体“吓翻车”的。也就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这种恐惧会让人产生严重的精神和生理反应。
此后的几次经历也让我再次确认这是一种不容小觑的症状。但是真正促使我要去深入了解并想克服这种恐惧心理的是大学舍友在宿舍养仓鼠的经历。我的舍友根本不知道我对鼠类有严重的恐惧,她们默认没有人会抗拒这种可爱的小动物,并且那时在大学中正流行着一种养仓鼠的热潮。由于白天我基本不在宿舍,所以自然不会和小仓鼠有直接的碰面。但是晚上我却无处可逃,只能听着那种令人神经发麻的吱吱声入睡。想想现在变成了人要躲着老鼠,真是有苦说不出。刚开始时,我会戴着耳机把声音调大,然后在音乐中入睡。后来因为半夜耳机掉落,我常常会被小仓鼠的声音吵醒。或许是因为小仓鼠嗅到了我的恐惧,它们还会瞪大眼睛盯着我。虽然我不敢直视它们,但是它们的眼睛会在夜晚的灯光反射下变成一个个亮点。哪怕这样一个小小的亮点,就足以让我产生呕吐反应。我躲在厕所的角落干呕,同时耳朵里充满了仓鼠的叫声。越想胸口越闷,我攥紧了拳头不让身体发抖,但最后还是像棉花一样瘫软在地上。随着恐鼠症状的不断加剧,我深知是时候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三
那时,我采取“自救”的方式,既搜索并阅读相关文献,又求助于心理学系的师兄师姐。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这种恐惧属于动物恐惧症(Zoophobia)也就是对一个或多个动物种类有着强烈且不合理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可以是针对特定的动物,如蛇、蜘蛛、狗等,也可能是对多种动物的广泛恐惧。因此,动物恐惧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就我对鼠类的恐惧而言,可以说是恐鼠症(Musophobia),或称鼠恐惧症,指的是对老鼠或类似的小型啮齿动物(如田鼠)有着强烈的恐惧或厌恶感。这种恐惧感可能是不合理的,即使恐鼠者知道老鼠不太可能对他们构成实际的威胁,但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情绪。因此,恐鼠症在心理学上被归类为一种特定恐惧症(Specific Phobia),是人们对特定物体或情境产生的过度恐惧和焦虑的一种表现。此外,我对鼠类的恐惧反应和恐鼠症的症状完全一致,如看到老鼠或想到老鼠时出现极度恐慌、焦虑,即使是老鼠的图片也能引起强烈的恐惧反应。在极端情况下,仅仅谈论老鼠或听到有关老鼠的声音都可能触发恐惧反应等。为了消除我这种恐惧,师兄师姐们提供了多种建议,如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即识别和改变导致恐惧的不合理思维模式,学习应对技巧;暴露疗法,逐渐地在安全的环境中接触害怕的对象(老鼠),以减少恐惧反应;放松技巧,学习各种放松技巧,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放松等;药物治疗,如果恐惧感极度严重,需要寻求医生并使用药物来帮助控制焦虑症状。在这些应对方案中,暴露疗法首先被我排除在外,因为在宿舍和小仓鼠的朝夕相处并没有缓解我的焦虑,甚至还加重了我的症状。而放松技巧操作性强且安全性高,后来再遇到与“鼠”相关的词、图片和事件,我就不断地做深呼吸,以缓解我的紧张情绪。即便如此,在硕硕提出养小仓鼠的要求后,我还是非常坚定且生气地拒绝了。我甚至不允许家人开关于鼠类的玩笑。这些都表明我内心依然充满恐惧,且并没有在心理辅导下获得解脱。于是,为了彻底打败这种恐惧,我勇敢地回想一件件往事,以找出引发这种恐惧的根源。后来在一次清理姥爷家粘鼠板的“运动”中,我找到了答案。2021年春节,我和我爱人带着硕硕和果果去看望我的姥姥姥爷。那天晚上,姥爷给我手电筒让我去把他放置的粘鼠板清理一下。当时我的脸直接僵住了,我爱人和女儿已经笑出了声,因为在我家是几乎不提“鼠”字的,更何况要我去收拾这些小东西。只听我爱人和女儿在津津有味地数着有几只小老鼠,什么颜色,多么可爱,他们还挑逗小老鼠不断发出声音。当时我直接跑出了屋子,想从距离上和鼠类隔绝,但是刚才的吱吱声又开始不绝于耳。直到我爱人把一窝小老鼠送走,我才松了口气。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才回想起在我很小的时候,姥爷就是端着那一张张粘鼠板从我眼前走过,那种惨烈的场景才造成了后来我对鼠类的恐惧。
虽然我找到了恐鼠的根源,且获得了相应的缓解方法。但是多年来的恐惧根本无法消散,哪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我的恐鼠症也未真正缓解。所以,在经历过一系列尝试并失败后,我认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和鼠类和解了,只不过由于现在很少和鼠类“打交道”,自然也不会过度担心鼠类带给我的恐惧。但令人欣喜的是这次南卡罗莱纳之行竟如此有效地治愈了我的恐鼠症。回想这一历程,不禁让人反思,其实不都是动物害怕人类,人类同样害怕动物,哪怕是并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小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和动物是绝对平等的。而“恐鼠症”的治愈在于我看到了小松鼠真实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小松鼠的靈巧与可爱是那么引人注目。相比被人类关在笼子里的小仓鼠、被粘在粘鼠板上的小老鼠,谁能说这种恐惧不是人为造成的呢?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