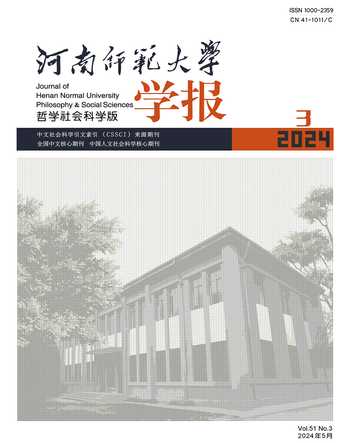新时代司法改革现代性与治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平衡
摘 要:中国自20世纪末开始的多轮司法改革具有现代性和治理性的双重特征,承载了民众向度与国家向度的双重表达。司法改革中这种民众向度与国家向度的不同表达,会在更深层次上导致来自司法改革现代性特征与治理性需求在结构、价值和效率等层面的错位,表现为权力架构与地方环境对司法改革的制约、实质法范式对形式正义与规则理性的消解以及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人案矛盾”。走出司法改革困境的长久之计,是在国家治理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社会辩证运动过程中,提出维持司法改革现代性-治理性结构动态平衡的共识性原则。
关键词:司法改革;现代性;治理性;矛盾冲突;治理方案
作者简介:张式泽(1990-),男,河南新乡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FX182)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4)03-0055-07
收稿日期:2024-01-15
中国自20世纪末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司法改革,始终是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目前学界对于司法改革的考察主要包括两种学术视角:一是从西方法学理论的视角进行观察,将中国司法改革的各项措施同西方法学理论进行对照,在评判其制度架构“合理性”的同时,对其实践可行性进行考察;二是从中国司法实践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司法改革各项措施的运行状况和问题所在,并给出具体化的应对建议。从传统西方法理学语境对司法改革进行的研究,往往陷入唯理性进路,即从法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延续,进而探讨司法改革的制度安排与路径前景,忽视了改革自身的经验性观察,也未能摆脱西方法学理论自身知识和经验的地方性因素局限,难以指导中国司法改革的具体实践。从中国司法实践出发的实证化研究,往往将视角局限于某项司法制度的优化,难以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
应当说,中国自20世纪末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多轮司法改革运动,从其背景上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国家现代化体制与寻求职能转型过程的一个具体要素,体现了优化治理的改革逻辑,带有强烈的治理适正性期待和法治色彩。在法社会学派看来,“法律既是由理性所发展了的经验,又是由经验所证明的理性”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5页。。因此,本文以法社会学为视角,将司法改革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从国家转型、社会变革发生和演化的历史语境出发,尝试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性质与主要矛盾在社会治理层面提出新的解释。
一、中国司法改革性质的多元化分析
(一)司法改革的民众向度:现代性表达
司法权之民众向度又可以称为市民性司法权。该用法最早源于美国吉布森法官,在伊金诉罗布案(Eakin v. Raub)的判决书中,他认为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划分为市民性司法权和政治性司法权,而市民性司法权被用来指代司法权在普通民众中定分止争的功能章安邦:《司法权力论》,吉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7年。。一般认为,市民性司法权起源于洛克有关“审理和裁判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纷矛盾” 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7-78页。的裁判权理论,在随后个人自主性的追求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与市民性司法权一体两面的“权利”概念。为了维护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避免多元社会中权利道德化或实质化破坏个人的自主性,古典自由主义以权利作为原子式的基本元素,借助建立在科学主义或者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程序理性,在西方社会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形式理性大厦 李学尧:《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法治国(Rechtsstaat)以及由此形成的形式法律范式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37頁。。权利概念的使用和形式理性的提出,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社会现代化的路径表达。此时,形式法范式的政治哲学基础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严格区分,契约自由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得到形式主义法律的切实保障和维护。此时的司法权能具有明显的民众向度:司法机构的中心任务在于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司法体系内部则恪守司法形式主义与规则中心;司法职能之核心在于定分止争,解决纠纷。
中国自20世纪末以“提高审判效率、减轻财政负担和案件的积压”为初衷开启的逐步具有体系化特征的司法改革,包含了上述司法权之民众向度的客观要求,并带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从改革目标看,司法改革的开端适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完善之时,因而蕴含着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果的客观要求 曹建明:《加入WTO对中国司法工作的影响及思考》,《法学》,2001年第6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司法改革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并指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法工作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8-149页。,突出强调了司法改革的民众向度。从思想层面看,司法改革的过程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达成关于司法改革目标之共同体共识的过程,完成了形式主义司法改革所需的比较法智识储备,从“功利主义”司法理念主导的审判方式改革,升级为追求权利至上的形式主义司法理念,并最终实现了“从惩治型司法向治理型司法的转变” 陈兴良:《刑事司法改革成果斐然前景广阔》,《人民检察》,2022年第18期。,继而引发了司法体制的系统性改革 李学尧:《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从改革内容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优化司法职能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参见自2012年至2022年党的十八、十九、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司法改革部分的内容。的改革目标,完善了司法职业惩戒及错案责任追究机制、人民参与司法的保障机制、繁简分流的司法便民机制、接受监督的司法公开机制,并先后兴起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化认罪认罚制度改革、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推进繁简分流的程序衔接体系、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等一系列推动我国程序法治建设、保障司法人权的改革举措。上述改革举措均表明,司法改革是中国在实现国家现代化体制与职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要素,具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民众向度和典型的现代化色彩。
(二)司法改革的政治向度:治理性表达
司法权之政治向度,又可以称为政治性司法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司法权作为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由国家垄断行使,包含着政治需要与国家运行逻辑;其二是司法权作为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具有人民性和政权保障之工具性 在此区别于西方分权制衡思想下的政治性司法权,参见章安邦:《司法权力论》,吉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7年。。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法治国向福利国家转变,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的根本属性,都要求在现代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对由纯粹形式法范式带来的非正义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纠偏,本质上是实质法范式对形式法范式的部分替代和补充。政治性司法权“将法律认作国家价值原则和政策的一种落实和实施手段,按照法律工具主义处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韩德明:《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司法改革的现代化向度》,《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
这种体现司法权政治向度的司法改革,在中国近几轮涉及社会治理举措的司法改革中也是屡见不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可以说是对司法改革政治向度的直接体现。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来,党中央围绕着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以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和省级人财物统管为重要内容的“四梁八柱”性质的司法改革及其综合配套为抓手,统一顶层设计的同时自上而下强力推进多项司法改革举措,其本意就是在分离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破解权责平衡、监督制约和人案矛盾突出的治理难题,实现国家司法治理体系和司法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的依然是行政管理的改革逻辑” 徐昕,黄艳好:《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9)》,《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不仅如此,随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继续作出了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布局,从健全完善审级制度,坚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全面贯彻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实施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机制,坚定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完善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等改革举措入手,进一步完善司法审判、起诉、侦查、监督和辩护制度,健全、提升司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徐汉明,丰叶:《论习近平刑事法治理论之价值意涵及实践伟力:兼论新时代“第三时段”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法学杂志》,2023年第4期。。由此可见,司法改革的政治向度,就是作为一项工具性手段,在国家司法体制与司法职能扩展的基础上实现治理能力的先进性、治理模式的合理性和治理手段的规范性。可以说,中国司法改革体现出的政治向度,本身就是对国家治理在司法层面的重申和具体化。
二、司法改革现代性与治理性的多重矛盾
中国司法改革由其市民性与政治性向度的不同,会在更深层次上导致来自司法改革现代性特征与治理性需求在社会空间中的错位。
(一)结构矛盾:权力架构与地方环境对司法改革的制约
1.司法改革与权力架构的横向维度
中国中央政府及其权力体系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多维度的、多层次的体系。在宪法层面上,中国的司法权是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监察权和军事权并行的六种国家权力体系之一,应与行使其他权力的部门机构成为平行关系。然而在权力的实际运作层面,尤其当以地方法院作为考察对象时,地方性权力体系与司法权所构成的横向权力维度之复杂性与权力优位性就逐步显现出来。过去,当司法机关与地方党委的意见不一致时,地方司法机关通常是听命于当地党委,因为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是归地方“块块”主管,这就事实上形成了“行政权”主导的体制 周永坤:《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规范化:论司法改革的整体规范化思路》,《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自2014年开始的省级统管改革拉开了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序幕,彰显了中央将司法权定位为中央事权与地方性事权脱钩的决心。但经过五年的试点实践,省级统管并没有达到“去行政化”“均衡司法供给力”的既定目标:在2020年对1535家基层法院进行的样本调查中发现,其中仅有741家完成了改革任务;而这741家法院中,有249家法院依然依赖同级财政的经费供给,同级经费供给占比平均为43.22%,而山西、河北某基层法院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7%;近33.6%的基层法院即使在完成改革后,也并没有在经济上与同级政府完全脱钩范丽思:《省级统管后法院经费保障机制再造》,《人民司法》,2021年第22期。。省级统管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艰难性也预示着,中国司法体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地方司法机关仍隶属同级政府(党委)和上级司法部门的双重领导,司法领域将受到来自地方行政领域持续的影响和干预。
在政治生活中,“政府是法院的领导”已经是政府与法院的共识,也是社会常识。政府领导人到法院去被称为“领导视察”,法院主动“接受领导”,而政府也安之若素地“领导法院” 周永坤:《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规范化:论司法改革的整体规范化思路》,《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这种司法与行政在社会治理层面职能的趋同和行政权力的优势地位,使得地方上包括法官在内的司法人员更容易受来自横向行政领域而非法律规范的影响。结果,自中央顶层设计并逐级推行的司法改革,其改革举措的落实程度、司法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往往取决于各地司法职能的规范化程度,并且因为各地方司法领域与行政领域之间的影响因子的不同而呈现出区域的差异性。这种地方横向權力维度的复杂性和行政权力的优位性,极大增强了本属中央事权性质的司法权与地方事权在职能上的混同,增加了司法权去行政化和地方化的难度。
2.司法改革与地方环境的纵向碰撞
前文已述,司法改革从背景上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家现代化体制与职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要素,发生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转型的大背景中。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乐观的改革者容易过高地估计中国社会环境以及根植在其中的行为习惯的转变。中国目前已经先后推行了多轮司法改革。上述多轮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由顶层设计的自上而下推行的为实现司法现代化而设计的国家计划,虽然在推行过程中经过了严格的区域试点试行及其合法化检验,但是对于各个地方在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差异性的准备和估计程度仍需加强,对于改革面临的地方客观环境需要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在社会治理领域,“原有的行为和习惯模式自有其行事逻辑和内在动力” 徐小群:《现代性的磨难:20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导论第19页。,如果构成这样行为和习惯模式的地方环境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那么原有的行为和习惯模式就仍能发挥作用。此时,来自中央司法改革规范化和职权配置合理化的运行要求就会与地方原有的行为和习惯模式发生碰撞。由于中央和省级司法机构和司法官员是在地方社会之上运作的,而地方的社会环境决定地方官员在履行司法职能时有其内在的行事逻辑和行为驱动力——无论这种逻辑和驱动力来自客观因素的制约或是个人私欲的膨胀。加之受限于中央和地方司法官对司法改革的动机、眼界的认知不同,中央政府和省级司法机关推动的司法改革与基层实际发生的司法现象之间往往有着不小的差距 徐小群:《现代性的磨难:20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导论第19页。。这种由区域性差异反映出的央地结构性矛盾,不仅会导致一部分司法改革举措在实践中异化,而且还会在异化中产生新问题,从而陷入“改革-异化”的不良循环。例如,针对过去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多次出现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行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对构建侦查规范化和庭审实质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也规定了侦查阶段所获取笔录证据的合法性证明方式:同步录音录像视频证据的出示和侦查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出庭。理论上,这种改革举措可以完美解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侦查行为不规范的老问题,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在2020年排除非法证据的庭审环节,公诉机关的同步录音录像出示率只有38.1%,而侦查人员出庭率仅为10.89% 李蓉,黄小龙:《审判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审视》,《理论探索》,2021年第6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侦查行为规范化的老问题用笔录合法性证明的新办法加以解决,但这种被认为是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有时可能又会带来新问题。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地方司法人员“认识不到位、决心不坚定”,还在于我们不能忽视的近六七年来中国刑事案件总量接近30%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案多人少、司法资源紧张的地方环境。
(二)价值冲突:实质法范式对形式正义与规则理性的消解
实质法范式对形式法范式带来的非正义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纠偏,不仅是出于社会公益与福利保障在社会中的日益强调,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的本质要求。现代社会需要国家在社会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经济领域强调的实质正义还是在司法领域强调的公益保护等,国家都注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干预作用。不过,在司法中,这种国家出于目的性的政策干预和国家对实质正义的价值导向并不总是有利于司法职能在实践中的发挥。尤其是在中国构建司法现代化的当下,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司法现代化在构建规则中心主义方面的努力和效果。
具体而言,其一,治理性的法律工具主义要求,致使被颁布和实施的政策一般都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无论这种目的是平衡某种不公正的分配规则,还是针对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加以治理,都带有施政者的主观目的和意愿。当仅仅乞灵于规则,并从规则推导出结论被认为足以进行每一个权威性的法律选择时,法律推理就是形式主义的;而当如何适用规则的决定依赖于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进规则所要达成的目的时,这种推理就是目的性的 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政策,包含着某种人为的价值导向和规则指引,这种政策导向使得法官在进行判决时,不得不被动地在原本不同的价值导向与规则取舍面前作出选择,这不仅会丧失法官的自主性,而且还会迫使法官的判案逻辑从规则性推理转变为目的性推理,从而彻底改变法官的审判逻辑。法官也会因此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从被动中立的规则维护者地位逐步转变为积极的政策实施者形象,进而模糊了行政与司法的角色界限。
其二,中国司法改革的治理性表达要求实质性正义式的价值期待。无论是以结果导向为责任追究方式的司法责任制,还是以目的导向作为政策落实的考察标准,或是以真实主义为导向的刑事诉讼侦查原则,这些都是实质性正义要求在司法领域治理性的表達。如果目的性政策和实质正义价值导向的适用愈多愈频繁,就会大概率产生这样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并不会导致法官在实践中出现许多冤假错案,不会体现为案件判决的“对错”,而是体现在司法领域越来越多的形式正义被实质正义和目的正义取代,越来越多的法官在判案中更加看重目的性、效果性与真实性的实现,相对应的就是程序性的举措、保障和制度被集体化地忽视、省略甚至架空,成为一种“走过场”的形式。形式正义与程序理性的体系化建立仅仅维系于制度构建的表面,而未能渗透司法机关的职能当中,体现在法官的判决里。真正决定法官审判精神实质的,依然是来自上层的目的导向的司法政策和对实质正义的殷切关注。这种“以政策本位的法律推理和实质性正义为名的审判……直接后果是把法院轻率地拖进引人注目的特殊的利益平衡活动之中”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将法院由一个尊崇规则之治的独立主体变为法律工具主义下的随从,进而导致法律文化层面上形式正义和规则理性的坍塌,作为一种规则的法律不再被人们信仰和崇拜。颇为矛盾的是,对形式正义与规则理性的构建,正是司法现代化过程中孜孜以求的现代性内核品质。
(三)效率错位: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人案矛盾”
随着司法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理念的建立和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司法领域案件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提升司法效率、增加司法产能和更有效地分配司法资源就成了几乎所有国家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现实中,造成司法负担过重、司法效率低下的原因纷繁复杂,但主要因素在于司法案件数量的激增以及其他传统的社会控制和争议解决机制衰退导致的司法资源紧张。
事实上,法治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含义为“司法的功能因为法治作为基本国家原则的确立而重新定位,司法在国家政治力退出、社会力解放后,必须承担起维系新秩序的主要责任” P. H. Brietzke, designing the Legal Frameworks for Markets in Eastern Europe, 7 Transnatl, 5l(1994).。由于中国司法现代化与作为建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举措相伴相生,司法现代化必然要求司法在处理社会纠纷过程中的便民化与普及化,即将司法体系延伸至基层社会,以司法标准化为前提,将司法职能向着服务化、便民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毕竟,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效、优质和统一的司法公共职能服务。因而,改革后的司法机构将面临来自中央和民众的双重期待:中央希望通过司法改革重塑地方法院解决、消化地方社会治理矛盾的角色(例如推行地方立案登记制),而民众则期待更加公正合理的司法职能与诉讼服务体验。考默萨指出,随着当事人人数和案件复杂性的增加,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供给有限性之间的张力可能导致“司法让位”,即因为司法的规模和自身的扩张力比其他制度弱,法院参与社会事务越多,就不得不更多地让渡自己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司法参与的社会事务越多,由司法权自身运转而产出的司法产品供给越有限,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刘峥:《司法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为:兼论司法职能扩张与权力限缩》,《司法论坛》,2011年第3期。。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内外交困”下,地方基层法院往往积案如山、不堪重负,表现为一种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独有的“人案矛盾”现象。
这种积案现象可以说始终伴随着中国先后进行的多轮司法改革,并在司法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这种积案现象曾一度作为中国第三轮司法改革的改革背景,促成了“速裁程序”试点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但以解决积案现象为目的的司法改革和司法现代化过程中进行的司法改革,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导向和目的上的差异。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司法改革,以追求形式公正为目标,以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为表现形式;而以解决积案为目的的司法改革,是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效率为价值要求,目的是衡平积案矛盾,是国家治理体系对司法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的政策性反应。两种价值要求和目的几乎完全不同的司法改革要求,却先后发生在近乎同一轮的司法改革中,这就容易导致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在思想、理论和操作上存在困惑和混乱。诚如学界所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庭审实质化的重大配套改革” 陈国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问题(下)》,《法制日报》,2019年12月4日。,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为代表的解决积案为目的的司法改革,本质上是在推进现代性司法改革过程中,对由于现代性改革本身缺陷而导致的社会治理问题进行的政策性纠偏。
三、司法改革现代性-治理性结构的衡平原则
不难看出,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以司法现代化过程为载体的司法现代性与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载体的国家治理性两大系统性要求。如果需要在此为现代性和治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那么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是复杂微妙的辩证关系:在某些层面上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但又在某些领域存在着多维度的矛盾性冲突。应当说,现代性与治理性的冲突,是根源于现代性规范的、标准的、程序的、理性的现代因素与治理性中机构扩展化、行政化、目的化、意志化的治理性因素之间的系统性矛盾。
那么,如何平衡社会辩证运动过程中现代性因素与治理性因素,就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令我们感到乐观的是,中国近现代先后经历的数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与司法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现代性因素与治理性因素相关的学术探讨与实践已经提供了大量较为成熟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概括起来,有两方面的共识性原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一,社会环境是支撑社会行为的逻辑起点与原动力;其二,在社会领域内,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意识和信息上的传递时间差。
社会环境是支撑社会行为的逻辑起点与原动力,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无论是现代性因素的发展还是治理性因素的落实,都应以社会环境之承载力为基础。社会环境是指自然禀赋、地理条件、意识观念与法律文化等客观存在的自然与人文因素,以及在此因素限制下的社会实践空间。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的种种影响,不同区域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这种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既表现为国内的区域差异性,同时还表现为中国整体社会环境与域外——尤其是西方社会——在社会环境方面的不同。一方面,从国内看,区域性社会环境的差异,为全国范围内构建规范化、统一化的现代司法体系增添了困难,而这种困难性因素需要我们正视并希冀在发展过程中长图徐治,否则,纸面上的改革决策部署与政策文件下达无论如何精致,都不能确保上述举措在实践中的遵循与落实。另一方面,从国际上看,中国实现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与法律改革,曾一直以西方近现代法制为基本标准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样板与目标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然而这种“样板与标准”注定只能是一定时期和阶段内历史的产物,如果背离本国社會环境的承载力,任何制度层面的司法改革都注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乏历史性教训。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改革中逐步破除以“先进性”价值为主导的盲目性法制输入,转而以“社会适应性”价值为依托,在尊重社会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探索和尝试适应我国法律改革的路径范式。第二,司法改革作为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其改革动力与落实都离不开社会环境。虽然中国的法律改革过程呈现出一定的“外源性”特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转型社会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商品化、政治文明化和思想开放的趋势,为中国法治提供了越来越显著的动力”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67页。。 “应承认的是,我国的司法改革实践中长期存在着改革者主导改革的问题” 陈卫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在强调司法改革“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改革道路的同时,也需要适当关注司法改革在社会环境的内生动力下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地方行为逻辑。“改革必须获得被改革者的参与和支持,完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会招致一线实务人员的愤恨甚至彻底的破坏,机构里面底层的人和顶层的人一样重要。” 格雷曼·伯曼,奥布里·福克斯:《失败启示录:刑事司法改革的美国故事》,何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5页。
在社会领域内,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意识和信息上的传递时间差,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一种系统性的变革,从个体意识的适应与转变到社会群体达成共识,其过程具有时间性。在中国司法改革中发布的政策性文件与改革举措,通常带有上层明确的意志和目的等治理性因素。由于这种改革举措的效力具有一般性,在执行上述政策和举措的同时,往往也要求司法人员乃至守法群体理解或接受这种举措背后的意志和目的。然而常常被忽略的是,司法人员和守法群体学习、理解和接受这种意志和目的的过程,是一种转变性意识从个体(顶层或精英层)向群体(社会或民众)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有时间维度的,并非即时性的。整个过程宛如从顶层一点发出的波,在时间维度上向四周不断扩散并最终传向整个社会面。然而,中国先后进行多轮司法改革,其改革数量之多、改革内容之丰富、改革频率之紧凑,致使基层司法人员不仅要学习、适应政策性举措带来的司法变革,同时还要应对实践中愈加繁重的案件量,因而背上了沉重的压力。不仅如此,中国的司法改革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爆发这一现象 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爆发是指,本应当在不同时間维度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却在某一阶段同时出现的现象,具体指我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建立法治”“深化法治”和“简化法治”要求的同时出现。。究其原因,除了中国特有的复杂国情,也包括了治理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共存的司法改革之频繁推动。由此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任务的繁重,同时还伴随着基层司法人员思想意识上的困惑。可以说,从个体到社会群体意识适应与转变之时间性这一过程,决定了司法改革的可接受程度和社会的适应性。反之,过于频繁的推行司法改革及其背后的治理性因素,会使“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政治机制的功能,其后果是使司改措施偏离法理规律,既加重法院的案件负担和功能负担,也不利于司法改革既定目标的实现” 姜峰:《央地关系视角下的司法改革:动力与挑战》,《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
四、结语
在比较法领域,通过提出关于司法改革现代性和治理性结构的范式研究,可以将中国语境下西式法治(西式现代化)之有无问题,转化为各国间社会秩序治理性与现代性的衡平问题,跳脱出“中国法治近代化的每个历史时期的立法都没有离开过的法律移植” 郭成伟,马志刚:《历史境遇与法系建构:中国的回应》,《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或者在更深层次,探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两极“建构-解构”之间的社会辩证运动问题,平视西方社会治理中同样遇到的关于价值与规则、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二元冲突与调和,从而跳脱出“本土资源论”与“法律移植论”逼仄的两难选择。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将面临来自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社会辩证运动带来的矛盾作用,“对于所有这些社会来说,根本的政治问题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统一能够调和的程度和意义”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98-199页。。实际上,无论认为法学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认为法学“具有规律般的普适性”,西式法治始终不是也不应当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最终标准。从社会治理层面看,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社会秩序的深刻批评,还是西方民主政治化最终导致的社会撕裂与无政府主义倾向,又或是西方世界在新冠疫情肆虐过程中展现出疲软的社会治理能力,无一不暴露了“西方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在现代性与治理性的辩证关系中过多强调现代性作用而忽视国家治理作用的倾向。中国的司法改革需要走出一条与西式社会治理模式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在国家治理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社会辩证运动过程中维持某种动态平衡。
The Contradic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Modernity and Governance in Judici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Zhang Shiz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he multiple rounds of judicial reforms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hav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and governance, carrying the dual expression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dimension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state in judicial reform can lead to a deeper mismatch between the modern 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needs of judicial reform in terms of structure, value, and efficienc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straints of power structure and local environment on judicial reform, the dissolution of formal justice and rule rationality by substantive law paradigms, and the "human case contradiction" in the context of judicial reform. The long-term solution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judicial reform is to propose the consensus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he modern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judicial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ialectical movement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modernity.
Key words:judicial reform;modernity;governance;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governance scheme
[责任编校 张家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