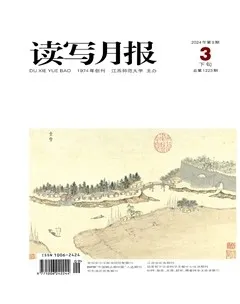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摹声之法
李月茹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是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古诗词诵读”专题中的一首古诗,以超凡的音乐表现力著称,清人方扶南将其与韩愈《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琵琶行》并称为“摹写声音之至文”。在语文课堂上,它也常与《琵琶行》作对比阅读。尽管无论是琴声、琵琶声还是石破天惊的箜篌声,复现他们当时的音色已不可能,但人们仍对以文字传达和感受各种声音抱有期待。而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常止于对写声的修辞手法和方式(比喻、联想、想象、动作描写、色彩描写等)的总结,或者将声音描写拆分成各个孤立的感官感觉(视觉、触觉、听觉等)。在将声音的被感知归结为概念式的意象、手法的功用之后,它也就凝固在单个语词中,声音与全诗割裂开来,失去了整体的浑融意味。这时,我们有必要重回文本,探寻李贺是用何种方法在文字中将声音——这个与文字分属不同知觉领域之物展现出来的。
一、以声写声
唐代音乐繁荣,郭茂倩在《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序》中有“凡燕乐诸曲……其著录14调,222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曲乐章11曲,石韶乐20曲”[1]的记载,可见乐曲调类之繁复。乐器亦是多种多样,在唐代诗歌中常见的就有琵琶、琴、箫、筝、箜篌等。音乐从各种乐器上流出,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被诗人听到,成为吟咏的对象,像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李白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白居易所作《琵琶行》作为“摹声之至文”之一,被列入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诗词名作一组中,可见其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分量。在《琵琶行》中,对琵琶声的描写主要在以下诗句中: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从演奏前的调弦试音,到“拢”“捻”“挑”的弹奏手法,白居易在演奏流程如实地交代后开始了声音的描述:嘈嘈如急雨声、切切如私语声、珠落玉盘声、莺语声、泉流声、裂帛声,众多日常生活中可听见的声音在这里逐一出现。尽管读者无法透过文字听到琵琶声,但可以借由这些具体事物所带来的联想与回忆,领悟琵琶声在不同阶段的特性:急促、低微、清脆、圆亮、幽咽、高亢清厉。白居易写琵琶声正是通过写他物的发声来引起对琵琶声的联想,可谓“以声写声”,这样的写法形象具体,因为诗人所举的例子全部来自经验,且与要描写的琵琶声同为声音,具有相同的性质,更使人觉得真实可感。
同为描写声音,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中对箜篌的弹奏是这样描述的: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这里以其他事物的声音来写箜篌声的只有两句:“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玉碎声、鸟叫声、哭声和笑声都是在生活经验中可感知的,但不同于白诗选用自然事物作为意象,李贺的意象更显出奇崛诡艳的特征。“昆山”指昆仑山,《山海经》有:“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2]在如此高地的玉碎声似乎也更清冷,更有穿透力。凤凰本身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3],有诗句“凤凰于飞,其鸣锵锵。”李贺在这里没有用“鸣”,而用“叫”来形容凤凰发声时的状态。相比于“叫”来说,“鸣”显然更厚重典雅,但诗人要的就是在没有贵贱、雅俗区分的自然状态下原始而充满生命力的叫声,由此也得见箜篌声的辉煌、高亢与凄厉。与之形成复调的,是芙蓉的哭声与香兰的笑声。花草的哭与笑使人感到声音的凄艳低宛,与前一句的清厉高亢之声复合,形成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声音气氛。尽管哭与笑、玉的碰撞与鸟叫声都可以从现实中所找到,但发出这些声音的事物却全凭想象而来,可见诗人侧重的并非写实,而是通过制造奇幻的意象,使声音不再是客观的、可以用科学仪器记录的声波震动,而带上了特定的、浓厚的情感因素。
可以看出,即使同是用以声写声的手法,李诗也比白诗多出了一点东西——使声音在一种情感中被听到。何其芳曾评道:“从《李凭箜篌引》也可以看出李贺的诗的艺术上的弱点。有许多警句,许多奇特的想象,然而连贯起来,却好像并不能构成一个很完整很和谐的统一体。那些想象忽然从这里跳到那里,读者不容易追踪。”[4]实际上正相反,白居易在形容声音时选取的意象才是分裂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联系,仅仅靠声音的相似将其串联在一起。李诗的意象看似甚为殊异,但却共同营造出一种情感氛围,在这种氛围里,各种意象成为浑融的整体,声音也就在这里出现。
二、以形显声
除去直接描述声音的诗句外,李贺的大部分笔墨都用来描述与声音一同出现的环境与其带给人的感性体验。通过可视的环境和物形的变换显出声音的不同特征,也称为“以形显声”。刘勰论创作思维时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5]作家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由想象而创作出生动的形象,借助形象来调动人们的联想,开通由视觉到听觉的感受线路,把有形之物幻化为无形之声,这种感觉上的通连现象即“通感”。在李贺这里,通感并不是作为手法刻意运用的,而是自然发生的,某一种声音与某种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
《李凭箜篌引》一诗的首句即是一处环境的展开:“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秋是季节,高秋却不好理解,为何可以用“高”来形容季节?在感觉中,高本指空间上的垂直距离之大,秋天是由热转凉的季节,相比于夏季,它更干燥、更明亮,云层和太阳似乎都稀疏淡薄,天看起来也显得更高更远。箜篌立在寥远的季节中,将天与地连接起来,构成了一种异常空旷的背景。山是空的,云也被惊到停滞不前。在这个场景中出现的声音也不能不是空而且高的。声音与环境似乎融为一体,带有了相同的感觉特征。在描繪整体环境之后,李贺引用了两位女性人物:“江娥啼竹素女愁”。江娥即舜帝的妃子娥皇,传说“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6],素女在弹奏黄帝作的五十弦瑟时“哀不自胜”。如果说首句是以空间来说明声音之寥廓,那么将两位悲剧性的女性人物放在环境中则首次为箜篌声定下了情感基调:悲愁。不同历史时间的娥皇与素女在这一刻共同感受到了悲愁,这是李凭的箜篌声所带来的情绪震荡,也使下面两句直接写声的诗句中所展现的情绪更加顺理成章。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在情感上仍沿着前文一脉写,而又有所变化。《三辅黄图》记载:“都城有十二门,霸城门、清明门、宣平门、覆盎门、鼎路门、便门、章城门、直城门、雍门、洛门、厨城门、横门”[7],是汉代都城的景观,紫皇即指天帝,是道家的神仙之宗。在诗人想象的场景中,箜篌声将整座长安城的冷气消融了,连天上的神仙也为之感动,支撑如此宏大的虚构场景的是诗人对于声音敏锐的感知力,箜篌声的响亮动人可见一斑。此时也到了乐曲的高潮:“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天裂处秋雨倾泻而下,这是声音传到天上击碎补天石而引起的后果,同时也带来了对于声音的感觉——它是激越的、暴烈的才能击破补天之石。至此,诗人似乎已经进入了音乐构成的梦幻世界。
三、以境写声
在“形”与“声”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相同性,声音才可能被称作“高”的或“冷”的。如果追问这种相同性是如何得来的,就必须回到不同知觉产生的源头。在李贺“听”箜篌声时,他并不只是用耳朵去听,而是用整个身体,因此他能够“看见”凤凰、香兰,也能感觉到连绵秋雨。在现实生活中,某人看到、听到还是闻到什么,也都不是个别感官所得到感觉的简单堆叠,身体作为整体,首先本原性地进入某种环境之中。
若考察李贺的其他诗作,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跨越不同感官领域的描写:“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8“]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9“]月漉漉,波烟玉”[10“]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11]。在对此类诗句的评注中,常出现“不可解,亦自好”的评价。所谓不可解是指无法以理性的或日常使用的的语言逻辑来解释诗中对于某个情境的展现。“亦自好”则说明这种情境并非不可理解,相反,读者在进入文本时感到非常自然和熟悉,似乎真正的环境由此才展露出来,李贺诗歌中的奇句也常出现在此类描写中。在“羲和敲日玻璃声”中,由敲日而有玻璃声得其外形的清脆透亮;“月漉漉,烟波玉”,月亮湿漉漉的如浸了水,以触觉得见光线朦胧。生活世界中的身体总是先于个别感官获得完整的感觉体验,不存在由单个的感官材料拼凑成的对某个事物的表象。身体如此直接地获得某种感觉,正如李贺诗所写的“吴丝蜀桐张高秋”,在感觉到声音时,人们就已然感觉到了琴弦的震动、高空和凉爽的气候——这些相互交织、处于同一种秩序中的物。身体所知觉的并非个体的物,先于所有个体事物而最先被知觉的东西是空间环境本身。在文本中,诗人使之显现的也不是单个的物,而是物处于其间的整个环境。
《李凭箜篌引》的最后两句,诗人已经不再用和声音有关的任何意象,转而营构一种景观:在这种景观中,现实退隐了,甚至连李凭、箜篌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为音乐所激动的神话人物和动物: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前面所述的箜篌声在此场景中更显诡怪奇幻。神女已成神仙而为“妪”,仙山中的鱼是“老鱼”,蛟是“瘦蛟”,使他们起舞的不是凡间仍享受青春的少男少女所喜爱的清靡之音,而是与“瘦”“老”的神仙相匹配的迷离恍惚的音乐;舞姿并不柔媚,而是与神巫世界相通的奇崛之舞。有人将李贺此种诗风的形成归结为用词诡怪奇崛:神女以“妪”为怪,鱼以“老”为奇,蛟以“瘦”为异,皆足以显示诗人雅不避俗,追求话语突围,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志[12]。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将“炼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分析方法,鉴赏诗句常先寻找“诗眼”,赋予某个字词点石成金之效。这样的鉴赏方式有利于学生快速找到诗歌主题和全诗的精彩之处,对于初读者和应试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学生在经过多次的练习后,常常将某字词的意义高举在全诗之上,忘记了它的突出正是因为它处在整体之中。它们作为某种标志点亮了整个诗句,把诗的意味完全显示出来,如同路标一样,它们存在的意义是将整体环境带到人们眼前,因为字的新奇而忽略诗歌整体意蕴的教学反而是舍大求小。在李贺的这一句中,尽管可见的部分是“神妪”“老鱼”“瘦蛟”,但自然界和天神对人间声音的种种神异感应而得来的幽僻气氛,作为不可见的整体更先被知觉到,也更先于词语出现在诗人的诗卷上。
当声音和环境相融后,即使声音停止,情感氛围仍然存在,听的动作持续着,只是这时我们听到的是“无声之声”,是声音的余韵: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前人评道:“结句使吴刚亦来听,不知久也。即白露沾衣意。”[13]这就是说,箜篌之乐音,使吴刚都忘怀了自己的千年不息的劳作,而转入沉吟。这一幅图画和前面的梦入神山老鱼跳波、瘦蛟起舞的动态相比,甚至与更前面的昆山玉碎、芙蓉泣露的纷纭飞跃相比,是相对静止的图画。就在这种相对静止的图画中,动荡的意象组合构成了张力,留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沉吟。而“露脚斜飞湿寒兔”中的“湿”,则是露脚的持续的结果,也是吴刚倚桂的不眠、出神忘情的姿态。在无声的环境中,人们听见了声音持久的留存。
不同的音乐诗对声音有着不同的描写方式。在《琵琶行》中,白居易通过精准的诗句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开始描写了琵琶女的高超技艺:“转轴拨弦”写演奏前的调弦试音,“弦弦掩抑”写到曲调的悲怆,“低眉信手续续弹”写舒缓的行板,“间关莺语”“幽咽泉流”则以类比突出音色。白居易的描写重点在于弹奏琵琶的手法“拢”“捻”“抹”“挑”,以及所弹奏的声音的类比。李贺的诗在描写声音时则致力于以各种物形搭建起带有浓重情感的环境,直接描写声音的诗句反在少数。对于此类音乐诗,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音乐、圖片、朗诵等形式引领学生进入诗歌的整体情境,在各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的知识性讲解之上,更应重视情感环境的描述和感受。李贺诗不谈演奏者和演奏过程的声音描写并未使读者觉得生疏隔膜,反而获得了强烈的审美体验,这种方式或许是通往音乐的一条更直接的道路,身体所察觉的首先是充满情感的环境,在环境之中声音才得以显现并带上自身的特性。
注释:
[1]朱晓娟:《浅谈唐代音乐诗》,《人民音乐》,2006年第11期,第41页。
[2]苏荣华:《从“昆山玉”意象走进李贺的梦——换种方式解读<李凭箜篌引>》,《高中生学习(阅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第19页。
[3](清)王先谦、刘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2012年,第181页。
[4]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8页。
[5]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
[6][7][8][9][10][11][唐]李贺撰、[宋]吴正子笺注、[宋]刘辰翁评点、刘朝飞点校:《李贺歌诗笺注》,中华书局,2021年,第3页,第3页,第43页,第65页,第213页,第59页。
[12]孙绍振:《雅俗交织,悲欢交集,人神共享——读李贺<李凭箜篌引>》,《语文建设》,2011年第3期,第51页。
[13]王穆之:《唐宋文学论赏丛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32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