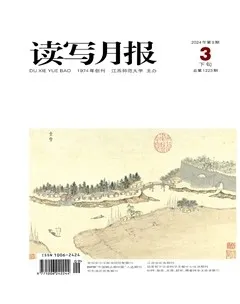年 火
王玉初
乡村的年,是一团火。
灶火是年的序曲。进入腊月,母亲便忙乎开来——做豆粑、印粑,还要炒爆米花、红薯干、花生,熬麦芽糖。做这些,都需要旺旺的灶火。
做粑是老家的习俗。做豆粑,要先将蚕豆、大米、高粱、糯米等拌在一起,磨成浆糊。灶中燃起茅草,待锅热后,用竹刷子刷少许油,然后将浆糊摊在锅上,盖上锅盖,一分钟左右即熟取出。做豆粑时,把握好灶火是个关键:火大了,容易烧焦锅中的豆粑;火小了,粑难蒸熟,且易粘锅。这时的灶火,就像是长跑,匀速跑才是最佳的。
炒爆米花、红薯干,得用大火将炒砂烧热,然后再倒入爆米籽或红薯干。这时的灶火要猛,得让爆米籽或红薯干爆开,那样炒出来的东西才香脆。可这灶火又不能太持久,一不留神会把锅中的东西炒得焦黑。炒花生,则用另一种炒法,不用炒砂,只在锅中干炒。这时灶火若大了,花生外壳会变得墨黑的,里面却还是生的,所以只能用文火慢炒。后来,家里有了高压锅,姐姐不知从哪学来了用高压锅炒花生,不盖气阀,也是小火慢炒,待到冒出青烟立马熄火。这种方法炒出来的花生特别香脆。
熬糖时的灶火最旺。爆米花和花生等炒好后,母亲会选个日子熬麦芽糖。糖水倒入锅中,得用大火猛攻。灶里的柴都是硬柴——家里请木匠做事留下的短木头、树蔸等。灶火笑红了脸,糖水就在锅中跳舞。待到傍晚时分,母亲拿双筷子,挑起一滴糖,用力一吹,成了蛇皮状,糖便熬好了。灶火未熄尽,便铲一部分出来倒入火盆,用来晚上拉糖、切爆米糖或花生糖时取暖。这时,挑几个不大不小的红薯埋入灶中,待糖切好后,扒出已熟透的红薯,香气四溢。
我家沒有团火,但住在山脚下的舅舅家有。他家的客厅有个火塘,也就是在地上挖个浅坑,平时用木板盖着,腊月天冷了便掀开,堆上一些杂木、树根之类的柴火,燃起。听说这种火塘很耗柴,住在山边的人才敢常用。
火塘上会架一个木架子,并在一角钻出个洞,立上一根木杆,然后斜伸出一根横杆,并打出阶梯格子,一级一级的。火塘有火时,可将水壶或砂锅吊挂在火的上方,边烤火、边聊天、边做饭。我坐在火塘边上吃过舅舅烤的糍粑和咸鱼,现在想起来依然满嘴留香。
不紧不慢中,我们迎来了最期待的一团火——除夕夜的火。在灶火的张扬之下,整个厨房升腾起了浓重的烟气。烟是柴火燃起的烟;气是蒸饭、炖各种食物的水蒸气。烟气中有柴火味,还有砂锅里煲的鸡香、墨鱼味,以及无以言表的年味。
“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这是父亲每年都会跟我说的传统。大年三十晚,不管天冷不冷,父亲都要烧一盆旺旺的炭火。在炭火边,父母会听孩子们汇报过去一年的成绩和来年的打算。当然,他们也会分享自己的收获和感悟,并给每个孩子送上一个压岁钱红包。围着炭火,母亲总是拿火钳敲我的脚尖,提醒我不要离火太近,不然会把新上脚的鞋烧坏。炭火很旺,容易催生睡意。孩子们回房去睡后,父母则坐在火盆边继续守岁,直到炭火快熄时,他们扒些炭灰盖住余下不多的火种。正月初一的早晨,扒开那些灰,火种仍活着,只要加上木炭,又是一盆旺火,预示着新年的好运道。
我们一直期待的家人团聚和对未来的希冀,都在年火中得到满足,也由此心生幸福。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