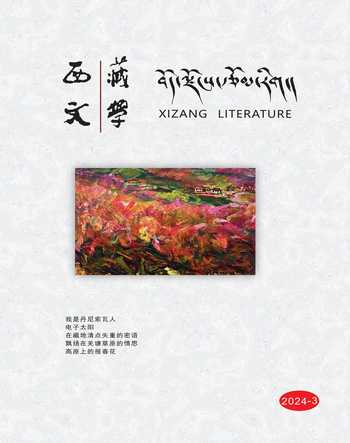池鱼
左中美
“那你说,在天堂之上和地狱之下,还会有什么呢?”
“我想,在天堂之上和地狱之下,若是还有什么的话,那一定仍是人世。”
1
鱼甲:“鱼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生活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得到,因为,你一直在我的心里。”
鱼乙:“我听过。这是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的。”
鱼甲:“我想,这是鱼水关系里写得最清澈的了。”
鱼乙:“主人都好些日子没给我们换水了。再过几天,怕是连泪都难以感觉得到了呢。”
2
鱼甲:“女主人把我称作鱼甲,把你称作鱼乙。你看,我们有二十多条在这里池和外池里,但是想来在她的眼里,我们二十多条都是鱼甲和鱼乙——我们都是一样的红色,有着差不多的身材,以及差不多的游动姿势。换一个时候,它可能把你或者别的某一条称作鱼甲,把我或者别的某一条称作鱼乙。”
鱼乙:“我想是的。就像女主人和男主人,他们虽然有各自的名字,但是在认识他们的人之外,走在大街上,在别人眼里,他们就是路人甲和路人乙——跟无数的路人甲和路人乙一样,大多数时候有着相近的平庸和安静的样子,不时有着差不多的茫然的神情。”
鱼甲:“事实上,在这茫茫人世间,所有的人都是路人甲和路人乙。就像我们,所有的鱼也都是鱼甲和鱼乙——游在相同或不同的水里。”
鱼乙:“当然,也有一点点分别。就像我们俩此刻,你是特定的这个鱼甲,我是特定的这个鱼乙。就像男主人和女主人,他们两个人相互叫‘哎!的时候,他们就不是路人甲和路人乙了。”
3
鱼甲:“主人上次洗完池子把我们重新舀回池里的时候,我被放到里面那个方池里,而这次则把我放到外面这个直角池里。我记得你上次没和我们在里面。”
鱼乙:“是的,我上次和这次都在这外池里。但之前也有几次被舀到里面过。里面的池子水深,池水凝静,外面半围着它的这直角池低一些,但是游弋的空间广一些,至少中间有一个拐角——拐角是重要的,它常常意味着新的情境,以及可能。”
鱼甲:“每次主人洗完池子,把我们重新舀回池里的时候,我们会被舀到里池还是外池,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有时候甚至只在于主人的鱼捞在从桶里捞起我们的时候是往左一寸,还是往右一寸。”
鱼乙:“可不是么,就像当时主人将我们从农贸市场买回来,原主人的手若是再往左一寸或是往右一寸,或许此刻在一起的便不是我们。”
鱼甲:“主人每两周洗一次池子,我们大家便两周一次,被主人手中的偶然性主宰着,分分合合。”
鱼乙:“主人手中的偶然性主宰着我们,而他和女主人被更大更多的偶然性主宰着。说起来,这世界不全是被偶然性主宰着的吗?我们、人以及所有的一切。无数的偶然造就了这个世界。”
4
鱼甲:“主人虽然换水还算换得勤,并随机地把我们放到里池或是外池里,借着这种偶然性,使我们得以不时地换换空间。而且他还专门寻来了易繁衍的绿萍给我们做风景,让我们在游弋的时候多了不少乐趣。然而说起来,这方天地也实在局限得很。”
鱼乙:“我想起以前我们在淮安的河后鱼庄里,院子里的那方池子虽然只有里面这个池子的一半深,却有它的两倍半那样广。你还记得吧,那时我们在一起大概有数百条,池里还有一只老乌龟,它总是游得很缓慢,我们常常取笑它。然而,那池子也不是最大的天地。”
鱼甲:“后来,我们从河后鱼庄被送到一方位于麦田间的池塘里,那里倒是宽阔得多,闻得到麦苗的青气,听得到风吹麦浪的声音,夜里看得到广袤的星空。可是,我们很快发现,那池塘只是一个中转站,原主人让我们的家族在那里繁衍得更多之后,便把我们分批地送到了农贸市场,放在一只红色的塑料盆里出售。”
鱼乙:“细想起来,其实人也和我们一样。你看男主人和女主人,上班、出门和朋友聚会,有着比我们大得多的生活天地。然而,和真正的天地比起来,他们这一点生活的天地也实在局限得很,就和我们每天在这池子里一样。”
5
鱼甲:“又一周过去了。”
鱼乙:“等下一周,主人就又该洗池子了。”
鱼甲:“听说以前他们的孩子养过一只小乌龟,还给它起名叫小翠,养在一只比钵头大不了多少的大肚、收脖、敞口的玻璃鱼缸里。那只乌龟每天无数次地从缸底爬上缸壁,试图爬出那只小小的鱼缸。可是无一例外,每次当它爬到那缸脖处,就又仰身掉了下去。女主人在看了它无数次的努力之后,实在不忍心,对孩子说‘我们把它放了吧,你看它每天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想要離开这只钵头大的鱼缸。”
鱼乙:“听说孩子虽然很不舍,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后来把这只小乌龟放进了一条河里,从乌龟下河的地方不远,就是江。小乌龟终于爬出了它的那只玻璃缸,进入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奔向它未知的诗和远方。”
鱼甲:“多年以后,他们一家人曾在一起忆起小翠,猜想它如今去到了哪里,经历了怎样的风景以及风浪。”
鱼乙:“又或许,栖身江河的小翠,偶尔也曾回忆过那只钵头大的玻璃缸,忆起它从缸底开始爬,一寸一寸地努力向上,直到爬到缸脖,然后,像过去的每一次那样,啪嗒一声,仰身掉在缸底。阳台上阳光明媚。女主人走过它身旁,出门去上班。”
6
鱼甲:“隔壁五号家这两天在装柜子。看样子,他们不久也要弄好了。听说他们都快装修了有半年了。”
鱼乙:“想来过两天,他们的窗子就会装上窗帘。我听女主人说,下面另外一家也已经装上了窗帘,应该不久就会搬来住了。”
鱼甲:“人一定要给房子装上窗,用来采光,透气,以及看见外面的风景。然后,人又给窗子装上窗帘,不让人看见自己,包括身体的隐私,以及那些无以向外人道的隐秘内心。”
7
鱼甲:“这两天池子里的绿萍又新发了许多出来。”
鱼乙:“新新绿绿的。天气越来越热,还好有这些绿萍遮遮凉。”
鱼甲:“听说在这池子里,一开始种过一株睡莲,是装修公司的一个年轻人拿来的,有着长而幽柔的茎。因为这睡莲带着根土,浑了池水,主人便放弃了。后来,女主人又带回过几株洗去了根土的小叶睡莲,在这池里时间一久,还勉强地开过几朵细瘦的、紫红色的花。可是后来,几株小叶睡莲还是慢慢地凋萎了,不曾在这池子里生发起来。”
鱼乙:“在我们之前,在这池子里还养过两拨和我们一样的鱼,都是主人从河后鱼庄买来的。在冬天,他们未能熬过寒冷,先后一条一条地浮在了清晨的池面上,然后,一条一条地被主人叹息着送出了门。”
鱼甲:“所有的事物都在时间里诞生,然后又在时间里消亡。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房子,听说以前是一片种着水稻、玉米、红薯和南瓜的河岸,在秋天时有着丰美的收成。”
8
鱼甲:“上次主人洗水池的时候,我们的两个同伴钻到出水洞里去了,卡在了里面。主人及时把它们拉了出来。在后面的那条,在水桶里休息了一大会儿之后,慢慢缓了过来。而在前面的那条因为拉出来的时候擦伤了身子,最后没能救过来。”
鱼乙:“他们可能是觉得看到了一个‘出口,可是那出水洞其实并不大,而且就算他们真的钻进去了,也极有可能是一条布尽黑暗的不归路,并不通向梦想中的远方。”
鱼甲:“主人很惋惜。这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第一条离开的鱼。”
鱼乙:“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9
鱼甲:“在我们身下池底里的这些石头,主人说是他从小区旁边的雪山河里捡来的。”
鱼乙:“听说雪山河是从北面苍山上流下来的。整条河里布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头。”
鱼甲:“这些石头,不知道它们被河水打磨了多少年,在河里每前进一米,需要多久的时间,以及怎样的机缘。”
鱼乙:“那样偶然的,它们被主人捡了回来,放到了这个池子里。这河里也有许多大石头,它们被人带离了河水和河岸,用大卡车拉着,带向了某个它们从未想象过的地方,被刻上它们并不认识的字。”
鱼甲:“池底的这些石头,它们远古的洪荒我们未曾得见,此刻却同处一室。更有无数曾与它们同沐于一条河流的石头以及被它所见证的时间,已被河流带着,或是被卡车拉着,去向未知的远方。”
鱼乙:“无尽的时间和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我存在着。”
10
鱼甲:“前两天鱼食没有了。连续两三天,主人下班回到家来,总是一拍脑袋责备自己,‘哎呀!又忘了买鱼食!为此,前天晚饭后他还特意跑去农贸市场去买,又说那卖鱼食的店关了门。而听起来女主人却并不怎么在意这事儿。”
鱼乙:“从主人把我们买回来,一直是他每天给我们投食。女主人只是偶尔闲暇才到池边来看看,看看我们游动,看看那些绿萍。”
鱼甲:“人对自己付出心力和时间越多的,便越是在意和关切。男主人就常说女主人:‘你最爱的就是你那些书。”
鱼乙:“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是你在玫瑰上所花的时间,让玫瑰显得重要。世间的玫瑰千千万,唯有那朵自己浇水长大的玫瑰最为珍贵。”
鱼甲:“由此不难理解,人爱自己的孩子总要比爱自己的父母多一些——因为他在孩子身上付出的心力和时间,要远远大于在父母身上付出的。人爱父母,大多是出于道德的自觉,而爱孩子更多的则是生物的本能。”
鱼乙:“人爱孩子、父母亲人,以及身外的事物、世界,是在爱他所付出的愛和时间——在爱他自己。一个人对身外世界所付出的全部爱意,最终都将绕回到他自身。”
11
鱼甲:“又有一个同伴离开了。”
鱼乙:“真是惋惜!主人洗水池,把我们暂时舀在水桶里的时候,它从桶里跳了出去。主人没有及时看见。”
鱼甲:“依然是和上次钻进出水洞的那条一样。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所谓出路或者广阔天地,或许只是一种幻象。”
鱼乙:“看上去,生是一种偶然,死是一种必然。就说我们这一群同伴,注定的,有一天都要离开这里外两方水池,最终告别这个世界。然而,在这注定的归宿里,又隐藏着多少偶然,或者说,这注定的必然,它最终总要以某种偶然的方式出场——假装它是偶然的降临。”
鱼甲:“这应该就是造物的高妙了,它让我们不管看过了多少死亡,都永远无法确定地预知属于自己的那个必然将在什么时候偶然降临,以致于我们在猜测和不安中,一路抱着渺茫和善意的幻想。”
12
鱼甲:“这段时间,这小区里有更多人家在装修了,整日里都是破墙、打柜的声音,实在聒噪得很。”
鱼乙:“听说主人家是第二家住到这小区里来的。前面第一家已经独自住了大半年了,见主人家装修入住,高兴得很,说终于有了邻居。主人家来了不久,左右也都开始装修,虽然噪音震耳,烦扰极大,但主人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新邻居表示了欢迎。另外,下面也有两三家陆续入住,小区渐渐热闹起来了。”
鱼甲:“可是现在,听说小区的路上到处堆满装修的沙子、水泥和各种建材,路旁停满装修师傅们开来的车。而且施工的师傅们为了赶工,往往连中午也不休息,让已经入住的人家实在烦扰得很,我们也都不得安宁。”
鱼乙:“人在没有同伴、没有邻居的时候,就希望有同伴和邻居,可是当同伴和邻居增多以后,相互间就开始起矛盾,为着这样那样的事,据说人类自古就是如此。当同伴和同伴、邻居和邻居之间的矛盾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就开始打仗。”
鱼甲:“等打完仗,变得孤单的人又开始找新的同伴和邻居。”
13
鱼甲:“据说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的,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我想这话有点太狂妄了。”
鱼乙:“若是按他这话,或许我们可以说鱼是万物的尺度,鸟也可以说鸟是万物的尺度。这天地间的万物,都可以以自我为万物的尺度。事实上,或许已经是这样了——我们鱼有自己看世界的尺度,天空的飞鸟有它们看世界的尺度,土里的蚯蚓和坐在井里的青蛙也有它们看世界的尺度。这位哲学家的话只是代表人类自己的角度罢了。可见人的认识也实在有限得很,难怪那个叫米兰·昆德拉的作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鱼甲:“若是真的有一种可以用来衡量天地万物的尺度,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鱼乙:“就是让鱼可以自由地游,让鸟可以自由地飞,蚯蚓可以自由地挖土,青蛙坐在井底,也觉得头上那片天空很美好——我想,这叫安宁吧,是的,安宁。万物自由而祥和,水自然地流淌,风自然地吹拂,季节自然地更替,而人,可以不必为了某种东西而付出尊严。”
14
鱼乙:“一段时间以来,河对面盖楼的声音每天都聒噪得不行。而且能够想见,这声音将会持续很久。”
鱼甲:“现在,人的房子已经够多的了,许多房子里大多只住着一两个人,若是另一个人不回来,回来的那个都没有个说话的伴儿。然而,新的房子还在不断地建盖。”
鱼乙:“盖的人不断地盖,买的人不断地买。许多人为了买更大、更多的房子耗尽心血。房子成了他们身上的乌龟壳,是他们最大的身家和避风港,更是他们卸不下的重担。”
鱼甲:“两三年之后,等对面那片房子盖好,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又将有许多人背负上新的更大的‘壳,在生活的泥沼里继续艰难地向前爬行。”
15
鱼甲:“女主人又要出门了,提着她那只小箱子。”
鱼乙:“她每次出门,就像一只风筝,离开家,出去短短地转上一圈,过上三五天,又回到这个家里来。”
鱼甲:“除了出门,我想着女主人每天晚上在楼上书房里的时候,也是一只风筝——借着读或是写,暂时地离开‘地面。直到她合上书本或是电脑,才又一次落到‘地上。而后离开书房,走进卫生间,拿起现实的牙刷和毛巾。”
鱼乙:“我觉得,风筝的关键不是翅膀,而是牵着她的那根线。”
鱼甲:“或者说是牵着那根线的地面。没有了现实的地面,风筝的飞翔就失去了意义。”
16
鱼乙:“楼下的小区路上,几乎每天傍晚都有一个相同的脚步声经过。我猜想他是从小区的中间穿下去,到滨河公园去散步。”
鱼甲:“我也早就听熟悉了那个固定经过的脚步声。我感觉那是一个工作安定、生活平稳的中年男子的脚步声——年轻人的脚步声大多快而浮躁,老年人的脚步声轻而迟滞,只有身体健旺、内心平和的中年男子,脚步平稳而有力。而且从他几乎每天晚上固定散步的习惯里能够想见,他的工作、生活都有着规律的轨迹。”
鱼乙:“我还从他健捷的脚步声里感觉到,这个人到中年的男子,他没有发胖。还有,他总是一个人。没有发胖,这说明他足够自律;一个人散步,说明他内心安静、有力——有许多人都学不会和自己相处,因为他们内心虚弱,难以自我支撑。”
鱼甲:“这样想来,即便是从一个人走路的姿态里,也都能看出他人生的样貌来呢。”
17
鱼甲:“之前傍晚常从楼下小区路上走去滨河公园散步的人,有一两个脚步声最近不常听到了。想来是生病了吧,又或者是出了远门,比如去了在外面的孩子的身旁。”
鱼乙:“可能是吧。有的脚步声消失一段时间后,在某一天又会重新从楼下走过,步律和声音亦一如从前。而有的声音可能再不会回来了——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人间,走去了另外的世界。”
魚甲:“还有一些人则走失在了这个世界里,失了自己的路。”
鱼乙:“往往,走失在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大多是先走失在了自己的内心里,心蒙大雾,不辨方向。待醒过来,发现路已非路,己已非己。”
鱼甲:“今天天气真好。咱们再游上几回吧。”
18
鱼甲:“河对面整日地传来盖楼的声音,从早上七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
鱼乙:“据说他们进展得很快,都已经起了几栋了。”
鱼甲:“我听说最近这三十年,这座县城已经比原先扩大了好几倍,城下的江和城侧的河两岸,许多早先长庄稼或是长野草的地方,现在都变成了楼盘。最早的县城所在的临江的一片,倒成了城脚冷清的一隅。老城里的人们但凡有条件的,都搬到了新城区,只有少量无力搬走的老居民和一些外来租户仍留在那条老街上。”
鱼乙:“自然,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由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显现出的精神世界也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世界就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你看人和房子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
19
鱼乙:“我记得去年奶奶来的时候,有时还拿一块毛巾蹲着擦擦地。今年这回来,每日便只是坐着了。她甚至在家里面稍微走动走动,也都离不开她的手杖了。”
鱼甲:“一方面是她的眼睛比之前又差了些,再者,看着她的精神劲儿也有些不如之前了。”
鱼乙:“除了一天吃两顿饭以及夜里睡觉,还有给她爱的两个女儿打电话,奶奶一天到晚便总是坐着,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或是坐在门外的小凳上,或是坐在客厅里,从清晨到夜晚。她的那根手杖,是她唯一能时时抓住的确切事物。”
鱼甲:“当一个人不再能够劳动,不再需要用力与时间争夺的时候,时间反倒在他的身上停了下来,本来由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黄昏、入夜等众多段落组成的时间,变成了囫囵而混沌的一团,变成了人在其间的几乎无晨无昏的无尽静坐。”
鱼乙:“但事实上在这里面,人和时间其实是进入了另一种交战:比如奶奶她用吃饭、睡觉、每天给二女儿和小女儿打电话这些事,一点一点地蹚过时间,尤其是她的静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地坐在某个地方,手里拿着她的手杖——任由怎样漫长的时间,都敌不过她静静一坐。”
20
鱼甲:“主人今天又给我们换了水。他把原来的水放出去,把水池擦洗干净,放上新的水,再把我们放回干净的池里。”
鱼乙:“这些水,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流来的,又在不辨晨昏的幽暗管道里流了多久,才来到这方能落进阳光、月色和雨水的池子里。同样,那些进到下水管里去的池水,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流向了何处,会流经怎样不知日月的路途。”
鱼甲:“其实这就像人一样。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落于怎样的混沌之中,无识无体。没有人能说得出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经历。人所谓的‘生前,说的并不是生之前的事,而是说的死前、是活着的时候。同样,人也不知道他死后的事,孟婆和奈何桥并不是死去的人讲述出来的。一个人,当他一旦离开这个世界,就如这池里的水流入了下水道。人就和这池子里的水一样,从无所来处来,向无所去处去,在中间,造物给了他一段时间,让他看得见日月,辨得清晨昏,识得出雨水和季节,感得到爱恨和喜乐。
21
鱼乙:“如果当初,把我们从市场买回来的不是这个主人,而是别的一个,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在哪里,每天在什么样的池水里游动,白天和夜晚都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还有,主人放在池里的会是什么植物,开出什么样的花,他会多长时间洗一次鱼池……想想,在我们相对漫长的一生里,决定着我们来去命运的,竟只是某些一闪而过的瞬间。”
鱼甲:“又或者,我们仍在这里外两方水池里,但主人却不是这两个主人,男主人或许更瘦一些,女主人或许更胖一些,男主人或许没有这个耐心,女主人或许留的是直发,他们两个人各自在这家里负责的卫生区域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分法,还有,他们每天回家的时间也跟现在的两个不一样。”
鱼乙:“像你这样说的话,也有可能,他们并不是另外的两个人,而是现在的两个主人,他们在时间里慢慢换了模样,移了性情,改变了生活以及时间的节奏。比如那时候,男主人喂鱼食的时间不是早上,而是换成了中午或是傍晚。”
22
鱼甲:“我发现,时间和水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无色无味,比如随境赋形。去年外婆在这里的时候,她总要找一些事情来做,比如她把一袋黄了的梅子一个一个地划开,摊在筛子里晒干;比如她把一袋花椒籽细细地抖揉去黑籽,在石臼里舂成面,装在一只小瓶里放在厨房的佐料台上;再有,她把几只木瓜切成片,放筛子里晒在楼顶露台上,一天上去翻一回。在她那里,时间就是一个一个划开的杏黄梅子,就是一片一片耳朵样的木瓜片,有时散发着花椒的微微香麻的气息。”
鱼乙:“女主人晚上总要看书,当她在书房拿起书本的时候,在她的面前,时间就是一页一页的书,散发着油墨的气味;时间就是一行一行的字,勾画出这世间的悲欢冷暖。”
鱼甲:“在小区近旁的公园里,时间就是流水,不分日夜地从那层层的跌水台哗哗飞流而下;时间就是柳树,春天里发芽,秋天里落叶;时间就是那在公园里散步的人们,小的才只几个月,咿呀着躺在推车里,老的已是耄耋,拄着杖,缓慢地走着。”
鱼乙:“时间就是一次次踮脚瞻望的目光。过些天,女主人就该回去老家看外婆了,她一定等很久了吧。”
23
鱼乙:“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人和我们从自我出发的对世界的认识,许多时候意味着误读。就像天气预报说今天要下雨,天却并没有下雨;说明日多云,却意外地来了一场冰雹。”
鱼甲:“主人看着我们在池里游动的时候,就像庄子看着濠水里的鱼,而我们看主人,一如惠施问庄子。‘我知之濠上也。庄子这是一句假答,濠之梁并不能提供鱼乐之明证。”
鱼乙:“作为一种常态,误读许多时候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体,误以为喜,误以为忧,误以为要,误以为不要,误以为将得,误以为将失,误以为蓬勃,误以为凋零……世界就像枯叶下面的蜗牛,许多时候只是隐约露出了半只触角。”
鱼甲:“误以为将开的花,结果半道上落了花蕾;误以为将雨的云,在化成雨滴之前被大风吹散;误以为将出的圆月,被一片飘来的暗云遮住;误以为要上楼的人,却听得他换了鞋,沉默地出门去了。”
24
鱼甲:“就要立秋了呢。这时间也过得快。平日里一天一天地,似是只慢慢地走着,等一回头,发现一大段时间又过去了。”
鱼乙:“人也常常感叹时间,叹‘朝如青丝暮成雪。尤其是平日里听主人从外面回来讲起的那些事,这家孩子结婚,那家生了孩子,这家老人去世,那家夫妻离了婚,谁家孩子又跳了桥……世事纷繁,竟常让我有‘池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之感呢。”
鱼甲:“这人世是纷繁扰攘,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啊哈哈今天你登台,哦呵呵改日他坐庄。然而这话又说回来,今日人世之事,与千百年来并无不同,人世就像一部大戏,在漫漫时光里换了一茬又一茬的演员,上演的却依然还是那些情节,上台的脸谱还是那些脸谱,唱段也还是那些唱段。”
鱼乙:“唉呀呀此一去风凉路又长,待明年盼君再回还。”
25
鱼乙:“前面下那一场雨,池壁高处都全湿了,一道一道地往池里沥水。这会儿出了太阳没多久,就全干了呢,就如根本没下过那场雨似的。”
鱼甲:“有太多的事物都匆匆走过,匆匆消失,别说是一阵雨,一片云,即便是生命,相比起漫长的时间,也都是匆匆过客,一如不知晦朔之朝菌,不知春秋之蟪蛄。所谓沧海桑田,时间能改变和带走所有的事物。”
鱼乙:“这其间,人会努力地抓住一些东西,比如一日三餐,比如房子,比如一些书籍和文字。”
鱼甲:“自然,这些东西也都终将被时间带走。”
鱼乙:“你说,时間都把这些事物带去了哪儿呢?”
鱼甲:“我不知道时间把这些事物带去了哪儿,我只知道,时间它一直还在原来的地方,一如初生。”
26
鱼乙:“小区下面临河的酒吧,听说自打开业以来生意火爆,每天晚上热闹到凌晨两三点。”
鱼甲:“大多数的人喜欢热闹,习惯在人群里栖身。你会看到这世上有许多人,一旦失去人群,他便不知身之何在。”
鱼乙:“人群或许让人感到某种安全,找到某种存在感。可是我想,人在人群里影影绰绰看到的,多是那些貌似自己的同类,却从不是真正的自我。”
鱼甲:“纷纷扰扰,喧喧嚷嚷。热闹就像河流上的浮沫,但是,这世上只有不多的人对它表示过怀疑。”
27
鱼甲:“昨天隔壁家的晚饭桌上,他们在讨论生儿子还是生女儿的事情。我听到有个男人说:‘生儿子一辈子能高兴三天,而生女儿除了生下来那天不高兴,余下一辈子都高兴。”
鱼乙:“这生儿子生女儿,原本由不得人自己做主,就像个瓮里抓阄,抓到什么是个什么。待抓到手,打开看了,其间又还有着丑俊愚敏的分别,却已全都由不得父母再造。”
鱼甲:“想起来,这人由不得自己的事也多,生,由不得自己,父母不和你商量,就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死,由不得自己,衰老、疾病以及那些意外的事故、无以把控的暗力会把你带离这个世界。父母,由不得自己选;儿女,由不得自己挑。就连干什么样的活,吃什么样的饭,一辈子走什么样的路,大多也都由不得自己。很大程度上,人是‘被活着的。”
鱼乙:“被活着,然后努力地活成是自己活着的样子,爱自己的孩子,孝自己的父母;努力干活,顯出热爱的模样;把碗里的饭吃出滋味,把脚下的路走成风景。”
28
鱼乙:“相比起这世间大多数的人都在追赶时间,赶着上班,赶着下班,赶着做事,赶着出门,甚至于赶着爱,赶着恨,一天一天地追着时间跑,奶奶却不一样,你看她,从白天到黑夜,总是安静地坐在时间前头。”
鱼甲:“可不是嘛。天亮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天黑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主人叫吃饭的时候,她正在客厅里坐着;女儿打电话说要来看她,她就坐在门外的凳子上。”
鱼乙:“我想,奶奶她战胜了时间,任凭你太阳升起,任凭你日落黄昏,她只管坐着。”
鱼甲:“当奶奶坐在那里,时间不管从哪个方向都不能够绕过她。清晨,午后,傍晚,入夜——她只静坐着,看时间落荒而去。”
29
鱼甲:“当人和我们一样,身处一个小的空间,前后左右都看不到更多风景的时候,我想,他们或许会更多地想到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
鱼乙:“天空里有云彩飘过,天空里有飞鸟掠过;风从它的远方刮过,雨从它的高处落下。天空无限高远,在无限高远的天空之上,传说有个无缺无憾的美好天堂。”
鱼甲:“大地上有泉水涌出,大地上有万物生长;蚯蚓在土里爬动,深埋多年的蝉卵从土里破壳,化作夏天的蝉鸣。大地无限深奥。在无限深奥的大地之下,传说有个刀尖烈焰的地狱,地狱的最深处有十八层。”
鱼乙:“那你说,在天堂之上和地狱之下,还会有什么呢?”
鱼甲:“我想,在天堂之上和地狱之下,若是还有什么的话,那一定仍是人世。”
30
鱼甲:“左边的邻居历经一年多的装修,前天进了新房,开了灶。右边的邻居孩子今年要上大学。再右边的人家,历经了整个小区最漫长的装修,这两天终于也要搬进新家了,听说在院里摆置花盆呢。”
鱼乙:“对面人家住在三楼上的叛逆男孩拉着窗帘,在里面放着很潮的音乐。底下某栋一户人家年轻的妈妈骑车带着女儿从门前路过,小女儿在向妈妈撒娇。”
鱼甲:“小区旁近来常有一个声音来回路过:‘叫花鸡,香麻辣叫花鸡。我猜那蹬着三轮卖叫花鸡的应该是个中年的男人,脸上写着风霜和疲惫,身后藏着一个家。每当有人从一旁走过,他总要向人露出期待的笑容——之后,看着渐渐走远的人,脸上一点一点收了笑意,一点一点升起努力掩藏的沮丧。”
鱼乙:“傍晚,总有许多人路过小区,去滨河公园里散步。我想到他们中那些退休和年老的人,除了吃饭和睡觉,傍晚的散步,几乎已变成了每天生活中最具体的目标以及内容。”
鱼甲:“那认识以及将要认识的邻居,那卖叫花鸡的男子以及傍晚散步的人,那就要上大学的、正在叛逆的以及在妈妈电瓶车的后座上渐渐长大的孩子,那缓慢迈步垂垂暮年的老者——这世间的芸芸众生,他们或许曾在某个时候窥见过天堂,他们或许曾在某个时候想象过地狱,而更多的时候,他们走在人间,把这风霜雨雪、悲欣交集的人间世,走成生命唯一的正途。”
责任编辑: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