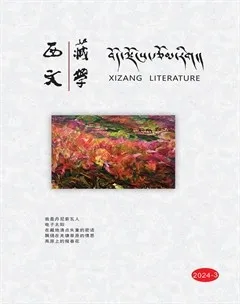柿子红了(外一篇)
李战
霜降了,大地上白白的一片,还微微地有点山雾。
“家里的柿子红了。”爸爸打来电话说。
“你把地址发过来,爸给你挑一些红的、硬的邮到你们单位去。”
“爸我还加班呢,完了再说好吧,柿子我们这也有卖的,就不麻烦你了。”
“家里的柿子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有农药,肯定比外边卖的甜!”
“爸,我还忙着呢!”
“你把地址给爸念一遍,用不了多少时间。”
我随口地一说,没想到爸爸真的邮了一箱家里的柿子过来,打开箱子的那一刻,一股淡淡的醇香迎面而来,看得出每一个柿子都是爸爸精心挑选的,大小一致,色泽光润,没有一点磕伤和虫蛀,红红的柿子就像是一颗颗红红的爱心,让我一时间五味杂陈。我很难想象年近花甲、平时都不太出门的老父亲是如何在秋风中骑着自行车带着一箱红柿子走了十几里的路,来到镇上邮局,又是如何去说服邮递员才寄来了这一箱柿子。
老家的柿子树是在家里盖新房那年,刚好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爸爸精心挑选了三棵,种在了新房的后院。二十多年来,爸爸每年都精心打理,就像对我们三个孩子一样爱护这三棵柿子树。记得小时候爸爸常说:“白露打核桃,霜降摘柿子。”每逢秋后霜降之际,三棵柿子树总会挂满红红的柿子。父亲看着挂满果实的三棵柿子树,就像看着我们三个已经长大的孩子一样,那是父亲的牵挂,是父亲想我们三个孩子了。如今这三棵柿子树都已经长得比我们家房子还高,而我和两个姐姐却因常年在外工作,不能时常陪在父亲的身边,不能每年秋后和父亲一块儿摘柿子了。
于是,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打开箱子拿出了一个柿子,小心翼翼地剥掉那层薄薄的红皮,轻轻地咬上一口,慢慢地吮吸,细细地品味,柿子的甘甜伴随着淡淡泥土的芬芳,这种纯朴的味道,不正是家的味道吗?母亲去世得早,这么多年父亲含辛茹苦把我和两个姐姐抚养长大,供我们上学,初中、高中、大学直至工作,十年如一日,而我还老觉得父亲啰嗦。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突然意識到我已然一年多没回家了,在外求学,工作十多个年头,忙碌的同时我竟然忽略了对最亲近的人的关心与沟通,一时间我思绪万千,不禁泪湿眼眶。我平复了下心情,拨通了父亲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父亲才接,听到我的声音,年近花甲的父亲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你吃了吗,西藏冷不冷,给你寄的柿子收到了吗,甜不甜?”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恨不得把心里积攒的话全说完。“爸,我准备回趟家,想看看你,吃你做的饭。”父亲压住心中的喜悦与激动继而说道:“我有啥好看的,家里啥都好着呢,你每月往家里寄的钱我都用不完,你忙着好好工作,别老往回跑,现在领导都不好说话,机票也老贵,你就别回来了。”“没事,我刚好回去出差,单位报销路费,机票订了我给你回电话。”挂掉电话后我甚至能想象到父亲喜悦的表情,这么多年父亲一直以我们三个孩子为傲,他总喜欢把我和姐姐给他邮回去的当地特产拿出去分给亲戚邻里,然后骄傲地告诉大家:“我女儿是铁路工程师,儿子是援藏大学生,这都是他们带回来的,孩子们都有出息,也都孝顺。”也许父子之间是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但父亲对我们浓浓的爱,正好比这火红的柿子,浓烈而又朴实。
茫茫的大雾再一次笼罩了整个大山,隐约中我似乎看到了父亲摘柿子的身影。秋后的日头渐短,乡村的黄昏古典而温情。父亲骑自行车接我回家时,村庄上已有炊烟升起。家乡的柿子红了,红了农家小院,红了八百里秦川,也红了咱老百姓的日子。在夕阳的余晖下同样也指引着每一个他乡游子的回家之路。
二号路口
题记:为什么说魂牵梦绕,因为所有关于童年快乐的记忆,都发生在这里。
(一)
二号路口的集市
我的父亲是一名厨师。自我记事以来,父母便终日围着灶台转。
小时候我很讨厌那个地方,父亲把前厅所有的空间全摆上了餐桌,一家人蜗居在后院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挤、压抑、终日吵吵闹闹的。最气人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时不时地到我们家饭馆里吃饭,每次都吓得我不敢出门。特别是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时候,但凡有我们学校老师到家里饭馆来吃饭,我都会乖乖地搬个小板凳趴在床边,假装着认真写作业的样子;然后天马行空地想象着小镇以外的世界——关于外星人和各种鬼神,还有我没见过的大山大河。等估摸着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再透过门缝偷偷地看一眼老师吃完了没,然后嘴里还不忘念叨:“老师咋吃这么慢呢?老师和爸妈究竟在说些什么?老师不会告我状吧?”
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有关家和童年的回忆,其中有一多半都发生在父母经营的那间小饭馆里。
那是位于西安市西南部的一个百年古镇,父母经营的小饭馆便坐落在古镇西边的一个路口,一个省道、县道和乡道交会处的市集,当地人都叫作“二号路口”。
每逢秋夏两忙,十里八乡的商户都会齐聚于此,有手艺人现场织箩编筐的、铁匠木匠做卖农具的和收易拉罐熔化了铸锅铲的,也有架起火炉子崩爆米花的、麦客小工找雇主的和摆摊卖小吃的,还有抓猪崽、羊羔和小狗、小猫、小鸡、小鸭的,当然还有耍猴、唱戏和耍杂技的……
二号路口有两家饭店,隔壁家老板是镇上的人,用的也是自己家的门面。而我们家算是外来户,是租的门面。
(二)
父亲的笔记本
那是二〇〇七年的春夏之交,父亲转让了他和母亲一手操持的饭馆,返回农村老家,专程陪母亲看病。
在收拾农村老宅时,我在老屋炕角的两个红色木箱子里找到了父亲的青春。打开箱子的那一刻,古老的气息迎面袭来,那一刻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经过简单的掸尘和擦拭,我才发现箱子的内侧竟然糊着一层一九六一年的《人民日报》,古老的印刷字体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知识青年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文章,经过周密的计算,我终于发现,那一年父亲也还不到四岁。
这两个红色木箱子就像百宝箱一样,里面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有我从没见过的粮票、油票、邮票,还有壹分、贰分的硬币和壹圆、贰圆、伍圆的老版纸币。我还发现一本印着毛主席头像的红色笔记本,笔记本每隔几页中间还有毛主席肖像和毛主席语录的彩页,中间还夹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从没见过的老照片。而另外一个木箱子,则装了满满一箱的手工账本。
我边整边问,越整理越起劲,在听完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后,我惊喜地发现夹照片的这个笔记本好像是个学习笔记,里面用红、蓝、黑三种颜色手绘着电机构造三视图,并标注了各种元件、线圈、螺帽,构图清晰逼真、标注严谨有条,简直就像是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样。我赶紧翻到笔记本第一页,一手干净利落的钢笔字,清晰地写着“户县六中工业班 李育林”。这不是父亲的学习笔记么,我激动地拿着笔记本去找父亲,想听父亲讲讲他上学时候的故事。父亲微笑着接过笔记本,翻了翻,便匆忙地交代我替他收拾好这些物件,赶紧干活。
那一年,我十四岁,父亲五十岁。
(三)
老家的新房子
由于长期接受化疗,母亲的身心饱受摧残。晚年卧病在床时,母亲常常感到自责,总认为她拖累了父亲和我们三个子女。
有时候,母亲也会抱怨两句:“别人在砖窑上搬砖的也都盖了新房子,我们也算是在外面打拼了十几年,还住在这个老宅里”。但更多时候,母亲总会悄悄地对我们三个子女说:“要不是我这个病,拖累了你爸,饭馆还能多开几年,兴许早就盖了新房。”
在关中一带,农家小院和两层洋楼,是一个家庭、一个男人、一个主要劳动力的脸面和底氣,谁家的房子修得好,谁家腰杆就硬,在村里说话也有底气。
母亲是个很有主见并且心气很高的人,所以早在很多年前,家里就已经在村里置办一套坐北朝南的新宅基地。那时候,母亲畅想着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盖一个两层的中式合院,有上下两个主屋,有一个大的会客厅、室内的厨房、洗澡间和冲水马桶,然后我们三个孩子各有各的独立房间,两个姐姐能从新房里风风光光地出嫁,我也能在新房里风风光光地迎娶。
可是,母亲终归没有等到她所畅想的两层中式合院。直到二〇一三年春,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也为了让父亲能够住得舒心,两个姐姐凑钱修建了我们家现在这个院子。
二〇一四年夏,新房正式落成。上下两层合院,有五个房间,有一个大的会客厅、室内的厨房、洗澡间和冲水马桶,前院的菜畦和果园种满了蔬果,宽阔高耸的门楼上插满了彩旗,打开枣红色的大铁门,轿车可以直接开进院内。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父亲五十七岁。
(四)
父亲的话匣子
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晾晒和期盼,终于在二〇一五年春节前我们搬进了新家,那段有关父辈们青春奋斗的历史,才正式被父亲提起。
那是二〇一五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主屋的炕上看着春节晚会,因为一条关于“家风传承”的公益广告,我提起了父亲的笔记本和那些老照片……
七十年代中期,高中是一个县城乃至整个片区的最高学府,所以高中学子也被大家尊称为“秀才”或者“先生”。据父亲讲述,那时候高中(含中专)主要分为中师、工业、农业和文艺等四个方向,而父亲则是在工业班。
当时,由于经济困难,学生是需要从家里背粮食到学校,然后统一交到灶上,由灶上的师傅根据大家交上来的粮食,来统一规划这半个月的伙食。条件好的家庭有带高粱米、玉米面以及土豆、红薯和白菜等;条件艰苦一点的学生有带麸皮、红薯蔓等,当然也有很多同学连麸皮、红薯蔓都交不上。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分产到户,家庭条件普遍比较清苦,一个青年后生那可是家里挣工分的主力。高中教育对于当时的农村学子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父亲也非常刻苦好学,所以才有了这个记满笔记的本子。
因为高考还没有恢复,大部分农村学生高中毕业就要回乡工作。一九七四年父亲正式毕业回乡,在生产队从事文书兼会计的工作,后经生产队推荐到县办企业户县太平林业场当会计。也许是因为从事会计工作的原因,父亲做事一直很严谨、很精细、很讲究,可能是有点强迫症,而且父亲打算盘的速度比一般人用计算器还快。
父亲在林业场工作多年,直至企业改制父亲才离开了他引以为荣的工作岗位。多年下来,父亲积攒了厚厚的一沓账本,视若珍宝地保存在那个木箱子里。每次收拾家的时候,我们总劝说父亲扔了这些没用的老物件,父亲却总说道:“这都是重要的工作资料丢不得,万一县里要查找当年林业场的相关资料,这都是有效证明。”
林业场改制后,父亲回到村里在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但民办教师的微薄工资和五年多来那遥遥无期的转正名额,最终还是迫使着父亲转行了。于是,父亲开始在寒暑假期间去西安、咸阳周边的工地上帮厨挣钱,这一帮便开启了父亲另一段精彩的人生。父亲从切菜、蒸馍、煮大锅饭,到面点、凉菜、热菜,稳扎稳打一步步成长为小镇上最出名的厨师。
那时候,父母已年近四十,而我都还没有上学前班(即一年制幼儿班)。
(五)
二号路口“西秦餐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思潮才真正在西北农村里扎下根,一些不甘贫穷的青年人,才慢慢抱团干起了个体户。父亲也是跃跃欲试,先后在“国营食堂”“杨师饭馆”“西秦餐厅”干炉头(在当地指高炉子师傅,即大厨),学手艺学经验,直至一九九八年,父亲正式以个人名义正式承包了“西秦餐厅”,成为“西秦餐厅”第二任私人老板。为了改善就餐环境,父亲和母亲走遍了周边县区购置新式餐桌、椅子,还设置了两个“雅座”(即饭店包间)。
一九九九年末,千禧年来临之际,父亲和母亲专程租了一辆昌河面包车,赴工艺百货商城购置了一台二十九寸的长虹彩电,并配置有影碟机和音响话筒。周星驰、周润发、成龙的电影,邓丽君、孟庭苇、罗大佑、齐秦的歌曲,从电视机、影碟机里播放出来,迅速带火了二号路口“西秦餐厅”,使饭馆成了古镇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生意最红火时,父亲同时经营着两家饭馆,还入选了餐饮协会,十里八乡有不少炉头都是父亲带出来的徒弟。不仅如此,父亲和几个同行的叔伯还根据本地饮食习惯,改良了“炒菜煮馍”“牛肉摆汤面”“臊子炒粉条”等多种小吃,一时间“李师”的招牌在古镇上家喻户晓。父亲讲着高兴,我们也听着激动。
为了维持生计,供养我和两个姐姐读书,多年来我们一家人都住在饭馆的后院,典型的前店后家,所以每年我们家都到年二十九或者年三十下午才正式歇业,哪怕店里的服务员们都放假了,爷爷、两个姐姐,甚至家里一些亲友也都会帮着爸妈,争取这年底来之不易的几天的高营业额。
那一年,父母四十二岁,我六岁。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六岁的我和十岁的二姐在大姐的带领下还是力所能及地帮着爸妈在做一些事情,哪怕只是收拾一下餐桌、扫一下地、帮客人倒一壶茶、盛一碗汤,完事儿还念叨着爸妈应该奖励我什么东西。其实那时候,我挺羡慕别家店子的,人家都是在年二十五前后就歇业放假了,而我们家总要熬到过年那个下午,卖完最后一根面条、最后一碗泡馍才肯关门。我也抱怨过,我们班同学早都买好了过年的新衣服,而我总是要等到年底了,还得挑店里不忙的时候,母亲才带着我和姐姐去商场买新衣服。
母亲常说我们家比别人家起步晚,让我不要和别的同学比较,别人家父母都还年轻。当时,显然我还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也对年龄和生老病死充满了无知。
我唯一清楚的认知,是那几年冬天真的很冷,二姐的手指总是被冻得通红。那时候,每个街口都会有几个常驻的流浪汉、拾荒者或是被遗弃的傻孩子,每逢晚上店子打烊收拾卫生时,街口那几个拾荒者总会来敲门,或讨点吃食或躲躲寒风。小时候我是很厌恶并且害怕拾荒者的,总感觉他们是“背娃婆”(关中话指拐卖小孩的人),会把小孩抢卖了去。可是母亲,总是很平常地递给他们一些馒头,有时候甚至还会有半碗烩菜。那会儿,母亲给我讲过一个道理,我用了很多年才记住并且真正理解这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责任编辑:康松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