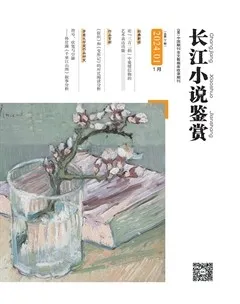《唐人街内部》中的亚裔群体困境与文化身份探寻
赖倩怡
[摘 要] 美籍华裔作家游朝凯的小说《唐人街内部》对好莱坞和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讽喻,情节既展现了亚裔演员遭受的漠视与沉默形象,也揭露了在唐人街的社會空间中,华裔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选择。本文从空间层面具体分析唐人街这一地缘政治环境下族裔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族裔间的纽带,以及从社会层面展现“通用亚洲人”的他者边缘化处境和刻板形象,进一步分析精神层面下亚裔群体处于凝视之中的精神危机,通过探讨亚裔这一群体的边缘处境与社会身份,试图寻找华裔移民后代在美国的自我定位以及未来道路。
[关键词] 《唐人街内部》 空间 生存困境 身份探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1-0085-05
族群的异质性以及移民的不断涌入,加剧了美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而亚裔也是美国主流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群体,身份书写问题是当代多民族国家构建与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美籍华裔作家游朝凯的小说《唐人街内部》获得202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以虚构的唐人街为故事背景,主要讲述了亚裔演员威利斯·吴在好莱坞奋斗的辛酸故事,小说以戏中戏的形式展开,以威利斯·吴在名为《黑与白》的警匪片中扮演龙套角色为线索,揭示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作为游朝凯的重要作品之一,《唐人街内部》集中体现了他关于“他者”和种族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这里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关注唐人街作为物质空间蕴含的不同含义,唐人街既是边缘群体所处的“他者景观”,也是亚裔群体的情感寄托之所,更是充满心理创伤的避难之所;其次,《唐人街内部》采取了反讽的方式来刻画亚裔在社会层面中的边缘处境,并揭露了美国主流社会通过为亚裔群体塑造刻板印象达到进一步维护自身的主体优越感的目的;最后,作品中体现出的“凝视”与“反凝视”,展现了亚裔的“被凝视”实则是主流社会的权力规训,而作者也通过“反凝视”的对抗来质疑美国主流社会的不公,进一步为亚裔群体的困境发声,并试图找寻未来的出路。
一、唐人街书写的物质空间内涵
对于流散的族裔来说,故国文化是他们处在一个新的主流社会边缘的诱因,同时又是他们在异国的精神寄托。对于美国华裔群体来说,唐人街的出现是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后果,并非出于华人自愿。唐人街作为华裔的主要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其文化内涵与空间意义既在华裔中传承保留下去,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因与主流社会有差异而产生冲突,每一代移民对于唐人街有着不同的情感。在游朝凯的小说中,唐人街的空间展现出三重不同的含义,其不仅是地域层面将亚裔与主流社会隔离开的边缘空间,也是情感层面承载着故国文化的记忆空间,更是社会层面充满创伤的心理空间。
首先,《唐人街内部》中唐人街的书写清晰地展现了亚裔群体所居住的“边缘地景”。小说全面而立体地展示了唐人街,给读者展示了一幅主流社会外的边缘景象。唐人街内部空间逼仄、人口密集,并且有自己的信息互通方式,只要朝着想交流的对象所在的方向,大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对方就能接收到自己的信息。每一层楼都有自己的生态系统,也有一套自己领域的规则。在这个独特的空间中,亚裔保留着母国文化的印记,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文化体,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同样的,在情感层面上,唐人街也意味着从原乡移植过来的文化习俗与情感。当共同的族群与社群生活在一起,往往会带给远在他乡之人一种心灵的抚慰。在唐人街里的单身公寓里,承载着威利斯·吴对家庭的美好回忆,母亲为他准备午餐,他和父亲共进晚餐,在自己家的这个小小空间中,威利斯·吴有了情感支撑与寄托,也形成了对家的依恋[1]。而小说中的另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华裔艾伦,作为第一代华裔移民,靠着自己的能力离开了唐人街,生活在主流社会中,也就是白人中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觉自己越来越依恋家,无比怀念故乡,于是他回到了唐人街,被当成了当地的名人。作为远在他乡的客居者,他们只能通过唐人街这种族群共同生活的形式,来维系母国的价值观与风俗习惯,以此来获得身份认同和共同的情感寄托。
“唐人街既是华人记忆滋生依附之所, 也往往是蒙受种族歧视、陋巷区隔之污辱的地方。”[2]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唐人街就是边缘的,是种族歧视的产物,因此唐人街也是充满着集体创伤的心理空间。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废除,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压迫与歧视却没有随之消失。在小说中,威利斯·吴的父母来到美国,幻想着这片“应许之地”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事实上,他们却处处遭到排挤,没有人愿意租给他们房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收入微薄,而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尽管这种理由是非法的,但却没有人在乎。于是他们去了唯一可以租到房子的地方,就是唐人街的单身公寓[1]。唐人街不仅是主流社会视为“东方异域”的地方,也是一个规训和惩罚华人的社会空间。美国社会的唐人街,实质上是种族隔离区,华裔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遭受着歧视与压迫,唐人街在美国就如福柯所描写的“圆形监狱”,在大众的注视下被惩罚与规训,其存在处处象征着集体的心理创伤。
同时,华裔移民内部对唐人街的情感也有着不同的文化认同。“唐人街成为两代华人文化差异与情感断裂的表征,是一个混杂着认同与否定的逃离空间。”[3]《唐人街内部》的主角威利斯·吴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却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融入这一片本该是族群共同体的地方,“你总是好像刚刚到达,但又好像是从未到达过,你本该身处一片充满机遇的新大陆,但不知何故却被困在了旧国的虚构版本中”[1]。对于华裔一代移民来说,唐人街就是故乡的代名词,他们对故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而对于二代移民来说,唐人街是他们的精神重负,是他们的阴影,他们始终在这种边缘处境中被隔离开,白人对华裔的歧视与限制,使他们始终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唐人街在小说中的描写既是故事发生的物质空间,同时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地理、情感与社会三个不同层面的意象。在呈现边缘景观与“异域”的同时,唐人街作为维系族群对于故乡情感的独特纽带的价值也显现出来。但本质上唐人街是一个由种族主义话语建构的“他者”空间,并暴露出亚裔群体的生存困境与集体创伤。
二、社会空间中的边缘处境和“他者”形象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指出,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他者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依赖“稳定性”的概念,而这种话语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刻板印象的塑造[4]。他认为,在殖民话语中,他者既是欲望的对象,又是嘲笑的对象,是包含在起源和身份幻想中的差异的表达。同样的,美国的种族主义移民与归化政策,也是用一系列的殖民话语来支撑的,通过将少数族裔边缘化的策略,来维护白人主流话语的地位。在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影响下,美国主流文学中对华人的塑造通常片面化、夸张化甚至是歪曲化。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不断增加,由此产生更加宽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但实际上,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种族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仍处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唐人街内部》不仅展现了亚裔群体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处境,同时,也以反讽的形式塑造出美国主流社会下亚裔群体的刻板形象,更进一步批判了对亚裔的歧视现象。
小说中处处体现着亚裔群体被边缘化的常态,男主人公作为一个亚裔配角,在电影中的角色通常是充当背景板的东方男人,之后可以升级为死去的亚洲人,紧接着是普通亚洲人三号/快递员,普通亚洲人二号/服务员,最后是普通亚洲人一号,这种无足轻重的角色将亚裔个体的个性与特点抹去。尽管威利斯·吴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将自己的角色在剧本《黑与白》中升级为一位特邀明星,但始终摆脱不了成为背景板的宿命。剧本《黑与白》中的主角格林和特纳,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格林聪明又漂亮,工作很出色,靠着自己的能力成为警队中最受尊敬的警探;特纳高大且结实,长相英俊,且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已经从警11年[1]。反观威利斯·吴饰演的角色的边缘形象,剧本并没有对他进行详细描写,仅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边缘角色,其他的亚裔龙套演员的存在也是为了主角服务,在美国人看来,亚洲人的脸和肤色会让他们感到出戏,从而想“这些亚洲人在我们的警匪片里做什么”[1],在这种边缘化现象的背后,是更為复杂的族裔关系与权力结构,小说展现出了亚裔群体在社会中长期失语的现实,他们也是美国主流社会话语运作的陪衬品。
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意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指出,定型化对于种族差异的表征是关键性的,并且这些表征似乎是自然产生的,定型化对“差异”加以简化提炼,并使“差异”本质化和固定化,并且其容易在权力明显不平衡的地方出现,而这种权力的一个表现就是种族中心主义[5]。对亚裔刻板形象的描写,就是种族歧视和文化压迫的结果,美国主流社会通过为亚裔定型,描写白人与亚裔之间生理上的差异,将肤色、五官等自然特征与亚裔顺从、沉默的特质联系起来,将这种形象定义为自然差异的结果,从而使亚裔成为合理化的“他者”。而小说正是通过对亚裔刻板印象的展现,揭露了美国主流社会对种族定型化的本质,展现了真实社会中白人与亚裔的权力不平衡,并进一步展现了亚裔族群的生存困境。
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大众文化传播最有影响力的媒介之一,其对华人形象的塑造也顺应着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唐人街内部》中,作为亚裔龙套演员的威利斯·吴是“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模范少数族裔”是美国主流社会用以规训华人的一种政治话语,强调了亚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表现出的顺从、吃苦耐劳与坚忍不拔的民族特性。这种政治话语,首先将亚裔美国人“族裔化”,抹杀了亚裔个性的多样性,同时将亚裔美国人“均质化”,掩盖了不同亚裔族群、不同亚裔阶层之间的差异,也造成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种族政治中的“疏离化”,导致其他种族对他们的嫉妒和憎恨[6]。因此,模范少数族裔话语的产生,实际上造成了亚裔群体刻板印象的再生产,并对族裔个体带来了心理创伤。
在小说中,第一代亚裔移民吴明辰、艾伦、金、朴等人来到美国,努力学习,并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成就。在这个小小的亚裔群体中,每个人都被起过带有侮辱性的种族绰号,对吴明辰来说,最使他难以忘怀的也是看起来最无害的一个绰号是“Chinaman”,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个描述词,但却在提醒着他不是白人社会中的一员[1]。他们努力且优秀,具有“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但亚裔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始终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并且永远无法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群体的另一种刻板印象体现在英语口音上,无论是亚裔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移民,这个典型的刻板印象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吴明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之后找工作却屡屡碰壁,终于在一次招聘面试之后,工作人员提点他,没有人想雇佣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口音,正因为他的口音太地道,所以显得很奇怪。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发音,成了一个带有口音的亚裔,他明白自己需要扮演好一个亚裔,才能在社会中谋生[1]。而这种偏见一直延续到威利斯·吴这一代,当他在片场说着纯正的英语时却被刻意提醒:“你的英语说得很好,好像你没有口音。”[1]之后他才意识到,作为一个亚裔背景板,必须迎合主流社会的话语,于是他只好故意带着口音说话,拍摄才得以继续进行下去[1]。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美国主流社会荒诞的运作规则,亚裔被贴上有口音的标签,这就是美国主流社会进行种族话语运作的一个巧妙的方式,亚裔也在这种虚伪话语之下以自我贬损的方式不断迎合主流社会,顺应了白人的话语权威。这种描写一方面既讽刺了边缘化的亚裔群体对美国白人的取悦心理,同时也讽刺了亚裔美国人为了生存而选择顺从卑微的屈辱选择。
小说以幽默讽刺的笔法展示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刻板形象的塑造,进一步表现出了亚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处境,仿佛他们只有迎合白人的话语,才能获得生存的空间,通过对亚裔群体真实生活状态的再现,《唐人街内部》揭露了美国社会中隐藏的种族话语压迫,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亚裔群体真实生存状况的关注。
三、凝视背后的抵抗与探寻
凝视理论在20世纪后现代理论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凝视绝不仅仅是感官层面上的观看,更涉及精神层面。从萨特、拉康到福柯,当代学者为凝视理论做了不同的补充,福柯赋予了凝视以权力属性,他认为,象征权力的凝视来自圆形监狱,社会通过军营、学校、工厂和医院,对身体进行监控,从而达到规训与控制的目的[7]。而在美国社会中,唐人街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用以压迫、边缘化少数族裔的产物,俨然形成了白人凝视下的异域、异文化之地。白人常常以观光者的心态看唐人街。剧本《黑与白》中,白人女警萨拉·格林将唐人街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他们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人[1]。在主流社会的观看、监督之下,他们成功对亚裔群体进行了规训。
小说讲述了剧本《黑与白》的拍摄故事,而演员的表演对应的就是观众的观看,亚裔龙套演员在这种观看之下,极易服从于主流权威,从而产生对自我的否定,当黑白警察称呼威利斯·吴为亚洲人时,威利斯·吴意识到自己一直都被这个词语困住了,他的亚洲人特征盖过了其他的所有特征[1],他的身份认同也受到了影响,通过这种被权力内化的视角看待自我时,他只能不断地贬低自我。当拍摄场地转移到唐人街时,威利斯·吴的朋友和邻居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他,这群亚裔演员沉默又努力,平均绩点超过了3.7,他们是努力奋斗的移民,仍然在等待着属于他们的一个机会[1]。在剧组拍摄的过程中,整个唐人街的亚裔群体的生活被展示在观众面前,也体现了他们被整个美国社会所凝视着。
除了亚裔男性,亚裔女性也处在被凝视、被观看的处境之中。作为欲望客体,亚裔女性满足了白人男性的窥视欲,受到白人男性的欲望投射。威利斯·吴的母亲作为一名亚裔女演员,在年轻时,她作为东方女性,被观看、被研究、被爱慕,面对着这种令人不适的凝视,她只能不断克制自己的厌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只有不工作的时候,她和吴明辰才会去唐人街外部,他们渴望逃出这种生活,但却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1]。而当亚裔女演员年岁渐长,她就只能扮演年老的亚洲女性,亚裔女性遭受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亚裔在白人社会里是一种“他者”景观,是被物化的对象,这也彰显了西方社会对东方的凝视。
随着故事的推进,威利斯·吴也意识到了自己一直处于他者的话语之下,并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做出了反凝视的对抗。对凝视的反思,首先要立足于消解凝视的权威性,也就是用对立的姿态来对权威进行挑战,对已有的话语体系进行颠覆并发出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置于能动的位置[8]。霍尔认为,挑战支配性的表征体系应当置身于表象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之中,并从内部进行争夺[5]。威利斯·吴从小就想成为美国人眼中的“功夫高手”,最后,他终于成功得到了成为功夫高手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他也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以白人社会的目标来衡量自身,陷進了美国社会为亚裔所建构的话语之中。经历了顿悟,他决定放弃成为功夫高手的梦想,开着剧组的车驶离现场,最后因偷窃罪而成为法庭上的被告。在最后的法庭审判之中,美国主流社会虚伪的种族话语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作为威利斯·吴的辩护律师,老大哥在法庭上罗列出历史上华人受到排挤与遭到歧视的历史事实,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引起轩然大波,亚裔在象征着美国社会权威的司法法庭上竟说出如此与主流社会思想相违的话语,无疑是在进行反击。但讽刺的是,尽管罗列出了种种有力证据,法官依然判威利斯·吴的罪名成立,最后,威利斯·吴看清了美国主流人士的虚伪面孔,意识到他想成为的功夫高手不过是另一种普通亚洲人的形象,他曾深陷种族话语的假象之下,被殖民话语内化,心甘情愿地成为美国人眼中的亚洲人,跟绝大部分亚裔一样,一直都被困在了唐人街内部。
小说展现了亚裔生存空间与个体被处在凝视观看之下的权力规训,同时,也通过法庭对峙的环节让主人公进行反凝视的抵抗,作者通过挑战美国社会的主流权威,试图颠覆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群体不公正的凝视,也揭开了美国种族话语的伪装,为亚裔群体的边缘处境发声。
四、结语
游朝凯曾经在采访里说:“我看到了我的父母和我出生在这里的孩子之间的跨度,看到了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同时,有些方面可能没有改变,仍然有部分人把我们视为外国人。”美国的亚裔群体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也依旧没有改变被边缘化的事实,《唐人街内部》中,威利斯·吴的女儿菲比在一个儿童动画片中为一个中国小女孩配音,讲的是小女孩在一个新国家冒险,随后发生的移民、文化适应和认同的故事,这个新国家是全新的空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地理位置模糊,中国小女孩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移动。这也隐喻着游朝凯对未来美国社会的构想。菲比作为第三代亚裔,象征着亚裔群体未来的希望。从儿童的视角来看,他们在与异质力量的交汇或交锋中顽强地寻找可行的文化“合作”或“合成”之道,从小就积极建构文化身份的归属感[9],这也是作者积极探索寻求族裔生存之道、文化自洽之路的一种构想。
故事的最后,威利斯·吴和父亲以及女儿坐在一起,三代亚裔同框的画面,也使人想起一代代亚裔移民在美国社会生存的历史。亚裔要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不能只谈论“一种经验,一种身份”,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因此既要保持差异,也不能忽视同一[10]。小说通过辛辣又讽刺的笔墨,揭示了亚裔群体在物质空间中的边缘处境,也向读者展示了美国主流社会话语下对亚裔群体的刻板印象,更通过凝视与反凝视的抵抗,来消解种族权威,重构自身话语,对亚裔群体的社会处境、民族身份进行探寻,同时也对亚裔群体的文化身份给出了自己的注解。游朝凯对亚裔群体做出了创造性的构想,解构了美国对于亚裔的片面化认知,小说不仅表达了亚裔群体努力摆脱“他者”形象的强烈意愿,同时也是为亚裔争取话语空间的一种全新尝试。
参考文献
[1] Yu C.Interior Chinatown[M].New York:Pantheon Books,2020.
[2] 蒲若茜.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3] 刘旻.历史与文化视野下好莱坞电影中的唐人街空间书写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6).
[4] Bhabha H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4.
[5] 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金学品.“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及其族裔意识形态考[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3(2).
[7] 福柯.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8] 朱晓兰.文化研究关键词:凝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 谈凤霞.论美国华裔唐人街童年叙事的文化身份建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10]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特约编辑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