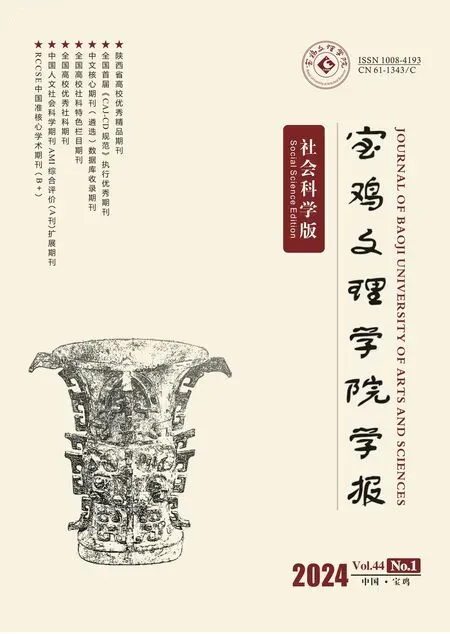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身体话语建构
——以《林泉高致》为文本的考察
韦拴喜,岳湘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林泉高致》是北宋时期一部重要的山水画论著,共包括山水训、画意、画诀、画格拾遗、画题、画记六个部分,前四篇由郭熙口述,其子郭思整理而来,后两篇则由郭思编述其父的创作见解而成。其内容不仅有关山水画的起源、创作经验与构图起形的技法,还囊括了山水画的功能和审美意涵。与西方古典绘画多以人物为题材有所不同,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李泽厚甚至认为“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1](P205),其指向某种准宗教性的皈依。在创作过程中,郭熙主张画家应该深刻地观察现实生活,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进而选择最“富有意味的形式”来加以表现。无论是郭熙从创作立场提出的“身即山川”“饱游饫看”“三远法”等身体力行的绘画之法,还是从欣赏角度所主张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可居可游”等身心安乐的审美体验,抑或从功能层面所推崇的“林泉之心”等身心合一的理想境界,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绘画艺术与人的身体或身心之间的深刻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是对于传统绘画创作经验的一种补充,进一步拓展了山水画的理论空间,使之有别具一格的审美蕴藉。
一、山水画创作与身体力行之道
《周易》中记载了伏羲创制八卦的过程,语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P335)论述了伏羲在绘制八卦图时,从对自我“身体”的观照的出发,自觉地利用自己周边的事物和经验,依此来试图体察世间万物的复杂状况,进而与天上的神灵产生交感与共鸣。春秋时期,孔子为当时的立志求学之人规定了六种必须掌握的技艺,即后来的“六艺说”,指出“礼、乐、射、御”等“身体”技能对于个人人格的完善的重要意义。
在佛教教义中,也有着高僧圆寂之后,肉体得以“涅槃重生”的说法。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身体一直处于“在场”的状态。正如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言:“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3]而艺术的表现历来讲究“言、象、意”的统一,易言之,艺术之“语言”是文本的“能指”层,是指构成艺术的基本单位,是艺术创造的基质,表现在绘画作品之中,则是画家借用符合一定比例的色彩、线条等介质在固定空间之中的交错搭配来体现其寓意“所指”的媒介。而“山水画创作不仅需要传统功力,需要师法自然,还需要美的冲动,有了美的冲动,才能激起强烈的创造欲。”[4]郭熙笔下的山水,它们所独有的形式和色彩之美正是凭借画家的个人经验、身体感知来体验到的,通过“饱游饫看”的身体力行,画家巧妙地捕捉到了不同的四时之景。
(一)身心与自然交接的“饱游饫看”
“山水”的出场最初是在郭思童年时期跟随父亲游览各地的山林泉石时,他这样写道:“思丱角时,侍先子游泉石,每落笔,必曰:‘画山水有法,岂得草草?’思闻一说,旋即笔记。”[5](P631)郭思认为,其父郭熙虽然是以他的《早春图》《幽谷图》《溪山访友图》等绘画而闻名遐迩,但是后世更应该知晓他不为人知的为人和为画的品德,他所终生奉行的“饱游饫看”的身体力行之思想的重要意义。嵩山、华山、峨眉山、武夷山,这些都是普天之下的名山大川,自然挺拔奇特、风景别致秀丽,所以常人很难全面把握它们的全部奥秘。因此在绘画创作时,势必要“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即画家要通过勤奋刻苦的训练来精通其要义,广博地饱览天下之山河,进而将自然山水之景陈列于胸中,以至于作画时忘记面前了有画纸,手中也忘掉笔墨的存在,进入了“无我之境”,此刻,无论是奇伟瑰丽或悠远迷蒙的山水之象,都可以在这一刹那间融于画家的笔端。
这与传统儒家哲学强调“知行合一”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张再林所言:“中国哲学的根本宗旨,不是主张思在同一的‘我思故我在’,而是坚持身在同一的‘我躬故我在’。”[6](P71)画家的身体在此变成了进行空间感知和自我观照的场所,“地上之山水”变成了“胸中之山水”,进而转换为“笔端之山水”。接着,郭熙举了草书大家怀素、张旭的例子,怀素夜闻嘉陵江的流水之声而令其草书之势愈佳,张旭因为目睹了公孙大娘舞剑而笔势益俊,进一步突出了艺术家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具备丰富驳杂的见识对于艺术创造的作用。因为从个人内在的生理性而言,“视觉是一种受制于条件的思想,它‘借机’从那种进达身体的东西中产生出来,它被‘刺激’去借助身体而思考”[7](P61)。
画家凭借自己的感官,得以寄情于秀丽山水之中,从而“游目骋怀”,享受“视听”之乐所带来的审美快感,这无疑是一种审美直观。近代美学家克罗齐提出过关于艺术的“直觉即表现”说,认为艺术的审美和创造是形象的直觉表现,不是某种物理的事实,而物理的事实是指“还未受到直觉或心灵综合作用的客观存在的事物”[8](P629)。虽然他在此否定了“自然美”的客观存在,不能不说是陷进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克罗齐对于主张艺术家通过感官经验去直觉自然事物之美的强调,正是肯定了“个人身心”对于艺术欣赏与创造的价值,即使他否定了艺术的社会性与社会功用。可以说,身体作为个体存在的基础,同样也是观察外在世界的窗口,然而,它并不是机械地反映或模仿自然山水,而是将自身能动地融入山水之中,在情感的综合参与下,构成一个称如叶朗所描述的“充满意蕴的意象世界”。
郭熙接着论证了由画家胸襟不广博、眼见不纯熟所造成的弊病,他以当今画手所作的《仁者乐山图》《智者乐水图》为例,认为前者之画只是描摹了一位老叟托着下巴在山边作思考状、后者也仅是画了一位老人在岩石旁边侧耳倾听水声,两幅画都只停留在对人物表象的表象摹画上,没有突出画中人物与山水融为一体、兼容互参的情状。如丹纳所言:“身体也有它的一套建筑程式,除了器官的联系连接各个部分以外,还有数学的联系决定身体的几何形体和身体的抽象的协作。”[9](P295)而卓越的画作,应该如白居易的《草堂图》与王摩诘的《辋川图》那般,充分流露出山水的别致意趣,注重绘画中所表现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人物表现与山水的整体性、一致性,而哪里又是像前两幅图一样仅凭一个人的形貌姿态就能完全表现的呢。因为中国的画法,“其要素不在机械的写实,而在创造意象”[10](P121)。画中的人物、泉石、松林、云海都是浑然同一的,互相镂刻在画幅之中,既有主客体在审美过程中的交融互渗,也蕴含画家独特的情志和意趣。
郭熙还从地域性的视角展开了论述,他认为近代的画匠若是生长在的吴越一带的就只会画东南高耸清瘦的山水,生长在咸阳附近的就只会画关中、陇西一带的壮丽辽阔之景;而绘画以范宽为师的,就难免缺少李成的妩媚秀丽,师法王维的,却又失掉了关仝画作的风骨之气。追溯以上所有的不足,都可以归结为是画家阅历太少、视野太狭窄的缘故,因此,就有必要对自我的身体行为进行反思。舒斯特曼在此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某人如果不能感受到他所坐、所站立的环境,他就不能感受到他自己在坐着或站着;同样,一个人如果不能感受到我们所吸入的周围空气,它也就无法感受到他在呼吸。”[3](P20-21)根据他的观点,正是由于“我”在某种特定环境之中与他物的整体性关联,我们得以感受到自身的存在状态和自我本质。
对绘画创作而言,若是画家的身体意识不能较好把握画幅中整体环境与某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对斑驳陆离的自然山水做出筛选或甄别,也很难采撷其精华而加以重点表现。因为千里江山连绵横亘,绘画创作不能像地图一样将所看到的自然风物全部在画作里表现出来,这时就需要“择其善者”,只把自然之中的精粹独到之处描画下来,以小见大,让观者能够“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正是源于对于自然山水的充分领略,画家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然之物的独特意义,所以郭熙强调在描画山水之时应该明白“山因藏其腰则高,水因断其湾则远”的道理,若是不能做到“耳濡目染”,就难免会犯将山体之形貌全部摩画出来的弊病,则很难表现此山之峻拔、此水之深远,而且那样的画,就与画人们用来舂米的木杵或地上爬行的蚯蚓没有任何区别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绘画史上,南朝的谢赫曾因他的“绘画六法”而独树一帜,在宗白华先生看来,“谢赫‘六法’中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是模仿自然,他要求艺术家睁眼看世界:形象、颜色,并把它表现出来”[10](P51)。同样是由“目”及“物”,从视觉而引起画家的情感与想象,都是建立在“博观”基础上对自然山水的“约取”,进而达到“迁想”与“妙得”。依此观之,这与郭熙饱游饫看的绘画理念是有契合之处的。
(二)作为审美直观的“身即山川而取之”
这是郭熙给有志作画之人的又一个忠告。按照俞丰的解释,“即”是“亲临”的意思,“身即山川而取之”即强调画家要“亲身进入山川之中观察,这样才能体会山水的真情实态。”[11](P34)自然之中的山川河谷可以通过远望感受它的非凡气势,也可以借助近距离观察获得其纹貌质地;自然气候中的风雨之态,可以通过远眺而观察到,而如果置身其中玩味就会连眼前河流与道路起止之势都难以分辨。如果画家不能涉身于真山水之中,那么,由于对这些自然风物体察的距离之不同,所带来的晦明之变化就很难客观地领悟了。因此,画家要善于将个人游历真山水之后所得出的经验和绘画创作结合起来,重视身心的真实体验,以直观的审美来观照自然山水。
山水作为画家有寄托的审美对象,如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杨恩寰所说:“任何具有审美性质的东西,只有在审美经验中才能成为审美对象。”[12](P55)而正是身体的介入使得个人审美经验成为可能,画家进入山环水绕的大自然里,经过个人躬体力行之窥察,得以发现别具一格的山水世界。学习画花卉之人,常将一株花放于深坑之中,从上往下俯瞰;学习画竹之人,也常取一竿竹子,让夜晚的月光照耀于其上。郭熙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获得所画之物的本来样貌,而这种方法与画山水画之法并无不同,因而都要对画之对象进行亲身观察,以此获取事物的真实形象。
诗人里尔克认为,“基督教的艺术失去了这种同身体的关系,并没有因而真实地接近山水;人和物在基督教的艺术中像是字母一般,它们组成有一个句首花体字母的漫长而描绘工研的文句。”[13](P74-75)他认为基督教使得艺术背离了原来发展了道路,“山水”在此变成了通往“天堂、尘世和地狱”的“短暂停驻”。如我们所知,西方传统美学自始便将审美活动视为在屏息凝视或静心聆听中获得对“理念”或“境界”的观照体悟。如此一来,审美活动就更多地依赖于视、听两种感官,而排除了其他身体官能的全面参与。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否认了美的感性形象与现实维度,忽略了审美的全身心参与以及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这种超功利的审美静观理论,肇始于柏拉图的“凝神观照”说,中经夏夫兹伯里的“内在感官”说,至康德“审美无利害”说而成为圭臬。
与上述不同,尼采则认为“美不在审美静观中,而在炽热的创造中”[14],他肯定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性,看到了审美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个体自由自觉的劳动恰恰是产生美的根本动因,画家也正是通过能动的实际体验才得以临身于山水之中,感受到自然山水带给人的无限乐趣。其实,郭熙“身即山川”的理论涵义并不仅止于此,在学者谭玉龙看来,“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并不只是吾‘身’来到自然山水面前做观照,然后对其进行艺术创作,而是画家亲临山水作多角度地审美观照,与此同时,画家自身与自然山水融合无间、浑化为一,身即是山川,山川即是身。”[15]而郭熙所主张的“山形步步移”和“山形面面看”的观点,恰是对中国绘画散点透视法的继续改造和发挥,重申了因空间距离的改变所引起画家的观察视角的变化。一座山,近几里看是这样,远几里看又是那样;一座山,正面看是这样,而侧面看又是那样,这就是“移步换景”的说法,也如苏轼所言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仅如此,一座山在一年的不同时节观看,其四时之景也不相同;在一天的不同时间对其观察,又会有“朝暮之变”。所以,画家要想对于绘画做真理性的把握,就要如郭熙所揭示的,一切的观察要时刻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因为西方的审美认知缘于西方传统“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所以需要建立“主客同一”的观点来改变这种难以调和的、分立和矛盾的不相适应关系,而在中国艺术家眼中,自然山水本来就不是与我相对抗、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本来就构成一个和谐共生的宇宙,并且彼此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是对西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纠偏与反拨,它不同于康德“人是目的”的论断,而是注意到自然与人的相互生成。
可以说,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的观念契合了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物我同源”的哲学观念,画家与他情之所寄的自然山水本就浑然同一、融为一体,画家以身体为载体,从不同的角度自觉参与审美建构,从而以一种高度自觉、包容开放的心胸与自然得以共生。并且在具体创作中,画家常以自然对人体的某个部分进行直接性的比附,山水仍然是心灵直观的观照对象。郭熙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5](P638)。在这里,他把人的肌体器官与自然界的存在物一一对应起来,彼此勾连其内在肌理,“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5](P639)经由这样一番比喻,原本凝固的山水仿佛也具有了人的情态和骨肉,变得活泼、灵动起来,给人以具体可感的形象。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里这样点评:“这真是把山水作为有机生命来看待了,古人作画不称为技而称为道,在他们的画中不仅寓含着哲理,还显示着生理。”[4](P128)因此,无论是“身即山川”的悉心洞察,抑或“饱游饫看”的躬行实践,郭熙都突出了个人的身心在绘画创作中的特殊地位,画家每一次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体认,都涵盖了知觉与直觉的相互作用,指向了对山水之乐的具身化体验。
(三)从静观走向流观的“三远法”
郭熙提出,画山有“三远说”,“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5](P639)从色调上看,高远的色调清晰明了,深远的色调深沉晦暗,平远的色调明暗交错;从意境上看,高远的意境高耸峻拔,深远的物象重峦叠嶂、相互掩映,平远的意境冲淡而悠远。作为中国绘画散点透视的重要经验,三远法可以视作画家分别从“仰视”“俯视”“平视”三个视角对绘画对象进行观察,因为画家每次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所以得到的关于审美对象的感知和认识就不尽相同。西方传统讲究“焦点透视”,即绘画者通过将视角固定在某一位置,以此来获得视域内的全景式摹写,是西方后来写实主义的滥觞。
可以说,相较于西方对画之物体的静止、机械地反映,中国的山水画更突出对自然及复杂现象的“流观”。《楚辞·九章》云:“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16](P131)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屈原被放逐之后的郁郁不得志的茫然神情与焦灼的姿态:“我”睁大眼睛来环顾四周、周流观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都。东晋时期,陶渊明也曾在《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中写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诗句[17](P82),强调了通过循环往复的“流观”之法,就可“以类万物之情”,达到人与自然的汇通与融合。至此,“流观”开始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观照方式被固定和延续下来,指的是艺术家通过不同角度的体察和介入来参与审美活动。
赏画之人“流观”的方式是“游目”,在学者张法看来,“阴阳互补、虚实相生的气的宇宙和在这个宇宙中的景象,只有通过仰观俯察、远近游目才能把握和体悟。”[18](P202)因为中国山水画家有着极为厚重的宇宙意识,而世间万物无时无刻地不处于流动变化之中,在他们的感受中,山水与人类心灵一样博大,所以“画家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大自然的内部节奏,把全部景界组织成一幅气韵生动的艺术画面。”[10](P57)但无论其表现技法如何不同,二者都与人身体的若干行为有关,杨恩寰曾对于绘画有过这样的定义,他认为“绘画艺术是心灵通过视感官与操作器官的合作,掌握相应物质性材料和媒介,从而创造二维空间即平面意象的艺术。”[19](P331基于对郭熙三远法创作规律的考量,可从身体美学的首倡者舒斯特曼提出的“分析的身体美学”的观点来分析。
首先是三种取景之法所运用的差异化身体姿态。“高远”之法需要画家采用仰视的姿势;“深远”之法需要画者以“垂首”的姿态观察山水;“平远”之法需要绘画者选取平视的视角,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视觉疲劳,有助于艺术欣赏。其次是不同的身体意识的参与。画家借此充分感知与身体内部刺激有关器官的位置或运动状态,是某种无意识的意识,通过大脑皮层的控制,清晰地感受到肌肉的调节和视野的疏通,从而引导肌体的行为迅速做出对应调整。最后是迥异的心灵感受,这是由于画家所关注的视点不同的缘故。以俯视的姿态(深远法)观照山水,因为看到的对象置于“我”之下,能够较为容易地把握其全貌,所以在心底产生了某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观者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以仰视之法(高远法)观察山水,巍峨高耸的山体直接矗立在观赏者面前,由于个体视野等生理的有限性,我们在对高山审视时很难窥其大部,所以一种“崇高感”在内心油然而生,如博克所说:“崇高对象的感性性质主要是体积的巨大,其次是晦暗,力量,空无,无限,突然性等等。”[8](P236)高峻的山峰向“我”投来压倒性态势,画家的心理受到胁迫力量的冲击,感到霎那间的惊惧与空无;在以平视的视角(平远法)进行欣赏时,“我”和山水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时的视野较为平坦开阔,画家与对象是“融洽”的关系,主体之“我”产生的是和谐的心灵感受。
不仅如此,这三种不同的观察方式对画中人物的体貌、身姿等细节表现也有规定。高远山水之中的人物明晰,深远之法所描画的人物琐屑细碎,平远山水中的人物较为冲和;在身体比例方面,明了的人物不能画短,细碎的人物不能画长,恬淡的人物不能画太大。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戏剧作品的整体结构时进而对“美”的性质有过这样的认识:“无论是活的动物,还是任何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若要显得美,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即不仅本体各部分的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因为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20](P74)根据他的理解,“动物的个体太小了不美,太大了也不美”[20](P74)。郭熙通过对画中人物形体进行合适、相宜的刻画,契合了三远法所要集中表现的涵义,符合了美的规律,使得观者在饱览画作时,借助“流观”之法也可以领悟到由相异的绘画技巧所营造的独特韵味。人物作为山水画的一部分,其或大或小、或明或暗,都与画家意欲展示的整体境意是一致的。也正是画家运用自觉的身体意识,对自己身体行为准确调控,得以在画幅中“谱成一幅超象虚灵的诗情画境”。
二、山水画欣赏与身安心乐之感
诚然,艺术观念需经艺术家个人的个性表达从而呈现为文本,从文本到作品的跨越需要读者的介入与欣赏,这是任何艺术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都不可缺少的一环。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以往的文学史往往只将焦点放在“创作者”本身,而忽略了欣赏者或读者在接受活动中的价值,事实上,读者的积极参与恰恰构成了接受活动的关键一环,因而他们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接受史”。由此迁移到绘画作品中来,就是指“一部绘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欣赏者的阅读史”,因为绘画作品乃至画家的地位都是不同时代的欣赏者所赋予的。所以后来的罗兰·巴特甚至提出了“作者已死”的主张,在这位法国作家看来,“一件事一经叙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21](P301)对绘画创作而言,一件绘画作品一旦产生,就意味着画家的“退隐”或“消亡”,同时欣赏者就在以后此画作的接受中占据了主要位置。
而正是“欣赏者”的介入,必然关涉到艺术的审美价值以及艺术品的文化内涵。如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言:“从一个人装点布置其居所的方式,从他所喜爱的颜色,从他所爱去散步的地点就可看出此人的品位、性格及面对世界和外部存在的态度。”[22](P34)迁移到山水画创作上来,就是说画家绘画的所有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技法都饱含了画家的艺术涵养、个人情趣。画家喜欢把自己的情感依附于对山水的临摹之上,画中山水也反过来滋养了画家个人的精神宇宙。纵然真山水之中蕴含着无比奇妙的奥秘,但是观者对自然山水的游览是难以穷尽的,岂能将山川美景全部揽于胸中,由于距离和时间的双重限制,一种无奈、悲寂之感随即而生。既然事事身体力行难以为继,那么,又该何以重拾“林泉之心”?
(一)“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坐卧观览之途
郭熙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法——“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卧游”之道,他认为,原先的隐逸之士大多是因为生逢乱世,所以不得已而遁世避俗,而如今正太平当道,很多人以忠君爱国、孝敬父母作为个人的道德准则,况且隐居远游或者入仕为官的行为都关系着忠孝节义的名分,因此,现在的文人雅士不用追寻许由、“商山四皓”等人的步伐,以求与他们一样。对于退隐山林泉石的志向,恬然如烟霞般的伴侣,这些普通人难以得之于耳目的事物,如若有人可以将此情景以绘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可以让我们不出厅堂,便可亲近山水之色、纵览泉壑之美。
如学者王晓华所言:“主体在作品中的隐身不意味着它不在场,身体依然是绘画的作者和观赏者。”[23](P243)根据郭熙的看法,品德高尚的人之所以钟情于山水,是因为在此可以涵养心性,澡身浴德,他们或赏玩烟霞胜景,或聆听猿啼鹤鸣,都是以一种澄静虚怀、怡然自得的“林泉之心”来观照山水的,欣赏者的个人身心不仅于此得到了放松,自然山水的不同之态也会影响观者的切身感受,“春山烟云绵联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同一座山的四时之景各不相同,也使观者获得了不同的精神疗养和心灵慰藉,欣赏者“身虽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事实上,画家以静态的“身体”来赏阅山林泉壑的方式不仅出现在郭熙的绘画思想中,依据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的记述,南朝宗炳曾提出过“卧游”之说,“宗炳字少文(中品上),南阳涅阳人。善书画。江夏王义恭尝荐炳于宰相前,后辟召,竟不就。善琴书,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以疾还江陵。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5](P584)在他所撰的《画山水序》中,他也强调了通过“居坐”的方式来游历于山水之间,“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聚,独应无人之野。”[5](P584)即观赏者以闲适自在的心境面对图景之中的四方山水,即使坐在那里也仍然能够体悟到丛林之荒远、景色之幽邃,这也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道之所在。此时,虽然画家的视野看似囿于方寸之地,游弋于陋室之中,但是由于“我”原先亲历亲为地观察真山水所得到了丰厚的异域经验,所以自我的心胸是畅开的,画之山水的形、质早已充斥于心田,“山林野壑”俯拾皆是,得以触目而耳闻之。可以说,“卧游说”的关键之法在于观者心境的“澄怀味象”与“应目会心”的神志意趣。而从词源学上看,许慎将“卧”释为“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24](P233)即身体躺下、趴着的样子。观赏者如若采取“卧游”的观赏方法,则需要屏气凝神,集中注意力,将全身心思投注于画之山水,以阔达的胸襟游目于其上,以此获取悦然畅意的心灵之感。
在对审美形态的划分中,李泽厚曾把主体获得的审美感受分为三个层次,即“悦耳悦目”“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而第三种境界作为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等级的审美能力,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相融汇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无论是郭熙抑或宗炳主张的观赏者以审美直观饱览自然山水,个人可以不需要凭借身体的亲身力行而感知到真山水之中的无限乐趣,通过“目之所观”来联想和想象此处映现的秀丽风景,或苍翠欲滴,或层峦叠嶂,都引起处在“居室”之内的人的审美愉悦,在李泽厚看来,亦是“表现为一种‘与天地参’的人的自然化”[25](P500)。这暗合了他致力于建立“情感本体”的需要,而身体的自觉运用与意识多功能的交错互参在此过程之中得以成熟,而正是从“人化的自然”里生发出审美动因,使得主体的审美行为成为可能。
除此之外,日本在13世纪前后曾出现过一种蔚为大观的园林艺术,名曰“枯山水”,最初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一种艺术形式,实际上是微缩制景观。其一般用细沙表现流动的水景,用大小不一的石块象征山峰,整个布局错落有致,结构搭配井然有序,颇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作为当地寺院僧侣用来静观与冥思的场所,它精巧玲珑的规制不由得引发人们由衷的喜爱之情。因为它的特殊样式,观赏者可以将园中情景尽收眼底,同样以“卧游”之法,不下堂筵,得以一览其样貌与形制。而其所追求的“枯寂”“幽寞”的独特意趣,自然地使人产生出某种“物哀”之感。
观赏者在赏玩的同时,由于近处的悲寂、枯瘦之景,个人的感伤情绪也受到触动,这与中国“感兴”传统是有共通之处的。僧人在“禅定”之中忘记了时间之维的存在,全然沉浸于内心深处的空无与寂静,获得了恬静幽玄的心灵体验,可以说,“枯山水美学是极度注重精神与内心的,并对之提出较高要求,关于心境沉淀,关于内心觉悟,关于精神冥想。”[26]客居者在庭院里驻足观赏,身心的疲惫之感逐渐褪散,灵魂得到了休憩和安顿,精神也因此获得某种归属之感。不论是郭熙“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艺术寄托,还是宗炳“卧游”的身临其境,实质上都是对个体的私域空间做了美学的延伸,有形之物是有限的,画家在山水画创作时借助区域的留白,在整体画幅上铺设起“无形”的意境,真山水的妙趣从而跃然纸上,鉴赏之人可以从中感受到同等的兴味,获得心满意足的身心体验。
(二)“行、望、游、居”的处身性体验
既然可以“坐穷泉壑”,那么观者还有必要涉身于真山水当中吗?郭熙承续前人的观点,认为今之山水分为可以漫步其中的、便于观望的、悉心畅游的和能够怡然安居的,而后两者似乎更合人的心意。事实上,郭熙在此营造了四种各异的居住形式,游览者进入不同的山水空间里,便会捕获迥异的审美体验。无论是通过“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的躬身履历[27](P301),还是借助变化性的游动欣赏,都旨在重构一个适宜我们“诗意地栖居”的现世家园。由于建筑是人得以安居的第一场所,是“客观存在”于外部世界之中,它与绘画艺术所营造的“空间意象”有着相似之处,其不可避免地与个人的处身性体验产生联系。诚如舒斯特曼所言:“如果说建筑空间的连接方式是出于改善我们生存、居住和体验的目的,那么,身体则是空间连接最为基本的工具,因为它提供了体验并连接空间的关键节点。”[28](P224)因为“自我不是一个内在化的意识或是一种深入的主观性,而是一个认识到自己的特性与其居住的地理位置想联系的扩展的自我。”[29](P76)恰是自我身体与不同环境之间所建立的空间性联系,由此萌发的关于生活的美学想象,人们得以从混乱与无序的现实之中脱离出来,在有限的生态之维中释放疲困的身心,来啜饮自然景致的甘泉、填充内心对美的饥饿感。
1.可行与可望的身体感知。“可行与可望”是郭熙主张通过山水来容身安心的第一重境界,观者在此或悠然闲步、或登高远望,个人的步态、形貌、体格无不融入一系列的身体行为之中,不仅是自我意识到的身体,而且在他人看来这种变化、运动仍然是一以贯之。单一视角与多重视角下的山水之景是不同的,登高而望时,山水之胜景全部收于观者眼前,秀丽壮阔的山河充盈了我们的心胸,此时个人的呼吸吐纳、说唱吟咏都感受到无比流畅,动情之处,自我的身体也仿佛贯穿了滔滔气势,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心自如,心底产生了某种“荡漾感”。
因为“环境是被身体体验着的环境,身体是被环境塑造着的身体,正是在环境中,身体才意识到其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30]当穿行其中,观者的视野时刻处于移动之中,韧带、脚关节、双臂进行着有节奏的运动,此刻人走景移、挪步换景,不仅如此,在山水画创作中,当画家笔下的山川林木都朝某一方向延伸时,原本不动的山川、远水这时似乎也具有了动感,这是心理认知的“共方向”缘故,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片段性的局部往往能在人脑中形成一个连续性的有机整体,观者敏锐地捕捉到整体之中的某一对象有向同一方向移动的趋势,其容易被我们感知为一个游动的整体。
正是眼睛、手脚的协调和配合,我们得以在山水中“极视听之娱”,享受身临山川的妙趣。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身体作为主体也受到这个世界的客体与能量的影响,所以也就吸收并隐约记住了它们的规则,并能记起空间与地点特征,而无需有意的追忆或反省。”[29](P97)无论是画家还是赏画之人都是个体的存在,本来就寓居于原生世界中,与自然共呼吸、和万物共命运,自我与外在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互为本质,主体之我与客体的山水之间的关系是一元性的,因而就无所谓“介入”和“参与”,对自然进行有意的观赏或模仿,甚至做出定义和判断。
我们只需要运用日常经验,凭借自己生活于此的肌肉记忆,追寻逝去已久的田园生活,重拾林泉之心,拥抱那份真挚的山水情怀。也正因为这种经由我们经验和习惯所习得的内隐性记忆存在,在设身处地的游览中,“我们不仅能记住我们所蛰居的空间,记得如何顺利走过那些空间的路途,我们甚至还第一次认出并学着记住了某处空间。”[29](P97)可见,画家在采撷经典的山川水泽时,也仍然有着运化无形的身体实践。台湾艺术家蒋勋也提出了“行走的美学”,强调人类要合乎美学规则的“移动”,通过行走的“快与慢”来平衡生命的节奏,经过长期对宋代山水画的观察,他发现“亭子”这种建筑形制的出现,就是引导观赏者注意游览中“行”与“停”的艺术,因为美的生成就是得益于身体之维在空间中的动态转化,郭熙可行、可望的观点,扩充了山水画的审美意蕴,衍生了“栖居与优游”的生活美学。
2.栖居与优游的身心同乐。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模式,人类除去获取维系个人生存的基本资料,也有求得认同与归属感的需要,郭熙所推崇的“山水之乐”,不仅是耳濡目染的浑然美景,更是“我”栖居山水之后在心理上得到的某种自足和安全感。“栖居与优游”是郭熙所极力认同的,他认为山水画创作理应以此为依据,作为赏画之人的存身之所,饱含了我们共有的家园意识与生命理想。也就是说,无论是画家或者观者,能够进入山水的这般境界,就不至于像现代人一样,身心陷入“进退失据”的两难之地。
如在对现代建筑缺乏“氛围感”的批判中,舒斯特曼坦言:“建筑的一个关键维度是,建筑组织严密的空间对居住于其中并在其中过活的人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又能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带来什么。”[28](P232)既然身体体验对于建筑设计如此重要,那么对于绘画创作而言,若是画家能传神地表现出“可游可居”的山水之境,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审美参与感。
构建一个真正适宜人类居住并能给予人精神满足的快乐环境,也同样属于环境美学的基本范畴。在对生活在北美的土著——印第安人,与他们所生活的土地二者关系的分析中,阿诺德·柏林特指出了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当地的纳兹帕西印第安人首领甚至认为“土地和我自己是一个概念,土地的实质和我们身体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以柏林特断言:“如果没有和环境的身体联系,尽管我们拥有住所我们仍会觉得无家可归。”[29](P77)而在生活美学领域,学者刘悦笛在批判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艺术的否定功能最终滑向“乌托邦式”的唯美主义解决方式时,他说:“任何一种审美乌托邦,无论是神学化的还是非神学化的,无论表现为强式还是弱式,都具有共同的旨归——‘人对感性幸福的终极诉求’。”[31](P35)然而要致力于建立艺术与“大地”、现实的联系,提供一种可能的“生存意义上的美学”,就需要将日常生活得以审美化,找出沟通生活实践与艺术表现的桥梁。
尤西林也认为,“审美主体力求回溯到现实审美的感同身受,如一幅画作与一首乐曲,从而引导欣赏者从艺术符号状态返回生存体验、沉浸于体验状态。”[32](P71)由此可以见出,如何准确引导个人身心与环境融合共生,把在艺术领域培养的审美注意、审美感受转化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力,将人对艺术品的“卓越”品质的关注转化为追寻一种高质量的幸福生活,成为中外文艺家一致关注的热点话题。
然而,强调绘画中对“栖身性”的关怀,并不是要求绘画表现应恪守某种“写实主义”,以抛弃理想化的形式而拘泥于摹画现实,而是致力于探索出一条契合人身体感受和美的规律的路径,让山水画不仅只“居厅堂之高”,也可以处于“田园之远”。因为“我们和空间的关联其实并不是一个不带肉身的主体与一个遥远的对象间的那种关联,而是一个居于空间中的主体和他所亲熟的环境或曰场所间的关联。”[22](P23)不仅身体寓于其中,而且环境中其他要素的改变也会引起我们观感上的变化,在欣赏郭熙《早春图》的时候,我们仿佛沿着那条青石小径拾级而上,在狭长幽静的空山中听到了早春时节的鸟鸣以及泉水解冻发出叮咚的响声,两旁的树已经绽开新芽,整个一派繁荣生机的景象。远山褪去了冬天时的冷峻和肃穆,如今变得活泼、明朗起来,而观者的心灵也因此受到触动,由烦闷忧郁转为舒坦愉悦。
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返乡诗”的评论中,他认为诗是人“安居”的基础,但人的安居并非停留在某种现实层面的活动形式,我们应该丢弃这种惯见,而我们得以安居的诗之创造,乃是一种“建筑”,还包括经由人手而制成的一系列作品,因为作品本身就创造出一个意蕴丰富的感性世界,“人只有当他已经在诗意地接受尺规的意义上安居,他才能够从事耕耘建房这种意义的建筑。”[33]这样看来,观者唯有诗意地接纳寓于山水之中的某种内在尺度,才能真切地体悟到山水的真正价值与内涵所在,从而由外在的感性认识变为精神的向内生成,以此临身于可游可居的真山水之境。
三、山水画功能与身心合一之境
天人合一是中国审美文化之魂,冯友兰认为中国人自古讲究四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就是指向“审美之维”。可以说,天人合一体现在个体身上就是身心合一,而山水画又是让人足不出户便可达成身心合一的有效途径之一。西方传统绘画强调以人物为中心,而中国山水画却与此不同,后者更突出人物与自然山水之间的“统一性”,有时省略了画中人物的性别,将人物有意地消融于山水之中。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印象派画师塞尚的《大浴女》,乃至后来波普艺术的领袖安迪·沃霍尔的名作《玛丽莲·梦露》,这些无一不是对画中人物进行近乎写实的刻画,突出他们五官的细节,如手的细节、眼部和头发的处理,放大了形象的“性别”特征,以放置于突出位置来实现某种预期的效果。和上述不同,中国山水画中的“人物”并不是作为某种“肖像”式的登场,他们在画幅中的形象是与全部环境密切配合的,并不刻意突出局部的细节,人物的样貌姿态其实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形式,当注视个别要素时,往往能够同时给画家和观者带来一种把握全局的“冲动”。山水画里的大大小小、或高或矮的人物,都深刻地关联在整体的画境氛围之中。画家不仅赋予他们相对应的“线条形式和色彩”(身),还予以特定的“内容和文化属性”(心)。这样一来,一旦欣赏者参与其中,不同的审美经验就产生了。
山水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样式之一,传世的像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明代仇英的《桃源仙境图》等,画中人物都与“场景”的表现相互契合,构筑了一片静谧安宁的自然空间。特别是《千里江山图》,可谓是宋代士人山水理想的缩影,茅屋草舍与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与山林鸟兽,都蕴含着自由和生机。篱笆院落中大人、孩童,泛舟而行的摆渡者,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的“身体特征”似乎并未有明显的“区别性”差异,彼此的生活都与这自然山水不可隔绝,但他们的在场都无可避免地附带了一定的伦理内涵。农人耕田播种、行人赏景游玩、荡舟之人也在专心于自己的活计,画中人物的行为与整幅画的冲淡悠远意境相适宜,体现了一种古代社会的“中和”之美。在此,消泯了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对立,一切表达均以“和谐美”为基准,包含了画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在郭熙的山水画中,人物在他的画作里“出场”很少,在他的画论中,主要叙述自然之景与画家或欣赏者个人身心之间的紧密联系,注意到自然山水所蕴含的某些“人格特质”。
因为追本溯源,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观不仅有审美形式上的,还有重视伦理关怀的道德践履,而后者仍然是以“身体隐喻”的方式来进行。绘画承载了画家对于美好人格的追求,借自然风物的情态比喻善的德性,蕴含了天人合德的儒家精神。事实上,这就是画家运用了“比德”的艺术技巧,在李泽厚看来,“比德”即是“以自然景物比拟于伦理道德的品德来造成与情感的联系”[25](P326)。比如,郭熙认为画家在画山和长松之时,要尽力呈现它们二者不同形貌,“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5](P635)“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其势若君子轩然得时,而众小人为之役使,无凭陵愁挫之态也。”[5](P635)在画山脉时也应把握如下尺度:“春山淡怡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5](P634)“山,大物也,其形欲耸拨,欲偃蹇,欲轩豁,欲箕踞,欲盘礴,欲浑厚,欲雄豪,欲精神,欲严重,欲顾盼,欲朝揖,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下瞰而若临观,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体也。”[5](P638)可以说,“中国画运用笔法墨气以外取物的骨相神态,内表人格心灵。”[10](P130)因此,无论是将高峻的远山比作君主,还是借高高的松树来喻指君子,或临摹山水浑厚庄严、磅礴壮丽的多元形态,都是把自然物的形貌进行了“伦理”化的表征,这种处理也使绘画的表现愈加活泼灵动。这种以文化的方式对山水的介入,呼应了“人天同象”的观点,即人与自然万物有着相同的“道”,二者在本质上是相符的,因为在山水画家这里,“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34](P23)。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画家将自然赋予某种人的动作、情感或德性,依然是“无功利”的,距离现实有着一定的间隔,并不等同于变相的“文以载道”式的劝说,观者的参与仍旧是自由的、开放的。
人与山水本来就是交感相生的有机整体,虽然山岳与古松象征了人的高贵品德,进入了文化的、伦理的维度,但是其仍然是从视觉和听觉所能观察的自然域生发才得以显现,“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35](P52)。寄托文人美德的自然,首先必然是符合它自身的客观性质的,像具备一定比例的体格、不蔓不枝的长势,这种整齐的形式便于画家进行把握和感知。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劳动创造了美,美可以看作是人某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为唯有人这个主体的能动参与,自然才能成为审美对象。蒋孔阳也认为,虽然有时候“人的劳动并不直接改造自然,但却通过自由的想象和幻想,来自由地支配和安排自然,使自然从自然的规律中解放出来,变成符合人的主观希望的自由形象”[36]。作为一种类比联想,正是这种有意味的造型形式激起了我们的“身体”观照,以追求对于高尚品质的景仰或认同。
“人画山水时,并不意味着是‘山水’,却是他自己;山水成为人的情感的寄托、人的欢悦、素朴与虔诚的比喻了。”[13](P76)移情作用正是将自然界原本无生命的东西赋予其意志和情感,按照劳勃特·费肖尔的看法,移情就是“我自己身体组织的象征,我像穿衣一样,把那形式的轮廓穿到我自己身上来。”[8](P589)可以说,他见出了主体身体与对象活动之间的微妙联系,画家以身体作为塑模自然的对象,不仅合乎自我身体的内在肌理,还流露出于以超以物外的“林泉之心”对体验山水美景的期待。而且在朱光潜看来,“人不但移情于物,还要吸收物的姿态于自我,还要不知不觉地模仿物的形象。”[34](P23)画家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方式来传达自己渴望超然物外的情操,并且,在儒家乐天知命的伦理观念下,曾点所持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理想也仍然是以“身体”的登场来呈现,万物合德,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得人性获得充分的“完善”,个人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这与郭熙的绘画理论是一脉相通的。
不仅如此,“逍遥”“齐物”的态度也可以视作道家在协调人性与自然伦理之后,对山水所做的观照与救赎。作画之人应该“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这样才能将“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而然地罗列于心中,做到心手同步;观者也宜“以林泉之心临之”,而勿“以骄侈之目”来进行观赏,以此来获得审美精神的领悟与理想道德的启迪。郭熙正是见出了身体的反思意识,从饱览“有色”山水进而通达观赏“无形”之神韵的艺术境界,经过个体的能动反映,我们消除了主体的自我与客观存在之间的裂隙,在“心”与“身”的统一里,仿佛进入了自在逍遥的意境,物与自我达到了人与自然世界本源的合一。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山水画论大多是画家或艺术家个人绘画创作经验的自觉总结,强调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个人独特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式,认为绘画是主客统一的活动,是画家精神世界的能动反映。山水画贵在“写意”,注重欣赏者的对画作的“妙悟”和“心领神会”,绘画主题则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以及艺术对观者现实生活产生的实用效益,其以身体实践为出发点,最后落脚于观者的身体改良。反观西方绘画理论,不仅有艺术家的经验总结,也有美学家、哲学家的感性批评,比如阿尔伯蒂的《论绘画》、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其更多的是从艺术的本体出发,揭示艺术的起源、表现及功能和价值。在艺术接受过程中,注意到观者对艺术作品进行阐释和分析的合理性,处处充满着“理性的玄思”,其内容更多刻画的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与“不相协调”,这缘于西方绘画贵在“求真”与“写实”,认为绘画是画家对自己的主观精神或客观世界的“模仿”。
可以说,中国画论关注人,关注人的身心自由;西方画论关注语言,关注艺术本体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山水画论的认识侧重于文本阐释或对画家主观精神的“超越性”分析,强调审美活动的“主客同一”性,虽将艺术作品视为“心感于物而生情”的产物,但往往把绘画创作近乎人为地割裂为“构思”和“传达”两个部分,认为前者重观念,后者重技巧,并未找到一条可以统摄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纽带。这正是因为忽略了艺术家主体的身心体验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这恰是审美经验得以生成的动因。然而,无论“身体”是作为传统山水画的直接表现形式,还是以“隐喻”的方式存在于文人对绘画的认识和品鉴之中,在古代都始终是一个“在场”的存在。
《林泉高致》虽篇幅短小,却微言大义,含蓄蕴藉,思虑周全。作为一部山水画论成熟期的理论总结之作,它以身体实践为起点,以身体感知和体验为主线,以身心改良为旨归,系统建构起了一个囊括艺术创作与身体力行之道、艺术观照与身安心乐之感、艺术功能与身心合一之境的层次明晰、内涵丰富的山水画论体系,揭示和阐明了身体与艺术之间的天然联系。作为北宋山水画派重要的代表人物,郭熙在长期的艺术观察与艺术实践中,不仅明确将身体知觉运用于“三远法”等绘画技法,注意到人在欣赏山水时内心所含有的某种“比德”的文化心理,此外,他还要求画家应该“饱游饫看”,充分地游览自然山水之景,将艺术家“身体力行”的实际体验提到了首位,观者尽管“居于堂筵”,也依然要怀抱一颗真山水之心。
重审“身体”作为绘画视角的合法性,有助于向内联结艺术家个人和艺术作品、向外建立起世界与受众之间的良性联系,可进一步激活古代画论的身体话语资源,为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及艺术的现实关切提供一条可以参寻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