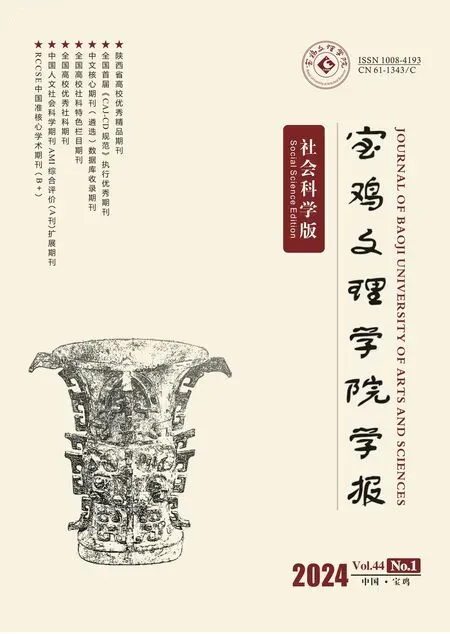20世纪日本的妇女解放斗争与法律发展
[日]渡边洋三 著 宋海彬 译
(帝京大学 法学部,日本 东京 173-8605;西北政法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中国 陕西 西安 710122)
一、总论
男女平等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持续进行的妇女解放斗争问题。虽然妇女地位从近代开始一步步提高了,但众所周知,在各个方面都还存在差别。这些差别广泛存在于家庭生活、雇佣劳动、政治权利,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但它们无非是资本主义阶级差别所带来的各种形式的差别罢了。因此,要求从这些差别当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解放斗争,就构成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但有的人却不从这种阶级观点看问题,而把妇女解放斗争歪曲为女性针对男性的斗争。男性的差别意识不是没有问题,但那种差别意识本身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包含男性在内的工人解放与妇女解放是表里一体的。不从阶级斗争整体当中把握妇女解放斗争所处的位置,而是把它偷换为针对男性的斗争,这完全是一种小市民式的构想。①
一般地说,整个19世纪对女性工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最醒目的印记。由于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导致资本主义对非熟练工人的大量需求,妇女、儿童被卷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构成整个工人阶级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撑因素。②因此,妇女、儿童劳动条件的改善同样是全体工人阶级的要求。在自由竞争阶段,在男性及成年工人的保护立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妇女儿童劳动保护立法的出现,在一个方面也是包含妇女在内的全体工人的阶级斗争的产物。③然而,这些妇女儿童劳动保护立法只不过是带来了部分程度的改善,女性工人的地位在整体上仍旧还是极其低下的。
整个19世纪,与女性工人的这种低下地位相呼应,她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很低。家庭当中妻子的地位与丈夫之间完全不对等,尤其在财产上更是受到大量制约。在政治上,尽管有些人很早就提出了妇女参政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所以历经整个19世纪,最终都没能实现。④
妇女运动的正式展开与提高妇女地位立法的正式出台乃是进入20世纪之后,尤其是“一战”以后的事情。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代替“一战”当中服兵役的男子,大量女性成为工人,女性工人的发言权提高了,其社会贡献也得到了广泛认同。“一战”以后,国际劳工组织(ILO)成立,其订立了各种保护女性工人的条约,宣告了女性劳动条件的国际标准,女性工人的力量成长起来了。作为对女性工人地位上升的反映,她们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一战”之后认可女性参政的国家也逐渐增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大的国民总动员的战争,女性代替男子走向职场的状况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而且战争结束以后也并没有退出,女性就业在社会上确立下来了。在此基础上,从信息、出版、教育等领域开始,新的专门职业种类的出现极大开拓了女性劳动市场。避孕技术的进步,育儿所的完善,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等等,这些对女性就业的进一步促进,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以后,致力于女性地位与权利状况提升的国际组织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被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等国际组织通过的条约、宣言,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与战前相比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从内容上看,从禁止人口买卖及卖淫条约⑤、妇女参政条约、婚姻登记条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到改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禁止就业及待遇上的不平等、保护妇女生育、反对教育上的差别对待等条约,确实包含了大量的内容。⑥[1](P233)这些国际条约和宣言的制定,促进了妇女解放斗争,成为促使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面对实际生活当中还广泛存在的男女差别的制度、习惯和意识而更加高涨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成果的促动下,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国陆续开启了旨在提升妇女地位和确认妇女权利的法制改革,形成了一个世界潮流。在家事法领域,夫妻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各自国家及文化圈所固有的宗教传统或文化传统的限定,很难为其确立共通的基准,但即便如此,在各国围绕夫妻财产制度、离婚制度等的法律改革上,仍然可以看到共通的方向。而且不限于家事问题,各国都开始着手确立各种法律保障措施,普遍禁止各个领域的性别歧视。作为这些动向的总体汇聚,1975年被设定为国际妇女年,世界妇女运动迎来了新的时代。
以上,我们回顾了战后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巨大进步和在其推动之下妇女法律地位提高的情况。尽管如此,妇女解放在实际上获得了多大程度的实现——各个国家自然会有不同——却仍然还是难以确定的。虽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不是本书的课题而在此不得不略而不谈,问题在于,尽管有了法律上的规定,而由于对现实社会当中妨碍妇女解放的各项因素并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分析,所以也难以从理论上对妇女解放斗争的前景做出多么清晰的展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妇女解放斗争在阶级斗争当中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清楚。这一点,我们从社会运动的层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妇女运动不再像以往那样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反过来说,现在妇女解放斗争的严重缺陷就在于,不能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到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环节上去。那种把妇女解放斗争消解到一般工人解放斗争当中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妇女解放乃是包含男性在内的人的解放这一政治课题的一种特殊形态,忘记了这一点同样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妇女问题如果不能被设定为包含妇女在内的全体工人的政治任务,那么到头来,妇女解放斗争就无非是一部分拘泥于两性差别现象的小资产阶级的运动罢了。
就世界范围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运动,在国际妇女年上都提出了各自的构想和目标。从这些构想和目标的巨大差异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上述问题的表现。比如,美帝国主义是人的解放的障碍,而美国的妇女运动注意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样就能够与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发展中国家妇女运动拥有共同的基础。但在美国的女权运动那里,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够充分,尤其在人的解放这一普遍立场上并不明确,所以与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之间无法形成共鸣——她们在面对性别差异之前,不得不首先面对民族差别问题。但我们又完全可以说,这些不同构想的斗争彼此共存的状况,恰恰又为发达国家的妇女提供了一个学习契机,让她们能够重新看到妇女解放斗争乃是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
二、“二战”前日本的情况
日本战前的女性工人处于日本低工资劳动的末端,正如女工血泪史所典型反映的那样,在封建身份性的劳资关系的媒介作用下,资本主义剥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家庭中,在“家族制度”的压迫之下,妇女的自由和人权是无从谈起的。至于其政治地位,不享有参政权是当然的事情(连男子也并非能够普选),而且在治安警察法之下,一切政治自由都被剥夺了,不能参加政治结社,就连政治集会也都一概禁止参加。哪怕我们说,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完全是在妇女在一切方面的无权状态和男女等级差别之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说法也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为使妇女从这种无权状态解放出来的斗争却绝非不存在。女性劳工运动在明治10年以后就已经出现。以纺织、制丝女工的罢工为中心开展以来,从大正到昭和,掀起了大量纺织斗争风潮。明治末年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站在妇女解放的条件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开始处理妇女问题,要求保护女工。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工厂法的制定(明治44年,公元1911年),其后在大正15年(1926)又被修订。众所周知,虽然修订后的工厂法,在改善妇女的低劣劳动条件方面比修订前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与其它国家相比,却仍然还是非常有限的。大正末年组建的日本工会评议会重视女工问题,要求制定进一步推进女工保护的法律,不但最终未能实现,反而在昭和时期战时体制之下,连工厂法规定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考虑到“一战”后国际劳工组织的保护规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战前的妇女保护立法与他国相比是何等落后。这种状况当然也是战前严苛条件之下阶级力量关系的反映。
女性工人的这种低下的地位,与支撑着无偿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的低下地位是相互规定的,二者合起来共同展示了日本妇女在资本主义与地主制度的双重压迫之下所具有的阶级地位。作为对女性工人和女性农民进行阶级统治提供支持的意识形态,“家族制度”得到强化,“贤妻良母”成为对妇女的要求,而其政治自由则被剥夺了。“家族制度”上妇女的无权利以及政治自由被否定的状态,并不仅仅只是女性工人和女性农民的问题,而是与包含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妇女的市民自由广泛关联的问题。因此,从家族制度和政治无权利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就成为比女性工农运动或者社会主义运动范围更广的一般妇女斗争的课题。也就是说,要求获得个体的自我确立、恋爱自由、政治自由等等,不仅仅只是社会主义者或工人的要求,同样也是那些属于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妇女,以及立足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女性的要求。
这样一来,在工人团体或社会主义组织之外,“青鞜”社、新妇女协会等妇女解放组织就产生了。在其运动的最高点上,终于赢得了部分的政治自由(大正11年《治安警察法》的修改)。但最终在整个“二战”之前,都没有获得加入政党的权利,而且尽管其后斗争不断,但还是没有获得参政权。就挣脱“家族制度”获得解放而言,尽管在实质上已出现“家族制度”解体的倾向,而且在其决定下,已经出现了判例法上的拓展以及立法上的部分修改,但从根本上看,还是没有实现解放。
在以天皇制国家和妇女劳动为基底的日本战前落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解放斗争道路艰险,相比之下,斗争主体力量弱小,那时的斗争只不过是为了从国家权力当中赢得部分内容而做出的让步罢了。因此,自下而上的解放斗争一直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最终在法西斯阶段,妇女们就被卷入到爱国妇女会、国防妇女会等自上而下的运动里面去了。
三、“二战”后日本的情况
战后改革当中有关妇女解放的一系列措施,即日本国宪法对人权和平等权的规定,以及在此前提之下对家族制度的取缔,政治自由和参政权的获得,劳动基本法上男女同酬和保护女工规定的完善,男女同校的实行等等,都毫无疑问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⑦[2]仅就法律制度而言,日本妇女此时在男女平等方面所获得的保障,放诸世界也都是高水准的。但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现实社会的水准尚且还赶不上法律的水准。因此,战败之后不久的妇女运动都以法律为武器,其目标就在于把现实社会的水准提高到法律水准的高度。在我看来,尤其是在战后头十年左右,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从“家族制度”当中解放出来。此外,由于参政权和政治自由得到了保障,妇女的政治自觉意识疾速增长,加上政治结社已经解禁,各种妇女团体一时间喷涌而出,妇女运动也就不再是狭义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和平运动开始扩展到各种政治运动、生活运动。在这些运动的共同作用之下,最终迎来了1955年的日本母亲大会。⑧[3]
通过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降的日本社会近代化过程,从作为家族制度象征的前近代身份性的不平等当中获得解放的任务暂且得到了实现,妇女解放运动开始面对从近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即形式平等下的实质不平等当中获得解放这一新的课题。在倡导夫妻平等的近代民法之下,夫妻在实质上果真平等吗?在倡导男女同酬的劳动基本法之下,女工在实质上没有受到差别对待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属于这样的课题。
对前者而言,涉及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特别家庭主妇的无偿劳动问题。对后者而言,则存在女性工人在职场上的从属地位和低工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起初都是一个一个单独提出来的,加上从妇女解放理论出发,看不到提高妻子地位与提高女工地位之间的关联,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妇女解放运动上的“混乱与迷茫”。⑨
但这些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具体社会生活场域里的妇女地位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也就是同一个问题。由于不管是家庭主妇的无偿劳动、还是女性工人的低工资,二者合在一起共同支撑着资本主义之下男性工人的低工资状况,从而妇女——作为工人是直接地,作为家庭主妇是间接地——就被置于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与掠夺的最底端。丈夫本身处在资本主义剥削之下的低薪状态,主妇无偿劳动的问题并不能归结为要从丈夫的低工资当中拿回自己的那一份。相反,造成主妇无偿劳动的是女性工人在工人工资结构上的低薪状态。从对这种工资结构进行批判开始,家庭主妇无偿劳动的问题就能够与现代阶级斗争的一个特定形态——女性工人斗争,进而也就与一般的工人斗争结合到一起了。⑩[4]
从这种阶级意识出发,妇女运动摆脱了暂时的“混乱与迷茫”,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各个领域当中普遍开展起来了。这一时期带来了客观条件上两个新情况的形成,从而使妇女运动能够超越诸如“是应该提高家庭主妇的地位,还是应该提高女性工人的地位”等抽象观念论的形态而向前发展了。首先的一个情况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妇女劳动市场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由此又进一步导致了妇女政策上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劳动力不足,被这种情况广泛动员起来的妇女劳动,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从传统那种出嫁之前的临时工作逐步向长期独立工作转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妻子参加工作、母亲参加工作的人每年都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妇女从现实出发,认识到家庭主妇或母亲的地位与工人的地位本身就是紧密结合的,那些评论家和学者在头脑中的争论就已经被超越了。
另外一个情况在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妇女运动在新的国民运动当中担负的任务增加了。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国民生活当中各种矛盾激化,生活保障斗争以及生存权捍卫斗争遍布全国。在诸如与破坏生活环境斗争的居民运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消费者运动等国民运动当中,实际担负着生活的妇女们就成为各种运动的重要主体。
就居民运动而言,外出工作的丈夫白天不在居住区域内(当然,伴随工作圈的扩大,上班地点远离家庭所在地,就可能造成他们被归属于其他自治地方的情况),无法成为家庭所在地的居民运动的主要担当者。在这种状况下,城市当中就客观形成了这样的条件,使每天的生活都在家庭所在地度过的家庭主妇成为居民运动的主力。再从消费者运动来看,由于日本不具有像外国那样与劳工运动紧密结合的生活保障组织运动的历史,工会对消费者运动的配合薄弱,以家庭主妇为核心的妇女团体就成为消费者运动的主要担当者。
这样一来,曾经只是部分知识女性的运动,而且还受到那种概念化、公式化的妇女解放理论的贻害,现在已经不再区分普通家庭主妇和女性工人,而是将二者共同包含在内,扎根于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并与其密切结合,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形态的大众化的妇女运动了。
在这一运动扩大过程中,一方面女性工人的权利斗争也一点点地向前发展。在立法斗争上,抵制那些总想把劳动基本法往坏处修改的企图,让他们到现在也没能实现,而且《劳动妇女福利法》(1972年)、《产假法》(1976年)等,虽说距离真正的劳动妇女福利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也难以否认它们未尝不是政府面对女性工人的要求所采取的粉饰门面的应对措施。但即便如此,这些法律还是反映了一定的斗争成果,而且也为今后的运动指明了路线和抓手。在审判斗争上,在抵制工资差别斗争、特别是抵制离职差别斗争(结婚离职制度、怀孕生子离职制度、一定年龄的退休制度,以及裁员及解聘临时工等)等方面,扎扎实实积累了不少成果。此外,由于一些企业当中还单独开展了要求怀孕、妊娠反应、产前产后、育儿等休假的斗争,所以已经超过劳动基本法保障水准的地方也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在家庭主妇法律地位问题上,围绕着主妇家务劳动的评价、妻子在夫妻财产制当中的共有权,继承时的份额、离婚时的财产分割请求权,以及税制改革等方面,慢慢出现了摆脱形式平等、努力实现实质平等的动向,并且在判例上已经有所体现,一部分内容还进入到了立法解决的筹备阶段。
尽管存在这些运动成果,但就眼下所达到的水准而言,日本家庭主妇和女性工人的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相比较来说显然还是不高,而且通过战后改革所获得的法制保障,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在后续的改革中真正兑现,所以众所周知,30年之后的今天放眼国际,日本的状况依然还是发展迟缓的。如前所述,在单独的问题上以及单独的领域内,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并取得了成果,但尽管如此,妇女运动作为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的整体,却只能说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而且发展缓慢。因此,不但达不到世界水平,甚至当前的“国内行动计划”简直是与“世界行动计划”反向而行的,让人担心妇女地位的下降。但问题在于,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却完全看不出会有大规模的抗议和批判运动的开展。
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单个领域内妇女解放运动有着诸多方面的进步,而作为整体的妇女解放运动却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是因为对于妇女运动在整个阶级斗争当中所占有的地位尚缺乏明确的展望,不能把一个个的单独斗争放在斗争整体之中,从而作为与之相联结的诸环节来加以把握。因此,不管是在密切联系生活开展斗争方面,还是在超越概念性的斗争公式方面,尽管都取得了扎实的成果,但是确实还存在着斗争被身边眼前的经验主义事物矮化的倾向。跨越不同阶级、阶层,彼此生活条件存在差异的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地位问题,必须要重新加以审视。在这一点上,尤其是那些连工会都没有的零细企业里的女性工人,家庭主妇出来做兼职的临时工,与此相同的受雇在别人家做家务劳动的家庭主妇,个体经营户、小店铺里家庭主妇兼女工的情况,以及农村妇女等,这些在资本主义最底层劳动的广大妇女的法律地位问题,可以说一直是被妇女解放运动抛在脑后的。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些身处底层的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上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各项课题,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做出回答。毫无疑问,截至目前一直为致力于确立妇女法律地位的各项运动提供支撑的,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和民主主义法学立场的劳动法学和民法学上的各项学术成就,并且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是在为这些运动提供法律理论武器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但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个单独问题的处理而已,并不能够对整个运动提供蓝图展望。例如,劳动法学看到的是无法获得财产的女性工人的地位问题,民法学看到的则是家庭当中妇女的财产地位问题,至于这二者的理论关系问题,却显然是不清楚的。在我看来,只有构筑一种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法学理论,才可以从法学上为妇女解放斗争提供理论武器。这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注释
① 过去的女权主义者所发起的运动虽然在妇女解放方面实现了一定的历史任务,但根本上还是一种小市民的运动。而在现在所谓的女权运动那里,虽然变换了形态,但还是能看出其中的小市民性质。
② 这些情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中都有论述。
③ 例如,在发达国家当中的英国,1846年制定了10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在美国,众所周知,虽然州政府制定了限制女性工人劳动时间的法律,但联邦法院却一再做出该法律违宪无效的判决。
④ 近代社会为什么无法实现男女平等,对于这一问题尚无充分的理论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必须从劳动和家庭两个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综合性的研究。
⑤ 原文如此,当指1949年12月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译者注。
⑥ 关于这一点,参见野田爱子《联合国、世界劳工组织当中的妇女问题》,载田中美寿子、日高六郎主编《妇女政策、妇女运动》(“现代妇女问题讲座”第1卷),亚纪书房1969年版,第233页以下。
⑦ 有关战后改革与妇女地位,特别是与家族制度的关系问题,截至目前已有大量的文献,近期的研究成果可参见依田精一《战后家族制度改革与新家族观的确立》,载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战后改革Ⅰ》,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
⑧ 日本母亲大会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显示战后妇女运动发展水平的大会。只要看一看每年母亲大会的记录,就能够明白日本的妇女运动在关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每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关战前、战后的妇女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轨迹,可参见日本妇女团体协议会《妇女走过的100年》,大月书店1978年版。
⑨ 所谓“混乱与迷茫”,是当时新闻媒体行业的用语,在昭和30年代前半期,围绕着石垣绫子的《家庭主妇第二职业论》(载《妇女公论》昭和30年2月号)、梅棹忠夫《妻子无用论》(载《妇女公论》昭和34年6月号)、矶野富士子《主妇家务劳动再评价》(《朝日杂志》昭和35年4月10日号)等提出的问题,在于妇女解放的关系上,家庭主妇问题受到热议。其后的妇女问题研究者也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参见下一条注释)。
⑩ 在前面注释中提到的当年矶野提起家务劳动评价问题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指向。在其后的论争中,又出现了从各种立场出发的观点。可查看竹中惠美子、广田寿子、伊藤セツ、毛利明子、高木督夫等人的研究成果。此外,作为整体综述性的作品,可参看神田道子《家庭主妇论争》,载青山道夫等主编《讲座:家族8》,弘文堂1974年版。这些议论涉及的是从社会科学立场出发,如何看待妇女解放与家庭主妇参加工作组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与在法学的框架中应当如何对家务劳动进行法律评价的法律理论,毫无疑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认为法学框架中的法律理论与社会科学上的认识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就会用家庭主妇替代妇女,为家庭主妇的地位问题所束缚,最终陷入人为缩限妇女解放视野的小市民倾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