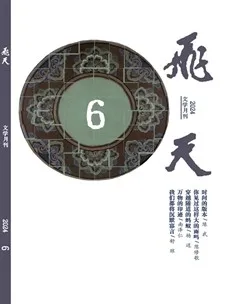小城叙事与现代性追求(评论)
白晓霞
作家杨逍出生、工作、写作于甘肃天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甘肃天水有着“羲皇故里”之称,是文学创作的宝地和福地。但是,已颇具人生阅历的作家却没有让笔致过多停留在历史深处,而是更愿意让小说直面当下复杂纷纭的人和事,现实和理想的矛盾被一点点撕开。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本面貌出现:在历史文化背景与现代性语境的碰撞、对接之中,拥有理工科教育背景与多年职场复杂体验的作家杨逍的创作选择了“向内求索”的路径,形成了某种“心理小说”的类型:比较关注人物的心理困境并试图理性分析困境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可能得到救赎的现实路径。这样的基本创作理路,无疑使得杨逍的小说超越了我们循着惯性所能想象的西部乡土语境带来的文本面貌,小说确实因之而带上了某些现代性的色彩,在甘肃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早在杨逍的小说集《天黑请回家》的一些篇什中,就体现出了上述心理小说的色彩,而小说中大多数故事发生的空间似乎仍有着西部村镇色彩,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即作家试图在西部文化的特定语境中破解现代性的文化命题,2013年《天黑请回家》在《创作与评论》(现《湘江文艺》)发表后,即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引起了文坛的一定关注,随后出版的小说集《天黑请回家》也获得了第五届黄河文学奖。
很明显,杨逍的小说新作《镜身》与《穿越隧道的蚂蚁》依然在延续着前述“心理小说”的某些特点。但是,经过了三年疫情、下乡扶贫、人到中年、人事更替等各种主客观环节洗礼的作家,自然而然会为文本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开始更聚焦关注在无情的小城时间之河中无奈漂流的小人物的心理生活,他们平凡渺小,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常陷入无力无奈感和虚无绝望感。作家以先锋笔触和现代性意识聚焦关注了“小城小人物”的“暗淡心理”,乍看文本表面灰色沉重,而在结尾处却往往有一道虽然微弱但从没有熄灭的光亮加持着即将完全崩溃的主人公走向了另一种重生。独特的“暗淡心理”叙事使得文本带上了现代性意味,结尾刻意闪烁而出的光亮一笔又提醒我们文本的根还是在温情敦厚的西部乡土文化之中。于是,杨逍小说文本的内涵展演路径便在城与乡、绝望与希望、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悖论式的对接,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作家主体性意识的矛盾与挣扎、放弃与坚守、沉沦与升华。文本叙事总体上比较成功,人物、情节、主题指向都在叙事中不断分裂,形成了某种出人意料的戏劇效果,从而使文本拥有了一定的阅读张力,较强的可读性承载着较深的思辨性。
《镜身》是一则关于小人物命运的黑色预言,前半部分凝重悲观,可贵的是,在结尾处作家主体会同人物形象客体一起做了不甘沉沦的挣扎与突破,让读者心生暖意,体会到的仍是“人间值得”的欣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公务员,在工作借调中奉献青春,蹉跎岁月,渐渐失去了晋升的机会,平庸而消极的“我”在家庭和社会中都被边缘化:“我越是安静的时候,我就越是深陷于这种自我怀疑中……我就像是砧板上一小块瘦肉,再也不能与整个牛身融为一体,面对挑剔的顾客发出的‘这一小块是不是这头牛的一部分的质疑。”作品的前半部分尽管弥漫着消极压抑的氛围,但依然是现实主义基调,“我”行尸走肉一般提前脱离了社会,受到出身优越的妻子的嘲笑与嫌弃。后半部分却用一个西方心理学上的陌生语汇“镜身”让作品陷入了神秘主义的叙事氛围,所谓“镜身”就是另一个“我”,可能是前世也可能是来生。那个寻踪而至的陌生的年轻人自称是“我”的“镜身”,人生的上半场与“我”一模一样,要从“我”身上寻找他人生下半场的正确答案。然而,“我”却是一个爱情上的负心汉,是一个事业上的失败者,是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厌恶的“两面人”:“我成了一个完全两面的人,及至现在,我已经无法将我的分裂合二为一,可我又多么想合二为一啊。”“我”早已习惯了自己丑陋消极的面目,然而,在面对执着寻找“镜身”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下一代年轻人时,“我”突然醒悟,羞愧无比,年轻人的执着单纯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终于激励“我”决心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在小说的结尾处有温暖的“阳光”照在百草山。阳光终将冲破乌云,这是宅心仁厚的作家在人物最后的精神死亡关口为读者打开了真善美的大门,新鲜空气如潮水一样涌了进来,“我本渺小”的平凡生命终于如火中凤凰一样涅槃重生。
《穿越隧道的蚂蚁》中表达的依然是小人物的黑色生活,想象生动而鲜活:“我”的“生理的病”与“心理的病”扭结在一起,如令人窒息的蚁群扑面而来,好在结尾处这些消极绝望的情绪终于被世间最为可贵的亲情做了温柔阻拦,依然有着几分好人终得好报的隐喻意味。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消极颓废的中年人,在作家笔下,这个生活在小城镇的普通人常年的“暗淡心理”情有可原:夫妻不睦、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事业平淡无奇。小说的开篇部分笔调散淡甚至带着几分慵懒的意味,颇有90年代新写实小说中“小人物小事情”的痕迹:“在我们分开的最初一年里,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那次分歧是一次意外,不就是我抽烟的时候不小心把她放在沙发上的一条新裙子烧了个洞嘛,大不了再买一条好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那条裙子有多好看。”平淡到无聊的烦恼生活让主人公压抑到近乎崩溃,被现实生活深度异化的他竟然拥有了神奇的感觉能力,为了确切表达这份神奇的感觉,作家渐渐从新写实的手法过渡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让人物从现实走向了虚拟,又在虚拟中努力追求着现实,“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视听幻觉:穿越隧道的蚂蚁。这种在医学上被称之为“颞叶癫痫”的疾病带来的幻觉死死控制着“我”,“我”却相信“穿越隧道的蚂蚁”是真实存在的,“我”的肉体常常因之而昏厥甚至可能会死亡:“我从另外一个反方向,在隧道里飞奔,而隧道越来越窄,越来越细,直到成了一个针眼大小,而我执意要从这个针眼里穿过去,去解救那只即将面临危险的蚂蚁。我想变成一只蚂蚁,那样我就能从那个针眼里钻过去了。但我钻不过去,我憋足了劲,屏住呼吸,我真的渴望我的呼吸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终于,在无比沉重又非常孤单的庸常生活中,“我”的“病”日重一日,幻觉完全控制了我:“后来,我成了蚂蚁中的一员,而不是蚂蚁的拯救者。”而唯一能让“我”保持最后一点清醒的人,是父亲和女儿,或许,作家想说,在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小人物的平凡单调的生活轨迹中,似乎只有亲情的力量才能让主人公保持着最后一点理性与尊严。而那个中年丧妻、女儿又不学无术的可怜的瘸腿鞋匠巴赫则是作家笔下另一只“渺小的蚂蚁”,也正是因为把全部的爱都无条件的给了女儿,巴赫这只“渺小的蚂蚁”才被渡化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
显然,杨逍的两篇小说都有着心理小说的味道:重视探索人物的精神困境以及救赎之路,文本的某些部分带有明显的意识流痕迹。然而,与绝大部分同大都市文化脐血相连的心理小说不同,这两篇小说有着比较明显的小城叙事意味:“小城里的小人物”被沉重的现实生活异化,消极悲苦,找不到灵魂救赎的出口。于是,在停顿与前行之间,在堕落与飞翔之间,他们满载着痛苦与分裂,又充满了挣扎与不甘,这或许是后疫情时代文学创作的某种必然选择。好在,天性善良的作家最终都让主人公有爱可以凭借,有力量可以前行,终于为读者拨开了满天乌云,带来了一道阳光。客观地看,在甘肃的小说作家中,杨逍所创作的这种聚焦关注人物被现代生活所异化之后的特殊心理的小说类型还是比较独特的,其上充溢的思想上的现代性意味与艺术上的先锋性探索确实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综上所述,杨逍的小说《镜身》《穿越隧道的蚂蚁》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书写了一种“小城小人物”身上所承载的现代性困境,写作意识先锋、笔触精致冷峻、情感體验细腻。“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确实如此,杨逍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这种共性的“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与此同时,小说也形成了值得称道的个性化特色:一方面,作家对人物在“小城之中”产生的由压抑而至分裂的心理体验的理性冷静的描写让我们容易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施蛰存的小说《梅雨之夕》,现代性叙事追求明显。另一方面,善良的作家却又不忍心真的让人物堕落、变形、粉碎、毁灭到万劫不复,所以,结尾处总有阳光闪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或被青春的明净所打动,或被永恒的亲情所拥抱,现代性叙事终于止步在人物精神分裂的边缘,最终化成了尽管微弱却依旧温暖的一束光,这束光回护着人物形象身上最后的精神的整体性,使其在危险的悬崖边完成了救赎,如过河之舟,渡化人心走向真善美。基于此,我们似乎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束“护人性于周全处”的文化之光来自底蕴深厚的“羲皇故里”天水,来自广袤敦厚的西部大地。一般认为,现代化所取得的科技与物质方面的成就与带来的某些弊病(如因空气恶化、资源减少、生态变差、物质至上带来的精神困境)都与工业文明有着密切联系,如前所述的“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的现代性困境也由此产生,毫无疑问,以“人学”为内核的文学对破解人类的现代性困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农耕文化长期以来的稳定性以及所推重的天人合一等“大自然中心”理念,有可能会为破解因“人类中心主义”理念而产生的现代性困境提供启发。甘肃天水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积淀,理应得到本土作家更多的重视,在理性研究农耕文化的过程中思考解决西部当代文化现代性困境问题,或许是甘肃作家的重要使命,从某种角度看,甘肃作家在面对上述问题时,似乎也具有某种潜在优势。目前看来,杨逍的小说创作似乎进入了长篇发力期:2023年11月,长篇小说《从来惜》获得天水市委宣传部文艺扶持项目立项;2023年3月,长篇小说《柳生芽》与重庆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将于2023年内正式出版。我们无从得知他新作品的具体内容,但“心理小说”也许依然会是他前行的重要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写作中确实不必刻意回避在西部语境中探索人的现代性的问题。前已述及,农耕文化在中华大地历史悠久、根脉深厚,其中的优秀因子对破解现代性困境有益,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益,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有益:“文明史编撰,要有中国视野和中国特色。中国视野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中国特色,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运用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和方法,对世界各国的文明史进行研究和阐释。”②甘肃天水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是传说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诞生的地方,传说母亲华胥氏“历十二年而生伏羲”于成纪,伏羲“一画开天,肇启文明”。文学是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甘肃作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成功书写或许会超越文本本身,产生更为重要的文明史意义。前述的小说文本也正显示出了杨逍在这一方面的探索以及相应的功力,这样的文学面向,是值得继续开掘的一座富矿。当然,道阻且长,上述的文化使命必然也会对甘肃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作家在理论学习、经典文本阅读、文史哲融通等方面进一步下功夫,以便为真正优秀的经典文学文本的产生提供根性营养。
①周宪、许钧主编,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总序,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②朱孝远《文明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