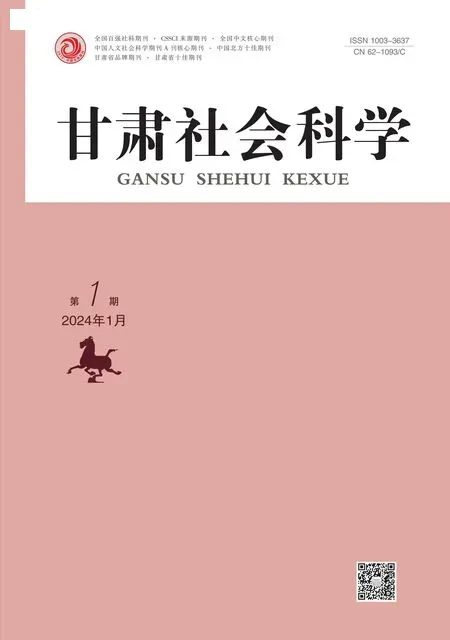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王长华 孙玉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提要: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今人关于以情解《诗》①的研究成果不少,可归纳为二:一是肯定它在《诗经》学(下文简称为:《诗》学)史上的创新意义,尤其肯定它在辩驳汉儒诗说礼义附会上所发挥的优势,“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二是认定它是宋代《诗》学彰显文学性的标志之一,宋代成为《诗》学史上从文学视角观照《诗经》的开始,“宋代学者已注意到《诗》的文学特点”“非常强调重视‘诗言志’,诗主吟咏情性,非常看重诗的文学功能。”[2]甚至认为“宋代的‘诗咏情性’突破了经学与文学的界限”[3],直指宋人将《诗经》当成文人诗歌而非儒家经典来看待了。
审视这些已有的成果,可知学界尚缺乏对以情解《诗》形成脉络的系统梳理;未能辩证地看待以情解《诗》的利与弊,缺乏对其局限、弊端的探讨,如此一来则难见宋人对“情”的真实态度;同时,将它作为宋代文学《诗》学的关键证据,更是没有完整还原古人的真实立场。我们认为,以今人语境下的文学去对标宋代视野中的《诗》学,正如宋人以今度古地以人情去度量先儒的《诗》说一样,先天之不足似乎是必然的,其“摒弃注疏只谈文本”“原诗背景不明而强为申说”的做派,存在“因套用新方法导致证据缺乏而多用推测之语”的错讹,终至于“新说异见迭出”[4]。因此,本文首先从梳理宋代以情解《诗》的渊源脉络入手,力争做到正本清源。
一、宋代《诗》学以情解《诗》的发展脉络及其成因
在我国古代《诗》学史上,以情解《诗》奠基于先秦的“诗言志”,萌芽于汉代的“发乎情”,承魏晋“诗缘情”之余绪,受隋唐佛学性情论之激发,最终成熟于宋代。
(一)以情解《诗》的发展脉络
《诗》学史上,从汉代开始就有了对《诗经》与人之性情二者关系的专题讨论,不过,这一时期并未形成以情解《诗》,而是止步于对两者关系的有限讨论。汉代“四家诗”中对性情有专门论述的,最早、最丰富的是“齐诗”②,如学者翼奉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提出了因缘《诗》学而“见人性,知人情”的观点[5]3170。但是“齐诗”论性情的本质是借性情比拟五行数术,其落脚点并不在性情本身,与通常意义上的人之性情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齐诗”最先佚亡,对后世《诗》学的影响较为有限。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毛诗”却恰恰对性情之说颇为疏略,它的专长是借《诗经》来阐述礼义教化,被概括为“以礼解《诗》”,这与以情解《诗》的旨趣正好相反。我们考汉代的《毛传》《郑笺》,书中对“情”的论述很少,两书共有20余万字,但涉及“情”字的仅有39处③,更没有像“齐诗”那样对性情的专题讨论。《诗大序》的确有曰“吟咏情性”“发乎情”云云,但它指向的是国史“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下以风刺上”之作,强调的是“王道衰”的“变风”“变雅”才“发乎情”,故必须以“止乎礼义”加以限定,这其中体现了汉儒对“情”明显的贬抑态度。最能说明性情在“毛诗”中地位的是《隰有苌楚》序,其曰“思无情欲者也”[6]464,吾辈生而为人,岂能无情无欲?这传达的便是“毛诗”派学者对人之性情的漠视与不屑。至唐代,以《毛诗正义》为代表的唐代《诗》学并未超出汉儒的拘囿,如同样是解《隰有苌楚》,《正义》曰:“作《隰有苌楚》诗者……思乐见无情欲者……思其无情欲之事。”[6]464此说同乎毛、郑诗说。与汉唐诸儒不同,宋人肯定情欲的存在,如杨简曰:“是诗大夫不乐夫君之淫恣,而思其未有情欲之时也,而《毛诗序》曰:‘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其无情欲者也’则微差。”[7]866所谓“微差”,正体现出汉唐诸儒与宋代学者解读《诗经》的不同理念、不同思路,而这正是由以情解《诗》带来的进步。
在古代《诗》学史上,宋代首次形成了以情解《诗》的理念。公认率先提出以情解《诗》的是欧阳修,其有曰:“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8]62欧阳修认为《诗经》是人之性情的产物,古人有情,宋人亦有情,且两者是相同又相通的,宋人正可凭此来忖度千年之上先秦诗人的诗情,进而理解《诗经》之诗旨。此说是对以情解《诗》的典型性解释,道出了人之性情与《诗经》的本质关系,创造性地提出诠释《诗经》的新方法、新思路。尚需指出的是,首先,《诗本义》的“人情”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之感情,如解《常棣》曰,“(诗人)取常棣之木……以比兄弟之相亲宜如此。因又极陈人情,以谓人之亲莫如兄弟”[8]60。《常棣》是诗人深感兄友弟恭、深情厚谊的作品,整部《诗经》正如《常棣》一样,是反映先秦诗人喜怒哀乐的有感之作。二是指人之常情,即人世间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常情常理,“古今人情一也”中的“人情”即是此义。其次,欧阳修此说在《诗》学史上意义重大,一是极大肯定了“诗缘情”的诗歌发生说,预示着《诗》学重情时代的到来;二是以人情作为判断诗义是否得当的标准,驳倒了汉儒解《诗》不顾常情常理,牵合《诗经》与礼义而带来的附会生说,拉开了宋代《诗》学的革新序幕;三是开启了宋人以性理论《诗》的先河,欧阳修虽主观上无意于性理之学,但在客观上引领了宋代《诗》学中道学意义上的性情之辨。最后,《诗本义》混用人情的两种含义而不加区分,直接为以情解《诗》之弊及今人对宋代文学《诗》学的误解埋下伏笔。
以情解《诗》一经提出就受到学者们的青睐,紧随欧阳修之后,传承以情解《诗》的大致可分为三脉,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以情解《诗》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脉,是以“新学”王安石与“涑学”司马光为代表的从政官员。荆公与温公二人虽在政治上针锋相对,但作为国家的宰辅大臣,从他们治国理政的需要出发,其经学思想都强调礼法规制,故二人的《诗》学思想颇与讲究礼义道德的汉儒相仿。如王安石解《载驰》曰,“宗国颠覆,变之大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然后尽于人心。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义”[9]409。司马光则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然则,观其诗,其人之心可见矣。”[10]二人之说可谓都是“诗言志”的翻版,注重礼义对人情的节制。同时,二人论《诗》又都牵涉“人心”,都是宋代道学家的言语,可见宋代中期以后《诗》学的性理特点。第二脉,是以“关学”张载、“洛学”二程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他们主张性善情恶,故诗说中有着对人情的明显贬抑,如张载论“何以郑卫之音为邪淫之乐”,曰“其人偷脱怠惰,弛慢颓靡。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11]263。二程解《硕人》曰:“人情故纵难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于夫人。……君情放纵,故礼法不能制。”[12]1055诗说都很合乎道学派的性情观,人情既然“故纵难制”,自然需要以礼法性理节制之。第三脉,是以“蜀学”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诗文名家,与前两家不同,二苏主张性、情一也④,褒扬人之情性的可贵,在这一点上和欧阳修的重情思想是共通的,苏辙曰:“诗之所为作者,发于思虑之不能自已,而无与乎王泽之存亡也。……及其衰也,有所忧愁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荡,不合于礼者矣,而犹知复反于正,故其为诗也,乱而不荡,则今之变诗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礼而忘反,则其诗远义而无所归向。”[13]所谓“发于思虑之不能自已”与《诗大序》“发乎情”意同,但苏辙认为《诗》之作与“王泽之存亡”无关,突破了汉儒的“德化说”。同时,《诗大序》之“变诗”尚在“止乎礼义”的框架内,苏辙在“变诗”之外增加了“大亡”之诗,以至于“怨君而思叛,越礼而忘反”,更是突破了毛、郑《诗》学的藩篱,因此,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情本论”[14]。总之,北宋中后期的学者在欧阳修“人情说”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以情解《诗》理念,正如北宋后期的学者黄櫄所说:“三百篇之诗,大抵皆近于人情,学者以情求诗,则思过半矣。”[15]宋人期望通过“以情求诗”,沟通先秦诗人之意、达于三代圣人之志。
以情解《诗》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运用在南宋达到顶峰,且愈来愈带有着与道学不同流派的派别色彩,这与道学在南宋形成明显的派系分支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宋代运用以情解《诗》可称为“最”的是南宋早期的学者王质,他的《诗总闻》提出“因情求意”,这是王质《诗》学的原则性、纲领性的理念。具体来说,一是《诗总闻》将情与性、理、心等道学最高阶的要素并称,而不再是“心统性情”[11]374一类的提法,如“以情以理”一词出现于解《常棣》《殷武》等多篇诗文,与其并称的是“天心人心,曾何异也”[16]350,“情”在王质笔下有着超越二苏“情本论”的主动性,具有同性、理、心一样的普适性,这样的表述在其他学者的《诗》学中是罕见的。其次,《诗总闻》中“情”的地位有时还要高于性、理、心,如解《鸿雁》曰:“哲人、畅于人情,悯我之劳也。愚人、暗于物理,谓我为民任劳,示之以骄。”[16]179王质在此将“人情”与“物理”对立——哲人尚能通达“人情”,可怜“我”的不容易,“愚人”胶柱鼓瑟于“物理”,以“我”为傲娇——“人情”与正面的“哲人”比肩,“物理”与反面的“愚人”的并列,充分说明了“情”在王质心目中的高大地位,这样的对比看待全不见于其他学者的《诗》学表达。
其次,南宋前期以后,以情解《诗》的道学派系色彩愈来愈浓厚。一是“理学”朱熹及其弟子,主张以“理”制“情”。朱熹认为:“‘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17]2072汉儒认为诗三百都是诗人的无邪之作,“正风”本就发乎礼义,“变风”则是“止乎礼义”,因此,“正风”和“变风”都处于礼义可控的范围内。与之不同,朱熹突破了汉儒旧说,认为“变风”是无关乎礼义的,为他的“淫奔诗”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如解《匏有苦叶》曰:“夫济盈必濡其辙,雉鸣当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济盈而曰不濡轨,雉鸣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乱之人不度礼义,非其配耦,而犯礼以相求也。”[18]31朱熹结合宋人的“理”与汉儒的“礼”,批判这种突破礼义、犯礼相求的“淫情”。其弟子辅广更直言此是“反常逆理而无所顾”[19]147。二是“心学”杨简、袁燮等学者。理学家提出以“理”制“情”,心学家则主张以“心”制“情”。如解《何彼襛矣》,袁燮曰:“凡人之情,不失之纵弛,则失之乖戾……(王姬)肃肃雝雝,犹执妇道,其不失夫本心者欤?”[20]16杨简进一步敷衍曰:“(王姬)有怀徳之心,有敬贵之心。虽不指言徳行,然而无邪也。无邪即道,即徳。”[7]726王姬秉持一颗“怀徳之心”“敬贵之心”,故能摒除“纵弛”“乖戾”的“人之情”,“本心”二字正是心学家的宏旨题眼。三是“婺学”吕祖谦及受《吕氏家塾读诗记》影响的学者。吕祖谦的学术具有兼容汉、宋,并包“理”“心”的集大成特色,他的《诗》学思想同样如此。吕氏论《诗》曰:“《诗》全是人之情性,须先得诗人之心……大抵圣人语言尽由德性中出,故须先得其心……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矣。”[21]既传承了汉儒的“吟咏情性”说,又包容了宋代的理学、心学二家。又如吕氏后学严粲论曰:“诗出于情之真,其感也深。故正人事之得失,使人舍非而从是。与夫动天地,感鬼神,无有近于诗者。吾心有此理,在人在天地在鬼神,亦同此理。”[22]同样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与王质相比,道学各流派对以情解《诗》的运用虽各具特色,但诸家对“情”的理解深度以及赋予它的地位,都没有再达到王质的高度。
总的来说,欧阳修率先提出了以情解《诗》,并由后代学者不断地改进与完善,这种新变可概括为三:一是“词形”上,欧阳修喜用“人情”一词来指代“情”,后学又加入“人之情”“性情”“情性”等词,乃至单用一个“情”字表达,所以纵览宋代《诗》学专著会发现书中遍布各类“情”字,“情”字的存在感要比汉唐时期强许多;二是“词义”上,欧阳修笔下的人情以常情义为主、以感情义为辅⑤,后学则多使用它的感情义,这和欧阳修与后学所处不同的宋代《诗》学发展阶段有关;三是“词性”上,欧阳修笔下的人情多取其常情义,常情是中性词,后学多取其感情义,且因宋人语境下的“感情”常带贬义色彩,所以必然要置于礼法、性理的约束之下。
(二)以情解《诗》形成于宋代的成因
以情解《诗》形成于宋代并广受学者所喜爱的原因大抵有四:根基属性、用其优长、学理沿革以及宋代学者的秉性出身。
第一,《诗经》之作“本于人情,自生民以来则然”[23],这句话高度代表了两宋学者对《诗经》创作本源的认识,不待论说而自明。
第二,破除汉儒旧说,构建宋人新论的需要,这是以情解《诗》——作为一种《诗》学史上新兴的解《诗》理念和方法——最大的优长及所具《诗》学史意义。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有宋一代士大夫始终怀有振兴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的理想抱负,力图构建一个有别于汉唐、宋人自己的学术体系。《诗》学体系无疑是宋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宋人之所以从人之性情的角度切入,正是针对汉儒过分以礼义压制人情致使诗旨扭曲的荒谬,以及抓住汉儒忽略性情的漏洞。俞平伯先生曾言,“说诗最要紧的是情理,而且比较有把握的也是情理。因为训故音声、名物制度古今不同,经师授受未必得古人之真;篇章呢……汉儒之窜乱,三家之亡佚,其中间错乱亦不知其几何矣;至于微言大义不传者多矣,臆造者亦多矣……惟推情论理,古今虽远,感则可通”[24]。所谓“训故音声”“篇章”云云,原本是汉代《诗》学的专长,但汉唐诸儒叠床架屋般的礼义附会蒙蔽了《诗经》本义,曲解了圣人本志,“微言大义”既不见传,反而多是“臆造”。因此,正如欧阳修多用“情”的常情义作为辩驳汉唐《诗》学的突破口,是因为他处于经学革新初期,首要任务是打破毛、郑诸儒的《诗》学权威,他用古今共有的“常情”去沟通诗人之意、圣人之志,为的就是以三代的权威破解毛、郑的权威,从“破”的层面冲击旧有的《诗》学体系。但“破”并不是目的,宋代学者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宋人对《诗经》的自身理解出发,以宋人特有的“情感”去感悟《诗经》,进而在欧阳修打破的旧有权威基础上进行新体系的建构,重塑宋人自己语境下的圣人之志,从“立”的层面构建宋人自己的《诗》学体系。
第三,自魏晋以来“诗缘情”说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理沿革。虽然文人之诗与经师之《诗》不同,但诗之作均“本于人情”无疑是共识,且诗学之“诗缘情”正源于《诗》学之“诗言志”,从“言志”到“缘情”,这个转变是魏晋士人将个人情感诉求提升到集体意志表达的高度的过程,“在个人情感表达日益得到重视的哲学思潮下,魏晋文人做诗,一反‘诗言志’之传统,提倡文学宣情以表达自我,在诗作中大量寄寓情思与情感,用创作实践为‘诗缘情’经验积累”[25]。至宋代,在《诗》学领域,“诗缘情”反哺“诗言志”,宋人不仅坚持、巩固了“诗言志”的集体意志表达,更将对个人性情的考察纳入《诗》学。宋人借助“二南”反复强调的“修齐治平”的落脚点是个人,宋人诗说随处可见的“性情之正”针对的还是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经学革新者们主动援“情”入《诗》、以“情”解《诗》,并且后世学者尤其是道学家们将其发扬光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它顺应了魏晋以来的“宣情以表达自我”的大趋势,弥补了汉唐《诗》学对个人性情的忽视。可以这样说,汉唐《诗》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以“诗言志”传达出集体意志的要求,宋代《诗》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诗缘情”的个人性情诉求也纳入进来,纳入经学范畴的德礼教化、心性义理中来。
第四,作为宋代社会文化阶层主力的士大夫们,他们的出身与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习惯于以世俗人情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理解、阐释《诗经》。有别于汉唐时代门阀贵族作为文化阶层的主力,所推崇的文化范式是雅致文化,宋代是由众多寒门庶族组成的新生的市民阶层,及其与生俱来的世俗文化。据《宋史》等史料记载,宋廷的“右文”政策催生了众多出身卑微、成长于困顿的士人⑥,随着这批士人的大量涌现,以及逐渐掌握上至庙堂、下到江湖的文化话语权,宋代世情的文化氛围便加速形成了。这是因为,对市井街坊的种种人间烟火气——它们是最世俗人情的事物——的享受是门阀贵族所陌生和不屑的,却也正是市井百姓所熟悉和溺爱的,“城市居民之最基本的心理特征之一便是:永无止境地渴求娱乐,对任何种类的消遣、社交和饮宴均十分热衷”[26]。这些未来的知名官员、学者、文人身上,天然带有所出身阶层与成长经历的思维定式与审美印记。因此,从世俗人情的角度思考问题,以平民老百姓能够理解的人之常情、常理来解读包括《诗经》在内的“四书五经”成为自然而然的现象。换句话说,文化阶层的下移和文化大众化共同促进了以情解《诗》的形成,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宋代才产生三百篇出于匹夫匹妇之手、“国风”是里巷歌谣的观点,而像郑樵、朱熹等胆子更大一些的所谓“废序派”学者,更将部分“变风”中汉儒认定的上层贵族政治叙事诗,解读为下层百姓的男女私情淫奔诗,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对《诗经》的解读在宋代正在经历一个由雅致到世情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也正是宋代文化大环境由雅转俗的产物之一。
总之,本于《诗经》“发乎情”之根基,秉承先儒“诗言志”之传统,延续魏晋以来“诗缘情”之新说,宋人出于秉性习惯而用其所长,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范式的《诗》学体系。宋人提出了以情解《诗》,并广受学者喜爱,由此从理论到实践在《诗》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宋代《诗》学以情解《诗》的弊端
以情解《诗》作为宋代学者革新旧学的先进理念与方法实际上利弊兼有。其优长已如上述,其弊端则常为今人所忽视,概括言之——以今度古,以偏概全。
第一,在理论层面,以情解《诗》在宋代《诗》学的发展过程中就有过反思的声音。比如与王质同时代的学者程大昌曾说:“朝廷不知而国史得之,录以示后,以见下情壅于上闻,而因为世戒,是或自为一理也欤?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27]敏锐地发现了用人之常情来以今量古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解经场景。清人皮锡瑞在其书中《论以世俗之见解〈诗〉最谬,〈毛诗〉亦有不可信者》也说道:“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28]同样敏锐地发现了以情解《诗》“误信”“误疑”之弊,尖锐地提出了其成因是“推测古事,妄议古人”。
第二,在实践层面,以最早提出以情解《诗》的欧阳修与运用最成熟的王质为例,阐述其弊。首先,是欧阳修《诗》学。如《诗本义》解《四月》曰:“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乱世,反深责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诗人之意决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训,圣人删诗,必弃而不录也。”[8]87《四月》是诗人沉郁之情压抑已久的一时激愤之作,对先祖的严词苛责反衬出他对昏君乱世的极度痛恨,正所谓“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欧阳修机械地将宋代的礼法人情套用到先秦诗人身上,殊不知恰恰未能站在诗人的情感立场。他以评诗时的冷静理性,自然无法深刻体验诗人处于极度热烈情绪状态下泼洒出的诗歌情绪,进而未能参透孔子未删此诗的“圣人之志”。朱熹曾评价欧阳修曰:“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17]2089恰切地道出了欧阳修好以今量古的毛病。实际上,这是宋代学者的通病,自己吟诗作词时一向诗情澎湃,解读《诗经》时却又限制于圣人的谆谆教导,认定《诗经》都是温柔敦厚之作,一定不存在违礼越情的诗文,自然也就做不到真正的贯通古今人情。其次,是王质《诗》学,暴露出的问题最多。一是以今度古之弊。《诗经》中有许多采摘花草的场景,比如《关雎》之采荇菜、《葛覃》之采葛、《卷耳》之采卷耳、《采苹》之采苹、《汾沮洳》之采莫等,王质认为这些采摘劳作都是卑贱之事,非身份高贵的后妃夫人们所当做,如解《关雎》曰:“处贵、适水采荇,治葅品、供祀事,后世虽卑者亦所不屑。”[16]3解《汾沮洳》曰:“水际、采草为人葅,采桑为蚕饲,此穷贱之事也。”[16]94王质以宋代视采摘为“卑贱之事”的观念,来度量先秦时代的风俗人情,认为采摘在先秦也是“卑者不屑”之事,这是他以今度古的典型错误。因为据《礼记》等记载,自西周初年始,为鼓励农业生产,每年春耕之时,天子与后妃都会出席春耕礼、亲蚕礼,天子扶犁亲耕,后妃采桑饲蚕;至于祭祀,后妃更是亲力亲为各项流程,包括亲手采摘用于祭祀的荇菜等贡品,这说明后妃不但不以采摘为“穷贱之事”,反而体现了对亲手采摘祭祀供物的重视。二是以偏概全之弊。如解《小旻》“不敢暴虎”曰:“暴虎、冯河、临深、履冰,四者皆危事,亦皆北俗。北俗强健,河东有一种打虎社,大抵平地日中则虎瞀,此时多伏,则惊起以搏之,孟子所谓冯妇者也。”[16]202历来学者对此诗的解读都把重点放在诗句表现诗人谨小慎微的特征上,“暴虎”四句明显是一种艺术夸张手法,但王质却从世俗人情的角度强释为“北俗”,以写实的地域风俗代替务虚的人物心境,曲解了诗文原意,与诗人想要传达的诗旨本义相去甚远。实际上,欧阳修曾说过:“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语言亦异。”[8]82王质在《诗总闻》原例中也承认制度、称谓会随着时间、地点不同而有差异等认识,但两位学者的解《诗》实践却表明他们似乎已经将众人所熟知的常识抛之脑后了。
除了欧阳修、王质之外,宋代其他学者的以情解《诗》均有此弊,仅举二人诗说见微知著,不再一一。总的来说,宋代学者以情解《诗》在用其优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毛病,而造成这种弊端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每个人阅读《诗经》都会心有所悟,读到饮食男女会心有所喜,读到死亡贫苦会心有所忧,这些情绪体验在宋人看来与朝代、时间无关,面对同一情景,宋人的情绪体验如何,那么唐代的孔颖达、汉末的郑玄、汉初的毛公乃至先秦的诗人也应当是如何的,宋人试图以这些情绪体验去和先秦诗人产生情感共鸣,达到理解诗人之意、圣人之志的目的,同时据此判断汉唐诸儒的诗说是否正确。当宋人的情绪体验与先秦的诗人、汉唐的诸儒合拍时,两者相安无事,但不合拍时,宋人就会认为这是毛、郑诗说不合常情的问题,也会像欧阳修那样批评《四月》的作者怎么会写出“先祖匪人”的诗句。但关键在于宋代的喜怒哀乐并不见得都与先秦、汉唐的喜怒哀乐相通,《诗经》有很多作品,尤其是情绪激昂的“变风”“变雅”,或者是诗人在特定情感爆发状态下的产物,或者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并不能以人之常情去理解,机械地套用必然出现错误。另一方面,这种弊端源于宋人对“情”作常情常理、世俗人情含义时的滥用。这是因为每一朝代、每一时期的常情常理与世俗人情都具有期限,这其中虽然包含着一些共性的、超越特定朝代且能够从宋代以上贯通到汉唐、先秦可以贯通的情理相通的部分,但显然并不是全部都能贯通,它们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像王质那样以宋代的常情、风情去解释采荇采草、暴虎冯河,必然会出现失之千里的错误。总之,无论是感情义还是常情义,虽在历时性上具有一定的古今一致性,即所谓“共情”,但这种一致性却并非一定必然,问题在于,宋人以当时之情衡量古人之情,此举虽一定程度地决定了以情解《诗》作为宋人解《诗》路径突破的存在,但事实上却并不能成为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
三、宋代学者对“情”的贬斥及以情解《诗》的经学本质
作为宋代《诗》学特色的以情解《诗》,常被当今部分学者当作是宋代文学《诗》学的标志。有的学者认为:“至宋代,随文学观的发展演变,《诗》学文学化倾向又呈现出越来越强烈之趋势。”[3]8认为宋代学者如朱熹对《诗经》从“抒情主体”“抒情精神”等方面的体认,证明他“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诗经》”[29]。实际上,以情解《诗》虽体现了宋人对“情”的重视,但宋代学者实质上对“情”持贬抑态度,以情解《诗》及其中的“情”始终都被置于经学而非文学的境地。
(一)宋代《诗》学对人之情的贬抑
宋代学者对“情”的真正态度在其骨子里是贬抑的。可从两方面证明:一是宋代诸家诗说凡涉及“情”字的,其后文往往紧跟着带有鲜明贬义色彩的字词,或者“情”字本身就处于贬义的语境;二是在宋人诗说诸多的“情”中,又以男女之情最易被今人拿来讴歌赞美,但宋人对待已婚的夫妇之情与未婚的男女之情的态度判然有别,夫妇是五伦之基,故夫妇之情得到肯定和褒扬,而未婚男女之情由于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属于私情,私情悖伦逆理,故遭到严肃的批判。
首先,宋人对“情”的贬抑叙写贯穿两宋《诗》学史。北宋时期,不同的学派虽争鸣不断,但对“情”的贬抑却是一致的,如王安石主性善恶相混说,其解《硕人》曰:“因河水兴人情放纵难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于夫人。”[9]415二程持性善情恶说,其解《子衿》曰:“人莫不肆情废惰,为自弃之人,虽有贤者,欲强之于学,亦岂能也?”[12]1057从政治思想到学术理念,王安石与二程多有龃龉,但他们都赋予人情“放纵难制”“肆情废惰”的贬义。再看以“情本论”著称的二苏,苏轼曰:“以余观之,(太史公)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30]苏氏兄弟的文学创作固然重情,但在他们心中,“诗之正”是“发于性止于忠孝”,即“正风”“正雅”是“发于性”的,而“变风”“变雅”是“发乎情”的。由于“正”高于“变”,“性”要比“情”醇正,故在苏氏看来,最好的诗篇必然是那些“发于性,止于忠孝”“一饭未尝忘君”的作品。由此可见,二苏也是正宗儒家诗教的腔调,所谓“情本”,也只是相对于毛、郑诸儒,以及张载、二程等道学家而言罢了。南宋时期,《诗》学对“情”的贬抑就更常见了,这源于道学在南宋的全面铺开,性理对人情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略举两例,可窥全豹,如戴溪解《角弓》曰:“人情不善,易于放肆,犹矫揉以为弓,稍纵则反矣。”[31]袁燮解《女曰鸡鸣》曰:“恶劳喜逸,气体颓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于宴安也,况于夫妇之间,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20]37“人情不善”“人情易溺”云云,饱含宋人对人情之恶的不满。由此可见,宋代学者对人情的贬抑已深入《诗经》“风”“雅”“正”“变”的各个层面,无一例外。
其次,对夫妇之情与男女之情的区别对待。第一,宋代《诗》学对已婚的夫妇之情均持肯定态度,这相较于汉儒的忽视态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宋代《诗》学的夫妇之情都符合儒家的礼义道德标准,是“正情”。如欧阳修解《女曰鸡鸣》曰:“见其妻之不以色取爱于其夫,而夫之于其妻不说其色,而内相勉励,以成其贤也。”[8]39妇人能“不以色取爱于夫”,丈夫能“于其妻不说其色”,夫妇相悦能做到不以“色”,而是“相勉励”“成其贤”,一副夫妇贤惠且守礼的美好画面,此夫妇之“情”即为“正情”。二是宋人将夫妇正情抬高到与夫妇之义同等的高度,夫妇正情深为学者所赞颂。如杨简曰,“夫妇正情,天地大义。人皆有是正情而自不知,其与天地为一”[7]848。三是宋人坚决否定汉儒“夫妇离绝”式的夫妻关系。“夫妇离绝”出自《谷风》序,类似的还有《中谷有蓷》序的“室家相弃”、《出其东门》序的“男女相弃”等,对于汉儒的如此决绝,宋人是拒绝认可的。如王柏曰:“谷风之诗,妇人为夫所弃,委曲叙其悲怨之情,反复极其事为之苦。然终无绝之之意,与柏舟思奋飞大有间矣。此圣人所以制‘三不去’之义,其意深矣。”[32]宋人认为夫妇关系断不能轻易破裂,更不用说断绝,因此,学者总能从这类诗篇中找出夫妇不忍相弃的忠厚之意,甚至不惜为之牵强附会。总之,宋人对“夫妇正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宋代《诗》学对未婚男女私情均持否定态度,男女情爱被置于批判的位置。这种批判的视角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承汉儒的“美刺说”,将反映男女情爱的诗篇定义为刺淫诗,诗旨是“刺”男女“淫情”,大多数宋代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如杨简解《隰有苌楚》曰:“虽长而知男女之道,生于正情,不动私意,则‘归妹,天地之大义也’,自无淫欲,如天地氤氲,如水鉴中之影象。”[7]867摒绝“私意”“淫欲”,将“男女之道”限定于“正情”之内。又如叶适解《蝃蝀》曰:“怀春之为正,以其礼言也;怀昏姻之为刺,以其情言也。”[33]叶适以“礼”为“正”,以“情”为“刺”,批判之意更为明显。另一种是郑樵、朱熹等的“淫奔诗诗人自作”说,他们定义的淫奔诗作者是诗人自己,相比于刺淫诗的“刺”来源于旁观者,淫奔诗无疑是“自曝家丑”了。朱熹《诗序辩说》解《桑中》曰:“夫子之言,正为其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18]25朱熹否定《桑中》一类的淫奔诗出于“无邪之思作之”,那么淫奔诗也就成了“有邪”之思作之,是偷情男子叙写自己与情人的私会之事,孔子没有删汰淫奔诗而留存于世的目的,在于期盼后世读者能够引以为戒,从而“得其性情之正”。而且,由于朱熹认为淫奔诗的作者是诗人“我”,即“第一人称视角”,这种视角非常有利于读者在吟咏朗诵时将自己代入诗歌情境,更容易诱发读者的自我警诫,惩创个人逸志。总之,两种对男女私情的批判视角虽有不同,但批判之旨是一致的,批判的目的也都是让世人坚守夫妇之正情。
综上所述,通过发现“情”字在宋人诗说中的位置,尤其是对比学者对已婚之情和未婚之情的不同评价,鲜明地体现出宋人对“情”的真实态度。将性情之辨纳入经学主题之一的宋代,性、理作为经学的最高存在,无论宋人如何抬高“情”的地位,其结果必然是以性理(或礼法)节制人情,这是宋人贬抑人情根本且内在的原因。
(二)以情解《诗》的经学本质
以情解《诗》的理念与实践属于经学范畴,宋代《诗》学并不是今人意义上的文学《诗》学。今人定义的文学与我国古典的文学,或者说诗学并不一样,而诗学与《诗》学又不相同,因此,古人的经学与今人的文学对“情”的判断有着不小的差距。“情”是现代意义的文学的核心:“情感性是文学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文学的主要目的是表达情感、以情动人。”[34]文学的主要目的是“表达情感”,但诗学的主要目的并不单纯是“表达情感”,《诗》学的核心目标更不是情感。
以情解《诗》属于经学范畴,首先在于包括夫妇之情在内的所有“情”都被纳入经学的“正情”之内。宋人论《诗》虽重“情”,但都有一个前提“正”,即“正情”。宋人论《诗》始终围绕着“正情”展开,且重心是“正”,宗旨是使个人归于“性情之正”,这才是真正的宋代《诗》学的“情”,即经学意义上的“情”。“性情之正”广见于宋人诗说,贯穿两宋《诗》学,如北宋张载解《草虫》曰:“未见则忧,既见则喜,性情之正也。”[35]南宋辅广解《日月》曰:“(庄姜)虽为庄公所弃,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厚也。”[19]142由宋入元的马端临对此总结道,“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36],自始至终,两宋的各家各派不厌其烦地在提倡“正”情。
以情解《诗》属于经学范畴,进一步体现在宋代《诗》学的“正情”是符合孔子温柔敦厚诗教的“情”,是经过礼义道德、心性义理过滤的“情”。宋人认为《诗经》所传达出的诗旨必然体现着圣人教化人心的敦厚之义,因此,学者将“温柔敦厚”作为自己诗说的旨归,并且视作评判、审视汉儒诗说是否妥当正确的原则标准。审阅所有宋代的《诗》学论著,文中遍布“温柔敦厚”“敦厚”“忠厚”“仁厚”“厚”等高频字词,而凡是被否定的汉儒诗说几乎都是宋人认为不符合孔子敦厚人伦的内容。上文所述的男女私情、“夫妇离绝”等,就是因为违背了宋代的夫妇敦厚之义而被否定。再比如毛、郑诗说中有关君臣之义的论述,如以仁兽驺虞比拟文王,以贪婪硕鼠譬喻暴君,以“蘧篨”“戚施”形容好色之徒宣公,以老狼“跋胡”“疐尾”刻画窘迫艰难的周公等,这些本是老百姓爱美憎恶的情绪表达,属于人之常情,但宋人普遍反对将君王圣贤与猛禽野兽相提并论,认为它们违背了敦厚诗教。如程颢解《狼跋》曰:“狼,兽之贪者,猛于求欲……周公者,至公不私,进退以道,无利欲之蔽……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兴周公不失其圣。……岂有以豺狼兴圣人乎?”[12]1069诗人以老狼比周公,本义是刻画了周公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如老狼般坚毅隐忍,程颢则认为豺狼“猛于求欲”,这与圣人周公“至公不私”的形象严重不符,反对以禽兽刻画正面贤圣。又如唐仲友解《硕鼠》曰:“誓将去汝,非决辞,适彼乐郊,非真情……硕鼠,非斥君之辞也……虽以硕鼠喻之,犹为爱君也。”[37]不但反对将人君比作硕鼠,且千方百计地将诗意往“温柔敦厚”诗教方面靠拢,其所谓的“非真情”“犹为爱君”云云,尤为牵强荒诞,倒是与夫妇不忍离绝的说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反对以禽兽譬拟反面昏君。总之,性情之正与敦厚之旨为是一非二的,都是宋人以情解《诗》的最终旨归。
与经学范畴的“情”相反,当今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下的文学范畴的“情”,不受礼义道德、心性义理的限制,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更不都是“正情”,尤其是未婚男女之情即今人所谓的爱情,一直被道学家视为“洪水猛兽”,但却是当今文学领域最被赞美的主题,对它的是非评价似可作为经学与文学的重要分水岭。总的来说,当今文学的宗旨格外强调“发乎情”,却很少涉及“止乎礼义”,更不会局限于“温柔敦厚”,而后两者才是经学的要义与旨归,所以张纲在给宋帝的《经筵诗讲义》中说道:“夫诗之为变,则以事有不得平者,咈乎吾心,故作为箴。规怨刺之言,以发其愤憾不洩之气。夫如是,则宜有怒而溢恶,矫而过正者。然以诗辞考之,虽触物寓意所指不同,而要其终极,一归于礼义而已。”[38]因此我们认为,今人讨论宋代《诗》学的以情解《诗》只是截取了宋人对诗情的阐释,选择性地聚焦于前半截对人之情的赞美、讴歌,而舍掉了后半截用来节制人之情的礼义道德、心性义理,无视宋人对情的实质性贬斥,由此而得出宋代《诗》学是文学《诗》学的结论,这是很不周延的。
总之,与汉唐《诗》学对“情”的关注缺失相比,宋代《诗》学者肯定了个人基础的食色情欲,也承认了个人情性存在的必要,这是“宋学”超越汉唐的地方,也是它的进步之处。但所谓“礼缘人情”,圣人制礼作乐本是为了更好地和畅人之性情,宋人最终的主张仍是以“温柔敦厚”诗教节制人情,“礼乐大矣,然于进退之间,则已得性情之正”[12]1181。因此,宋代《诗》学的以情解《诗》还是被大体限定在了经学的范围之内,而将其完全视为今人文学定义下无节制的抒发情性是缺乏可靠历史依据的。
注 释:
①宋代《诗》学范畴的“以情解《诗》”之“情”首先指人情,这源于《诗》学革新引领者欧阳修以“人情”首倡,因此,关于“以情解《诗》”之说,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称谓,如以人情论/解诗(如陈战峰:《宋代〈诗经〉学与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人情说(如李冬梅:《苏辙〈诗集传〉新探》,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情性论/以情论《诗》(如谭德兴《宋代诗经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这些名称或有小异,实则大同。本文为体现“情”在宋代《诗》学中的价值与地位,通称为“以情解《诗》”。
②“虽然汉代四家诗都有关于《诗》中‘情性’的论述,但鲁、韩、毛三家论《诗》只是与‘情性’论偶有关合,而《齐诗》则将‘情性’真正引入对《诗》的解说之中,从而使‘情性’论《诗》成为《齐诗》的一个重要特征”(王长华:《〈诗经〉学论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1页)。另,本书同样论证了“齐诗”性情论的五行、数术特征,与人之性情无关。
③此39处包括《毛传》《郑笺》解读《诗大序》《诗小序》,以及解读《诗经》正文的所有文字。
④如有研究者论曰:“苏轼在这里很明显想把性情说成是一个东西,还要把‘命’也包括进来,性成了一种运动状态,溯其源为‘命’,触物而动则为‘情’,说到底,性、情、命似乎都是一个东西。”(叶平:《苏轼、苏辙的“性命之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86-92页。)
⑤《诗本义》一书共有“人情”一词21处,另有“常情”一词1处,除《常棣》《车辖》等少数诗篇取感情义,其他诗篇基本取其常情义。
⑥据《宋史》等史料记载,两宋很多著名学者出身卑微、生活困苦,“力学”“苦学”二字常见于他们的人物传记,比如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二岁而孤……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7页。)引领北宋学术革新的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75页。)等,他们是真正出身平民阶层的士人,天然带有平民阶层特性。
⑦古代《诗》学对夫妇之情的阐述源于汉代《诗》学,如解《小雅·杕杜》,《毛传》曰:“远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郑笺》曰:“序其男女之情以说之。”(李学勤:《十三经疏·毛诗正义:上、中、下》,北京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604页。)不过,毛、郑关于夫妇之情的解读文字非常少,除解《杕杜》外,其他只有《日月》“相好之恩情”和《鸡鸣》“亲爱之无已”等寥寥几篇。准确地讲,在“二南”25首“正风”中,没有一篇正面谈到夫妇之情,这说明汉儒尚未能正视夫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