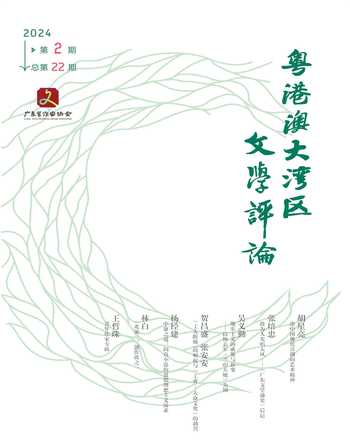历史视野的转换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变革趋势
摘要: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出现了不少或隐或显的变化。这些变化,蕴含并预示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变革趋势。从国族史观到全球史观这一历史视野的转换,是其中颇为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这在近期被纳入到“新南方文学”进行讨论的作家作品中体现尤为突出。这种转换,既体现于观看的方法与视野,也体现于写作的主题,是更新中国当代文学的路径,也会导致作家与世界之关系的变化,带来文学和历史学之间众多的互动和对话。
关键词:全球史;国族史;视野转换;文学;史学;变革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根本性的激变,但是也出现了不少或隐或显的变化。这些变化,蕴含并预示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变革趋势。从国族史观到全球史观这一历史视野的转换,则是其中颇为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国族史观,指的是以民族国家作为空间分析的基本单位或最大单位,历史叙述主要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为主要言说对象,又以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为目的;全球史观则是指在历史层面,采纳跨区域/跨国家/跨文化的路径,或者说,采取跨边界的方法,强调不同国家、区域或文化之间的连接与互动,主张人类彼此互联、共享一个世界,因此应该站在世界公民的位置去认识历史。这两种史观,在历史分析的方法、内容、目标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从晚清以来,构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历史认知和文学书写也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视野。围绕民族国家叙述而展开的文学书写则具有正典性质,形成了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的传统。民族国家的视野是统率性的,决定了观看的角度和范围,决定了哪些人、事与物是可见的,在历史层面也同样如此。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在书写时的历史视野开始有所变化,视野明显扩大,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全球史的视野,或者说,直接就是全球史的视野。
这种历史视野的变化,不受限于地域,在全国各地作家的作品都能看出。徐则臣在其小说创作中就着意从世界看中国、看北京,他的两部代表性长篇《耶路撒冷》和《北上》的历史视野都不局限于国族史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写的虽然是大兴安岭地区鄂温克族一个部落的历史,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但是迟子建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眼光并不局限于地方,而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意识,蕴涵着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思索。《额尔古纳河右岸》有鲜明的地域关怀意识,同时也省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全球逐渐扩张的时代,跟不上发展步伐的共同体、部族与个体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已能看到作家历史视野的扩展和全球史视野的萌发。而历史视野的转换,在近期被纳入到“新南方文学”进行讨论的作家作品中体现尤为突出。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熊育群的长篇小说《金墟》,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还有林森的中篇小说《心海图》,郭爽的短篇小说《新岛》,都是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作品。1
一
《平安批》的全球史视野,首先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它主要围绕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移民、商贸、宗教传播等活动所带来的种种跨国连结展开叙事。这些都是全球史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全球史的核心关怀在于流动(mobility)和交换(exchange),以及超越国界与各种边界的进程(process)。其出发点是互联的世界(interconnected world),其主要议题则是物质、人口、观念、制度的流动和交换。”2移民,还有商贸等联系,使得潮汕和世界之间较早就有了复杂的互联。而种种互联的景象,正是《平安批》所想要重点书写的。肇始于16、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以各种微妙的方式呈现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的许多方面当中,《平安批》中的潮汕也是如此。不单万金油、西洋镜、糖果、饼干、洋酒、雪茄、老唱片等来自异域的事物随处可见,各种外币也仿佛成了寻常之物,“马上会有各种外币从箱底翻出来,西班牙十字银币、葡萄牙双柱银币、美国大鬓小鬓银币等等,谁也少不了。最受欢迎的是墨西哥银币,名叫墨银或鹰洋,图案为雄鹰,用手一摸,雄鹰仿佛可以活过来展翅飞翔,而且这种鹰洋一枚能顶好几个银圆。最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雅银了,那种成色好、分量足,刚刚开始流通的银币。”3汕头的许多地方则行走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头班车里就有几个外国人,其中一个还操着标准的潮汕口音。汕头的大街上,外国人似乎比本地人还要多,有些和本地人一样,一大早就坐在面街的骑楼下,静静地喝着茶,精致的嘴型,神圣的清晨时光,不以天下为大,不以汕头为小的神态,和本地人毫无二致。”4
这种种随着贸易而来的事物,让人感知到了正在逐渐形成的全球网络。与他国之物、他国文明的往来和互动,则导致了人的生活世界的变化。《平安批》中这样写到西式建筑的引入:“外国人的洋行多在小公园这一带,遍地是西式建筑,尖顶教堂、挂着中国灯笼的花园洋房。花旗银行、太古银号、福音医院和老妈宫、存善堂、伯公庙这些闪闪发光的潮式建筑混杂其间,使各自的特征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势不两立。不过转眼一看,又觉得十分和谐,至少有一点两者极为相似,那就是过分的精心和过分的雕琢。让人眼花缭乱,叫人自卑,似乎是它们共同的目的。”1这段话,既是写以建筑为中心的生活世界,也反映了当时中西相遇时既相互渴望、又不免存在冲突的心理。
地方和全球的相遇,导致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巨大变化。这一点,首先可以在《平安批》中的郑梦梅、乔治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出。郑梦梅是小说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还是少年时,郑梦梅就知道自己有很多亲人成了番客,在海外工作、生活。过番也是郑梦梅所渴望的。长大后,郑梦梅也选择了过番,在暹罗替人写批,同时行走于东南亚各地,借此揭开家族历史的一些疑团。行走于不同地方的經历,也使得他看取潮州时有不同的视角。乔治这一角色也同样值得注意。他来自英国,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到中国来是为了认识中国并完成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久居中国的经历,还有外在者的身份,使得他对中国、潮州的认识与他人有别。
郑梦梅和乔治是彼时全球网络的连接者,在他们身上,能见出不同的地方、区域与文明连接时的复杂。正如黄挺所指出的,要理解作为“区域”的“潮汕”的历史,要注意两种视角——中国大陆的视角与海洋世界的潮汕,要注意潮汕的三个文化元素: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海洋世界的土著文化、来自北方大陆的中国文化、在大航海时代随潮流而至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理解16-20世纪的潮汕历史,必须注意西方文化传入后和本土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与重构,要注意与全球互动所造成的对潮汕文化的结构性变化。2黄挺对潮汕历史的研究,陈继明对潮州历史的讲述,都融入了全球史的视野——既从中国看潮汕,也从世界看潮汕;既从潮汕看中国,也从潮汕看世界;重视看潮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
《平安批》既写到郑梦梅、乔治这样的行走于全球网络的旅行者,也写到不少“在地之人”(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借用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概念。比如其中的老祖就是很值得关注的人物。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形象。她德高望重,行事干练,其人格力量、行动方式会让人想起乡土中国中的乡绅。她和《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一样,处处透露着人格魅力。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众多新事物的相遇,周遭世界的众多新变化,也使得她有了新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比之于《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也许更适合用来与她进行比较的,是另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朱先生”:朱宗元。朱宗元生于1616年左右,卒于1660年,一生生活于浙江宁波,从没有跨出国门的经历——老祖也是如此。可是在朱宗元身上,也同样经受了跨越国界的文化冲击。面对来自异域的宗教,老祖并没有产生认同感,更没有想要信仰的愿望,相反,她对此非常抵触。朱宗元的态度则与此有差异,他接受了来自异域的众多新观念并借此来论证儒学的合法性。在小说中,陈继明写到不同人在面對异域宗教在潮汕传播时的不同心态。《平安批》通过众多中西人物形象的塑造,再现并重构在世界日益互联的背景下、人们不断变化的意识模式和情感结构。在这一层意义上,《平安批》可以与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进行对读。
熊育群的《金墟》则涉及全球史与全球化、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这部小说有两条时间线,其中一条是民国时期,司徒文倡从广州回家乡建城,另一条是当下,镇长司徒誉面对一座古镇,思考如何使之重新振兴并付诸行动。其中,司徒文倡是司徒誉的曾祖父。小说中还贯穿了司徒氏和关氏两大家族的叙事。在书写司徒文倡的部分,小说中主要从全球史的视角去切入,司徒誉推动古镇开发这一条线索,则放置在当下全球化的视野中展开。
《金墟》用了较多的笔墨来展现全球和地方的关系。赤坎古镇,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赤坎古镇,可以说是全球地方化的典型例子。全球在地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物上有不同的表现。在赤坎古镇,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建筑——既有岭南建筑的显著特征,也带有鲜明的欧陆风格和情调。建筑工程师的专业背景,使得熊育群在表现这一方面时,甚是得心应手。对建筑景观的书写,是《金墟》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此外,熊育群在小说中也写到种种外来事物如何融合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开平的华侨家庭追求时尚,他们用的是旁氏面霜、柯达相机、三支枪牌单车、胜家衣车,时髦的雪茄、咖啡、洋酒、牛排、留声机、收音机也不鲜见。后生女抹英国口红,洒法国香水,穿玻璃丝袜,年纪轻轻就剪短发,烫卷发,穿旗袍和高跟鞋。后生仔学金山伯打领带穿西装,一双进口牛皮鞋在乡道上蒙了一层浮土,一到墟镇,有的人掏出手帕弯腰拍打,闪闪发亮了才上街。”1
《金墟》还用了不少篇幅来书写华人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生活的场景。对拘留囚禁华人的天使岛等历史场景的书写,尤其值得注意。小说中采取的是一种从当下回望历史的视角,这使得对历史现场的重返可以融入当下的省思。历史和当下两条时间线索同时展开的叙事结构,使得《金墟》能够呈现早期全球化到当下更有深度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金墟》既写历史中的全球拼搏故事,也写当下的全球拼搏故事;既写出了不同时代人物命运各自的时代性和戏剧性,又写出了不同历史时空中人物命运之间的呼应和相似。
《平安批》和《金墟》在题材层面有一定的互补性,尤其是在对贸易和移民的书写上。广东华侨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潮汕、梅州和五邑。潮汕和梅州等人的华侨大多去往东南亚,五邑等地的华侨则以去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居多,在区域分布上有其特点,《平安批》和《金墟》在书写上正好各有侧重。岭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有着连接中国与东南亚、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悠久历史,这种历史影响一直延伸至当下。《平安批》对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区域的书写,《金墟》对海上丝绸之路在北美区域的书写,对于我们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下和未来,不无启发。
二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林森的《心海图》和郭爽的《新岛》都涉及战争这一全球互联的负面形式,重视思考战争与文明的关系。
在《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篇幅宏大的长篇小说中,邓一光回到历史深处,把目光投向香港保卫战,以倔强的认知意志深入到一个地狱般的世界的内部,以史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呈现战争如何扭曲人性,如何把人抛入非人的境地,也反思战争如何借助国族、文明之名而获得合法与正义的假面。小说中对战争的思考,既从政治的角度展开,也从文明的角度展开。比如小说中写到饭岛要人作训示时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英美长期榨取亚洲,摢夺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亚为彼等称霸东方之据点,日本与西洋文明冲突苦痛愈深,对西方反抗决心愈强,自不能屈服于英美强权,任十亿东亚人民陷落为奴隶。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战争,日本身为东方盟主,决心拯救东亚各国命运,迅速铲除英美势力,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以此贡献于世界持久和平,亦不外乎源此崇高之精神。”1当文明被这样利用,文明就成了野蛮的一部分。《人,或所有的士兵》以一种罕见的笔力展现战争本身的残酷,对文明的反思也异常深入、透彻。
《人,或所有的士兵》的空间场景的选取,包括历史叙述,都跨越了国族史的边界,在全球史的视野当中展开。这部小说在叙述上独具匠心,以众多人物的证词为主体。小说中的人物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也有着不同的利益和立场。而其中关于战争之破坏性的思考和呈现,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中曾借“郁漱石案”的辩护律师冼宗白这样说道:“战争的结局不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了下来,也不是世界经过胜利者的分配拥有了全新的格局,它最大的结局是人性的改变。人性的改变潜伏在价值观下、政治主张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任何建立在对世界重新瓜分诉求和修缮立法秩序上的愿望都要重大无数倍,它决定了未来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类,它比战争本身更加危险。”2小说的题词则为:“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
《心海图》的主人公名叫方延,是海南人,出生于1918年。他曾在海南读书,后来被父亲送往香港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方延成为费尔曼号上的侍应生。1942年,费尔曼号从南非德班港出发前往荷兰殖民地荷属圭亚那的一个港口时,被德军击中,方延成为费尔曼号上唯一的幸存者。在海上经历无比漫长的、噩梦般的一百四十多天后,方延才得以获救。几经辗转,方延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又回到中国、回到海南,并在此过程中回忆起种种往事。小说主要是从他回国的情景开始写起,逐步回溯并展现过去的种种。
《心海图》重点写了方延个人的生命历史,却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同时还写了他的父辈,写了海南的一段历史,也写了方延所经历的时代和世界。在展开叙事时,《心海图》也有全球史的视野,不管是方延的个人历史还是海南岛的历史,都被放置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去进行打量。尤其是在书写方延获救后在英国、美国的遭遇时,始终能结合彼时的世界局势来展开。
郭爽的《新岛》试图以精简的笔墨呈现一座岛屿的方方面面。“这岛虽靠近大陆,离得最近的镇子不过十海里之外,但毕竟是个小岛,孤悬海上,船开出去十几海里就到了公海。整个南中国海域,这里是日本人最早登陆、最晚撤离的地方之一。教堂原本叫露德圣母堂,日本人来之前,是岛上信天主的教众弥撒聚会之处。日本人数次登陆后,最终选中岛的北角作战略部署,教堂也改作‘南支海防軍挺进队基地指挥所。”3这座小岛的地理位置、历史、自然景观都有其独特性。岛屿虽小,但承载着广阔的世界历史,是政治、宗教和商贸等活动的重要节点。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先天听力缺损的哑巴,从小生活在岛上,后来也一直生活在岛上。他弟弟聪明,健全,有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给香港人的渔船打工、出远洋、挣美金,却在远洋船上染上毒瘾后自杀而死。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兄弟二人实际上构成对岛的不同面相的隐喻。哑巴代表着岛屿相对封闭的一面,哑巴弟弟则隐喻着岛开放的一面。他们的不同特点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反映岛屿的全貌。
在具体的书写上,《新岛》采用了非常合乎小说艺术规律的写法,先从岛的自然景观写起,然后带出各种不同的人物和事件。《新岛》对不同事件的书写,则采用短篇小说常见的方式——放弃事无巨细的描写,选取横截面,以有限的笔触展现岛的不同方面。比如岛民原本有原始的信仰,天主教等外来宗教也在当地留下众多印记,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江能士神父曾在此看病、收孤、办学、传教;日军多次在此登陆,引起当地渔民的反抗,江能士被杀,他所主理的露德圣母堂被焚毁。小岛的沙滩上,则至今埋藏着形形色色的瓷片,它们有的出自外销瓷,原本打算运往英国、中东等地。历史在此有许多流变,至今也仍旧有着众多的痕迹。这种种事件的横截面,因为哑巴等人的存在而建立起基于小说逻辑的关联,同时也是基于全球史视野的关联。从中,我们能看到全球互联下的众多活动如何影响一座岛屿及其住民的方方面面。
三
在上述作品中,历史视野的转换,既体现在观看的方法与视野上,也体现在写作的主题上。葛兆光提倡一种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认为全球史,包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具有如下特质:“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移民的互相影响,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互相的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1葛兆光所谈到的全球史的这些主题,也包括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大多有所体现。
从国族史到全球史的历史视野转换,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历史视野的转换,是更新中国当代文学的路径。这是因为,视野的转换,会相应地带来很多方面的变化。比如,以往作家们对地方的理解,往往是在国家-地方的框架中展开的,国家构成理解地方的视野,而近年“新南方文学”方面的创作与评论,除了国家-地方的框架,也有世界视野或世界性元素的融入,有一个全球-地方或全球-国家-地方的新框架。认识框架的改变,会带来很多的改变。以往在历史研究或小说创作中的次要问题,现在可能会变成主要的问题;一些原来可能压根就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又可能会变得非常引人瞩目。比如宗教的传播问题、不同的文化和艺术的融合的问题、跨国界的交往伦理问题,如果以国族史为视野,那么它们会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则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历史视野的转换,还会让一些以往被遮蔽的问题重新显影,得到再认识。正如程美宝所指出的,“中国地方史的叙述,长期被置于一个以抽象的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也是导致许多具有本土性的知识点点滴滴地流失,或至少被忽略或曲解的原因。18世纪以来广州的历史叙述,最好用来说明这一点。当历史家以广东为例正面地讨论‘中西交流的时候,不会忘记容闳,不会忘记康梁,不会忘记郑观应,更不会忘记孙中山,但他们往往会忘记大批为欧洲人提供服务的普通人,许多中西文化、生活、艺术和技术的交流,是通过这些人物特别是商人和工匠实现的,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和实物史料,在中国几乎是荡然无存,只有在欧美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拍卖市场上才可以找到。我在这里不打算展开讨论,但我想提出的是,近代广东的文化性格的‘地方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地区各阶层的人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因为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交流/交换的结果;而其‘中国元素,则是读书人竭力加入、营造和论述的体现。因此,要了解像广东这类‘边缘地区近代地方文化的发展,只有跨越地方,跨越国界,跨越以抽象的中国文化为中心的视角,才不致对焦错误。”1在这段话中,程美宝所谈到的认知盲点,虽然是立足于史学界而提出,但是这样的问题,在小说创作领域同样存在。相应地,程美宝所提倡的跨越地方、跨越国界的视野,这样的视野更新,对于小说创作领域也同样适用。实际上,这种史学观念的更新对小说创作领域已有所辐射。这一点,我们在《人,或所有的士兵》《平安批》《金墟》《潮汐图》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随着认识框架的改变,作家对地方性的理解其实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新南方文学”而言,对地方元素的征用是不少作品的特色,涉及方言、地域文化等地方经验或地方知识的征用。可是,这些作品,又往往尝试超越地方性,和人们以往所熟悉的地域文学或国族文学大不一样。
其次,历史视野的转换,会导致作家与世界之关系的变化。葛兆光曾谈到,“进入全球史研究的时代,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第一,它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是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2葛兆光谈到的三点变化,在上述论述中都可略知一二。这里想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历史视野的转换,会使得作家更多地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去书写。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夏志清曾谈到中国现代文学有“感时忧国”的传统,这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指认。在指认的同时,他也隐约地指出,这会构成一种限制。如王德威所言: “夏志清当时对‘感时忧国这四个字的这个描述其实是有贬义的。他其实是认为,一个伟大的批评者,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不见得只应该把眼光局限在一时一地的历史辩证上而已,尤其是党同伐异的宗派姿态。文学以及批评的创造者当然立足家国,但他的心胸应该是无限开阔。换句话说,它應该同时也是个 cosmopolitan,就是一个四海一家、有世界观的、世故的文化人。”3的确,作家不妨有国族意识,是国民的一分子,同时也应该是世界公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埃德加·莫兰所主张的,同时应该以地球为祖国。这两者并不矛盾。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不只是意味着要作家从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去书写,而是在书写中承担着文明、文化的阐释者和沟通者的角色。这意味着,作家要往返于不同的文明体系、文化体系,着力促进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作家的书写要成为跨文明、跨文化的桥梁。这不只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愿景,实际上,也是迫切的任务。在本文所谈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长篇到中短篇,几乎每一篇都涉及战争。回顾我们的过往历史,战争或形形色色的冲突,是笼罩着历史与我们的巨大阴影。而在今天,种种形式的冲突仍旧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包括战争、冲突在内的全球互联的负面形式,最终可能导致互联的彻底中断,让世界变得四分五裂。只有在多元文明、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文化、文明的互观、互识、互补、互利、互渗、互融,不同的国家、区域和人群能够真诚地理解和承认,做到求同存异,世界才有可能会变好。
再次,这种历史书写是具有当代性的。历史是当下的起源,影响着当下,也是当下的参照。历史有其独特的在场性,如赵汀阳所说,“过去发生的事情虽在线性时间中流逝了,但其历史意义却始终在场,堆积于现时,迫使时间发生折叠,因此,历史性的‘现时并不是线性时间的某个点,而是时间折叠了的复合时间或多维时间,包含着自古至今的许多时间维度,而折叠起来的多维时间形成了超出时间性的历史性。”1这也是当代人不断回望历史、书写历史的动力。这种回顾能给人带来启发,打开理解问题的视野。读《潮汐图》,我们会注意到林棹用了不少篇幅来书写西方博物学引入中国时的情景,而近年来,博物学在中国恰好有复兴的趋势。这些书写所带来的历史与当下的对照,成为写作之当代性的范例,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视角和历史景深。
第四,历史视野的转换,会带来文学和历史学之间众多的互动和对话。《平安批》《人,或所有的士兵》《潮汐图》的写作,也包括对这些作品后续的阅读和阐释,都说明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互相滋养、互相促进的可能。一方面,目前中国当代小说中历史视野的转换,显然得益于史学研究的众多成果,尤其是全球史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实现历史视野转换后的小说创作,也有可能为史学著作的书写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或是和史学著作构成独特的参照。这也会带动人们在新的语境中思考小说和历史学著作在书写方法上的同一与差异。读有的小说作品,我们会注意到,作家对史料的消化还有待加强,如何保持文学性,或是生发出新的文学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而历史学著作在书写方法上,也可以向小说借鉴经验。比如史景迁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胡若望的疑问》,还有史蒂芬·普拉特的《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都显示出小说同样可以为历史著作的书写提供有益的写作经验。这样的历史学著作又能够给小说家的写作带来启示。比如小说家李洱就谈到他对史景迁的写作方法很感兴趣,“惊叹于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史,令人感到他既是司马迁的后人,又是希罗多德的徒孙,还是兰陵笑笑生与曹雪芹的徒儿,同时又是吉本的师弟”。2史蒂芬·普拉特同样注重历史书写的可读性,被称为史景迁的接班人,他的《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中提出的史观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虽然有待商榷,但是其历史书写的笔法确有可观之处,可读性非常强,甚至比不少历史题材的小说还要引人入胜。
第五,历史视野的转换,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小说在历史书写方面的多样化。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从国族史观到全球史观这一历史视野转换是大体相似的,而从微观的层面看,不同的作家作品显示出或大或小的差异。差异首先体现在全球史观和国族史观的关系上。从历史学科的内部来看,全球史的兴起,存在着试图超克国族史的意图。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梳理全球史研究的起源时就指出这一点。程美宝也认为,全球史的倡导者“希望从根本上推翻以民族或国家为前提的史观”。1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写作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史和国族史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正如杨斌所指出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考察跨地区的联系和互动。在很多时候,世界史或全球史挑战甚至解构地缘政治的边界或地理空间的划分。从狭义上来说,全球史关注当今我们所处的全球社会形成的过程,倡导那些超越并将不同地区联系起来的主题、问题、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式。这样,在全球史和地方史(国别史作为其最耀眼的代表)之间就有某种张力。实际上,全球史从来没有宣称自己可以替代地方史,相反,全球史渴望、需要并召唤地区研究。更何况全球史不但以区域研究为坚实的平台,其本身也是从区域研究中诞生的。”2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也认为,“全球史不必因为大尺度的思考而放弃充满细节的地方视角。全球史史学家也不只是撰写流动的历史或开放而联动的历史。”3葛兆光则谈到,全球史也能容纳国别史,“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叙述形式。”4这就意味着,全球史、地方史或国族史之间,可以互相成全,相得益彰。全球、地方和国族,实际上也会互相影响,不断互动。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历史视野的转换,并不体现为一个全球史观截然替代民族国家史观的过程,而是呈现一种地方史、国族史或全球史双重叠加或多重叠加的状态,而且不同作家在具体的写作中会有多样化的表现。在《耶路撒冷》《北上》等作品中,全球史观的萌芽,主要体现为从国族史观的基础上扩展。林森的《心海图》和郭爽的《新岛》的全球视野,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全球微观史的书写实践——把一个人、一座岛的历史放置在全球视野中去进行打量。《人,或所有的士兵》和《平安批》则侧重展现全球互联如何造成结构性的变化,对世界互联的结构也有所展现。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的写作可以是非常多样化的,正如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所言:“全球史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5这样的多样化,在小说创作中远未穷尽,每个小说家都可以设想一种属于他/她的全球史/全球-中国故事的讲法。
本文为“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1 关于《潮汐图》的全球史视野,笔者已有专文解读,为避免重复,这里不再对之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具体论述可参见李德南:《世界的互联与南方的再造——〈潮汐图〉与全球化时代的地方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7期。
2 [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3 陈继明:《平安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4 陈继明:《平安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25页。
1 陈继明:《平安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27页。
2 黄挺:《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4页。
1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化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1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2页。
2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4页。
3 郭爽:《新岛》,《钟山》,2023年第3期。
1 葛兆光:《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声回响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頁。
1 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知识: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想》,《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5—16页。
2 葛兆光:《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声回响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3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46页。
1 赵汀阳:《邀请古人成为我们的当代人》,《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期。
2 李洱:《李洱:“有痛”与“有警”,札记二则——2023年度私人阅读》,“文艺批评”公众号,2014年2月7日。
1 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知识: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想》,《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2页。
2 杨斌著译:《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3 [德]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张旭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65页。
4 葛兆光:《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声回响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页。
5 [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