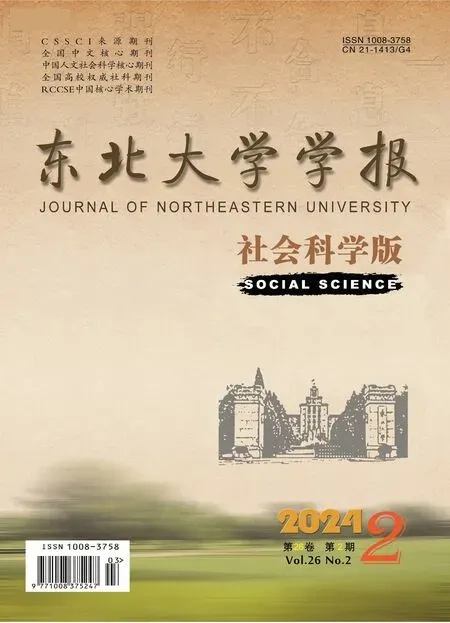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及其理论启示
营 立 成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44)
法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重镇,也是现代社会学的诞生地。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一段时间内,法国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理论家,他们围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特点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假设、方法的社会理论著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谈及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特点,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便是它的“总体性”。“总体性”(tot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一个关键概念(1)张桂枝:《从总体性到总体化——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探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被卢卡奇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决定性区别(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79页。。按照总体性原则,人们在考察社会现实时要将“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80页。,“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4)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页。,勇于打破各种决定论、经验主义、学科条框的桎梏,在一个开放的总体性坐标中定位具体问题,在整体与部分、现象与本质、总体与差异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社会现实。深受卢卡奇、柯尔施、萨特、阿尔都塞等人影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们非常熟悉“总体性”概念,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对总体性原则的阐发与运用。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认识、梅洛-庞蒂对社会事实的总体性把握,体现出从人的总体性出发理解社会的理论视野;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戈德曼基于发生结构主义视角彰显的总体性、普兰查斯(又译作波朗查斯)所阐释的“社会实践总体”则反映了融合建构与结构的社会总体性视野。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逻辑,构筑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所裨益。
一、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作为追寻总体性的场域
被誉为“法国迄今为止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5)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胡文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的列斐伏尔与柯尔施、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非常重视“总体性”范畴的重要性。列斐伏尔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指出研究个别事物只是思维的第一阶段,一切哲学活动归根到底还是要再现总体(6)Lefebvre H.,Dialectical Materialism,trans.John Sturrock,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113.。然而,这个“总体”往往是难以定义,甚至难以研究的(7)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2页。。一些人把人类活动当成抽象活动的机械总和,以一种形式逻辑来探索整体,这种古典唯心主义方法得到的只可能是抽象的总体性。一些人试图凭借想象回到具体活动发生之前的阶段,借助模糊的直觉、原始的精神状态来寻找整体,这种“理智与反理智主义的奇怪混合”实际上简单否定了抽象活动,抛弃了这些活动的条件性,不可能发现真正的总体性。一些人将总体简单看作各部分的简单加总,将事物之间的分离看作一劳永逸的,这必然陷入机械论的错误。还有一些人(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试图通过考察孤立的存在物或局部来推断和把握总体,但这种“整体化”的方法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事先知道整体是先于各个要素的,整体作为一种实践或实际结构而存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的统一性正在被破坏,被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原因弄得支离破碎(8)Lefebvre H.,Dialectical Materialism,pp.113-116.。更重要的是,我们很难从方法论意义上有效地确定总体。列斐伏尔问道:我们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吗?如果是,这个整体是哪一个?是资产阶级社会、工业社会、技术社会,还是一个转变中的不知去向的社会?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但他却又把这个“整体”看作受到内部矛盾撕裂、不久要被革命所打碎的整体(9)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96页。。这样看来,“总体”这个概念似乎不甚明了、难以把握。
那么,要如何把握“总体性”——或者用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末尾所强调的,把握“总体性内容”(total content)(10)Lefebvre H.,Dialectical Materialism,p.155.呢?列斐伏尔将我们引向了日常生活(11)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页。。列斐伏尔在与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合作的《神秘化: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1933)(12)该文后来被扩展为列斐伏尔第一部广为人知的著作——《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1936)。一文中首次提到了“日常生活批判”的概念,他认为所有对被资产阶级神秘化的意识开展的分析都可以被归结为日常生活的批判(13)Lefebvre H.and Guterman N.,“Mystification: Notes for a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in Lebas E,Kofman E,Elden S,eds.,Lefebvre H.,“Key Writings”,New York: Continuum,2003,p.72.。由此,日常生活批判乃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拜物教批判和异化批判。在1939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列斐伏尔谈及实践范畴时也涉及日常生活,他写道:“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点和终点……这个词本身表示常识所指的‘真实生活’,这种生活比思辨理性的生活既平淡无奇又富有戏剧性。”(14)Lefebvre.H.,“Dialectical Materialism”,p.100.可以看出,这个蕴含着实践总体性的“真实生活”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当然,列斐伏尔从总体性的视野考察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追寻“总体性革命”旅程的集中体现,还是在耗费三十余年写就的《日常生活批判》三部曲中。总体而言,列斐伏尔从四个维度向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所蕴含的总体性逻辑。
第一,日常生活蕴含着人的总体性。对列斐伏尔来说,“总体性”问题首先是关于“人”的问题。列斐伏尔指出:“人是被自然所限制的生物,他是一个整体,一个能动的主体、一个致力于巩固和提升自己的自发生命。”(15)Lefebvre H.,“Dialectical Materialism”,p.119.抛开一切社会生活条件的“人性”并不存在,只有当我们仔细观察每一个物、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把人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时,“人”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16)Lefebvre H.,“Dialectical Materialism”,p.137.。因此,要理解作为总体的人,要把握人的全部东西,必须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回到社会实践之中。对于作为总体的人而言,日常生活是生产与生活、工作与闲暇的空间,是不断被异化同时也超越异化、追寻自由的场域。在一些人看来,日常生活琐碎而缺乏价值,而且每个地方的日常生活都不一样,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始终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小小的、个别的、偶然的事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无限复杂的社会事件,比它本身所包含的“本质”要丰富得多(17)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52页。。例如,一个妇女买了一磅糖,这件小事背后是她的生活、经历、工作、家庭、阶层、支出计划、饮食习惯、如何用钱、观念想法,乃至于涉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历史(18)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52页。。因此,只有在日常生活之中,自然的人和生物的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人;只有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个人、这个后天的人、这个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成为自然人;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历史、劳动、社会生活和文化才得以改造人的器官使之“人化”(19)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88—89页。。总之,日常生活的物质乃是“人的原料”,人的总体性——人与他自己相统一、与社会相统一——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不断实现。
第二,日常生活蕴含着未分化的总体性。列斐伏尔指出,在所有那些清晰的、高级的、专门的、组织起来的活动之外还存在“剩余”,这种剩余被日常生活所填充(20)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90页。。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是一个现代社会组织化、专业化领域之外未分化的世界,是一个自然和文化、历史和现在、个人与社会、现实与不现实相互混合,一个过渡的、相会的、相互作用的、冲突的地方(21)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76页。。因此,列斐伏尔强调日常生活既是平淡的,又是富有戏剧性的。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面临的日常生活的问题是不同的: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忍受着有限而单调的时空环境,他们和他们的关系附着在各种符号周围,弱小但顽强地生活着,对他们来说,时间是循环的;身处上层的人们享受着宽广的时空范畴、追逐着权力和反自然,他们在线性的时间中前行,但他们也更容易丧失自我(22)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81—283页。。日常生活便包含着一个个这样的片段,并把它们捏合在一起。对于这样一个未分化的世界,人们不能从空中、从遥远的地方去考察,既要拒绝分割出来的专门化,也不能把任何专门科学当成社会科学的总和,必须居于事实与理论的交界面中去理解它(23)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57—258页。。从这个角度讲,日常生活构成了一个未分化的人类实践总体性(24)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第121页。。
第三,日常生活蕴含着批判的总体性。列斐伏尔认为,是否采取批判的方式使用总体性范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25)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72页。。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宣称,他们可以完全掌握总体,可以描述总体,可以用非批判、非辩证的方式呈现总体。在这种情况下,“总体”总是被贴上各种抽象的标签,成为任人摆布的玩偶。马克思主义者则始终立足于社会实践,他们拒绝离开现实世界去追逐另一个世界,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深厚根基之中开展对人的批判和对人类状况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分析了日常生活。在这里,劳动者与他们的工具相分离,仅仅通过他们与雇佣者联系起来的“合同”与他们劳动的物质条件联系起来。他们以不幸福的方式体验着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常常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神话所遮蔽(26)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36页。。在个体劳动者的社会生活层面之外,马克思主义还将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综合起来,呈现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认识”(27)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36页。。
第四,日常生活蕴含着开放/可能的总体性。列斐伏尔提醒人们,对“总体性”的把握绝不能教条化,用一个体系化的、封闭的、僵死的总体结构去理解日常生活是不可取的。他举了一个关于贝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沙滩上的贝壳有着精美的纹理,这些纹理记录了贝壳变迁的细节,勾勒了贝壳表层的样貌,似乎以结构化的方式把贝壳的全貌展现出来。但是,如果仅仅关注这些“结构”容易忘记如下事实:一个活的贝壳不仅有这样一个“硬壳”,它的里面还有一个柔软的、黏糊的、无法定性的生命(28)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76页。。日常生活跟贝壳一样,它始终包含定形的部分和不定形的部分,后者具有偶然性、模糊性与可能性,它们构成了日常生活行动和自由的支撑点。因此,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始终对“可能性”开放,这个“可能性”不是虚构的或幻想的可能性,而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29)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30页。。我们应该跳出“真/假”“是/否”这样的二元范畴去把握现实,从“真、假、随机(或可能)”的范畴去理解现实(30)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404页。。“可能性”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如此重要,因此列斐伏尔提醒人们,在关于“怎样生活”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解决“生活落后于可能性”的问题(31)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12页。,我们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确定“现代生活”与“可能性”断裂的关键部位,确定新的可能性重返日常生活的关键节点。
由此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辽阔的总体性空间。在这个未分化的、充满着无限可能性的场域之中,人的异化与去异化交替上演,平庸与神奇交相辉映。用辩证的、批判的视野考察日常生活,既要求我们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充分认识人们重构自己生活、在对抗异化的生活中寻求可能性的具体实践,也要求我们跳出经验性范畴,把握作为对象的劳动者的异化、生产活动的异化、作为生物人的异化、作为自然人的异化等范畴,批判性地揭示日常生活的异化过程,进而探索与自己相统一、与社会相统一的“总体人”的可能性。
二、梅洛-庞蒂:重塑关于社会事实的总体性知识
列斐伏尔面向广阔的日常生活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与列斐伏尔同属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梅洛-庞蒂也在对社会事实的创造性分析中阐释了一种以主体经验为中心、彰显实践性与处境性的社会总体性理论。梅洛-庞蒂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现象学哲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赢得了“哲学家的哲学家”(32)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2页。的赞誉。不过,梅洛-庞蒂并不赞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表达的绝对自由的主体哲学,而主张在充分考虑社会状况与他人共在的条件下阐释一个主体间性的社会世界,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社会学的视野。当梅洛-庞蒂将关注感性知觉的现象学纳入社会范畴时,他必须向人们说明包含着复杂主体经验的社会总体性是何以可能的。我们知道,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是在严格排除个体观念等主体经验基础上建立对社会事实的总体性理解的。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自成一体、不可化约的“整体”,社会事实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我们只有把社会事实作为“物”进行观察,只有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才能达到因果解释的目的。因此,社会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总体性存在(涂尔干称之为“非人格神”),它塑造着有机体中每一个“器官”的运动和命运(33)孙帅:《神圣社会下的现代人:论涂尔干思想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这样,梅洛-庞蒂必须与涂尔干对话,重塑关于社会事实的总体性理解,将社会事实从纯粹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中解放出来。
梅洛-庞蒂首先对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基础进行了猛烈批判。在他看来,涂尔干所谓社会事实的科学性和社会的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迷思。梅洛-庞蒂写道:“他因此假装把社会事实作为外在于他的东西来涉及……借口社会学实际上尚未按照这一真实的经验被构成,借口它乃是对这种经验的分析、说明和客观化,借口它搞乱了我们对于社会关系的最初意识、并最终使我们感受为我们最初意想不到的动力的非常特别的变种的那些关系呈现出来……”(34)梅洛-庞蒂:《哲学赞词》,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页。如此说来,那种把社会事实看作外在于个人、外在于经验的“物”的做法貌似客观中立,实际上切断了社会事实与主体经验的联系,将意义排除在事实之外,因而只可能得到一种形而上学的“伪客观性”。从根本上来说,这不过一种追逐“绝对真理”的唯科学主义,它忽略了现实的、具体的人,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社会决定论”以一种抽象的总体性掩盖了问题,并没有真正给出问题的解释。例如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用“神圣”定义宗教,并将神圣与社会同一化,进而得出“宗教生活只是社会获得自我意识的方式”的结论(35)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张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9页。。然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这里的“社会”不过是在外延上组装起来的一个概念,用它来解释宗教现象根本不能深入宗教生活内部,不能使得种种难题从晦涩抵达清晰,只不过原来这些难题被归于“宗教”这个概念之下,而现在则被转移到“社会”的概念下。实际上,与其用社会/社会事实解释宗教,不如把社会和宗教都看作被特定文明建立起来的既真实又虚幻的人类联系的两个方面(36)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第120页。。在批判性地检视了涂尔干所确定的社会事实总体性之后,梅洛-庞蒂向人们解释了自己对于社会总体性的理解。梅洛-庞蒂从卢卡奇的总体性观点出发,认为“总体”不是所有的可能存在和现实存在,而是“支配权的总体”,也就是“我们已知的全部事实的融贯汇聚”(37)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30页。。因此,“总体”不可能排除主体,它并不是存在于抽象的普遍真理之中,而是存在于实践之中,存在于主体的认识、体验与现实的感知之中。梅洛-庞蒂说,主体总是参与到总体化的任务中,既在历史中认识到自己,又在自身中认识到历史,让“自己”既作为知识,又作为“事件之所”(38)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31页。。因此,社会的总体性并非一种“物的辩证法”,而只能是“主体在其中起作用的总体辩证法”(39)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34页。。这种辩证法要求主体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在解读历史中呈现意义,在践行意义中沉淀历史。在这种历史交替的循环之中,有意识的主体得以不断在建构自身的同时建构社会,社会也能从离散状态不断整合,从而实现“社会的社会生成”(40)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38页。。
因此,梅洛-庞蒂认为,必须抛弃一种貌似客观的纯粹社会学,在主客体的交互之中,在“处境”之中把握知识、探索真理。处境(situation)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场域,是主体经验的生成空间。“主体置身处境”不同于“客体存在于空间”。我们的处境是我们好奇、探索和兴趣的源泉,这些处境被他人澄明,被作为他人处境的变体而被他者把握,进而使得我们的生活与人类经验的整体链接起来(41)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77页。。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凭借我的处境才能与对我具有某种意义的整个活动和整个认识联系起来,只有在我的处境的有限性中建立与社会的一切联系,人们才能找到整个真理的起点,社会学家才有可能界定和追求真理。因此,梅洛-庞蒂提示我们应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当我们洞见到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客体,而首先是我的处境时,当我在自我中唤醒这一我的社会意识时,正是我的整个共时性向我呈现出来,透过这一处境,我能够真正将之视为共时性的东西是过去,正是历史共同体的一致与不一致的整个活动将‘我’实际上置于整个活的现实之中。”(42)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81页。从“我的”处境出发,社会事实便是客观性与体验性交互构成的总体性经验,我们的社会便构筑于这种经验之上。
梅洛-庞蒂认为,上述对于社会事实的总体性观点虽然与涂尔干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却可以在涂尔干的弟子莫斯那里看到一些影子。莫斯在对巫术的研究中发现,要理解巫术现象的深层次理由,必须始终把握“制度在人与人之间构成的交换的世界”(43)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83页。,这样一个“交换世界”绝非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实在,而是象征有效的系统或象征价值的网络,它将深入个体的最深处(44)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84页。。因此,莫斯所呈现的交换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社会事实,不如说是对“土著理论”的加工,这些理论展现出将多种要素链接起来的情感纽带,它既指向自己也指向他人,本质上体现了对一种不可见的总体性要求。在这里,莫斯并没有像涂尔干一样去争论社会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他把社会作为一个象征系统,将交换实践看作社会本身。在这个系统中,尊重个人的存在、社会的实在与文化的多样性彼此共存,形成了一个与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有所区别的社会人类学视野。
不论将社会事实看作“处境”,还是把社会看作“象征系统”,都要求我们打破学科壁垒,在更加综合的理论视野中去把握社会事实,更好地实现社会学与哲学思维的融合。关于“哲学”,梅洛-庞蒂谈道:“人们将哲学称作这一意识:我们应该捍卫与生活的、说话的、思考的别的自我的开放而连续的共同体,两者彼此在场,都与自然处于某种关系之中,我们于是在我们背后、在我们周围和在我们前面,在我们的历史领域的限度内推测,这一共同体来自于最后的实在,我们的理论构造描述了它的运作但不会取而代之。”(45)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77—78页。不难发现,梅洛-庞蒂所谓“哲学”并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向内求索的思辨之学,而是以主体经验为纽带,联结自我、他人与社会的总体性之学,它要求我们摆脱种种既有知识体系的束缚,直面“前知识”状态下的主体经验,通过逐步将我们与整体历史连接起来的主体间性来把握生活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家必须在记录和描述事实的基础上,同时作为一名“哲学家”,才能真正形成对社会事实的理解(46)梅洛-庞蒂:《哲学赞词》,第67页。。
三、戈德曼:探索意义结构的总体性生成
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西克指出,作为总体的现实并不是全部事实的总和,而是一个结构化的、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整体(47)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25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总体性生成与总体性场域、总体性经验一样,也是总体性的社会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范畴,这将我们引向了法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对总体性发生学的研究。戈德曼是卢卡奇的弟子,他对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概念十分重视,同时戈德曼又深受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影响,“发生结构主义”“有意义的结构”等概念均源于皮亚杰。在卢卡奇和皮亚杰的双重影响下,戈德曼试图以总体性视野把握文本,揭示蕴含其中的意义结构及其发生学机制。因此,在其成名作《隐蔽的上帝》自序中,戈德曼这样描绘他的理论旨趣:“人的行为始终构成全面的意义结构,这样的结构同时具有实践性、理论性和情感性,并且只有从接受某一系列社会准则基础上的实践的角度,才能对这种结构进行实际有效的研究,也就是说才能同时解释它和理解它。”(48)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作者序言”,第1页。
“意义结构”(meaning structure)是戈德曼以总体性视野把握文学文本的重要概念范畴。戈德曼指出:“一种思想,一部作品只有被纳入生命和行为的整体中才能得到它的真正意义。”(49)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第8页。需要说明,戈德曼这里所谓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想要赋予作品的主观意义,而是一种客观意义。作品的主观意义完全由作者赋予,这就使得这种意义变动不居、难以恒定,而且也不见得真正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而客观意义则不同,它存在于作品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之中、存在于历史演变的整体中,乃是对于人存在于世间所遇到的特定问题的较完整回答,是一种于社会而言的功能性。戈德曼进一步指出,人们不应当从作品内容与社会集体意识的关系中去找寻意义,因为作品的具体内容往往只是整个社会集体意识非常窄的一方面,很难系统、全面,而且那些有创造力的伟大作家也不屑于在作品中简单再现社会集体意识内容(50)戈尔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4—235页。。因此,我们要探寻的不是意义的内容,而是意义的结构。具体来讲,“意义结构”就是作品在概念的层次或在言语的或在感觉意象的层次上表现了一种连贯的世界观(51)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85页。。这种内在一致性可以调和一切纷繁复杂的因素或章节,让作品不同元素之间的必要关系聚合,这也是作品哲学、文学或美学价值的来源。另外,对于伟大作品而言,它还在更高级的层次上表现出有意义的结构,那就是“它们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为人类相互间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表现了各种全面的态度”(52)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83页。。换句话说,伟大作品的文本意义结构与特定时期人类社会的精神建构是同源的,这些作品在内容方面可以拥有完全的自由,被作者的个人经验与想象世界所支配,但在精神范畴却与那些将社会成员(往往表现为一个社会阶级)聚合起来并与其他群体抗争的全部意愿、感情和思想紧密相连(53)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第21页。。
戈德曼强调,意义结构的一致性并不是一个静态事实,而是一个存在于各个社会集团之中的动态事实(54)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84页。,这样一个动态事实的总体性生成构成了“发生结构主义”研究的内容。戈德曼认为,“发生结构主义”筑基于这样的基本假说之上:人类总是要对一些特殊境遇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并因此倾向于在行动的主体、与主体相关的客体及客观环境之间创造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始终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人们总是不断消除旧的不相适应的平衡、创造新的平衡整体(55)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178—179页。。如此说来,任何意义结构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人们对境遇的反映、行动与不断平衡中构建的,这一过程也体现在文学作品或人文思想的建构生成过程中。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尽管戈德曼谈到了“行动的主体”,但这里并不是指个人主体,因为单一的个人经验极为短暂且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所讲的是所谓“超个体主体”,或者叫“集体主体”。这种“主体”是由一群相当数量的、存在于同样环境下的联合行动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如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些社会集团总是与其他集团对立,但又与那些对立的集团一起,在这种对立之中共同对自然采取行动(56)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罗国祥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8页。。戈德曼还认为,从个人主体出发还是从集体主体出发,这是整个辩证的社会学与实证主义社会学最重要的不同之处(57)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第48页。。
与作品的意义结构同构的是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如果在意义结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的是“超个体主体”,那么我们便能理解如下论断:“往往有助于理解作品的行为并不是作者的行为,而是某一社会群体的行为(作者可能不属于这一社会群体),尤其是涉及重要的著作时,那便是社会阶级的行为。”(58)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第8页。在具体开展文学作品的社会学研究时,要如何有效地揭示那种社会群体行为(或者说“超个体主体”行为)与文学作品的内在联系呢?戈德曼提出了一种关于“理解”与“解释”辩证统一的总体性方法。他认为,阐明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而将它纳入一个更为广泛的结构则是一个解释过程,对作品发生的结构主义分析就是在“理解”和“解释”中循环往复、不断递进。为了说明这一点,戈德曼以自己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辛的悲剧之研究举例。首先,阐释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辛的悲剧结构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解过程;其次,将它们纳入冉森主义极端派并阐释后者的结构,对于帕斯卡尔和拉辛的作品来说是一个解释的过程,而对冉森主义极端派而言却是一种理解;接着,把冉森主义作为表现意识形态的运动纳入17世纪的穿袍贵族史,从而解释了冉森主义和理解了穿袍贵族;最后,将穿袍贵族史纳入法国的全部历史,同样是解释前者而理解后者,以此类推(59)戈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第240—241页。。
张一兵在评述戈德曼“既是理解又是解释”的方法时认为,他只是在一个非常外在的层面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60)张一兵:《全面的意义结构:总体类型学》,《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就上述嵌套式的递进展开而言确实算不上高深,不过却非常好地展现了戈德曼的总体性视角:这是一个从表象到本质、从局部到整体、从经验材料到结构化总体的过程。不过,这里没有绝对总体,只有体现意义结构的“相对总体”,在更高层次上,这个“相对总体”又是表象,是局部、是经验。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揭示一个至高无上的“总体”,而在于这一总体的意义性。由此,“总体”不再作为一个相对抽象的哲学范畴,而成为一种社会学分析的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
四、普兰查斯:在结构与实践的辩证总体性中理解社会阶级
戈德曼对意义结构的发生学研究向我们展现了文本总体性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家尼科斯·普兰查斯则在结构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作为总体性的社会阶级之构型。普兰查斯是阿尔都塞的弟子。阿尔都塞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始终强调在多元结构的辩证关系中把握总体性。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这是断言,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6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6年,第172—173页。因此,只有从各个部分彼此共生、相互作用,在结构与要素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普兰查斯接受了阿尔都塞的多元结构总体性观点。但与自己老师不同的是,普兰查斯不仅强调结构,而且十分重视社会实践。普兰查斯关于总体性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社会阶级的研究之中。
为了阐明自己的社会阶级理论,普兰查斯首先批判了两种错误的社会阶级分析——“历史主义”和“经济主义”。“历史主义”(historicist)将阶级演进看作一个历史的能动过程:它的起点是没有分化的一群个人,进而组织成为“自在的阶级”,最后以“自为的阶级”告终(62)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7页。。普兰查斯认为,这一观点除了重复了“人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外并无建树,它过分强调阶级实践的能动作用,以致将阶级结构弱化为阶级行动的附庸。而“经济主义”则强调经济结构对阶级的决定作用,社会阶级表述成经济方面的一个问题。普兰查斯认为,阶级关系确实主要是由经济领域中的实际地位来确定的,但绝不能说经济结构是决定社会阶级的唯一因素,实际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摆脱了单纯的经济标准的界限,他们都十分明确地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63)Nicos Poulantzas,Class in Contemporary Capticalism,London:NLB,1975,p.14.。在对上述两种阶级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普兰查斯把社会阶级理解为“作为结构影响而生产的社会实践关系”(64)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83页。,从结构与实践的辩证总体性中去把握社会阶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兰查斯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他对社会阶级的把握是有所侧重的。
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一书中,普兰查斯站在结构总体性一侧,同时也考虑了实践的影响。他这样定义社会阶级:“社会阶级是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示结构的整体,表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对承担者——他们构成社会阶级的支持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指示出社会关系领域内全部结构所产生的影响。”(65)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64页。将社会阶级界定为“结构的影响”是普兰查斯的理论创新,这表达了双重含义:第一,从根本上说,社会阶级是由社会结构总体决定的,这个结构不仅是经济结构,也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各方面的结构。具体而言,一方面这些结构是指“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或从属关系”(66)Nicos Poulantzas,Class in Contemporary Capticalism,p.14.,另一方面这些结构还体现为“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结构之间的联结”(67)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69页。。第二,总体结构对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不是体现在社会结构内部,而是体现在社会实践的影响上。普兰查斯指出:“社会阶级不仅表示一种结构整体,而且还表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是一种社会形态母体对结构承担者所产生的影响,即结构整体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影响。”(68)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5,pp.67-68.可见,社会阶级虽然植根于总体性结构,但不能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中找寻,而必须到社会实践领域探索,这就把实践与结构统一了起来。
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一书中,普兰查斯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社会实践总体”的概念,对社会阶级的讨论聚焦到作为总体的实践层面。他谈道:“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社会阶级是根据它在社会实践总体中的地位,即根据它在社会总体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加以定义的。这一总体包含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阶级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指示出社会劳动分工内部的结果。因此,这一地位是与我称之为阶级的结构决定一致的,也就是说,是与结构所决定的阶级实践内部的存在一致的。”(69)Nicos Poulantzas,Class in Contemporary Capticalism,p.14.可以看出,普兰查斯所强调的“社会实践总体”指向整个社会的总体劳动分工场域,包括其中的种种竞合关系与实践行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普兰查斯不再将社会阶级界定为“结构影响”,而是界定为“社会地位”,特别是考虑它削弱了生产关系对于社会阶级的决定性地位,一些学者据此批判普兰查斯的阶级概念实际上与西方社会学中诸如“阶层”“利益集团”等分析性概念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例如克拉克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是经过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修改和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理论。”(70)Clarke S.,“Marxism,Sociology and Poulantzas’s Theory of the State”,The State Debate,London:1991,p.91.但无可否认的是,普兰查斯所谈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还是指向于社会劳动场域,而且普兰查斯明确指出特定事件中的“阶级立场”与“社会阶级”是两码事,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有可能采取与自己的利益不一致的阶级立场,典型例子就是所谓“工人贵族群体”。他们在面对特定事件时常常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资产阶级,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1)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82页。,这与多元化的阶层理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尽管普兰查斯对社会阶级的界定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但还是始终沿着结构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逻辑展开。他始终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反对将结构看作“僵死的实践”,同时他也反对将实践同化于结构,强调实践所蕴含的强大理论。普兰查斯反对社会阶级的化约论,认为无论哪个维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都不能完全解释社会阶级。从这个立场出发,他认为“只有阶级实践才能表达社会阶级,这些存在于对立之中的实践,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构成阶级斗争的领域”(72)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83页。。因此,社会阶级既是作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总体辩证作用的结果,但一旦生成,其自身便具有某种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不能被外界的任何因素所解释,只能从内部做出实践性考察与结构性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发展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将“总体性”作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提出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围绕这一概念开展了极为丰富的研究,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如何以总体性的视野直面社会现实、开展社会问题研究,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探讨了四位法国重要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理论研究中所展现出的“总体性”视野。其中,列斐伏尔以“人”的总体性为起点,将日常生活作为总体性场域,引导我们以辩证的、批判的视野把握这个充满着模糊性、偶然性和各种可能性的未分化社会世界;梅洛-庞蒂从主体经验出发,借助“自我”与“他人”共在的处境重塑关于社会事实的总体性知识,揭示了社会总体性的经验基础;戈德曼着眼于文学文本的“意义结构”,在文本与社会的同构性逻辑中揭示了意义结构的总体性生成,提出了“解释”与“理解”相结合的文本—社会总体性分析方法;普兰查斯在社会阶级这一具体的社会研究领域,揭示出社会结构总体与社会实践总体的辩证性关系,并指出内含于社会阶级之中的总体性实践。应当看到,在理论渊源、逻辑起点、立论依据、研究方法、思想观点等方面,上述四位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呈现出的“总体性”逻辑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共同构筑起对社会学总体性视野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对于我们讨论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何以可能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
首先,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总体性”的研究表明,作为“元假设”的总体性与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之间并不冲突。正如卢卡奇所言,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7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80页。。因此,一些学者将总体性的基本逻辑理解为打破不同学科的边界,实现新的学科整合,激发理论的想象力(74)仰海峰:《从分化到整合——重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方法》,《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的确,马克思的理论呈现出知识与现实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75)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第15页。。我们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化约为一门个别学科。然而如果把学科性与总体性对立起来,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学是一门专门学科(76)列斐伏尔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称为一门“专门学科”,或“具体的社会学”,参见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页。,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总体性的;如果我们承认总体性整合了学科、消弭了学科边界,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社会学的。然而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那里,总体性与学科性并不对立,更明确地说,“总体性”乃是对社会现实状态的一种“元假设”。在此假设之下我们可以对具体的对象开展经验性研究,得出相应结论。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的人类知识已经不可能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那样,可以不顾及学科的专业化,作为一个总体加以描绘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现实的总体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假设,一种承载着可能性的层次,这样一个层次以不侵害其他学科权力的方式运作(77)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第16页。。日常生活作为追寻总体性的场域,它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而毋宁说是一种前提或“元假设”。例如,我们说家庭问题是日常生活的,那是因为家庭问题的一切——爱与怨、信任与怀疑、利用与滥用、保护与窒息等等——都要从模糊性(作为日常生活的特征之一)范畴加以把握(78)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426页。。这么看来,并非日常生活总体性迫使家庭社会学解体,而是家庭的社会学必须以日常生活的总体性为前提展开。正因为如此,列斐伏尔强调马克思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社会学(79)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第15页。。在梅洛-庞蒂那里,以主体经验为基础的总体性框架并不妨碍客观层面的社会事实研究,而是更加强调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性,这恰恰是批判性、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前提。在戈德曼和普兰查斯那里,总体性的前提更是直接服务于具体领域的社会学研究,这才有了戈德曼在文本研究中“理解”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和普兰查斯在社会阶级研究中的多元结构决定论和社会实践总体方法。因此,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是去除社会学学科边界的“新学说”,而是以社会现实的总体性为假设前提(这彰显了社会现实的模糊性、辩证性与主体经验性等),对具体社会领域问题的经验性研究和批判性分析。
其次,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研究进一步彰显了总体与差异、总体与个体、总体与过程的辩证统一性。人们常常将“总体”与整体、统一、结构等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体性”似乎更多地体现了统一性而去除了差异性、保留了集体性而排除了个体性、彰显了结构性而忽略了过程性。然而,本文所揭示的总体性研究却非如此,它们都是在差异性、个体性和过程性的基础上强调总体性。差异性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中至关重要。列斐伏尔竭力指出,社会总体性并不像一些学者描述的那样范畴明确、协调统一,相反,这是一个模糊的、偶然的、极为纷繁复杂而充满可能性的生活世界。因此,总体性不是普遍性,它不是从本体论提出来的,而是在战略上,或者说在分析意义上提出来的(80)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98页。。个体性范畴对于梅洛-庞蒂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在梅洛-庞蒂看来,把握社会总体性的起点只能是“我”的处境,是主体经验构成的生成性空间,当“我”的处境被他人澄明,被作为他人处境的变体而被他人把握时,“我”的生活也便与他人乃至人类经验整体连接起来。在这样一种“我”与“他人”的共在之中,在客观性与体验性交互构成的总体性经验之中,社会的总体性才能得到认识。过程性或者说生成性则是四位社会理论家都谈到的范畴。列斐伏尔反复强调日常生活充满了“转换过程和历史过程中珍贵的和暂时的结果”(81)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79页。;梅洛-庞蒂的社会事实总是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中不断生产;戈德曼直面作为总体性的“意义结构”之生成过程,将其看作人们对境遇的反映,在行动与平衡中持续性生成;对于普兰查斯来说,社会阶级归根到底具有其内在的生成性,这就是他强调阶级只有在阶级斗争中生成的原因(82)Nicos Poulantzas,Class in Contemporary Capticalism,p.27.。总之,“总体性”从来不是静止的、僵化的、教条的,它本身也具备无限的开放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总体性的结构性探索。但我们必须清楚,结构与情境始终是辩证统一的,结构也是情境的,它蕴含着一种不稳定性和暂时的成果;情境也是结构的,它构成了人们相遇和彼此作用的持续性机制(83)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78页。。因此,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根本上讲是辩证的社会学,只有在辩证关系中把握社会现实,才能真正理解总体性的内在深意。
最后,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范畴提示我们必须形成对于“社会现实”的全新理解。关注社会现实、研究社会现实是社会学最基础的研究任务,但究竟什么是“现实”,这常被看作一个卑之无甚高论的问题。然而正如科西克所言,把握“现实是什么”是研究具体总体性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84)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第24页。。从本文考察的情况看,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们的确修正了我们对于现实的传统观点,将可能性、主体性、意义结构性与实践性注入“总体性现实”之中,为我们理解社会现实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列斐伏尔试图在真实、虚假和可能的三元辩证法中把握“现实”。在他看来,通常显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被实证主义者观察到的“现实”不过是现实很小的一部分,作为可能性的“现实”不止有一种,而是充满了无限可能。后来列斐伏尔提出的契机理论、差异空间、城市权利等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作为可能性的现实”中发展出来的。梅洛-庞蒂将主体性纳入“现实”之中,他要求我们善于直面作为“前知识”领域的主体性经验,借助主体知觉与身体体验,凭借与整体历史连接起来的主体间性来把握这种“前知识”,从而以把握“己身”的方式理解世界。戈德曼的“现实”乃是一种作为意义结构的现实,他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个别的文本中的意义内容,而是概念、言语与意向层面的连贯一致的世界观,是作为“集体主体”共同持有的精神结构。这就是说,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本现实”并不是由个人造就,而是特定时期某一社会群体的行为后果。普兰查斯强调了社会现实的“实践性”,也就是说,不能单纯从社会关系中探索结构性现实,必须同时考察实践性与结构性,特别是要充分考虑社会劳动分工场域中的种种生产性竞合实践。总之,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固守于现实的客观性与功能性,而是批判性地探索社会现实的多种可能性、主体介入性与社会构成性。
尽管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总体性”的探索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少未尽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是要解决“总体性”范畴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实操性问题。前面已经谈到,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家们不仅化解了“总体性”与“学科性”的内在张力,而且从多个角度对“社会总体性”的范畴做出揭示。这些研究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的总体性,但这些范畴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也使得我们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变得异常困难。例如,总体性蕴含着结构,同时也具有开放性和可能性,那么当我们面对社会阶层/阶级问题研究时,在何种情况下以特定结构性逻辑为前提,在何种情况下以开放性和可能性范畴为前提,这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正因为如此,我们较少看到以总体性为框架开展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戈德曼的理论由于展现出强烈的皮亚杰式的结构主义,侧重总体性的一端,因而可以形成实操性较强的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只是建构于文本与社会高度同构性上的“理解—解释”方法仍然面临着有效性检验。另外,科西克的“螺旋运动前进”方法考虑到了总体性的结构性与开放性,它主张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从总体到矛盾再从矛盾到总体的具体化过程,在具体总体的逻辑下不断指引实践,也不断完善总体(85)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第30页。。从其实践来看,这一方法与扎根理论方法有更多契合空间。
其次是如何处理现代性条件下“总体性”范畴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列斐伏尔非常重视总体性范畴,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但似乎更多地将“总体性”作为一种愿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种可以实现、可以探索的东西。比如,他认为我们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是一个“打碎了的总体性”(86)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第16页。。他还谈到,现代性实际上起源于总体性革命理想的失败,当下的现代性不过是对总体性革命的拙劣模仿和替代(87)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第238、241页。。因此,“总体性”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批判性武器,但这个“总体性”需要伴随着新的总体性革命才能再次复兴,同时,我们还不得不面临各式各样虚假的总体性(那些被现代性形塑出来的所谓“总体性”)的欺骗。如果此言不假,那我们就不得不正视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理论家对于总体性的拒斥了。比如,福柯强烈反对那种聚焦于线性的、连续的、长时段的“全面历史”,强调历史的断裂性并试图“重构和考察作为认识、理论、制度与实践的深层的可能性条件的知识”(88)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译者引言”,第2页。。可以看出,福柯实际上是在拒绝虚假的“总体性”基础上探寻去总体化的、断裂的“知识考古学”方法的。因此,如果我们直面的现代性不能让我们顺利寻找到真实的“总体性”范畴,甚至不得不将“总体性”作为愿景,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是否还需要执着于“总体性”范畴呢?这便是总体性本身的合法性危机。
最后是如何构筑不同理论范式下的“总体性”脉络的“元总体性”问题。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研究是比较丰富的,欧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诸如科西克、詹姆逊等也提出了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总体性范畴。但我们也会发现,这些“总体性”理论彼此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彼此之间的理论整合还不够充分。即便是从本研究考察的四位理论家来看,列斐伏尔虽然和梅洛-庞蒂多有笔头上的论战与交流,戈德曼和普兰查斯大体上都属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范畴,但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学者围绕“总体性”范畴开展的讨论与形成的共识,在他们的理论中也更多地呈现出多样性。这样,我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探索基于若干“总体性”理论的“元总体性”理论,从而构建起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理论发展的、更加系统的总体性范畴。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离不开发掘和总结不同国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的学术观点(89)刘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丁费之辩”谈起》,《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3期。。考察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所包含的理论知识,厘清其中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地方,最终目的是接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于上述讨论,进一步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总体性“元假设”,不断厘清总体性与学科性、总体性与差异性、总体性与个体性、总体性与过程性等关键问题,破解总体性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与实操性难题,必将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有所助益。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解读
——解读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