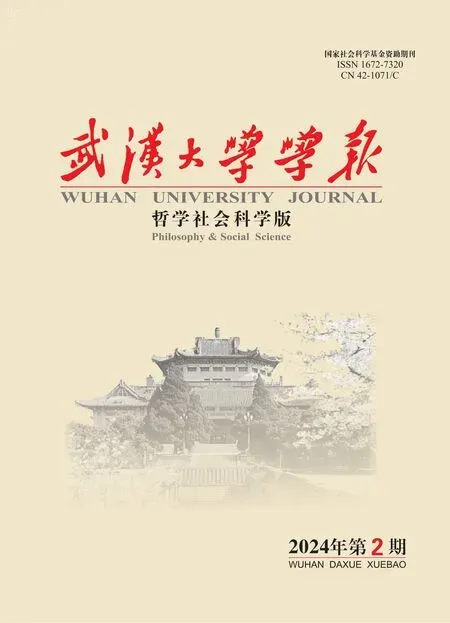奥西里斯的远征:跨文化神话与托勒密埃及的认同政治
徐晓旭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iotes)是公元前1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他写了一部长达40 卷之多的世界通史巨著《历史丛书》(Bibliotheke historike),现存15 卷。第一卷的内容是埃及史,其中的1.17-20部分①本文所引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文献出处均按古典学和古代史学界惯例标注国际通用的卷、章、段、行等标号。如引用狄奥多罗斯文本内容的夹注1.13.5是指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的第1卷第13章第5节;引用希罗多德(Herodotos)文本内容的句末括号中夹注为2. 42, 144, 156,指的是希罗多德《历史》的第2卷第42章、第144章、第156章。对于仅有一部著作的古典作家,国际惯例通常不必写明其著作书名,这些书名通常也都是后人所加,当时本无。为节约篇幅,对于凡正文中已出现作者名字或著作书名或标题者,夹注中不再重复出现此类信息。讲述了一个关于埃及国王奥西里斯(Osiris)率军“远征”全世界,在世界各地传播文明的神话。在这则篇幅很长的神话中,人物有埃及的,也有希腊的,故事发生地点涉及欧亚非三大洲多地,情节主要是他们在各地传授各种具体的文明技艺。
对这样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神话该做如何解读?它的创造者是谁?是希腊人,还是埃及人?创造动机是什么?生成的情境和过程又是怎样?对于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以往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当中的某些方面,但至今依然有待一项专门来全面整体解释该神话的研究问世。我们在这里即尝试做这项研究。我们的基本认识是,这样一个跨文化神话构成了托勒密埃及认同政治的一项内容。
一、奥西里斯远征神话概览
奥西里斯远征神话的内容大体是说,埃及国王奥西里斯有着访问整个人类世界,教授人类种植葡萄,播种小麦和大麦,“制止野蛮,促使人类采取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志向。他在安排好埃及事务之后,便率领大军远征。随他一起出征的有他的兄弟阿波罗、他的两个儿子阿努比斯(Anoubis)和马其顿(Makedon)、潘(Pan)、擅长种植葡萄的马隆(Maron)、擅长种植谷物的特里普托莱摩斯(Triptolemos)等人。奥西里斯到达了包括从埃塞俄比亚边境到印度,再到欧洲的色雷斯、马其顿和阿提卡等地的整个“人类世界”(oikoumene)。奥西里斯并不好战。他们一行在所到之处,不仅习惯于不动干戈,而且还传授各种文明技艺,从而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例如,他在印度建造城市,印度的尼萨(Nysa)就是其中一座。他还把常春藤引种到尼萨。在色雷斯,他杀了抵抗他的“蛮族人的国王”吕库尔戈斯(Lykourgos),并任命马隆留在那里主管农业和建造城市,该城因马隆的名字而被命名为“马罗内亚”(Maroneia)。奥西里斯还把他的儿子马其顿留下担任马其顿国王,马其顿的国名Makedonia即来自其人名。特里普托莱摩斯则被委任管理阿提卡的农业。在不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他便传授大麦酿酒的技术。
这个神话看上去混合了埃及和希腊两种神话传统的因素。就神话人物的名字而言,奥西里斯和阿努比斯是埃及神灵,其他人物则是希腊神灵或英雄。希腊人有将自己的某个神等同于某个外族神的习惯。希罗多德(Herodotos)说“奥西里斯是狄奥尼索斯”“阿波罗是荷鲁斯(Horus)”(2.42, 144, 156)。狄奥多罗斯和他一样,只不过希罗多德用的是“是”这个动词,而狄奥多罗斯使用了“译为”这样的字眼:“奥西里斯译为狄奥尼索斯”(1.13.5), “荷鲁斯译为阿波罗”(1.25.7)。
J. 古万·格里菲斯认为,到狄奥多罗斯的时代,用希腊观念过度解读埃及宗教的偏好变得十分流行。早自希罗多德,就明显开始有将两种宗教等同,甚至将一种宗教的现象溯源至另一种宗教的持续愿望,而托勒密王朝建立并传播的希腊—埃及宗教崇拜又极大地加强了宗教合流趋势。在格里菲斯看来,从希腊古典文献的记载中,是可以获知有关埃及宗教的信息的。对于狄奥多罗斯所记录的奥西里斯神话,他像20世纪40年代其他学者一样,将研究集中于争论奥西里斯是一个植物神还是一个凡人国王之上[1](P83-84)。
我们则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即将神话作为一个叙事整体来对待,观察它是怎样讲述埃及和怎样讲述希腊的。从整个叙事框架来看,奥西里斯远征(尤其是远达印度)和传播常春藤、葡萄、谷物种植等农艺发明这样的主要情节都更多地属于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神话传统,而非埃及的神话传统,当然埃及啤酒的发明权被归于这位假以奥西里斯之名的狄奥尼索斯。
二、关于神话史源的讨论
在现代学术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曾长期被视为一位惯于机械抄袭史料的拙劣史家,较近的研究者则强调他对史料的运用事实上服从于自己的一整套写作思路和框架安排。无论如何,其第一卷的史源研究(Quellenforschung)始终都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在谈到埃及祭司说他们记载中的底比斯城里的王陵有47座而到托勒密一世时代仅15座后,狄奥多罗斯接着说不仅埃及祭司拥有历史记载,而且托勒密一世时代很多到过埃及底比斯的希腊人都著有埃及史,海卡泰奥斯(Hekataios)就是其一(1.46.8)。《阿里斯泰亚斯致菲洛克拉泰斯书》(Aristeas Philokratei31)、约瑟福斯(Josephus,Kat'Apionos1.183)、普鲁塔克(Ploutarkhos,Peri Isidos kai Osiridos9.p.354D;Symposiakon problematon biblia hex4.3.1.p.666E)、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Clemens,Stromateis2.21.130)、埃利安(Aelianus,Peri zoion idiotetos11.1)、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 9.69)、优西比优斯(Eusebios,Euengelike proparaskeue8.3.4, 9.4.1)、《苏达词典》(Soudaepsilon 359)均记载了一位“阿布戴拉(Abdera)的海卡泰奥斯”,(伪)斯居姆诺斯(Ps.-Skymnos, 869)和斯特拉波(Strabon, 14.1.30)则提到了“泰奥斯(Teos)的海卡泰奥斯”。学者间关于这被冠以两个籍贯的海卡泰奥斯之名是否指同一人有不同意见[2](P2750-2769)。其中,爱德华·施瓦尔茨的意见似乎更为可取。他主张两者实为一人,并认为 “阿布戴拉的海卡泰奥斯”只是一种习惯称谓,从最早的史料来看(即Ps.-Skymnos, 869; Strabon, 14.1.30),他的实际籍贯应为泰奥斯,最先是犹太作家约瑟福斯把他说成是阿布戴拉人,而后人们沿用此称。阿布戴拉是泰奥斯的殖民地。施瓦尔茨就此指出,混淆殖民地和母邦人群名称的情况不少,而在海卡泰奥斯身上还有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他通过由德谟克利特到阿那克萨阿尔科斯,再到皮浪,最后到他的师承关系,可以被与德谟克利特联系起来。后者正是阿布戴拉人[3](P223-262)。从狄奥多罗斯的记载(1.31.7, 46.7, 84.8)来看,这位海卡泰奥斯的《埃及史》(Aigyptiaka)的成书年代似乎落在托勒密一世在位时期[2](P2750-2769)。由此可见,他应是亚历山大和托勒密一世的同时代人。
长期以来,海卡泰奥斯的《埃及史》通常被认为是狄奥多罗斯第1卷的唯一或主干史料,学者们也在不停地讨论狄奥多罗斯同时又在哪些地方少量穿插使用了其他一些史料[4](P391)[5](P47)[6](P26-38)[3](P223-262)[2](P2750-2769)[7](P53-56)[8](P75-87)[9](P141-171)。与这种主流认识不同的是,安娜·伯尔顿认为狄奥多罗斯“无疑使用了阿布戴拉的海卡泰奥斯的某些东西,同时又将来自其他多位不同作者的史料纳入他自己构建的框架之中”[10](P34)。查尔斯·E. 曼茨则走得更远。他指出并不存在海卡泰奥斯的著作是狄奥多罗斯所用主要史料的证据,其他古代作家引用的海卡泰奥斯残篇都不支持这种看法,人们无法利用狄奥多罗斯第1卷本身来重构其史料[11](P574-594)。
对于上述神话所在的第1卷第17-20章,学者多认为它来自另一部作者不详的佚书,被插入了以海卡泰奥斯著作为史料的叙事主体当中。伯尔顿部分接受了施瓦尔茨和雅科比的理论[12](P671)[8](P78),即认为第1卷的15.6-8、 17-20.5和27.3-6这些章节来自一种更晚的“狄奥尼索斯传奇”(Dionysosroman),狄奥多罗斯在第3卷(63及以下)和第4卷(2及以下)中再次使用了该书[10](P5, 16-17)。仅就与我们有关的第1卷的17-20.5而言,在伯尔顿看来,其中的20.2提到色雷斯地区的城市马罗内亚能够为确定史料年代提供线索。马罗内亚连同色雷斯沿岸的其他一些地方曾被托勒密三世(公元前247-221年在位)征服,落入埃及统治之下。到公元前200年,它又被马其顿王国夺走。之后该城大多数时候处在马其顿统治之下,但始终都是不同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直至公元前167年被罗马宣布获得自由。伯尔顿据此把狄奥多罗斯这一章史料的年代确定在埃及统治该城的短暂时期或公元前200-167年间。她把来自埃及的马隆在色雷斯建立马罗内亚城的神话看成是当时被记录下来的埃及方面的说法,其理由是埃及那时正在力图重新夺回该城,于是想在埃及和马罗内亚之间构建起一种古老的联系[10](P17,88)。接着,她又指出,马其顿的埃及起源的说法(18.1, 20.3)是为证明托勒密王朝具有埃及起源而提出的,这更可能由阿布戴拉的海卡泰奥斯而非后来的某个作家所为。不过这样对同一段史料就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定年。伯尔顿又认为关于马隆和马其顿的信息不可能来自一个以上的作家,于是她做了这样一个推理:如果关于20.2史料的定年意见正确的话,那么这则史料就不可能来自海卡泰奥斯;相反,如果20.3的史料是海卡泰奥斯的话,就很难想象他为什么会对马罗内亚这座城市感兴趣。她最终的结论落在了施瓦尔茨和雅科比都赞同的一种“看似最合理的假说”上:这则史料是“狄奥尼索斯传奇”的一部分,但它可能包含了海卡泰奥斯著作影响的因素[10](P17-18)。
三、马隆进入奥西里斯的“朋友圈”
这里如果换个角度看,海卡泰奥斯也未必对马罗内亚缺乏兴趣。无论他的故乡在阿布戴拉还是泰奥斯,马罗内亚都应该属于他从小就熟知的地方(幼年获得的地方性知识通常会成为一种终生珍视的认知成果),阿布戴拉和马罗内亚是近邻,两者都是色雷斯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而泰奥斯又是阿布戴拉的母邦。自公元前544年,忒奥斯人将阿布戴拉重建为其殖民地以来(之前克拉佐美奈人在阿布戴拉的殖民并不成功),殖民地和母邦之间在宗教、货币,乃至政治制度和运作方面一直到罗马时代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发现于泰奥斯的一则公元前480-450年的公共诅咒铭文(SEG31, 985)同时适用于泰奥斯人和阿布戴拉人。在泰奥斯还发现有两则阿布戴拉的法令铭文。这类情况表明两城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城邦的两个部分。两城古典时代的货币上都出现有狄奥尼索斯的肖像。狄奥尼索斯也许还是阿布戴拉的城邦保护神。阿波罗的崇拜在该城也很重要,公元前4世纪的钱币上常见其形象[13](P872-875, 1101-1102)。而近邻马罗内亚更是以出产优良的葡萄酒而闻名。狄奥尼索斯很可能是其城邦保护神,他的画像出现在该城的钱币上,圣所狄奥尼西翁(Dionysion)是公布官方文件的地方。虽然马隆为其名祖的神话在现存古典文献中仅见于狄奥多罗斯的著作(1.20.2),但马隆在该城早就和狄奥尼索斯一起受到崇拜,在约公元前500年的钱币上就出现有马隆名字的铭文ΜΑΡΩΝΟΣ(属格)[13](P879-880)。
马隆也很早就出现在了传统文献当中。荷马在《奥德赛》(Homeros,Odysseia9.196-205)中讲到了埃万泰斯(Euanthes)之子马隆是阿波罗的祭司,他护卫着伊兹马罗斯(Ismaros)城,他赠送给了奥德修斯很多黄金、一只银兑酒缸和大量的葡萄酒。伊兹马罗斯是色雷斯的基科奈斯人(Kikones)的城市(Odysseia9.39-40),位于马罗内亚与斯特律蒙(Strymon)河之间。(伪)赫西奥德在《女英雄谱》(ps.-Hesiodos,Gynaikon katalogosMW fr. 238)中说马隆是奥伊诺庇翁(Oinopion)之子、狄奥尼索斯之孙。欧里庇得斯(Euripides,Kyklops141)则说马隆是狄奥尼索斯的儿子。这些更早的文献讲到了马隆与阿波罗、色雷斯、葡萄酒和狄奥尼索斯的关联,足见他作为狄奥尼索斯圈子里的一员的“知识”早就扎根于古代希腊的神话乃至宗教传统当中了。既然马罗内亚盛产葡萄,狄奥尼索斯崇拜又在该城早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将马隆与马罗内亚联系起来的努力应该也不会很晚:马隆身为马罗内亚名祖的神话十分可能属于同一批更早的神话传统。而后来一旦狄奥尼索斯被与奥西里斯等同后,马隆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奥西里斯的圈子里。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狄奥尼索斯传奇”在狄奥多罗斯著作的第3卷和第4卷再次出现时主人公的名字都是“狄奥尼索斯”,他以“奥西里斯”之名现身显然是为了适应埃及语境。而且,在第1、3、4卷中他对全世界的征程中被直接或间接提到的几个著名到达地都是印度、色雷斯和希腊。4.3.2还提到希腊人和色雷斯人为纪念他远征印度设立了对他的祭献。在希腊人的宗教观念和神话中,作为酒神的狄奥尼索斯是与色雷斯有关联的一个神,而马罗内亚又是位于色雷斯地区的一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地和酒神崇拜地,其早就被虚构出来的名祖马隆作为狄奥尼索斯/奥西里斯的随员出现在神话中也许就是一种故事情节自然而然的逻辑拓展,他不一定非要等到托勒密埃及夺取和失去马罗内亚时才进入这一传奇。
这样一来,上述20.2和20.3之间被指称的年代不协调也就不复存在了,它们很可能来自一种统一安排的狄奥尼索斯远征神话叙事。但20.2是否也像20.3一样是受海卡泰奥斯著作影响的因素?如果接受了查尔斯·E. 曼茨的意见,那么这个问题似乎无解。
四、在奥西里斯远征和亚历山大远征之间:政治认同与认同政治
然而,如果不是把注意力放在马隆一个人物身上,而是转向观察狄奥尼索斯/奥西里斯远征故事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对这一神话文本生成的另外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其叙事更适合托勒密一世时期,尤其是公元前301年伊普索斯战役之后的政治和社会情境①保尔·高科夫斯基(Paul Goukowsky)把亚历山大及其与狄奥尼索斯相联系的神话的形成放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尤其是公元前271-270 年[12](P79-83)。然而,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那样,更早的托勒密一世时期的若干证据表明该神话更应该产生于这一时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其部将即所谓的“继承者”随后展开争夺帝国的战争。从公元前306年起,安提柯、戴麦特里奥斯、托勒密、塞琉古、吕西马科斯和卡珊德罗斯纷纷称王。公元前301年伊普索斯战役后,形成几个并存的王朝,托勒密在埃及,塞琉古在亚洲,吕西马科斯在色雷斯,只有本土马其顿的统治权频繁易手。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82年吕西马科斯在科鲁派狄翁战役中战死。在长期的争夺过程中,继承者们除了诉诸战争外,也忘不了动用各种宣传手段。强调与亚历山大的联系是他们常用的宣传手段。斯特拉波(17.1.8)、狄奥多罗斯(18.26-28)、保萨尼亚斯(Pausanias,1.6.3)、阿里安(Arrhianos,FGrH156 frr. 9.25,10.1)这几位古典作家都记载道,早在公元前322年底,托勒密就劫持了运送途中的亚历山大的灵柩,将之安葬于埃及。据斯特拉波(17.1.8)和阿里安(FGrH156 fr. 10.1),他劫持的目的是想占据优势和夺取埃及的统治权。保萨尼亚斯(1.6.2)和库尔提优斯·鲁福斯(Curtius Rufus, 9.8.22)都讲到,马其顿人当中流传着名义上是拉戈斯(Lagos)之子的托勒密一世实则腓力二世的私生子以及他曾救过亚历山大之命的传说。这种关于与亚历山大同父手足情的传说很可能也是托勒密一世本人编造并推广的。
对亚历山大的官方崇拜在托勒密一世在位时期(也许早在公元前290年,肯定在公元前285年之前)也已建立起来[14](P213)。虽然托勒密始终无意成为整个亚历山大帝国的继承人而只专注于固守埃及这个基地,但此举无疑为自己抢到了一种观念上的正统。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打造上亚历山大的形象也是对自己作为亚历山大“继承人”身份的合法性的宣讲。伊普索斯战役胜利后,吕西马科斯在自己的钱币上打上了带有宙斯—阿蒙公羊角的亚历山大头像。塞琉古一世发行了带有狄奥尼索斯特征的男性头像钱币,该头像不应该是他自己的,而很可能是亚历山大的。托勒密的钱币上则带有戴着象头的亚历山大头像和亚历山大驾驶象车的画面。这些都提醒人们亚历山大是印度的征服者,而自己曾跟随亚历山大成功地征服了印度。亚历山大的形象被塑造成带有宙斯—阿蒙、狄奥尼索斯、阿波罗、潘神等多种神灵的特征[15](P162-164)[16](P79)。
除了利用神化亚历山大进行宣传外,虚构自己的神灵后代的身份也是王朝统治者确立自己王权合法性的手段。塞琉古王室将阿波罗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自认为是阿波罗的后裔。这种神话无疑始于塞琉古一世。神话把他大腿上的锚形胎记描述成他身为阿波罗亲生儿子的证据,而且塞琉古的子孙也都宣称大腿上有同样的胎记①优斯提努斯(Iustinus, 15.4.3-9)为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已佚通史著作所作的摘要中保存了这一神话,并记载了它在政治上的各种利用情况。该神话的主要情节是塞琉古之母拉奥狄凯嫁给其父安条克后,在梦中与阿波罗交合并怀孕,阿波罗赠其戒指并嘱其将之交给儿子,戒指的宝石上雕有一个锚的图案,塞琉古出生后大腿上便带有一锚形胎记。。公元前281年伊利翁城所立纪念塞琉古的一篇铭文(OGIS212.14-15)里就提到“阿波罗,其家族的始祖”这样的说法。而该城于公元前279-274年间纪念其子安条克一世的一篇铭文(OGIS219.27-28)对阿波罗再次使用了完全相同的称谓。塞琉古还早在公元前312 年就在达芙奈建立了阿波罗神庙,并到狄狄马的阿波罗神庙祈问神谕(Diodoros Sikeliotes, 19.90.4)。
狄奥尼索斯则成为托勒密王朝的祖先。托勒密三世宣称其父系祖先是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母系祖先是宙斯之子狄奥尼索斯(OGIS54.4-5)。托勒密四世又提供了一份更详细的祖先谱系,里面狄奥尼索斯的后代有多人,其中包括马隆(Satyros,FHGIII fr. 21 p. 165)。托勒密四世还专门颁布了一项规范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法令。里面规定从事崇拜活动前登记时要证明自己祖上三代都已崇拜狄奥尼索斯(B. G. U., 1211)。这暗示了狄奥尼索斯崇拜在他之前的三代国王时期均获得了官方的重要性。托勒密二世曾在亚历山大里亚举办过盛大的狄奥尼索斯崇拜游行(Kallixeinos Rhodios,FGrH627 fr. 2)。托勒密一世时期的一尊狄奥尼索斯青铜胸像带有他本人的特征,因此对狄奥尼索斯的特殊崇奉很可能在托勒密一世那里就已经开始了[14](P211)。塞拉皮斯(Sarapis)崇拜的真正创立者应该也是托勒密一世。这位新神是奥西里斯和公牛阿皮斯(Apis)的合而为一,在吸收了埃及因素的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强的希腊特征[17](P186-188)[14](P121)。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5.1-2)在记述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尼萨时,也讲到了尼萨城是以前狄奥尼索斯前来建立的(5.1.1-2),并且说亚历山大愿意相信狄奥尼索斯远游的神话,坚信尼萨就是狄奥尼索斯建立的,而他自己已经到达了狄奥尼索斯到达的地方,甚至比狄奥尼索斯走得更远,认为马其顿人不会不愿与他一道努力效法和赶超狄奥尼索斯的功业(5.2.1)。稍后,这部分还记载了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在尼萨那里的麦罗斯(Meros)山上发现了葡萄、常春藤和月桂,描述了他们见到常春藤这种狄奥尼索斯圣物之后的狂喜场面,原因是印度其他地方都没有常春藤,甚至没有葡萄:他们用常春藤编织花冠戴在头上,并向狄奥尼索斯高唱颂歌,呼唤其各种名号;亚历山大向狄奥尼索斯献祭并与部下欢宴(5.2.5-6)。阿里安在其著作开篇就说明,他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罗斯两人的著作,他对史料作这样选择的理由在于两者都曾参加了亚历山大的远征,其史料更可信。据塔恩分析,上引记载的史料很可能最初来自阿里斯托布罗斯,但经克雷塔尔科斯的著作转手而最终进入阿里安书中②塔恩在这里还提出,阿里安这一部分记载中5.1.3-6和5.2.2-4两处为编造,但不知出自谁人之手;5.2.7关于身份显贵的马其顿人为酒神附体而尖叫(即所谓的komos,“酒神狂欢”)的描述也采自克雷阿尔科斯之作,该故事也并非为克雷阿尔科斯所创,而是他由某位二流诗人那里借用而来。[18](P45-51)。如果说阿里斯托布罗斯了解亚历山大需要利用狄奥尼索斯建立尼萨这一神话用于鼓舞士气的军事目的的话,托勒密也不难发现这一神话在事后的政治用途。作为亚历山大贴身卫队成员亲身参加印度战争的他(5.13.1, 23.7, 24.3),不仅与阿里斯托布罗斯一道是历史的共同见证者,更会对这段神话创造历史的往事记忆犹新并加以更新的利用。
比较之下,我们会发现狄奥多罗斯记载的奥西里斯远征神话与亚历山大利用的狄奥尼索斯远征神话,乃至亚历山大本人的远征颇为相似。奥西里斯远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也是印度的尼萨,他传授的也是葡萄种植及酿酒等技艺。亚历山大和狄奥尼索斯征服的都是“整个人类世界”,奥西里斯的征服地也是如此。奥西里斯是穿过阿拉伯沿“红海”(非今红海,而是波斯湾和印度洋)前往印度的(Diodoros Sikeliotes, 1.19.6),其中的海路恰恰是亚历山大所派遣的海军由印度返回至幼发拉底河口所走的路线,而阿拉伯也正是亚历山大本人返回到巴比伦后计划由波斯湾取道海路征服的地方(Arrhianos,Alexandrou anabasis7.1.2, 7.19.5-20; Strabon, 16.1.11; Ploutarkhos,Alexandros68.1)①阿里安(Alexandrou anabasis 2.20.4-5; 3.1.2)和库尔提优斯·鲁福斯(4.2.24-4.3.1, 4.3.7)都记载了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2年进攻腓尼基城市期间,就曾对邻近的阿拉伯边缘地区有过军事行动。。这样看来,亚历山大仿佛试图再度完成一次与奥西里斯的阿拉伯—印度远征线路大体重合而方向相反的印度—阿拉伯征程。
奥西里斯远征神话着力强调的几个关键地点还反映了伊普索斯战役之后希腊化世界分成的几个政治单元:埃及、亚洲、色雷斯、马其顿、希腊。提及埃塞俄比亚(Diodoros Sikeliotes, 1.18.3, 1.19.5)显然是为强调埃及最南的边界。亚洲其实并未明确提到,但印度作为“人类世界的极限”已经暗指了整个亚洲,虽然塞琉古丢掉了印度。色雷斯被提到,显然是由于它构成吕西马科斯王国的主体。而马罗内亚这座城市被特别提到,显然是由于其地名与狄奥尼索斯圈子里的马隆这个神话人物名字之间的联系。雅典作为古典希腊最著名的城市完全有理由可以代指希腊。马其顿和希腊的统治者虽然频繁更换,但并不妨碍它们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地理单元。同时,神话人物也差不多同这几个地区相联系:阿努比斯和奥西里斯一样,代表埃及;马隆与色雷斯,特里普托莱摩斯与希腊,马其顿与马其顿相关联;阿波罗应暗示着塞琉古王国。在这些人物和地区当中,埃及和奥西里斯的地位尤其重要,这与亚历山大遗体的埋葬地的重要性相吻合。按照希腊化时代王权继承的惯例,埋葬死去的国王就意味着获得继承人的身份,而奥西里斯在埃及的宗教观念中也恰恰是死去的国王的化身。事实上,释放出自己是腓力二世私生子这一说法的目的应该也是为了与亚历山大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五、奥西里斯之子马其顿:新名祖神话中的认同政治
除了希腊神话的一面,奥西里斯及其两个儿子的叙事带有很强的埃及特征,也具有某种王位继承凭证神话的性质。伯尔顿在她对狄奥多罗斯第一卷的注释中调查了奥西里斯两个儿子的埃及背景。她指出,根据金字塔铭文,阿努比斯是拉神的第四个儿子。他被吸收进奥西里斯神话系统,被讲述成奥西里斯和奈普提丝的儿子,后又被伊西丝收养并成为其护卫。随后他伴随奥西里斯征服世界。其形象是豺狼。这与狄奥多罗斯书中(1.18.1)将他描述为戴着狗皮头盔随奥西里斯出征的情节相似。
在同一句话的下半句中,马其顿则被描述为戴着狼头。伯尔顿认为马其顿应该被等同于维普瓦维特(Wepwawet),即埃及所谓的“狼”神。“狼”神与阿努比斯联系在一起,都是奥西里斯的伴侣和护卫者。有一篇咒语把维普瓦维特也说成是奥西里斯的儿子:“我是维普瓦维特,森维(Senwy)的后裔,奥西里斯之子。”[19](P194)[10](P83)国王被认为与维普瓦维特密切相关。这特别体现在塞德(Sed)节上。节日仪式有一部分叫做“献土”:国王要迅速跨过一块献给诸神的土地,这样象征性地宣布他对埃及土地的统治权。贯穿整个“献土”仪式,国王都要有维普瓦维特神的旗帜伴随[10](P83)。
赋予马其顿以奥西里斯之子和王权之神的身份,这种对埃及神话的修改是为面向埃及人,尤其是想通过懂得希腊语言和文化的埃及精英阶层,向习惯于本土法老神权政治的埃及民众传输一种身为马其顿人的国王们本源其实仍在本土的观念,使之在对马其顿人统治的接受上不会产生抵触,而是心安理得,甚至觉得理所应当。
当然,这样做同时也颠覆了以往根深蒂固的马其顿名祖神话的希腊传统。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伪)赫西奥德的史诗《女英雄谱》(MW fr. 7)讲到马其顿是丢卡利翁之女推娅和宙斯的儿子。同一部史诗(MW frr. 2, 3, 4)又说到希腊人的名祖希伦是丢卡利翁之子。这样,马其顿就成了希伦的外甥。海拉尼科斯(Hellenikos,FGr.H1 fr. 74)等人则说马其顿是爱奥利斯人的名祖爱奥洛斯之子。如此一来,马其顿就成了希伦家族的直系后代,因为按照《女英雄谱》(MW fr. 9)的说法,爱奥洛斯是希伦的儿子之一,而两者的父子关系又是一个具有泛希腊影响的谱系,这也意味着马其顿人被想象成了希腊人的几大支系之一,爱奥利斯人当中的一个小支系。拜占庭时期的塞萨洛尼基的优斯塔提奥斯为狄奥尼修斯的《世界地理志》所作的注疏(Eustathios Thessalonikes,Parekbolai eis ten Dionysiou Periegesin427)里也记录了这一谱系。他在同一处注疏和为《伊利亚特》所作的注疏(Parekbolai eis ten Homerou Iliada3.623)中还记载了另一个谱系说马其顿是宙斯之子。(伪)阿波罗多罗斯的神话著作(Ps.-Apollodoros,Bibliotheke3.8.1)中保存的一个谱系中,马奇德诺斯是阿卡狄亚人的国王吕卡翁之子,吕卡翁是皮拉斯戈斯(Pelasgos)之子。马奇德诺斯之名Makednos与马其顿之名Makedon是同一族称和同一名祖名字的不同变体,因此这一谱系相当于把马其顿的名祖置于阿卡狄亚人的祖先神话体系当中,而阿卡狄亚人尽管毫无疑议地属于希腊人的一个支系,但其包括名祖在内的神话祖先谱系独立于希腊人的名祖希伦的家族谱系之外。埃利安(Aelianus,Peri zoon idiotetos10.48)也记载了马其顿为吕卡翁之子的谱系,但该谱系把吕卡翁说成是埃马提亚国王。埃马提亚之名Emathia 是马其顿的一个地区和一座城市的地名,斯特拉波(7.fr.11)还说它是整个马其顿以前的地名。(伪)斯居姆诺斯采用诗体讲述世界地理的著作(Pseudo-Skymnos,Periegesis618-620)中保留的一个神话则说在马其顿为王的马其顿是“地生人”(gegene),这显然是一个土著名祖谱系。不难看出,在以上所有关于马其顿人名祖的谱系讲述中,这位名祖马其顿虽然被赋予了不同的谱系关系,其亲缘却均未超出希腊和马其顿的地理范围,亲属皆为希腊的英雄或神,叙事程式也都在希腊文学范畴之内。
相比之下,现在与埃及神灵嫁接成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的新谱系,的确颇为异常,难怪达斯卡拉基斯称之为“一种奇怪的传统”。他认为,它一定是在托勒密王朝希望把他们和亚历山大的起源地与他们统治的国家联系起来的时候,由亚历山大里亚的作家创造的。他还指出亚历山大被宣称为法老和阿蒙之子[20](P12, 52)。他的这一点看法,与我们上面关于远征叙事的分析也不谋而合。亚历山大似乎是托勒密王室永远不会忘记佩戴的一枚像章。在修谱一事上,如何做到对标亚历山大?方法就是把埃及的神灵打造成马其顿人的祖先。
毋庸置疑,奥西里斯远征全世界的神话,是利用已有的希腊神话和埃及神话的多种元素编纂而成的,编纂者希望传递的信息当中自然也包括它所呈现的播化文明的叙事外观。并且,能够如此编纂,也是希腊与埃及神话、宗教乃至文化长期接触和互动所积淀的自然后果。不过,经过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神话还具有其叙事外观之外的多重政治和族群深意,它构成了托勒密王朝认同政治的一项内容。神话预设了两方面的听众,将两套认同政治的修辞编织为一篇播撒文明的神话叙事:对国际上的马其顿竞争者,它旨在强调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正统性;对国内的埃及臣民,它宣讲了马其顿人国王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这则神话应该是在托勒密一世时期由希腊化埃及官方制造的。它之所以能传承到狄奥多罗斯的书中,很可能最初是由海卡泰奥斯或像他一样的在托勒密一世在位期间前往埃及的希腊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它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另类的马其顿名祖谱系,以一种巧妙的曲折方式表述了托勒密埃及官方在这一时期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对自身马其顿族群身份的重新界定,这种族性定义当中自然也灌注了意图明显的政治宣传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