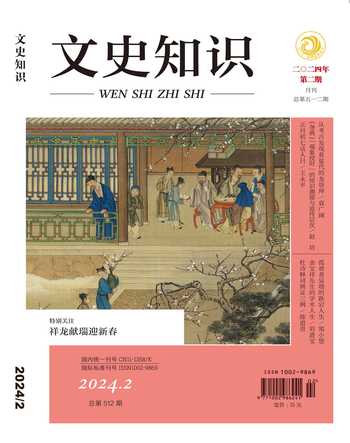文本的迁徙
王心仪

宋元时期,话本与市井“说话”艺术有密切联系,因此有着很强的民间口头文学特征。和作家文学的稳定性不同,民间文学有较强的变异性。美国学者阿尔伯特 ·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如此解释:“每一次表演都是具体的歌,与此同时它又是一般的歌( generic song)(a text)。我们正在听的歌是‘特指的歌( the song)(the text);每一次表演的意义又不限于表演本身;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再创造。”(阿尔伯特 ·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 2004,145页)如果放在宋元小说家话本中,我们同样可以说,小说家的每次表演都会根据当下表演的场域进行调整和发挥,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 the text),也即“异文”。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些异文之间也有很强的相似性,因此现在我们在阅读时经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一点在灵怪类话本小说中有很好的体现。
萧相恺在《宋元小说史》中指出《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定山三怪》三篇小说“大情节基本一致,若干细节也甚接近:三篇中都有一怪与男主人公相通,又都有一怪(或鬼)較为良善,出来救护男主人公”,在入话与正文的韵语中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与‘神仙类中的《福禄寿三星度世》也有某些相类的地方”(萧相恺《宋元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23页)。三篇灵怪小说从名字上即可看出,分别讲的是西湖、洛阳、定山的故事,而神仙类的《福禄寿三星度世》则定位于江州浔阳江。同时,《西湖三塔记》《福禄寿三星度世》又分别有西湖三塔、浔阳江寿星寺这两个古迹留存。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将这些文本放在民间文学文类中去考虑,相比于“故事”,它们更类似于“传说”。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中用“动物”和“植物”来形容故事与传说的区别:“民间故事奔走于四方……传说扎根于某一土地,并不断成长壮大。……可爱的民间故事的小鸟,多数在传说的森林、丛中建巢,同时,把芳香的各类传说的种子和花粉搬运到远方的也正是它们。 ”(〔日〕柳田国男《日本的传说 ·序言》,转引自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 172页)宋元话本的“三怪”类小说中,“三怪”的模式及一些韵文套语,正像“故事的小鸟”,它们在传播中与不同地域文化和地方风物相结合,形成了既地域化又模式化的“三怪”类小说。
一 “三怪”类小说的地域化
宋元话本小说对真实性的注重向来是被充分肯定的,这种真实性往往体现于对地域风貌的展现。程毅中曾评价宋元话本小说“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气息”(程毅中《宋元小说的写实手法与时代特征》,《社会科学战线》 1996年第 6期)。刘勇强在讨论西湖小说的地域性时提道:“真实的场景与虚构的故事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这不只是为了给人一种历史般的真实感……也是为了唤起受众的亲切感和现场感。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 2001年第5期)对于“三怪”类小说而言,表演者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地域化来使奔走四方的故事能扎根于某一土地。这使得它们最终实现了世俗性与神异性的交织与相互渗透。下面笔者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对小说的地域化进行分析。
故事起点上,背景设定与地方习俗或历史结合,这也是神怪故事中世俗色彩的渗入。《洛阳三怪记》以几首探春诗词开头,赞颂春天好景致。接着话头一转,说“到春来,则那府州县道,村乡镇中,都有游玩去处”。于是自然引出洛阳人好在春天到定鼎门外、寿安县路上的“会节园”赏花。接着主人公出场,“时遇清明节,因见一城之人都出去郊外赏花游玩,告父母也去游玩”,才引发了后面一系列故事。《洛阳名园记》《东京梦华录》《癸辛杂识》《梦粱录》等书中都有园林赏春游乐的记载,可见春日去园林赏花确实是北宋洛阳的风俗。将故事发生的背景与当地春游赏花的习俗勾连在一起,增添了观众的代入感。相比之下,《西湖三塔记》主人公同样以春游的行动出场,但开篇的重点放在了对“西湖好处”的称赞上,通过对地域的夸耀增强了听众的情感认同,又因地制宜,将洛阳人看花变成了杭州人游湖,并细致说明主人公游湖路线,“一直出钱塘门,过昭庆寺,往水磨头来,行过断桥四圣观前”,一连串真实的地名进一步强化了听众听故事的现场感。《定山三怪》则以唐玄宗与杨贵妃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作为开篇(特别是里面写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私通的情节,可能是受北宋秦醇的传奇小说《骊山记》的影响),其中蕴含的女色祸国的讽刺也为下面主人公的经历奠定了基调。崔丞相被贬定州中山府是李杨故事到主人公遇怪故事之间的过渡,同时将故事的背景拉近到了定州。以上三篇均在开篇通过内容对地方习俗、历史的勾连从而实现了故事的“在地化”,这种世俗色彩让后面的神怪故事有了现实背景,这种合乎人情事理的情节也与后面出现的离奇甚至血腥的场面形成了张力。
故事发展中,灵怪空间与世俗空间界限模糊。前面提到的在地化,严格来讲是故事发生的背景,真正的灵怪活跃的空间其实与之仍有一定距离。《洛阳三怪记》中潘松“步入一条小路,独行半亩田地”,在“游人希少处”遇见了白鸡精化成的婆婆,随后又被婆婆“引到一条崎岖小径,过一条独木危桥,却到一个去处”。《福禄寿三星度世》中刘本道也是“走来走去,不知路径。走到一座庄院前……”。《定山三怪》崔衙内“独自一个牵着马,行到一处,却不是早起入来的路。星光之下,远远地望见数间草屋”。主人公往往是通过一段较长距离的行走,才由世俗空间进入了灵怪活跃的空间。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分隔,相反,这种中间过渡过程的拉长反而造成了越界感的缺乏,从而模糊了灵怪空间与世俗空间的界限。这种界限的模糊性使得主人公的逃脱往往需要狂奔疾走、长途跋涉,但灵怪通过“驾香车”、飞行、变化,则能时时侵扰主人公,呈现出了灵怪空间对世俗空间进一步侵入的趋势。这些情节都缩短了听众心中故事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也使得世俗性与神异性交织糅合。
故事结尾处,故事的“遗留物”成为当地古迹。这看起来将神异性收束到了世俗性中,但实际也让世俗空间蒙上了神异色彩。《西湖三塔记》结尾奚真人用符压住三个怪物,“造成三个石塔,镇住三怪于湖内”。《福禄寿三星度世》结尾南极寿星在寺庙中引刘本道与鹤鹿龟三物重归天上,而“那一座寺,唤做寿星寺,见在江州浔阳江上”。话本结尾处遗迹的存在使得整个故事显得煞有介事,也让当地的遗迹增添了神秘感。这种说法使得小说形似于解释性的传说,遗迹则类似于传说核心的“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眼前的实物唤起了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又联系着古代信仰。 ”([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26页)当然,话本小说中提及遗迹的目的仅在于增强真实性,而至于是否能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则要取决于民众的接受度。事实证明,《西湖三塔记》通过后世演变形成的《白蛇传》确实成了民间四大传说之一。
由此可见,从开篇将当地的民俗风景融合到故事背景,到发展中模糊灵怪空间与世俗空间的界限,最后以遗迹结尾,话本小说家在故事的头、中、尾都可以对故事进行地域化的讲述,让神异性与世俗性得以互相渗透,同时巧妙把控着神异与世俗的距离,使得故事既有世俗的基础以便听者代入,又能拥有不同于日常的奇异色彩,以满足听者对奇闻轶事的欣赏欲望。
二 “三怪”类小说的模式化
去除“三怪”类小说这些地域色彩,其共性依然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三怪”类小说中基本都有主人公通过窥视从而明白自身处境的情节。上一节说到,灵怪空间与世俗空间界限比较模糊,主人公往往不会在进入灵怪空间(一般是一个庄院)后就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窥视则让主人公直截了当地面对对方的真实面目,窥视所见的画面在给主人公感官与心理冲击的同时也让听众随之产生内心波动。《洛阳三怪记》中王春春引着潘松“蹑足行来,看时,见柱子上缚着一人,婆子把刀劈开了那人胸,取出心肝来”,这才知道“共娘娘做夫妻”的下场。《定山三怪》崔亚听到“将军来了”,于是“去黑处把舌尖舔开纸窗一望时,吓得浑身冷汗,动掸不得”,原来将军就是自己日间一弹子打的骷髅,骷髅还称:“若捉得这厮,将来背剪缚在将军柱上,劈腹取心。左手把起酒来,右手把着他心肝;吃一杯酒,嚼一块心肝,以报冤仇。”《福禄寿三星度世》中刘本道也是听到女娘的哥哥回来了,于是“走入一壁厢黑地里立着看时……叫声苦:‘我这性命须休! ”女娘的哥哥就是自己一棹竿打入江里的人。窥视的动作让叙述进入了人物的限知视角,胡亚敏在《叙事学》中说过,人物限知视角作为一种内聚焦“在阅读中它缩短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获得一种亲切感”(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7页)。主人公、说话艺人、听众的视角在此时达到了统一。主人公偷窥时的紧张以及所见画面给自己带来的惊恐等种种情绪都会通过说话艺人的表演传递给听众,这种共情自然会增强表演对听众的感染力。
除此之外,笔者发现话本小说中还有对这种窥探心理的反用。如《西湖三塔记》中卯奴两次背着奚宣赞逃离,以及婆婆乘飞车将奚宣赞抓回时,都警告奚宣赞要闭目,若开眼则死于非命。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窥视的行动被限制、视觉被剥夺,因此没有了窥探时的那种视觉冲击,但同时增添了一份神秘性。奚宣赞“耳畔只闻风雨之声,用手摸卯奴脖项上有毛衣”,心想:“作怪! ”说话人正是要引着听众一同猜想,利用好奇驱动听众继续听下去。同属于灵怪类的《西山一窟鬼》中也有对窥视的反用,吴教授与李乐娘和锦儿第一次见面,“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儿,张一张,喝声采不知高低,道:‘两个都不是人! ”听到这里听众必然会心中一惊,但后面却说:“如何不是人?元来见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妇人是南海观音,见锦儿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 ”这种故作玄虚是对同类小说中窥探情节的反用,也让笔者联想到了如今脱口秀表演中常用的技巧:“预期违背”。这种违背实际是对惯性的打破,以引起更新奇有趣的感受。由此可见,宋元说话作为民间口头文学,十分注重对一些常用情节的套用,以迎合大众的欣赏趣味、满足听众的心理期待,但有时也会有意反用,从而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而无论正用还是反用,其实都是要以吸引听众作为根本目的。有文章曾评价:“说话人时刻处于失去听众的焦虑之中,他不断采取各种措施与听众形成良好的交流关系,使他们时刻处于继续听下去的心理动机之中,而不至于中途退场……这种艺术形制无不体现了‘说 —听交流过程中的长期的筛选与磨合过程。”(王委艳《交流诗学 —话本小说艺术和审美特性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2012)笔者认为这种以接收者为中心的特点是话本小说与文人文学很重要的差异,也是我们在欣赏和理解话本小说时应当十分注意的问题。
第二是情节的突转。“三怪”类小说需要依靠惊悚情节吸引听众,这种惊悚氛围的营造通过减弱主人公的主动性来实现。小说中主人公的行动被动性较强,往往处于被驱使、被摆布的位置,这从小说结尾主人公都是靠寻道士驱邪收妖才能解脱就可以看出。而这种命不由己的状态让主人公的遭遇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主人公身上順境与逆境的转换可以十分迅速,极大地加快了叙事节奏,营造了紧张的氛围。情节的陡转在文本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辨识鬼怪,另一种是重遇鬼怪。上面提到的主人公窥视就是辨识鬼怪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他人告知,如《洛阳三怪记》潘松认出王春春时就被告知“你可急急走去,这里不是人的去处”;以及直接目睹,如《西湖三塔记》娘娘直接在奚宣赞面前让力士将一个后生剖腹取心。主人公通过这些方式明白自己当下已经身处灵怪空间,由顺境进入逆境,情节也随之发生突转。重遇鬼怪的情节也很多见(这也是前文所说灵怪空间与世俗空间边界模糊化的表现)。如《洛阳三怪记》潘松第一次逃脱,当时潘松才出“虎穴”,又遇上了天应观道士徐守真,徐守真又宽慰潘松:“我行天心正法,专一要捉邪祟。若与吾弟同行,看甚的鬼魅敢来相侵! ”有他同行,潘松应当处于一种较为放松的状态,听众自然也是如此。但这时潘松却见两个白鹩子在瓦上厮啄,结果一捉,就“被人一掀,掀入墙里去。却又是前番撞见婆子的去处”。可见情节转换之迅速。在明知潘松被邪祟相扰的情况下,徐守真不见了潘松,却“只道又有朋友邀去了,自归”,足见徐守真前一番豪言壮语的作用只在于让潘松和听众放松警惕,让情节的突转来得更加措手不及,小说家对叙事节奏缓急的精妙把控可见一斑(《西湖三塔记》中也有奚宣赞第二年清明射老鸦,结果老鸦变婆婆,奚宣赞又被掳走的情节。《福禄寿三星度世》有刘本道在妻子与黄衣女子斗法时,趁乱逃到一间寺庙,却正好遇见自己之前打伤的“球头光纱帽、宽袖绿罗袍、身材不满三尺”的人。仅罗列在此,不在正文详述)。
和对窥探的反用一样,情节的突转同样有反用的情况,也即小说家通过造势,让听众误以为会发生突转,最终却并未按听众的预想发展。例如,同样在《洛阳三怪记》中,潘松在王春春的帮助下第二次逃脱,急急走了一夜,到天明,望见一座庙宇:“灯火灿烂,一簇人闹闹吵吵,潘松移身去看时,只见庙中黄罗帐内,泥金塑就,五彩妆成,中间里坐着赤土大王,上首玉蕊娘娘,下首坐着白圣母,都是夜来见的三个人。惊得小员外手足无措。 ”结合前面的情节,听众肯定为主人公捏一把汗,以为这次还是没能逃出妖怪的手心。结果“问众人时,原来是清明节,当地人春赛,在这庙中烧纸酌献”。小说家有意打破之前情节产生的惯性,从而使故事不显得重复无趣。《福禄寿三星度世》中对突转的反用则更为巧妙:与白衣女娘共同生活后,刘本道偶然在街上见了一个自称“皖公山修行人 ”的道士。小说用了近三百字,写道士自述“炼一炉丹、寻一件物、救一城人 ”的三件好事,又看出刘本道有阴祟缠扰,接着指出刘本道的妻子正是祟物,于是给他一道符,教他如何装睡,并趁妻子不备将符安在她身上使其现形,刘本道也按其所言回去装睡了。这一番铺垫可以说是十分充分,刘本道与听众必然都等待着安符后的结果。结果刘本道妻子却一眼识破,并指责他信了道士言语,放出话说:“你好好把出这符来,和你做夫妻;不把出来时,目前相别。 ”在这种情况下,刘本道也不怀疑妻子如何知晓,竟直接“怀中取出符来付与女娘。安排晚饭吃了”。夫妻间的风波竟然就此轻巧地化解了!不过符咒虽然未能显灵,但对于那位道士,本篇小说内已经用几百字铺陈其能力,加上相似的“三怪”类小说结局往往是道士出马降妖,相信很多读者都和笔者阅读时一样仍对其法术抱有期待。结果,第二日女娘找道士说理斗法,道士却一招就败下了阵来,认错求饶,女娘的算卦生意反而因此做了个风生水起。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预期违背”了。小说家打破了道士降妖的情节惯性,让听众期待的突转落空,但是听众的疑虑并未被打消:女娘是如何知晓道士说与刘本道的法子的?女娘果真只是前任刺史的女儿吗?若真是如此,女娘又如何会有这么高的法术?可见对“预期违背”的巧妙利用能够让故事对听众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好奇必然紧紧抓住听众,让他们继续听下去。
最后一个共同点是小说对灵怪的他者化。《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定山三怪》的结局都是道士将缠着主人公的妖怪收服,《福禄寿三星度世》则是南极寿星将主人公及鹤鹿龟三物引归天上。相比较而言,《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两篇相似度更高,与男主人公相通的女性都显得心狠手辣,“新人换旧人 ”时能毫不留情将旧人剖腹取心。《定山三怪》《福禄寿三星度世》中,与男主人公有过节的往往是三怪中的男性,而与男主人公相通的女性则并没有威胁到男主人公的生命,甚至对他有所帮助,她们唯一的问题好像只在于没有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对方。《定山三怪》中女娘在将军面前帮崔衙内说情,自己也一直未伤过崔衙内,只说“与衙内是五百年姻眷”,甚至显得颇为痴情。最后二人被崔丞相发现,崔丞相还未问清情况,竟然就拿剑向女娘刺去,即使面对这种情况,女娘都没有发怒,仍然只道:“相公休焦!奴与崔郎五百年姻契,合为夫妇。不日同为神仙。”从头至尾一直没有展现出妖怪伤人的一面,但即便如此也和《西湖》《洛阳》中剖腹取心的妖精落得一样的下场。《福禄寿三星度世》中女娘也帮刘本道打掩护,后面又用金银资助他,摆卦铺过生活,刘本道都称:“全仗我妻贤达。 ”后面女娘发现刘本道听道士所言要用符害自己时,抛下的狠话也只是:“不把出来时,目前相别。 ”无半点要害人的意思。结尾处与黄衣女子打斗,女娘也一心要救刘本道。但面对这样一个对自己有情、有恩、有义的妻子,刘本道却表现得有些自私,甚至绝情,前面听了道士所言就打算用符害妻子,后面见妻子为了自己与黄衣女子打斗,刘本道却“顾不得妻子,只顾自走”(颇有几分《白蛇傳》中许仙的样子)。小说家仿佛并不要求主人公对女娘付出平等的情感。可见,“三怪”类小说要传递的趣味不同于“烟粉”的情爱,而在于主人公与三怪周旋从而产生惊悚效果。对于三怪而言,不论他们是否作恶,都会因为非人的身份,而被“他者化”。小说家以主人公视角为主,三怪是被观看、被辨别的对象,而不会成为听众共情的主体,这是“三怪”类小说的共同特点。有学者曾用“引起感情”和“激发兴趣”两种不同效果来区分宋元话本的情节特征(参蔡美娟、杨健《欣赏效果与宋元话本的情节特征》,《九江师专学报》 2003年第 4期),那么对于“三怪”类小说而言,希望给听众提供的体验自然是“激发兴趣”而非“引起感情”。“三怪”的作用在于给人以恐怖、紧张、新奇的感受,而非引导听众与其产生更深层的情感交流。这是小说家选择将三怪一律他者化的原因。
从口头文学的变异性出发,对宋元话本中“三怪”类小说的地域化与模式化展开赏析。地域化重在不同文本的差异性,看各个文本如何将故事与某一地域的风俗、历史、遗迹联系在一起,实现故事“在地化”的同时,也让神异性与世俗性交相融合。模式化则考察文本之间的相同点,看文本在情节安排、节奏把控、情感倾向上的一致性。笔者认为,无论地域化还是模式化,判断小说家的安排是否行之有效的依据就在于表演是否能对听众产生吸引力。把宋元话本放归到表演场中去考虑,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纯粹的文学、艺术活动,这是理解和欣赏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