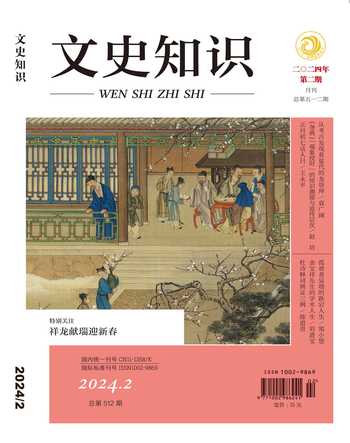金宝祥先生的学术人生
刘进宝


金宝祥先生,历史学家, 1914年生,浙江萧山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先后在四川大学、浙江英士大学任讲师、副教授。 1950年调入西北师范学院, 1951年被西北教育部评为教授,曾任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教学》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等。著有《唐史論文集》《陇上学人文存 ·金宝祥卷》等,主撰有《隋史新探》。
一 金先生的学术道路
金宝祥先生 1914年2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一个殷实的家庭。先生五岁失怙,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成长,十三岁小学毕业后离开家乡到杭州高级中学(即杭州一中)读书。金先生回忆说:杭高“是一所很不错的中学。教师讲课认真、负责,讲究质量是罕见的”(《金宝祥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四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285页)。
杭高是一所历史名校,曾经培养过鲁迅、沈钧儒、陈叔同、马叙伦、郁达夫、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徐志摩、丰子恺、金庸、华君武、张抗抗等大批的革命家、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徐匡迪、李兰娟等五十多位两院院士。金宝祥先生 1933年毕业于杭高,也是杭高培养的著名学者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曾“在杭州一中校史陈列部看到金先生的大名与蔡元培、沈钧儒、马寅初、邵裴子、苏步青、夏承焘等名流同列”(李华瑞《平坡遵道集》,凤凰出版社, 259— 260页)。
先生于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有杨志玖、孙思白、王德昭、余行迈(文豪)等。在北京读书期间( 1934—1937),图书馆藏书丰富,“几乎应有尽有”,老师们讲课认真,据金先生四十多年后回忆说:“我初听钱宾四先生讲中国通史,特别是先秦两汉之部,总觉得他把中国古史的精神,似乎都讲出来了,听了有新颖之感。 ”(《金宝祥自传》, 286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被迫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在云南蒙自上课,这也是先生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他听了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因眼病,闭目讲课,言语低沉,初听似觉平淡,慢慢已入佳境。我在大学四年,得益最深的,大概要算那几位确有自己创见的先生的讲课了。从他们的讲课中,使我念念不忘的,是他们功力深厚,治学谨严,决不人云亦云。”(同上)
1938年7月大学毕业后,金先生先在艺文研究会担任特约编译, 1939年2月至1940年7月,在云南蒙自、昭通两地中学任教, 1940年8月至1941年7月,在“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任助理编辑。这个时期,金先生的学术兴趣是宋史,撰写并发表了《宋高宗南渡前后两淮及西北居民之南迁》(昆明《中央日报》 “史学”1940年 9月10日、 17日、 24日)和《南宋马政考》(《文史杂志》 1941年第 8期)。
1941年8月,先生被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在川大任教期间,金先生侧重于中西交通史,阅读了大量相关史料和研究论著,撰写了《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一文的初稿。
1947年8月,应浙江英士大学之聘,赴浙江金华任历史系副教授。英士大学,原是 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成立的浙江省立战时大学, 1939年5月改名为英士大学。据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其日记中记述:“浙江战[时]大[学]改为英士大学,办农、工、医三院云云。 ”“教部已准浙江设立战时大学,更名为英士大学。此全系一种投机办法,因教部长陈立夫系陈英士之侄也……专设医、工、农三学院而无文理,焉望其能办好! ”(《竺可桢全集》第七卷《日记 ·1939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88页)由此可知,英士大学的办学背景和专业设置,即开始时只有医、工、农而没有基础学科。 1947年初,学校增设文理学院,设历史、中文、外文等系,并于暑期开始招生。据金先生自述: “1947年暑期,浙江金华英士大学新设文学院,聘我为史学系的副教授,于是我携眷离开四川,到金华英士大学去了。我到英士大学,除了讲授中国通史,还开设一门隋唐五代史。从那时起,我的兴趣,已偏重于唐史的研究了。 ”(《金宝祥自传》, 287页)
1949年5月,金华解放。 7月,英士大学撤销,工学院、农学院等并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各系和文理学院的历史系发给学生肄业证书,由学生自行转学”(《金华市志》第五册)。这意味着教师要自主择业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先生于1950年7月应西北师范学院之聘来到兰州,任历史系副教授。 1951年8月,由西北教育部评审为教授。据有关档案, 1951年8月,西北师范学院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呈文,提交了金宝祥先生从副教授升等为教授的报告:“一,据本院历史系副教授金宝祥请求升为教授……各等情,前业交升等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二,经将各该员著作并陈列图书馆,公开征求意见,无人提出异议,当即提请本院升等委员会审查合格,并经院务会议通过:副教授金宝祥准升等为教授,月支工资小米八百三十斤……均自八月份起实行,纪录在卷;三,特此具文呈报,敬请鉴核备查。”
同年12月,西北教育部批复了西北师范学院的呈请,同意金宝祥先生升等为教授。
当时实行大区管理,全国分为西北、西南、东北、华南等大区,由各大区代表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西北地区各高校的职称评审由西北教育部负责。由于币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有些部门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金先生的教授工资是小米830斤。同一时间评审的同一职称,可能由于资历、能力各方面的不同,工资数额也不一样。如与金先生同批升等为副教授的刘闳宇(艺术系),工资是小米750斤,宋福僧(教育系)则是 700斤。
50年代中期,金先生被选为《历史教学》的编委。 1956年,《历史教学》杂志的“负责人向中央教育部汇报请示了本刊的工作。当时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研究决定”了相关工作,其中之一是聘请雷海宗(时为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翁独健(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万九河(时为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金宝祥(时为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沈炼之(时为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担任编委。 1966年“文革”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 1979年1月,《历史教学》复刊,金宝祥先生继续任编委,直到2004年去世[参《〈历史教学〉三十五年总目索引( 1951.1—1985.12)》,歷史教学社;杨莲霞《杨生茂先生与〈历史教学〉》,《美国史研究通讯》 2017年第 2期]。
金先生从 1950年到兰州后,五十多年一直在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任教,直到 2004年8月25日在兰州逝世。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陇原大地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
二 金先生对我的教诲 —读书得间
“间”,本作“閒”,从门,从月。《说文解字注》:开门月入,门有缝而月光可入。《庄子 ·养生主》讲庖丁解牛,按照牛体的自然结构,顺着筋肉骨节间的空隙运刀,“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由此可知,“间”的本义为门缝、骨缝,后来泛指事物间的空隙。这个“间”和读书联系起来,就有字里行间、文字本身之外、书的夹缝中、书的空隙等含义。所谓读书得间,就是从字里行间读出“字”来。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本来没有字,当读得深入时,便会读出字外之字。读书能够“得间”,才会领悟作者的言外之意,算是把书读懂了,读尽了。因此,“读书得间”是方法、是功底,更是一种境界。就是要在字里行间得到弦外之音,看出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思。
“读书得间”是旧时老师教诲弟子的惯用语。我在随金宝祥先生读研究生时,金先生也常常用“读书得间”来教导我们,认为“读书贵能得间,或者说要看出问题”,“如何得间,如何发现问题,关键在于狠下功夫”(金宝祥《治史门径》,《兰州学刊》 1984年第5期)。金先生既重视新材料,但又不依赖新材料,而是提倡读常见书。金先生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史学家一样,对历史文献都是多次阅读,非常熟悉。如他读《资治通鉴》、唐五代史书等,都是通读,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认识和收获,他将自己认为重要或需要的资料摘录出来,然后再琢磨、斟酌和思考。
金先生虽然也注重新材料,如在研究唐代经济史时,就曾使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但并不依赖新资料,而是以读常见书为主。在读常见书中看出别人未能发现或解决的问题,才是真本事。我的理解是,新的史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时候可能会有许多的新史料发现,有时候可能几百年都没有新的史料发现。读书是没有明确目的的,可以说是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读书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自己感兴趣而不懂的问题,这时候再去阅读前人或同时代学者的论著,大部分问题可能就懂了,或者解决了。个别还不懂或不能解决的问题,再去探索、去研究。有的可能没有学术价值,不值得花力气;有的可能史料有限,无法进一步深入;有的问题可能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史料,就是个人的能力和知识结构局限,无法深入研究。只能选择那些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史料,个人还有能力去研究的问题着手。如 2007年我的归义军经济史完成后,有次在敦煌开会时,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先生问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课题,我当时说还没有想好。他说让我好好想一想,他也帮我考虑考虑。不久姜先生说他帮我想了一个题目,就是敦煌吐鲁番与江南的往来,并解释说:“这是一个重要课题,此前唐长孺先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你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比较熟悉,又是甘肃人,对西北的历史文化有感受,也比较熟悉,现在又生活、工作在江南(当时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对江南也有了了解和感受,正适合做这个题目。 ”后来由于我的学术兴趣转向学术史,未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不能不说姜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和让我做的理由,确实是值得深思的。我们现在的青年人,不是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力争解决问题,而是先提出问题,再用检索的方式获取资料、填充论据。这样写出来的论著就有许多夹生饭的味道。
读书不能有功利心。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经典著作都是应该阅读的。在长期的阅读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写作水平,古人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意思。即通过阅读,自己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三 金先生的治学特点和人格魅力
金先生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坚持,即对认准的问题会不懈地探索。正如金先生自己所说,当研究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只要把重要的历史文献,反复研读,反复思考”,自然就能从表象到抽象,再从抽象的规定中,探索出事物最一般的关系。“只要探索出这个最一般的关系,问题的本质也真正找到了。所谓解决问题,就是要探索出反映问题本质的关系。 ”(《治史门径》)“我每写一篇论文,总先考虑,是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否有自己所掌握的比较精确的史料,如果有,就写,否则,决不写。所谓有独到的见解,我的体会,无非是对某个历史问题的本质,多少有接近一致的认识。只要有这样的认识,去写文章,文章必然有具体之感,而不致蹈空。 ”(《金宝祥自传》, 292页)
金先生的许多论文,都是长期思考的结晶,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金先生将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转向了中西交通史。开始探讨史传、释典中所记载的割股、燃灯祈福等风俗的渊源和演变。“探索的结果,我确认这些风俗,自张骞西征以后,随着印度佛教寓言、佛教习俗的东渐,到了唐代,由于受中国儒教思想的影响,于是由割股供养变为割股疗亲,燃灯祈福变为燃灯歌舞的富有儒教内容的新兴的儒教习俗了。 ”(《金宝祥自传》, 287页)并于1947年撰写了《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初稿,但直到 1956年才改写定稿, 1958年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第 1期发表。
另如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金先生就开始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尤其是均田制的探讨,并于 1966年撰写了研究均田制的专文《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但由于“文革”的爆发而未能发表。“文革”结束后,金先生于 1977年进行了改写, 1978年定稿后才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第 3期发表。
金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或者说作为学人的金宝祥先生,有着怎样的学术人生?这正如金先生自己所总结:“寂寞、坚忍、读书、思考,便是自己真实的写照。”(金宝祥《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西北师大学报》 1993年第1期)
金先生的学术人生,除了“读书、思考”外,还有“寂寞、坚忍”,这可能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金先生一直工作、生活在西北的兰州,与外界联系较少,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学术探索中,从而养成了比较坚忍的性格。唐代文史研究的名家卞孝萱先生是这样记述金先生的:“金宝祥,浙江人,西南联大出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甘肃与赵俪生齐名,赵俪生在兰大,金宝祥在西北师大,是历史系主任。金宝祥脾气比较犟,所以在外间没有什么大名。”(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冬青老人口述》,凤凰出版社, 264页)从金先生的同辈朋友卞孝萱先生的记述可知,金先生性格“比较犟”,有什么就说什么。但金先生是光明磊落的,所有的意见或看法都是当面阐明。黄永年先生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 1980年10月,在西安成立唐史研究会时,他提交了 “‘文革前撰写这时定稿的《唐两税法杂考》。《唐两税法杂考》在会上曾见斥于金宝祥教授,说‘还有人讲什么两税法,意思是我这个其时名不见经传的人是不配研究两税法的”(黄永年《从我的两篇旧作说起》,《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 308页)。学术界普遍认为,两税法中的两税是指地税和户税,金先生则独树一帜,早在 1962年的《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范大学学报》 1962年第3期)中就提出:两税法中所规定的两税并不是指地税和户税,而仅仅是指户税,因户税是夏秋两征的缘故而称为两税。黄永年先生的《唐两税法杂考》仍然强调两税是户税和地税,金先生可能就当面表达了不同意见。
李华瑞认为,“金先生对学术的追求具有一种献身精神,虽然他晚年对学界新的研究了解不多,而且愈加坚信自己的史学见解”(李华瑞《平坡遵道集》, 260页)。
金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做事细致是我辈的榜样,他的做人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我与金先生接触较多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还是有规范的,学人也是比较自律的。金先生经常和我谈的是做人问题,即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学问。如果做人不行,学问是不可能做好的。哪怕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是不足挂齿的,不会为学界和社会所认可。我们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梅贻琦、郑天挺,就能理解金先生对做人和做学问关系的阐述,可见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说有根和魂的。
金先生他们那一代学人,虽然学业有专攻,但他们的学术视野都比较宽广。虽然不能说他们是大师,但绝对是权威。金先生长期担任甘肃省历史学会的会长,是甘肃史学界的灵魂人物,尤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的权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白光弼先生是化学系的教授,他就住在金先生的楼上。我在金先生家曾多次见过白校长,他主要是来和金先生谈历史系教师的职称评审问题,即哪些人应该升副教授或教授。金先生也常常对系里的老师讲,不要多写论文,要写有质量和有自己见解的论文,只要你有一篇论文达到了教授的水平,就可以升教授。因为当时的学术氛围是学者有诚心,做人有公心。学术界还有权威,这样的权威不论是人品还是学问,都能得到大家的公认。如当时历史系有几位与金先生来往比较密切的老师,我在先生家遇到的次数也比较多,在职称评审时,他们也会找先生来说项。但由于他们的学术水平略低,金先生并没有因为与自己来往多而推荐或同意。反而是几位与金先生关系比较疏远的老师,由于学术水平较高而得到了金先生的推荐或同意评上了职称。我也从没有听到有人说金先生处事不公正这样的议论。
金先生那一代学者,由于从小的家学和以后的师承都比较完善,学术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广,他们对别人论著的水平能够把握,再加上为人正直,坚持原则,所以被评审者即使没有评上职称,也很少有埋怨的。
综观金先生的学术人生,他能在唐史研究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并能长期坚持,成为“自成一家之言”的唐史研究名家,是有许多主客观条件的。这除了他的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对理论和史料都特别重视外,还与他的经历有关。金先生出生并在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江南的浙江,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师就是知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中学又是在享有盛誉的杭州高级中学度过的。江浙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为金先生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江南水乡又养成了金先生细腻的性格。大学又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度过的,其中既受过钱穆、陈寅恪等史学大家的教诲,又有杨志玖、孫思白、余行迈、王德昭等同学可以相互激励,有学者指出:“在抗战前 20多年中,北大史学系共培养出了 28位后来比较有影响的史学家”,其中就有 1934级的金宝祥(参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 2006年第1期)。后面的五十多年又一直工作、生活在兰州,大西北的辽阔、粗犷又培养了金先生宽广的胸怀。这许多因素的组合,成就了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