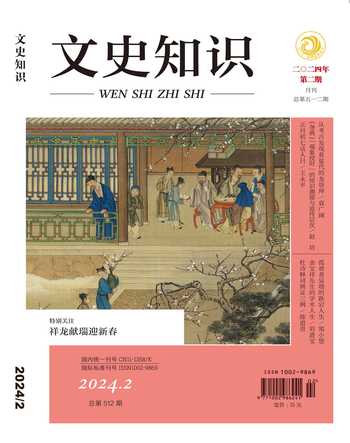《尧典》“观象授时”的知识溯源与流传层次
赵培


《尚书 ·尧典》,顾颉刚先生认为其为战国秦汉间的伪作(参《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屈万里先生定其成篇时间在孔子之后,孟子中晚期以前(参《尚书集释》)。陈梦家先生认为出自战国人之手(参《尚书通论》)。三家皆留心于此篇中晚出的痕迹,此为古史辨派,或古书辨伪者惯常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陈梦家先生认为关于夏、商、周三代之书的保存与拟作,应该分属晋、宋、鲁三国所为。周书多是鲁国太史所藏,而夏、商之书所谓晋、宋两国之人所拟作。并认为这些拟作,也应有所本,因之也保存了许多史料。
关注文本晚出痕迹以断定成篇时间的做法过分强调了编定者的工作,实际上,《尧典》当中很多模块,其形成同文本自指时间基本一致,而其现存形态又因为流传过程跨越了多种媒介形态而变现出多层次性。结合甲骨文中相关记载,能够发现《尧典》中实多祖述之内容,就其“观象授时”部分而言,应该是跨越了漫长历史,经历过多种流传形态(口传、明·杜堇《伏生授经图》记录、写定、流传改移等)。
一 《尚书大传》关于“寅宾出日”与“寅饯纳日”三种讲法
《尚书大传 ·略说》言:“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执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东郊,以为万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报天德。迎日之辞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东郊。 迎日,谓春分迎日也。《尧典》曰:‘寅宾出日。 此之谓也。 ”《大传》解“寅宾出日”为迎日于郊之礼,但是关于行礼的时间,兼存“正月”与“春分(在二月) ”两说。又《唐传 ·尧典》言:“中春辩秩东作,中夏辩秩南讹,中秋辩秩西成,中冬辩在朔易。 ”此处则主“春分”说。
又《唐传 ·尧典》传“寅饯入日,辩秩西成”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将率,选士厉兵,以征不义,决狱讼,断刑罚,趣收敛,以顺天道,以佐秋杀。 ”皮锡瑞疏证曰:《春秋感精符》曰:“霜,杀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鹰率击。王者顺天行诛,以成肃杀之威。 ”《明堂之制》曰:“秋治以矩,矩之言度也。肃而不勍,刚而不匮,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 ”《洪范五行传》曰:“仲秋之月,乃令农隙民畋醵,庶氓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季秋之月,除道成梁,以利农夫也。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牛马,收泽赋。 ”《王居明堂礼》亦与《五行传》略同。据《春秋感精符》则“寅饯入日”当在季秋,而《明堂之制》《洪范五行传》和《王居明堂礼》则并无明确区分孟秋、仲秋、季秋。更需留意的是,对“寅饯入日,辩秩西成”的解释,无论是《唐传》还是皮疏所引,皆已不关涉郊祀送日,而是以秋季之政事与农事(仲秋之田猎、会饮,季秋之修治道路建架桥梁等)解之。
辑本所见记载皆明确标记出自《大传》,但在此句的解释上有相异的三说。梳理相关材料能够发现,《大传》所展示的三种说法皆有其传承与流传脉络。
二 迎日于郊之礼
《礼记 ·玉藻》载:“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 ”郑玄注:“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南门,皆谓国门也。”《正义》曰:“按:《书传 ·略说》云:‘祀上帝于南郊,即春迎日于东郊。彼谓孟春,与此春分朝日别。 ”又《郊特牲》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 ”郑注云: “《易说》曰:‘三王之祀,一用夏正。 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分,分而日长也。 ”《正义》曰:“按《书传》云:‘迎日,谓春分迎日也。 即引‘寅宾出日,皆为春分。知此迎长日非春分者,此云‘兆于南郊,就阳位,若是春分朝日,当在东郊,故知非也。 ”依据孔疏,则古天子迎日之礼有二:一建寅之月,迎日于南郊;一春分,迎日于东郊。但据《大传》所言,“正月朝迎日于东郊,以为万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报天德。”当是正月迎日在东郊,郊天在南郊,春分亦如之,而非言迎日与郊天分属立春与春分两节。
郑玄主春分朝日说,《尚书正义》引郑玄注云:“寅宾出日”谓春分朝日,又以“寅饯纳日”谓秋分夕日也。又《周礼 ·冯相氏》:“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又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郑玄注:“辨其序事,谓若仲春辩秩东作,仲夏辩秩南讹,仲秋辩秩西成,仲冬辩在朔易。”据《南齐书 ·礼志》载东昏侯萧宝卷永元元年( 499)何佟之议礼可知,马融同于郑玄,而卢植主立春说。何佟之认为当从马、郑,用二分之说。《国语·周语上》“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韦昭注:“礼,天子搢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于东门之外。然则夕月在西门之外也。 ”则韦昭同于马、郑。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孔颖达疏解孔传云:“王肃亦以星鸟之属为昏中之星。其要异者,以所宅为孟月,日中、日永仲月,星鸟、星火为季月,以殷、以正,皆总三时之月。 ”王肃虽未明言郊日之礼,但依此当亦从正月说。又《魏书·儒林传》载孝静帝天平四年( 537)李业兴使梁与梁武帝的经学问对,萧衍问: “‘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也? ”据此及李业兴之对答可知问对双方均从正月说。
三 立春(正月)春耕说
《尚书大传》中另有一说将“寅宾出日”和“寅饯纳日”同政事和农事联系起来分析。此类讲法亦常见。《尚书帝命验》载:“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谓‘寅宾出日。秋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谓‘寅饯纳日。春迎其来,秋送其去,無不顺。 ”此类传解不言,或忽略迎日之祀,偏重讲春耕之起。相较而言,伪孔传和孔疏基本上属于这一系统。虽然表面上讨论东方之官的导引,实则更偏重解释“东作”与“西成”,即言农事。孔传:“寅,敬;宾,导;秩,序也。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东方之官敬导出日,平均次序作之事,以务农也。 ”
经文孔疏:“既主东方之事,而日出于东方,令此羲仲恭敬导引将出之日,平均次序东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务勤种植。 ”传文孔疏更为具体,不具引。
四 甲骨刻辞中的相关记载
甲骨文中有“宾日”“出日” “入日”“出入日”“各日”的记载,如:
乙巳卜,王宾日。(《合》 32181)
辛未卜,侑于出日。辛未侑于出日兹不用。(《合》 33006)
丁巳卜,侑出日。丁巳卜,侑入日。(《合》 34163)
戊戌卜,内乎雀于出日于入日。(《合》 06572)
各日,王受祐。(《合》 29802)
此类卜辞,陈梦家、郭沫若、胡厚宣、丁山、常玉芝、赵诚、艾兰、具隆会等皆以祭祀日神解之。如陈梦家先生言:“卜辞习见之‘王宾某某,罗、王以来皆作名词,至郭沫若始改易为动词,其说至确无可易(原注:《卜通》 39)。《说文》:‘宾,所敬也。 此谓宾日者敬日也,《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 ”后又于《殷虚卜辞综述》中关于“日神”部分言:“所祭者是日、出日、入日、各日、出入日,入日、各日即落日。祭之法曰宾、御、又、、岁等,也都是祭先祖的祭法。《说文》‘暨,日颇见也,于日暨日,即日出以后祭日。《鲁语下》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日 ,大采在天明之后,约当于‘暨。《尧典》‘寅宾出日‘寅饯入日,与卜辞之称‘宾日相同。《史记 ·封禅书》齐有八神主‘七曰日主,祀成山……以迎日出云。”
与之不同,如岛邦男释“宾”为“由外至于家室或祠室”,而认为“王宾日”为省去神名之辞。他通过辞例汇析,指出“宾”的本义,彻底否认了卜辞中存在日神。其关于宾的解释,赵诚、刘源等先生皆信从。关于商代无日神说,则得失参半。其关于“王宾日”非祭日之说可信从;但认为商代无祀日,与“出日” “入日”非祭祀太阳的讲法,则不能成立。宋镇豪先生在《甲骨文“出日” “入日”考》一文中已有针对性辨析,兹不繁述。
粗略言之,甲骨刻辞中同日相关者不能混杂处理,当分而言之:“王宾日”类非祭日之辞,当从岛邦男之说为同类卜辞的省略形式;“又(侑)日”“帝(禘)日”“比(.)日”“祼日”等确属祀日神之祭;“出日” “入日”等迎日相关祭礼中的日或同日神无关,并非日日祭祀,而是有固定的行祭季节(或言日期),这一系列卜辞同《尧典》等典籍中关于礼送太阳的记载相关联。
五 《尧典》“寅宾出日”“寅饯入日”天文历法背景追索
通过梳理结合传世文献与甲骨中“出日” “入日”相关刻辞的研究,我们注意到几个明显的问题。据文献所载,迎送日之礼有两大类,一为同日中朝夕祭祀,一为春分、秋分祭祀。前一种如《礼记 ·祭义》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又《国语 ·周语上》云“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韦昭注:“礼,天子搢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于东门之外。然则,夕月在西门之外也。 ”《鲁语下》亦云“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韦昭注:“天子以春分朝日,……冕服之下则大采。……夕月以秋分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谓朝日以五采,则夕月其三采也。 ”韦昭即已混淆两种形式,以春分、秋分之祭来训诫同日朝夕之祭。大采、少采(小采)见于卜辞,据董作宾《殷历谱》、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之说,大采、少采(小采)乃上午 7—9点、下午 5—7点。大采即《礼记 ·祭义》所谓朝,少采(小采)即《礼记 ·祭义》所谓闇,亦即夕。后一种如前引《尚书大传 ·略说》言:“迎日,谓春分迎日也。 ”郑玄注《尚书》《周礼》《礼记》皆主此说。马融、韦昭、何佟之等皆主此说。
第二个问题,主春秋说者,往往径直将春秋说等同于春分、秋分说,而忽略掉尚有孟春之说。孟春说亦有其脉络,如《尚书大传 ·略说》云“以正月朝迎日于东郊”,《尚书帝命验》、卢植、王肃、伪孔传、萧衍、李业兴等皆持此论。就《尧典》而言,以农耕说来解释者基本上都从正月说。
第三个问题《尧典》所载能否同卜辞所刻简单对应。首先,无论其行卜与祭祀的时间是否仅在春秋二节,甲骨中所载实际上仅为一日之事。《尧典》所反映的礼制则是在不同的时间(春分、秋分)来祭礼出日、入日。其次,诸家讨论“出日” “入日”刻辞同《尧典》关系时,基本上皆为简单比附,观其核心词近同而已。复次,这样的机械比较实则忽略了《尧典》“观象授时”部分的系统性。
就“出入日”相关刻辞内容来看,殷人实际上要在(春分、秋分)一日之内早晚完成日出与日入的全部祭祀活动,参照《尧典》“观象授时”部分,这意味着出日、入日的祭祀恐怕并不仅仅是为着敬日之宗教目的,应当是一种测日影、定四方、判知四时的测量活动(参常正光《殷人祭“出入日”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只是在当时人的眼中,测量活动,可能具有科学实验与宗教情感的双重属性。《大戴礼记 ·五帝德》记载孔子言黄帝“历离日月星辰”,王聘珍解诂:《史记 ·历书》索隐云:“《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聘珍谓:离者,别其位次。又曰:帝喾“厤日月而迎送之”,解诂:厤读曰歷。《尔雅》曰:“歷,相也。 ”相日月之出而察之,若寅宾寅饯然,故曰迎送之。可知,在东周人的记忆当中,确有先王历象日月星辰之事。又《墨子 ·节用中》载:“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 ”则“出入日”之用法至战国尚在使用,可见其事其文之流传自有统序。
结论
实际上,据岁差推测《尧典》所载“鸟、火、虚、昴”四中星之观测年代,能田忠亮推算为约公元前 2000年(参《东洋天文学史论丛》),新城新藏推算为大约公元前 2500年(参《东洋天文学史研究》),而竺可桢先生推算为星昴乃距今4000多年前,鸟、火、虚乃距今 3000年前,折衷而推测“盖殷末周初之现象也”(《论以岁差定〈尚书 ·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各家之说有异,然均定在距今4000年前后。从《尧典》“观象授时”部分的系统性上来看,测影定方定时的时间当亦不晚。山西省襄汾县新时期时代陶寺文化城址发现有 4100多年前(相当于帝尧时期)的古观象台遗址,经实测确实有观象授时功能。如此,作为《尧典》“观象授时”核心部分的宾日、饯日(测影定方定时)与四方仲星(昏中星定季)所搭起来的時间框架,让我们不能不认为当时的“记载”通过口述或者其他辅助形式传承了下来,这构成了“观象授时”文本的第一个信息层。
蔡沈《书集传》言,“历既成,而分职以颁布,且考验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测影定方定时,作为分时制历的步骤之一,在后者既定以后,剩下的就是核准与校定的工作。据甲骨刻辞所记,则在春秋二分礼日出入的同时,常伴有不同种类的祭祀活动。另外,如果我们进行机械比较,能够发现“寅宾出日”“寅饯入日”,所对应之“宾”和“饯”在卜辞中均非祭名。依照前文对“宾”的分析,结合“出日”的相关辞例,则“寅宾出日”或为省略了祭名的刻辞,而“寅饯入日”当亦同之。春秋二分的这种祭祀活动一直延续,未曾断绝。马融、郑玄等注经笺传实得此脉络,形成了《尧典》经传的第二个信息层。
《礼记 ·月令》载:“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此为天子迎春之礼。又《乐记》云:“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 ”《墨子 ·三辩》程繁问于子墨子云:“昔……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聆缶之乐。 ”春耕夏耘秋敛冬藏与天子迎四季之礼,前引丁山说,以为亦当肇端自甲骨文中“迎日”之礼,实则二者区别明显。就《墨子》载程繁追述“昔”以及《月令》所载,结合周人始祖后稷为农业之始祖,则此礼周已有之当无可怀疑,其同天子籍田之礼一样,当同为重视耕作而设。迎春与耕作由立春始,故后世以孟春(正月)、以农耕解《尧典》者当在此脉络之中,而《大传》又当后来者之先导。此可谓《尧典》经传的第三个信息层。
从这三个信息层当中,我们看到了早期知识经“三代损益”的轨迹。如果仅仅为了研究的方便,粗暴地将《尧典》定为战国或秦汉人的“作品”,我们就可能忽略掉了对其所涵蕴之信息层(其中包括早期的“实录”)的开掘,以及对先民辛苦传述过程的追寻与体味。与此同时,经典的丰富程度也就大打折扣了,这将会是令人遗憾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