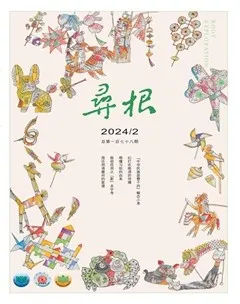一个晚清士大夫的政治圈子
赵广军



张佩纶,河北丰润人,人称张丰润,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二甲第十九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擢侍讲、起居注官。他曾一度左右朝野舆论,是风头最健的清流人物。某种程度上说,晚清言路之开,始于光绪三年(1877年)张佩纶带头上书言事,敦促清廷广开言路。张佩纶可谓为近代清流党、清流现象做了一个最典型的注脚,也是数千年来主掌言路的清议现象最终止于晚清大变局、让路于民间报刊等新舆论媒介的一个典范。
张佩纶一生之起合,绝不亚于其孙女张爱玲笔下的小说人物。这样一个末世王朝的士大夫,若从其被野史时论所评,对比其日记、书信、诗文等文献所表露出的抱道忤时、易言偾事、身世之感、家国之故等心路历程,可以映照出近代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晚清各种势力胶着的政治生态。
邻居圈:张佩纶与吴可读、陈宝琛
张佩纶出身官宦、士人家庭,曾祖、祖父均为县学生。6岁时,张佩纶之父死于安徽按察使任上,年幼的张佩纶随家人转徙各地,备尝艰苦,甚至在13岁时亲手埋葬了死于兵乱的五姐。最终,张氏在江苏海门渔村寓居,与沈氏为邻居,生活逐渐稳定。
沈家是举人之家,有古书千卷,良田百亩,代有秀才,一度有父子两人同时被举孝廉方正,而此父子两人又均累辞不就,于是被地方高看。张佩纶与沈家子弟一同就学,结识了人生中难得的友人沈熊。13岁时为了能够多看书,他时常到沈家借书,回家手抄,由是诗笔顿进,练得一手好字。
23岁时,张佩纶入直隶应顺天试,并与其侄张寿曾一起考中举人,叔侄同捷,一时传为佳话。24岁,他中进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自己的京官生活。后作为散馆人员,张佩纶受到了同治皇帝的引见,被授职编修,这一年张佩纶27岁。
在翰林院,张佩纶借助师门、同年、同乡等逐渐构建起自己的人际圈,圈子里的人多是有功名者,与这些人的交际多通过诗歌的唱和、为长辈撰写寿序等文化活动来维系。从张佩纶的一生政治活动来看,此时,他获得了人生最为真挚的两个朋友,与两人的交往除了有传统意味的交际途径,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交际途径——邻居。两人中,一个是与慈禧太后较真而死的吴可读,一个是马尾海战失利后福建籍京官攻击张佩纶时处处为张辩护的福建人陈宝琛。
光绪三年九月,张佩纶上《请广开言路折》推动清廷开言路。也正是从该折起,张佩纶开始发挥言路之权,成为这个白简搏击时代的宿主,民生、吏治、洋务、时议等折片渐多,尤多弹劾。对于张佩纶之起,张曾扬在《涧于集·序》中称:“君之为讲官,当光绪初纪,方内定而外患日炽,君与同直诸君奋起言事。”掌控朝政的孝钦皇太后听政,虚衷采纳,后擢典译署,筹内治外交诸策等国家大计,而张佩纶所“论奏尤以上下交儆,黜邪去蠹为图治之要,危言急论,弹劾不避权贵,朝右震悚,自二三同志外,多侧目视之”。张佩纶成为清班中以最敢言著称,主持谠议,俨然为清流党要角。
刚入都为翰林时,张佩纶对其姐夫称:“京秩无不高寒,而敝署尤为清苦,俸钱最薄,盐关津贴近俱未复。惟同年世好友外任者,相率为馈岁之举,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岂复可耐。”五年后给其师夏如椿信中仍称“京华薄宦,忽忽五年,乞米典裘,进退维谷”,并且“家计拮据异常,俸薄官闲时嗟仰屋”,连赴京应试的老师也招待不起住宿。赴福建之前,生活面临支了俸禄后多人凑钱饮酒的情形:“名士醵钱聊纵饮,冷官支俸许浇愁”,曾作《移居用膳姜韵》自谓“闭门肯书乞米帖,赏音谁解回帆挝”。
张佩纶每月在家坐等翰林院小吏到家送俸米俸票,获钱后则喜邀同好共酌。如其《篑斋日记》所记,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初七,午后院吏送俸米票来,晚上即偕友人找吴可读等人同酌。其日记中记载京居时期最多的就是交游、宴饮、肆购等活动。几乎每日均有招饮、小酌、小饮、集宴等,吃喝中构建起张佩纶的清流交际圈子,这是晚清政治背后的人际生态。
张佩纶与吴可读“恨结邻迟”。在安慰因上书言辞戆直而降职调用、返里主讲兰山书院的吴可读时,张佩纶率诸同好为之饯行,并互赠诗歌相慰。张佩纶作《柳堂先生言事谪官归主兰山书院赋诗为别》等十二首诗送别,规劝吴可读“时疏狂”“沥胆真能伏阙陈”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言路之开的信心,“早晚朝廷求直谏,就家或更问春秋”,这使得颇具清望的吴可读“乐甚”。30岁时,翰林院侍讲、起居注官张佩纶已获得专折上奏的权力。居京不易,屡屡迁徙赁屋而居,而立之年,张佩纶择居南横街一带,与吴可读为邻。吴可读起废复出,又来京师,仍旧住在其南横街旧宅,与张佩纶宅仅一墙之隔。共同的志趣,往往雅集同人,以诗和酒表达心绪。张佩纶与吴可读的诗和渐多。
光绪五年(1879年),同治帝下葬,吴可读恳请主持迁陵的恭亲王奕將他派到惠陵襄礼。梓宫奉安后,在返回京师途中,吴可读自尽于同治帝陵墓旁马神桥的一座小庙内。在小庙里,吴可读闭门具疏,写了一联剖明心智:“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
吴可读的死激起在京读书人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吴也被誉为“铁石一儒冠”,跃跃欲试的清流乘势而起。被谏的慈禧也誉其“孤忠可悯”,吴可读尸谏事件无疑成为撬动张佩纶等清流群体兴起的杠杆。吴可读的那份奏折成为千古绝唱,他的死对张佩纶影响巨大。
同治帝大葬,张佩纶扈从而行,十七日从陵上归来,人甚“疲荼”,更为折磨的是又遭“柳翁之变”(即吴可读“尸谏”),意兴阑珊,久久无心日课。另外,生母及内人朱班香同时病倒,一时间张佩纶终夜不得安枕,闷急之至。张佩纶自称“余自东陵归,用世之志锐减”,想回南方奉养,但是苦于“菽水无资,不能自决耳。枯坐冥想,万念奔驰”。四月六日,生母亡故。五月五日,妻朱班香去世。
张佩纶日记对吴可读身死的细节记载,可以补充一些史料:闰三月初,“柳翁疏入奏,旨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正在清廷征求朝野诸臣意见的时候,初五日晚上吴可读即自尽身亡,张佩纶记载的细节:“柳翁初五日卯刻仰药自尽,读其庙中周道五纸上有血迹,盖初拟自刎,复拟自缢,以白绫三尺余环结,书十四字,曰:‘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旋以无梁可悬,一板庋门上,动摇易坠,恐有声致救,乃服洋药以终。可谓百折不回矣。”
十八日,有人投书于张佩纶门内,署名“粤东布衣古铭猷”,文称要伸吴可读其未伸之志,“非公而谁”?要张佩纶“会议时但当据理直言,不可稍有惕疚,以失朝野之望,以辜皋兰(指吴可读)之知,天下幸甚,士林幸甚”。还称自己人微言轻,又不认识张佩纶,因此冒昧投书。这天是张佩纶大女儿的弥月,张罗好午间的客人后,下午,张佩纶出门见李鸿藻,在李鸿藻处见到了吴可读那篇奏疏。友人纷纷从外地寄书信来,以诗哭吴可读。居京的同好,互相谈论的主题仍旧是“论柳翁疏”。吴可读死后,张佩纶等一干友人,忙于其葬事,有三河县查某愿意舍地十多亩,为吴可读葬地。
光绪六年(1880年),吴可读子将其临命前所作家书装成卷册拿给张佩纶看,张佩纶泣跋数行。
28岁时,张佩纶在翰詹大考中列为一等,擢升为翰林院侍讲,不久又充任起居注官。此时居京师南横街与北半截胡同之间的张佩纶,结交了居住在丞相胡同西的新邻居陈宝琛。两家所居的两条巷子相连,两人一南一北过从甚密。两人同岁,仕途经历几乎相同:中进士、选翰林、擢侍讲、充起居注官,最相似的莫过于两人都因中法战争遭弹劾。
两人情谊相投,交称莫逆,居京时期,几乎每日相往,做了十年邻居。陈宝琛是张佩纶一生的至友,友谊也维持一生。即便是张佩纶戍边之后,两人交情始终不渝,荣瘁无间。张佩纶被慈禧调往福建战场时,至友陈宝琛在张佩纶出都前一晤,观察到他“以气类太孤为忧”,发自内心地为张佩纶的性格和前途担忧。后来在马尾海战中张佩纶的所为,几乎被陈宝琛语中。
马尾海战失败后,朝野将张佩纶推至风口浪尖,极尽嘲讽,由于战败,幼翁在福建舆论中被讥为只会在闺房中画画眉毛的“张敞”。将张佩纶与福建大员何、何如璋、张兆栋放在一起作词讽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意指其粉饰无实际用处。野史描述则十分鲜活,说张佩纶兵败出逃,一夜狂奔三十里,顶着个铜脸盆以躲避炮弹,饿了则大嚼猪蹄,狼狈之状,斯文丧尽。未战之前,张佩纶常作大言,好言而无识,曾经说过,失败了当以三钱鸦片殉难,于是产生了尖刻的联语:“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当败之时,何如璋督福建船政,也是敌至不战,败了就跑,跑到彭田乡依张佩纶,张佩纶怕敌人侦察到,把他骗走。时人有联讽二人云:“堂堂乎张也,怅怅乎何之?”当时闽人有“两何莫奈何,两张没主张”的说辞。还有一联讽刺两张、两何四人:“堂堂乎张也,是亦走也;伥伥其何也,我将去之。”
作为好友,陈宝琛曾为张佩纶辩护,也被讥讽。好事者作一联:“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谢恩折有“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的话);三洋会办,请先看侯官(指陈宝琛)降级,丰润充军。”嘲笑陈与二张。舆论声浪之猛,也使得张佩纶感觉到自己“诗名官谤遍东南”。
张佩纶马江失事后,陈宝琛正丁母忧,挽联相慰:“狄梁公奉使念吾亲,白云孤飞,将母有怀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东风未便,吊丧无面愧登堂。”
张佩纶之逝,陈宝琛作《入江哭篑斋》:“雨声盖海更连江,进作辛酸泪满腔。一酹至言从此绝,九幽孤愤孰能降!少须地下龙终合,孑立人间鸟不双。徒倚虚楼最肠断,年时期与倒春缸。”又有《检篑斋手札怆然有感其二》云:“君才十倍我,而气亦倍之。等闲弄笔札,时复杂怒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下南洋募集铁路股款的陈宝琛胫肿复作,在病痛中仍然梦见张佩纶:“魂何来此岂其仙?驾海乘风路万千。地下相思应更苦,天南独客有谁怜?余生病归犹及,穷岁幽忧死傥贤。三岛十洲粗一览,与君恨不册年前。”张佩纶故于南京,陈宝琛特地千里唁之,时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邀其游庐山,而陈宝琛称“吾为吊丧来,非游山也”,直言力辞,可知张陈之交。张佩纶墓志也由陈宝琛撰写。
陈宝琛称张佩纶生平希慕苏轼,“遭际复相类”,其“一身之升沉荣瘁,实为人才消长、国运荣替所系”,身世与国势相系,实为确论。所谓“与君生不幸,值此时事艰”。
政治圈:张佩纶与张之洞
清流言官中,以张佩纶、张之洞两张势头最盛。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清流谐音为“青牛”,牛头指李鸿藻,是为精神领袖;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欧阳昱记载:“同治、光绪间,御史翰林参劾内外官,声名赫赫者,有陈启泰、孔宪谷、邓承修、张佩纶、陈宝琛五人,时称为‘五把刀,又加张之洞、周德润、何金寿、黄体芳,内尚有一人,予忘之。共五人,为十友。”另外还有所谓的“松筠十君子”“十朋”“清流六君子”“翰林四諫”“四大金刚”以及御史言官“五虎将”等称呼,其中多将两张列入。在时论中风头最健者,是张佩纶,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主盟。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称:“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他“得名最远,招忌最深”。对此张佩纶并不在意,自诩其谏诤气魄“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
初入政坛,张佩纶以新进少年的锐气,奋发言事,有澄清之志,弹劾庸吏,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张佩纶侍讲任时,过往密切的多南方人,如状元洪钧、林则徐三子林拱枢、榜眼黄自元、吴大等,其中不乏以清流著称者。而对于直隶同乡则相交不多,即便是同乡公饯延约时,对于座客谈笑,张佩纶深感“甚鄙”。自幼在南方长大的张佩纶无疑骨子中具有南人情结,这也是张佩纶与南北清流诸人交往的感情基础,与北清流交往可凭籍里之便,与南清流交往则以寓居浙江的身份。与张之洞的交往则具有多重圈子意义:直隶同乡、清流身份。
公事之余,张佩纶与张之洞一同游厂肆赏鉴选购书画文献以及闲谈遣闷之事,筹商修建畿辅先哲祠和编纂《畿辅先哲录》。
从31岁开始,张佩纶奏折中弹劾折子的数量和影响力骤然扩大,此时也正是其与吴可读、陈宝琛、张之洞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光绪五年初,崭露头角的张佩纶被李鸿藻约话多次,每次多叫上张之洞,日记中未言约谈内容,但是约谈后多有重要事件和奏折出现。
作为清流两牛角,两人行事风格不同,张之洞的奏疏对事不对人,而张佩纶则直接对事对人。好搏击的张佩纶弹劾之策是善于攻击人身,对人不对事,而张之洞则“但谈时事,不是搏击”,对事不对人。清流时期,张之洞上奏折、附片共39件,没有弹劾他人,多是因事陈言。同时期的张佩纶则无一不是弹劾诸官。张佩纶的搏击最易陷入政治派系争斗,弹劾的命中率较大,也最易得罪人。连张之洞也在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邀饭时对张佩纶称“疏太辣,亦颇称其胆”。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光绪六年,张佩纶收张之洞12岁的儿子为弟子。张佩纶一直尊称张之洞为“前辈”。在送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任时,张佩纶作《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表达自己与之的关系,“公昔朝阳应鸣凤,居庐初解承明从”。张之洞山西之任是其渐渐隐退清流身份的开始,地理空间的隔绝逐渐淡化了兩张之间的关系。
马尾战前,张佩纶共上弹劾和直谏折片31件,联衔折片8件,为宦则不善迎逢、不善任事。张之洞则不以参劾为能,劾人的折子仅有董恂、崇厚寥寥数片而已,上陈时务者多,表现出长袖善舞、细致任事、工于宦术的本领。赫德对出任总理衙门的张佩纶的看法:“这人曾力主对俄作战,倡言以杀头严惩崇厚的罪状等等,锋芒必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这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的产物。这位先生经过培养和适当驾驭,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新人物。”正当朝野、中外看好张佩纶仕途时,张佩纶的人生发生了逆转。
光绪十年(1884年),张佩纶倚仗自己了解一点洋务和军务,年初上疏建议朝廷武科改试洋枪。四月十四日,奉旨会办福建海疆,被推向了战争前线,同时被赋予了专折奏事的特权。一时间,频发议论的清流陈宝琛会办南洋,吴大会办北洋,张佩纶会办福建。
两张之间的关系自两张外放京外开始逐渐疏离,戍边期间两人偶有书信。释戍后,张之洞邀请其主持湖北铁厂、枪炮厂、织布局等三厂,张佩纶拒绝了。张佩纶来南京定居时,两人身处同一个城市,此时的张之洞官至代理两江总督,而张佩纶是宦海潦倒,成为备受时论寻疵的闲人。陈宝琛撰《张佩纶墓志铭》称,张之洞几次提出要见张佩纶,皆遭拒绝。但另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深知西太后憎恶张佩纶,为了避免嫌疑,曾经派人向张佩纶暗示,愿意为他修理苏州的拙政园,请他搬到苏州去住。张佩纶非常恼怒地说:“我固被议之人,奈何南京亦不容许我住?他不来看我,随他!”直到半年后张之洞微服来拜访,一对清流故人才得一见。张之洞细数张佩纶之际遇,四目相对时称:“就谈身世,君(张佩纶)累郗不已。”谈到往事,张之洞大哭而别。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张佩纶逝后一年,张之洞作《过张绳庵宅四首》称:
北望乡关海七昏,大招何日入修门?
殡宫春尽棠梨谢,华屋山邸总泪痕。
廿年奇气伏菰芦,虎豹当关气势粗。
知有卫公精爽在,可能示梦儆令狐。
亲戚圈:张佩纶与李鸿章
张佩纶有三任正妻,27岁在京为翰林院编修时娶朱学勤女朱班香为妻,而朱学勤与翁同交好。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两人成婚时,翁同因与朱学勤友谊往贺。但是朱学勤似乎并未给这个中意女婿太多荫庇,成婚五个月后,朱学勤就去世。朱学勤是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家有结一庐藏书楼,搜罗甚富,有宋元明版及旧抄校本千种之多。而这些图书多为张佩纶获得,也算是青年翰林人生的一大财富。朱班香与张佩纶相处时论史、和唱,朱班香的论史之作也辑为《班大家集》。朱班香喜好读史,朱班香的舅舅便将珍贵的宋本《汉史》作为其嫁妆。光绪五年三月四日,朱班香“震将”,九月忽然吐血升余,委顿殊甚。长女出生后朱班香患有儿枕痛,有时号叫彻夜。五月五日,朱班香因病剧去世,张佩纶将朱班香的灵榇暂寄佛舍。两月后长女也殇。加上刚刚去世的生母毛氏,三月内顿失三个挚亲。朱班香死后,张佩纶不得已出下策,将两子寄于朱班香娘家,每月给十两白银的生活费用,张佩纶则扶柩南下苏州。七月下旬出都,十月初回到北京,在朱宅赁其东院,接回两儿团圆。
张佩纶的第二任妻子是边宝泉之女边粹玉。边宝泉是汉军镶红旗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官至陕西、河南巡抚,闽浙总督。边宝泉是同治十年辛未科的同考官,故张佩纶以“润民师”相称。在张佩纶谪戍次年丙戌,久患肝病的边粹玉病故于北京府中。生离死别,伤悼弥深。
张佩纶的个体命运、清流的集体运数与大清国易于变脸的政治均在光绪十年发生了转折。马尾既败,张佩纶为众恶所归,声名狼藉,朝士切齿,人们认为“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最终在朝野舆论的弹劾下,张佩纶戍边张家口等地三年,成为“朝是青云暮逐臣”的失落人。释戍后,北京居所已经变卖无法回京,也无脸面回京,踌躇之时,洋务大佬李鸿章向其伸出援手,安排其到天津的北洋大臣幕府。张佩纶又有了“淮戚”的形象。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推测:“马江战败,丰润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近代名人小传》也称张佩纶与李鸿章婚姻成事的原因也是因为马江战役:“佩纶初数弹鸿章,鸿章以五千金将意,且属吴汝纶为介,张李遂交欢。及闽事败,实由于鸿章,至是乃以女妻之。”
事实果然如此吗?李鸿章因马江愧对而许亲,确否?事实上,人们混淆了政治和生活的边界。张佩纶是李家之婿,在李家往往是闭口不谈政治。张佩纶的最后一次婚姻——入赘淮门,使其招致时论打击,也最终使其失去政治参与热忱,远离政治,最终以诗人终老。两家结姻不像舆论所议的突兀,而是与两家的世谊关系和李鸿章长期的生活庇护有关。
在御史台任职时,李鸿章曾赠张佩纶旧乘马车,就戍时缺资的张佩纶卖车以充资用,将马留在京师,但是无力资养,于是将马又归还李鸿章。事实上,早年张佩纶父亲客死浙江时,李鸿章资助其扶灵回籍,并为其撰墓表;庶母李太恭人从苏州迁葬丰润老家,李鸿章又资助白银千两作为营葬之需,张佩纶称“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这是多大的恩情,而这一切早期均得于李鸿章与张父早岁在剿太平军时的“并马论兵,意气投合,互相激厉劳苦”之谊。后半生的李张关系则有政治因素掺入,自称阅人无数的李鸿章为何着力赞助,与张佩纶的关系则直接影响其余生。张佩纶曾对李鸿章称:“师门父执而知我者,仅公一人。”这是为婿之前两人的师门、父执、知遇关系,但是在政治立场上,此时的张佩纶有独立的政治判断。而终其一生看,无论政治利益博弈如何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变化,李鸿章对张佩纶的支持始终不易。由于政见有别,张佩纶力拒了李鸿章的举荐,保持着清流门面。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李鸿章与张佩纶之间通信六百多封,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沟通,但是张佩纶仍表现出政治的独立性。
光绪四年,居京的张佩纶为李鸿章母亲作寿文。对于与李鸿章的关系,张佩纶也未曾避讳,甚至专门夜请陈宝琛来宅,将所作的《合肥太夫人寿序》一文拿给陈宝琛请正。光绪五年三月初九日,李鸿章甚至登门造访,张佩纶答拜。两人频频书信交流政治意见、家事。年底,张佩纶托李鸿章为其父张印塘拟写墓志。对此,李鸿章称:“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以不文辞?”希望与张佩纶当面再商量。光绪六年二月五日归葬父亲骨骸返丰润途中,在天津李鸿章约谈,询问海防问题。三月返京时在天津至李鸿章衙署,讨论北洋军务,李鸿章也亲自造访其住处,如三月六日上午张佩纶应邀到北洋大臣署拜访李鸿章,下午李鸿章来住处回拜,次日晚上李鸿章又来拜谈,三月十日李鸿章约其到电线房,十一日晚李鸿章来访,十三日、十四日、十六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又来。在天津23天的时间里,两人互访谈话十余次,张佩纶欲返回北京,又被挽留三天。在天津时张佩纶也多与李鸿章幕僚交往,参观大沽炮台、机器局等。李鸿章问其对朝廷大臣意见,张佩纶则称不可妄言天数,但是又建议李鸿章赶快拟奏折上奏,以阻浮议,李鸿章将此事委托于他。李鸿章这次主动邀请丁忧的张佩纶来天津近距离观察北洋军务。此后,张佩纶对李鸿章的称呼也改称为“肃毅师相”,待之以师,尊其为相。光绪六年九月在游历了塞北各处回到北京后,张佩纶又来天津,李鸿章邀谈,这次李鸿章干脆招其到府中居住。
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二十八日,依例丁忧期满的张佩纶起复,又出任翰林院侍讲,十二月八日复任起居注官。因为长期不居京师,张佩纶丁忧间与清流的来往要少于与李鸿章的来往。复任后回到北京则又与清流维护起旧谊。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二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十一月十五日,张佩纶与比自己小十七岁的李鸿章女李菊藕结婚。这种老少配、门第悬殊的婚姻一时间让世人咋舌。局外各种议论纷沓而至。
有人作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东床变西席,不是东西。”
有人作诗曰:“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有人作对曰:“摇尾来北洋,赘婿妻娇嫌夫老;辱国幸身全,欺世饮罪满军台。”
后来有人戏为张佩纶作挽联称:“三品功名丢马尾;一生艳福仗蛾眉。”
有人演绎出小说的情节:张佩纶在李家作菊藕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
有称张佩纶入都会试,李鸿章为主考,发榜后到李宅谒师,李鸿章喜其才华,说:你的才气与我的小女相同。张佩纶即跪地称婿,李鸿章也不能推辞,于是许其婚姻。
这些都与史实大相径庭,其他野史记载多类此,为了更具戏剧化,因此极尽讽刺“淮戚”之意。
张佩纶夫妇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篑斋”之说。李经方旋运动御史端良弹劾张佩纶,获上谕:“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这样,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
对此婚姻,张佩纶非常满意,曾在李鸿章夫人的祭文中表达知遇之恩,称:“光绪十四,我来自边,谤满天下,众不敢贤,夫人相攸,亦具深识,申以婚姻,毅然勿惑,始终无间。”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李菊藕生母赵夫人过世,临终前未有一言,回头看张佩纶“若有所嘱”。再者,李菊藕的才情、相貌无双,《孽海花》称她“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
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笼络的考虑。张李之间的跨代友情似乎持续颇久。李鸿章死后,张佩纶撰《祭外舅李文忠公文》,自称“门生、子婿”,赞其“创二千年未有之宏规,通商、惠工、选兵、厉械,百废俱举”,但是独于外交备受谗谤,受谗谤似与自己身世类。
张佩纶称其父孤军转战,始识李鸿章于庐肥,患难定交。他指出自己是以翰林身份拜谒李鸿章,李鸿章喜故交有后,“乃深责其来迟”,但是两人坐谈天下事时,张佩纶自述自己少年意气毕呈:“年少气盛,侃侃而进危辞,流俗所不能堪者,公虽变色欲起,旋温然而易怡。宾僚燕见,或及不肖姓氏,辄叹赏。其瑰奇东陵道上评骘当世人物,虽盛名或见鄙夷,已而拊吾背曰:子之于我大体相似,然而硗硗者易缺,皎皎者易缁,尚其敛刚锐之气,忍辱负重。”释戍后,李鸿章仍规劝其养晦:“当日若肯耐事,不驻马江,乃无谪戍之累,总由忍辱二字未做到。今愈忍愈辱,何补于事耶。”张佩纶此时并未理解李鸿章点到为止的劝说。戍边之灾,张佩纶明白了“养晦而待时焉”,而此时张佩纶则已“谤满天下”。
光绪十年盛昱评骘当朝人物时,就“力诋张幼樵(指张佩纶)一‘巧字”,指斥其政治的投机性,翁同对赋予张佩纶“巧”字深以为然。之后,为人诟病的清流张佩纶最终入淮系李鸿章幕、赘淮系为婿,被视为政治投机性的表现。在天津寄居篱下的生活,张佩纶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甲午战争中绝口不论兵事,唯一能够为李鸿章做的是弥合李鸿章与李鸿藻、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很难恢复当年为皇帝开讲筵的气概。对于李鸿章的安排,张佩纶以“非隐非吏”“非主非客”的尴尬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离开督署的张佩纶携家人由水路离开天津,迁居南京七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迁居张袭侯旧园为终隐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七日,在清流与淮戚的尴尬身份中,张佩纶终老南京,时年56岁。
史学界所谓的南北之争、清流与洋务的对立等论断似乎并不能解釋张佩纶的政治圈子,晚清的政治生态也不像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人际状态。
—————————————————————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