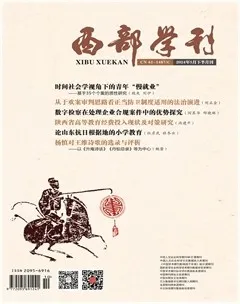对亚里士多德勇敢德性的思考
白朝元
摘要:在古希腊城邦保卫战频发的背景下,“勇敢”一词逐渐成为城邦精神的基本内核和思想家们探讨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第一次对“勇敢”德性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他在批判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基础上转向柏拉图主义,深信勇敢不仅是对外在威胁的克服,更是对内心深处恐惧的征服,并详细论述了五种与勇敢相类似的公民的勇敢、经验的勇敢、激情的勇敢、乐观者的勇敢和无知者的勇敢并非真正的勇敢,彰显了勇敢的真谛。其思想对于当下培育公民道德仍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勇敢
中图分类号:B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0-0154-04
Reflection on Aristotles Virtue of Bravery
Bai Chaoyu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requent defense wars between ancient Greek city-states, the term “bravery” gradually became the basic core of the spirit of the city-states and an important category explored by thinkers. Aristotle, i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firs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idea of the virtue of “bravery”. He turned to Platonism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Socratess “virtue is knowledge”, convinced that bravery is not only the overcoming of external threats, but also the conquest of fears at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and discussed in detail that the five kinds of bravery similar to bravery, namely, civic bravery, empirical bravery, passionate bravery, the optimists bravery, and the ignorants bravery, were not true bravery, which highlighted the true meaning of bravery. His ideas still have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ivic morality nowadays.
Keywords: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bravery
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三贤”之一,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对哲学和其他分支学科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勇敢作为古希腊最崇高的德行之一,其地位极其重要,但对其阐述众说纷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作的伦理学著作,约公元前330年成书。全书共10卷,132章,探讨了道德行为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等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成为西方近现代伦理学思想的主要渊源之一,为西方近现代伦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该书对中世纪和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发展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中,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勇敢”德性思想进行首次系统梳理,对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进行阐释,以此为契机,使伦理学成为独立于哲学的专业学科。在他看来,勇敢是一种习惯性、高尚性、自愿选择性的品质。
一、勇敢德性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来源
(一)勇敢德性的时代背景
古希腊的地势崎岖不平,土地贫瘠荒凉,加上地中海气候导致夏季高温少雨,冬季温暖潮湿,这既不利于农耕经济也不利于畜牧经济。但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当地的文明呈现出与东方大河文明截然不同的海洋文明,海洋性气候极为突出,另外该地区海岸线蜿蜒曲折,造就了许多优良海港,海上商业来往密切。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导致海盗活动肆无忌惮,使得这片土地长时间内充斥着纷争与冲突。基于古代泛希腊地区与地中海周边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城邦分制和多民族交杂以及战争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希腊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通过勇敢的战斗去击退来犯之敌,保护城邦不受侵害。因此,他们提倡勇敢无畏的城邦精神。
一个城邦想要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生存,就要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就需要在与对手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着全民皆兵的状态,城邦的年轻士兵们,经历了严酷的军事训练,一步一步培养出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他们举着长矛,挥舞着盾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目光。面对敌人的冲锋,他们毫不畏惧,宛如钢铁般的防线,稳稳地挡在了城邦的边界。每一个斯巴达战士都清楚明白,他们的背后是家园、是亲人、是无数生活的希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斯巴达的子民逐渐铸就了一座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捍卫着文明的灯火。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和保卫家园信念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勇敢文化传统。
(二)勇敢德性理论来源
按照哲学界的主流观点,将西方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古希腊时期,这一时期哲学家们的研究中心是本体论,侧重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试图找出现实存在的本源、现象构成的本质或者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最主要的是对世界的组成成分的探究。因此,古希腊哲学有寻找本原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其关于勇敢德性思想的阐述受其老师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双重影响。
苏格拉底曾提出的重要思想之一是“美德即知识”[1]。也就是说拥有知识就是拥有德性,拥有了人原有的本性。这个命题在古希腊哲学后期产生了伦理学意义的转向。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勇敢作为一种德性,理应是一种知识。但亚里士多德否认了这一观点,这种将德性与知识混同起来有失偏颇,两者不能混为一类。在把德性等同于知识后,消除了灵魂的非理性因素,也就等同于排除了人的激情与性格。另外,知识不是德性的充分条件,一个人拥有知识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德性。亚里士多德强调区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理论知识是不探讨实用性知识的,如存在之存在“存在之存在”:“存在之存在”是哲学上的存在本体论问题,即探究存在本身的本质和特性,可以理解为探究存在的本质和特性,即研究存在是什么、它的本性是什么、它的存在方式如何等问题。的经典问题,而实践知识则集中于研究人的道德活动。西方哲学中首先系统提出实践观点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将人的活动分成理论、实践、制作。其中实践是一种实际行动,是一种实现个人的善的道德活动,它还包括实现城邦之善的政治活动。实践依据明智的理性原则即实践智慧,去思考与人相关的具体可变的事物,就本质而言是在道德的引导之下,去实行一种非技术性的道德活动。勇敢作为一种德性,应归属于实践知识范畴,而“德性即知识”中的“知识”则更偏向于理论知识,在两者中间画等号是亚里士多德所不认可的。
亚里士多德在否定苏格拉底后,投向了柏拉图的怀抱。在《理想国》中,勇敢则被认为是一种能力,即灵魂的不为危险的驱使而始终保持正确的逻各斯的能力[1]。亚里士多德在接受柏拉图观点的同时,深信勇敢不仅是对外在威胁的勇敢,更是对内心深处恐惧的征服。也就是说,只有在勇者的内心深处,才能真正超越世俗的困扰而勇往直前,敢于直面生命的苦难。这种内在的勇气,是一种超越肉体的高尚境界,可以塑造出真正伟大而不可动摇的灵魂,是一种卓越的品质。谈及品质,这和我们现代汉语意义上的品质含义有所不同,它代表了我们与他人情感之间的正面或负面的联系。比如,当我们沉浸在适度的悲伤中时,我们实际上是与悲伤的情感建立了良好的聯系;在感情的天平上,适度的悲伤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发泄。而当我们感到无论是过多还是过少的悲伤时,我们都可能与这种情感建立不良的联系。
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勇敢德性
(一)勇敢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划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两类,两者对应灵魂中的服从理性和拥有理性两部分。”[2]其中,伦理德性的获得必须要从幼儿时期就开始培育,要经历多次勇敢的事情,逐渐形成个人的习惯,从而培养起勇敢的品质。亚里士多德把勇敢认定在战斗的环境中,濒临死亡却仍镇定自若,在战斗中用生命去护卫城邦。他还认为,勇敢具有长期性,不能间断。只有长期保持这种习惯才能说一个人是勇敢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十年前很勇敢现在却很懦弱,那他依旧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因此,勇敢并不只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提及的文字概念,而是一种经过长期实践,不断培养并持续保持的一种习惯。一两次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只有在每次面临突然出现的危险时,依然可以做出符合勇敢的行为举止,才是真正的勇敢。
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勇敢时认为:“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3]这就是说,“勇敢者并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有着适度的畏惧。”[2]在适度的畏惧中,人们找到了对抗恶的勇气,勇者会显得更加坚毅,能直面内心的恐惧,从而更好地超越困境。因此,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勇敢的人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得住所该经受的,也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1]。因此,勇气十足的人通常会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恐慌和自信。总的来说,勇气并不是毫无畏惧,而是在面对正确的事物时能展现出适当的恐惧感。人们在追求勇敢的道路上常常陷入对自身能力的怀疑,然而,正是在这种怀疑中,他们才找到了前进的动力。勇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每一次挑战中重新定义。当我们学会接受恐惧,并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时,勇气便得以涌现,帮助我们跨越种种障碍,走向光明的彼岸。以上的叙述体现了勇敢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以“高尚”为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无常的人生中,真正的勇敢并非仅存于死亡的阴影之下,真正的英雄也并非总是战胜死亡,他们是在生与死的边缘,用无畏的灵魂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因此,勇敢意味着只能在英勇的战斗中高尚地死去。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的战士的危险性是最大的,他们肩负着承载历史的责任,每一次挥洒的汗水都将成为城邦的坚实砖瓦。在战场的尽头,是荣誉的光辉,是城邦的安宁。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战士是当之无愧的最高尚的人。
至此,亚里士多德关于勇敢的定义已经清晰,我们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勇敢的阐述是具有革命性的。首先,他表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说明了勇敢的定义,即勇敢的人并非毫无胆怯,而是将畏惧化作前进的动力。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并没有关于勇敢德性的系统且规整的理论,而亚里士多德对勇敢德性的总结不仅为后人对道德德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体现了古希腊人对美好德性的追寻。其次,对德性的研究也开创了伦理学的先河,使得伦理学成为独立于哲学的人文科学,更好为人类文明服务。再次,他解释了怎样做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敢。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对勇敢解释仅停留在书面意义上,并没有强调其实践意义,但亚里士多德突出了究竟怎么样做才是真正的勇敢。这种由强调理论性转变为强调实践性的范式转换,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方向的转变,使得古希腊哲学脱离了原有的局限于本体论研究的框架,用伦理学的方式拉近了哲学与人的距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勇敢德性的理论。
(二)其他五种勇敢
那么,为什么某些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它们与真正的勇敢区别何在呢?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区分出五种与勇敢相类似的勇敢,分别是公民的勇敢、经验的勇敢、激情的勇敢、乐观者的勇敢和无知者的勇敢。”[4]亚里士多德对这五种勇敢做了详尽分析,它们看似与勇敢相似,但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实则与真正的勇敢有所差异,对五种类似的勇敢进行分析解释,有助于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
“公民的勇敢”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最像真正勇敢的勇敢。那么,公民的勇敢和真正的勇敢二者的差异性在何处呢?答案在于自愿性。勇敢是一个人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每一次在危险的情况下都能自主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勇敢。而公民的勇敢是出于一种被迫状态下和自身荣誉感形成的“类勇敢”,它不是主体发自肺腑、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无法成为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士需要的是内心的力量,而不是被迫的束缚。真正的勇敢是在面对恐惧时的选择坚持,而非被迫从事。这样的勇气源于内心的信念和意志,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经验的勇敢”是亚里士多德通过士兵的例子总结得出的。例如,城邦的职业士兵与城邦雇佣兵的区别,职业士兵别无选择,只能拼死战斗击退敌人,保卫城邦不受侵害;反观那些雇佣兵,他们在战场上并未选择撤退的原因在于,他们深知敌我之间力量悬殊,并认为凭借自己过去的战斗经验能够有效地击败对手。因此,他们会根据不同情況作出相应的反应和策略来避免被对方抓住战机而导致自身伤亡。此外,雇佣兵本身装备齐全、训练精良,并且擅长击败敌方军队。这种勇敢基于经验的累积,也并不是真的勇敢。
“激情的勇敢”也无法被看作是真正的勇敢。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假如一个人在大街上遭到犯罪分子抢劫,他在情绪高涨的状态下将对方击倒,但这样的行为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这样的行动往往会使对方产生恐惧从而导致受伤甚至死亡。实际上,这只是人们在极端环境下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它源自愤怒的冲动。这种无意识的行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达到一种高尚的目的,因此,这种基于情感和本能的勇气并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勇气。
“乐观者的勇敢”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勇敢。所谓乐观,是对事物的未来发展抱有积极向上的态度。但是乐观并不意味着是对事情发展持有正确且合理的分析,有时候属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侥幸心理。因此,在真正勇敢定义的对比下,这也不是真正的勇敢。
“无知者的勇敢”是一种在无知状态下的行为,即没有认清现实,盲目无畏地做出错误的决定。无畏的行为看似是一种勇敢但本质上是无知,并不是真正的勇敢。而且,“盲目的无知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就像《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例子一样:阿尔戈斯在战斗前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斯巴达,而斯巴达的英勇善战是人尽皆知的,所以结果可想而知。”[5]
三、对勇敢德性的新解读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勇敢”只能发生在突发的危险中,而不是在已经知道的或自然的危险中;是出于内心的荣誉感而不是强制性、追逐利益或担心耻辱;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而非冲动、盲目或无知,是以此做出高尚选择的一种道德品质。我们可以总结为:“勇敢就是在临近死亡的突发危险中,在理性情感的驱使下,做出崇高选择的一种品质。”[4]
以上是亚里士多德对勇敢的理解,笔者曾将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中的第一实体理解为一种关系集合体,同样本文认为,也可以将勇敢这种难以理解的词汇转化为通过其他词汇间接理解的方法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勇敢,大多数是通过勇敢的行为来表现。勇敢的行为与勇敢其实是一种表里关系,勇敢的行为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有时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的。比如,看到孩子掉进井里去施救,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防暴警察对抗恐怖分子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则体现了社会关系;在偏僻的山路行进却碰到迅猛的野兽,与其对抗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人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物,同时,人不可能不与自然发生关系,无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人都必须依赖自然。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它本身就是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集合物,因此,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也是关系的产物。所以,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勇敢:勇敢行为是一种关系的集合体,因为勇敢的行为与勇敢是表里关系,所以勇敢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关系的集合物。勇敢是通过各种关系体现出来的,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关系。这样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思维去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也有利于培养创新性哲学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四、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变得越发冷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仿佛被无形的隔阂所阻拦。在这个“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道德和情感仿佛成了稀缺的资源,爱心和关怀貌似也变成了奢侈品,人们逐渐丢失了曾经的奉献精神。“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古希腊人的高尚道德观念,回想古人非功利的生活态度。”[6]在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需要下,公民必须提升道德意识,超越功利,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价值,重新定义人生的高度,进而保证社会可以健康向上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妍.亚里士多德“勇敢”德性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9.
[2]彭曦葶.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勇德[D].吉首:吉首大学,2020.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
[4]张妍,赵昆.亚里士多德勇敢德性探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9-12.
[5]戴素芳,张家海.论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2(6):50-54.
[6]宋作宇.亚里士多德论“勇敢”:德性伦理的研究视角[J].玉溪师范大学学报,2004(9):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