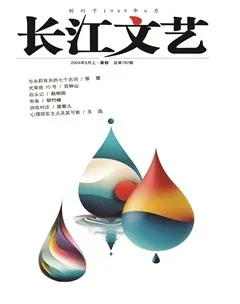无声的青春漂泊在“存在”的河流上
傅逸尘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从乡土叙事向城市书写的大规模转移,使得中国文学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70后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小说创作,覆盖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城市青年乃至更广泛人群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疑难做出了正面回应,亦为21世纪的中国小说提供了新质的文学经验。在70后作家中,张楚的小说总给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的是他对日常生活经验细腻而准确的捕捉、强大具象的写实能力,陌生的是他对青春、人生、命运的描摹和想象总伴随着跳脱公共价值判断的独异思辨。不随波逐流,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姿态甚至是反向思维的定力,这使得张楚的小说在文本形式、叙事方法、情感结构、思辨角度等层面,内蕴着一股先锋的姿态与冲动。
或许是因为作批评的缘故,读完张楚的中篇小说《与永莉有关的七个名词》,我想到的第一个概念便是“底层叙事”。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以及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底色可以说是这一文学思潮的基本元素。兴起于21世纪初年的“底层叙事”,确曾打开了一扇理解、认识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窗口,那种城乡二元模式下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冲突甚至对抗,将某些压抑已久的社会矛盾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令人触目惊心,也感同身受。然而经过二十余年的延续与积淀,“底层叙事”不再单一与纯粹,而是变得有些含混与暧昧。对现实生活的负向解构、对失败青春的夸张渲染、对人性下限的反复试炼使得“底层叙事”陷入了“为了苦难而苦难”的怪圈。部分70后作家在这种“形而下叙事”的闭合回路中彼此模仿,也重复自我,作品的气象、格局和境界亦越发狭窄逼仄。我无法想象“底层叙事”还会延续多久,会不会有新的思潮取而代之,因为这几乎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除“现实主义”之外唯一持续发展的文学思潮。我便希冀着它能有所变化,或者提升,以至于将来留存下文学史意义上有价值的经验。怀着这样的心绪,试图发现某种新质,便成为我阅读《与永莉有关的七个名词》时的一种期待。
张楚以高度空间化的结构方式,讲述了农村女青年郭永莉以及与其关联的一组人物,二十余年间的苦难遭际和多舛命途。“七个名词”表呈着七重空间,人物在这些空间中生活与存在。从出场时的高一学生,到十六七年后的北漂者,郭永莉经历了七个空间的转换。她成长进步了吗?她的思想性格改变了吗?没有,至少没有明显的迹象。张楚不想写某个人物的成长,而试图呈现一众人物的生活与“存在”状态。郭永莉既是叙述的线索,又是勾连他人的环节。当然,她也是这些“存在”空间的主要人物。昆德拉认为,小说家最巧妙的艺术就是通过构思,把不同情感空间并列在一起,然后通过每一情感空间进行“存在”的追问。张楚用七个表达空间的名词,为郭永莉及一众人物的“存在”进行“编码”。七个名词既是一种叙述策略,也是一种结构方式。
最初改变郭永莉人生的空间是“屋顶”。郭永莉和郭亮、肖恩慧不但一个村,还都在镇上的中学念书。郭永莉和肖恩慧学习上要比郭亮好些,尤其是肖恩慧,成绩更好。有年夏天,郭亮约上郭永莉和肖恩慧上房顶去吃自己炖的排骨,还拎了啤酒,就都喝多了。郭永莉醒来时发觉郭亮的手搂着她的腰,这是她跟郭亮未来关系的重要暗示。而郭永莉随后的思想——能跟他们在屋顶上坐一辈子也挺好的,则象喻了她的情感结构与精神格局。小说后面的情节证明,离开家乡十六七年后,她也没能真正提升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境界。
决定郭永莉人生或者说命运的是在学校里的“水塔”上。当郭亮将郭永莉扑翻,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郭永莉人生的根本性转折在于,当双方家长对婚事达成共识时,郭永莉居然没有反对。她的性格存在缺陷,遇事没有自己的主意。用郭亮的话说,郭永莉脑子笨点;用郭永莉母亲刘兰英的话说,看上去傻乎乎的,心也宽,万事都不入眼。所谓性格即命运,用在郭永莉身上实在是再恰切不过了。随后的一个事件对郭永莉而言就不是性格的问题了,而是她的人格与精神的缺陷,她潜意识里对家乡的逃离也许与此相关。面对保卫处老王对郭永莉的非礼,肖恩慧出手相助并最终因此被开除。在如此涉及女性尊严与人格的严重事件上,郭永莉最终选择了妥协,没能挺身而出。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在他们中间转动。
怀孕、生子、休学、错过高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在家哺育孩子,随后的故事里郭永莉的命运已然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高考成为她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也是心底最大的痛。离家出走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意外的是郭永莉竟是被長途车司机误当作乘客而推上了去北京的客车,稀里糊涂、纯粹被动地开启了北漂打工的人生。这是一个更大空间的转换,意味着人生新的机遇或可能。随后,张楚对郭永莉的北漂人生展开了具象写实,这种写实不仅关乎日常生活、物质世界,还牵系着人的内心、精神和灵魂。张楚的写实并不基于郭永莉成功与否的逻辑,而是在北漂新的空间里,她的生命“存在”彰显出了更为深重的悲剧意味。
郭永莉最先遇到的是同在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的郝丽梅,俩人住在饭馆老板租的“阁楼”上。郝丽梅生活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她的理想是当一名企业会计。而此时的郭永莉却是茫然无措。此前她是头蒙了眼罩的驴子,被人牵着走,倒也省心,如今牵绳子的人没了,眼罩也摘了,却委实不知道往哪里走了。郝丽梅与郭永莉构成巨大的反差,她是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然而这种粗犷直爽的性格也间接使郝丽梅殒命于一场没有破案的车祸(不能排除郝丽梅因帮郭永莉出头而被人报复致死的可能)。此后,郭永莉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郝丽梅。那个曾经的郭永莉被郭永莉自己从人间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为她而死”的郝丽梅。
身份替换后的生活并不平静,煎熬的日子里,已更名为郝丽梅的郭永莉处于惶恐之中,仿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无比焦虑地等待着行刑日的来临。她还去了郝丽梅的老家,让自己变成了身份证意义上的郝丽梅。何以如此呢?我想,一是她意识到了郝丽梅之死与自己有关,她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郝丽梅。二是郝丽梅的敢爱敢恨,勇于面对任何事情的性格与精神对她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虽然她没有明确这样的态度,依赖心理一定是有的。郭永莉在焦虑、惶恐不已的时候,望到了镜子中的自己。或许郝丽梅并没有抵达另一个世界,她的魂灵跟郭永莉的魂灵住在同一具躯壳里。但问题是,现实中郭永莉缺失的正是郝丽梅所具有的。那么,郭永莉潜意识里渴望自己能像郝丽梅一样?换言之,郝丽梅与郭永莉的关系,似乎构成了拉康所论的自我“镜像”。如此说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吊诡的哲学与心理学命题中,郭永莉居然有着深刻而清醒的感悟,这反而让我不能不感到些许的惶恐与焦虑。小说看似写的都是现实生活的自然流态,但这里,在近乎傻笨、愚钝的郭永莉的惶恐与焦虑中,张楚却进行了整篇小说中唯一的一次形而上思辨。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可能才是小说最核心的思想与主题——只有在镜像中,人才有可能认知或实现我不是我。也就是说,郭永莉渴望镜中“自我”显现出的不是郭永莉,而是郝丽梅。
小说中的人物,除了开头处试图非礼郭永莉的老王以外,没有什么人做过明显的错事,更别说是坏事,然而个体生命被剧烈变化的时代碾压、抛弃的漫长过程,在张楚笔下丝滑得令人无感、昏昏然令人窒息、无声到令人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对时代的疑难、反抗、妥协,对自我的认知、寻觅、救赎构成了小说的核心价值。时代的某种“共同的精神”或者早已形成共识的价值判断,对小说内部“孤独的个人”构成了威压和伤害。在各自情感结构的深处,郭永莉与郝丽梅早已超越了一般性的朋友关系,互为灵魂告解、救赎的镜像,却并不自知。郝丽梅死后,其男友岑亚楠曾经对郭永莉有过暧昧的试探。两个孤独的青年,承担了太多超越年龄的负累,也隐藏着太多无法言明的心事。两个孤苦灵魂间的互相吸引和抚慰,苦涩、突兀,却也掀起了略显温情的命运暗面。小说经由郭永莉和郝丽梅这样一组意味深长的人物镜像,传递出疑难和反抗带来的生命痛感,寄寓了作家复杂纠结的情感以及对时代、现实的总体性思考。
郝丽梅应该是郭永莉的新生,于是她开启了自我救赎,在两个三年里,先后获得大专和本科自考文凭。这或许是她凭借自己的学习能力触碰得到的社会角色的天花板了。可惜的是,没有企业肯聘用她当会计,人家甚至觉得她可笑。此时已是北京奥运会的第二年,时代已经大变了,她的所有努力都被抛到了时代之后。问题在于,她没有能力反思,现实中的自己与飞速发展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因此,她才会希冀着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生。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与时代的差距仅仅是一张文凭。这就有了一点祥林嫂的味道了。命运在拐过一个戏剧性的大弯之后,郭永莉终于回了趟老家。村子几乎没有变化,只是父母都已过世,仿佛她不是离开了十八载,而仅仅是一个昼夜。
小说结尾处,作为大学宿管员的郭永莉偶遇了她的儿子。郭永莉心中的痛苦与激动可想而知,她的嘴巴翕合了几次,她以为自己在说话,但她和儿子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实际上,她没有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就如同她“被动”的青春与命运,被他者、被婚姻、被意外、被愛情、被灾祸、被时代裹挟的她和他们,为滚滚向前的时代增添了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小小注脚。无声的结局,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在张楚看来,此时用百感交集,甚至万感交集恐怕也难以描述郭永莉的心境与情感了。
十八年,生命的一个轮回,郭永莉的生命与存在是一个时间与空间合谋的空转吗?她收获了什么呢?是曾经抛弃了的生活与儿子?是苦苦煎熬六年换来的那张被时代遗弃的文凭?是那些或因为她,或为了她,或有因果关系,或偶然事故而死的人们?小说于无声处戛然而止,我却不能不思考一个近乎残酷的问题:在“七个名词”后,郭永莉会拥有未来么?
在中国的乡村,类似的生活状态并不罕见。如果仅仅从苦难艰辛的角度理解这部小说,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困扰郭永莉的是世俗之外的精神困境,她始终没有获得一种存在感、一种主体性的觉醒、一种生活与精神的自由。即使付出青春与生命的代价,却终不能获得,回到人生的原点是出于无奈,饱蘸着宿命的轮回感。小说无声的结尾,让我陡然生出无限的感慨与怅惘。郭永莉翕动着嘴唇,真的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么?或许,时代转圜后的回响、被遮蔽的个体生命的声音,已然炸裂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了。
以往的“底层叙事”,小说家的笔力或者叙事向度,主要还是集中于生存境遇中的苦难与艰辛、命运的多舛,以及心理的焦虑与情感的漂泊,普遍呈现为一种形而下的情势,甚至是一种苦难的泛滥;为苦难而苦难,缺乏对苦难本身的超越,更谈不上思想、哲学与精神的高度。《与永莉有关的七个名词》也在书写苦难,张楚甚至让已经跳脱世俗价值与伦理的女青年郭永莉重归生命的原点,但小说没有囿于“底层叙事”的惯常逻辑,而是近乎残酷地让女主人公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困境。她的逃避、躲藏、觉醒与挣扎,尤其是以她为表征的这一代人,对自身社会处境、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感受与体察、叩问与反思,尽管从头到尾都处于“被动”而不自知的状态,却为“底层叙事”注入了一种新质,凸显了一重新鲜的叙事向度——即对主体精神与自由困境的觉醒与挣扎。这种觉醒与挣扎,对张楚而言,包含着小说介入生活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也鼓荡着变革和创造的激情。
责任编辑 喻向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