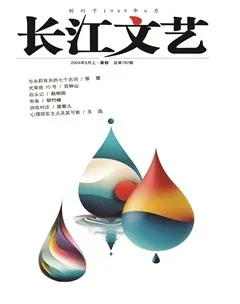风从海上来
黄大刚
一
少年早上上学经常手忙脚乱。少年在县城读初中,骑单车要半个小时。当日头浮出海面,霞光抹红门前的竹梢,少年就放下饭碗,嘴里还嚼着食物,匆匆推着单车出了家门。
村口,江爹拄着苦楝树枝做成的拐棍,早候在榕树下,手中捏着一块钱。少年到了他跟前,也不刹车,伸手接过钱,塞到口袋,什么话也不说,抬起屁股猛力踩着脚踏。
少年中午放学回来,江爹还坐在大榕树下的石板上。
少年发现,江爹总是面对那片木麻黄林,目光迷离。木麻黄林那边是大海,海浪翻卷着涌上沙滩,又退回大海的怀抱,日夜不停。少年好奇,这海浪从哪里涌来的呢。海风穿越木麻黄林,带着咸味吹了过来,江爹如入定般,眼皮缓缓地合上。
少年小时调皮,一看见江爹关上眼皮,兴奋招呼旁边玩耍的伙伴,轻手轻脚往他的帽子上堆小石子或者撒树叶,往他的布袋里放小青蛙,有时还把他的拐棍藏起来。江爹发觉,扬手起身要打人,少年和伙伴一哄而散,跑出十多步外,停下来,扮着种种怪相,跳着脚喊叫:“来呀,来打我呀。”江爹却不搭理他们,抖掉帽子上的小石子,掏出袋子里的青蛙,把手撑在好腿的膝盖上,拖着残腿,径直把少年他们藏的拐棍找出来,抻平衣服,撑着拐棍,一点一点向家移去。因捉弄过江爹,经过他身旁时,少年提心吊胆,时刻做好逃跑的准备,但江爹似乎已把少年的捉弄忘得一干二净。一次,少年把青蛙放到江爹的布袋时,不经意发现江爹浮肿的双眼露出光芒,少年吓得手一缩,稍停一会儿,江爹没有反应,少年慌慌地又把小青蛙往袋子里丢,转身跑了好远,才敢回头。
少年把报纸在江爹耳边轻轻一抖,江爹的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放学啦。”江爹嘟哝着,接过报纸,戴上老花镜翻读起来。
“一个农村的糟老头,每天看什么报纸,还要多花一块钱,嗤。”少年撇撇嘴,带着嘲笑,奔回家安抚已饿得叫了半天的肚子。
每天都要给江爹买报纸着实让少年厌烦,但少年拗不过奶奶,奶奶气得直喘粗气,“你这小崽子,竟敢说这话,要不是江爹从南洋带回阿公的侨批,你爸早就饿死了,从哪里出来你。”
少年最怕奶奶生气,奶奶一生气头就晕,有一次软在地上,少年慌得四处呼喊救命。奶奶说得多了,勾起了少年的好奇。
“侨批?奶奶,什么是侨批啊?”
“我们这里把信叫做批,侨批就是像你阿公那些闯南洋的华侨寄的信,这些信啊,既是家书,也能寄钱银。我们家还保留着你阿公寄的侨批。”
“奶奶,寄钱不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吗?”少年问。
“你阿公下南洋那时候,哪里有什么银行和邮局,寄钱都用这种侨批。”
奶奶从箱底翻出一封侨批递给少年,侨批的红色已被时间漂洗得发白,有蛀虫留下大小不一的小洞。红色的条封上写着收件人的姓名,几行字浮在发黄的信纸上,“我于九月间接到一函,阅信之后重重泪,悉知其生得男儿,家中大小各得平安,方才安慰,今托水客代带光银20元,望母亲自己调理好身体,安置孩子去学堂读书。”
少年扫一眼,便把侨批还给奶奶,不以为然地说:“就他那个样子,哼,都追不上我,还从南洋把那個什么批带回来。”
“可别小看江爹,江爹那时可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水客,侨眷见到他就如见到了亲人那样激动。”
“水客?水客又是什么?”少年不解。
“就你的问题多,”奶奶用食指点了一下少年的额头,想了想,“就是像江爹那样专门替人携带侨批回乡的,可能经常在海上漂来漂去吧,大家都叫水客。”
奶奶的话少年似懂非懂,可他很快便当成耳边风。
奶奶不但让少年给江爹买报纸,还经常从鸡窝里捡出鸡蛋,从菜园里拔出时令蔬菜让少年给江爹送去。
江爹一个人住在村头一间小屋里,屋子虽小,但收拾得干净齐整。少年还没走到江爹家,隔老远就闻到“歌碧黑”(方言,咖啡)的香味,进屋一看,江爹正用纱布过滤“歌碧黑”的渣,抬头见到少年,便招呼少年坐下,拿出一个精致的杯子,倒了一杯,欣喜地说:“亚三,你真有口福,来,尝尝。”少年皱眉,连连摆手,“我不喝。”江爹直起身体想了想,手轻轻拍了一下脑门,从五斗橱柜里翻出牛奶和糖,倒进杯子,又用匙子细细地搅匀,“这下好喝了。”江爹如完成魔法,成功地拍了拍手,把咖啡再次端到少年的面前,少年浅浅地呡了一口,果然不苦了。少年见江爹不放糖也不加奶,指着咖啡问:“不苦吗?江爹。”“哈,这样才能喝到‘歌碧黑的原味,不过,谁开始都喝不惯,我开始也像你那样。”少年喝着咖啡,目光在屋内睃巡,停在了墙壁上挂的那柄发旧的黑雨伞和那个大得有点离奇的竹篮上,问:“阿公,听说你当过水客,给我讲讲水客的故事好吗?”
“咳,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啥。”江爹摆了摆手,端起“歌碧黑”呷了一口,又说:“不过,如果不再给你们讲讲,到时候我们把这些故事带进土里,真的就没人知道了。”
“听我奶奶说,你是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水客。”少年仰起头看了看江爹,目光被江爹那沟壑般的皱纹烫了一下。
“我那算什么,我给你讲一下我三叔的故事,哦,你应该叫三公。”
江爹把烟点燃,陷入了记忆的深处,在袅袅的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三叔戴着黑色的礼帽,穿着长衫,肩斜挎着布袋,左手拎着一个竹篮,右手撑着雨伞,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三叔还是那么年轻。
二
“三叔认准了,只有去南洋才能咸鱼翻身。
村子虽然靠海,海里的鱼很多,但大鱼都在深海里,摇着小舢板只能在海边捕些小鱼小虾。村后是一片沙土地,贫瘠得连草也长得半死不活,老天爷要是不赏点雨水,地里的庄稼全干成柴火。不要说身单体薄的三叔,就是如牛的壮汉起早贪黑,也不能填饱全家的肚子。不知何时起,这一带村人陆续飘洋过海,到大海的另一边谋食,有南洋客的家庭,时不时递回侨批,日子过得让旁人流口水,家里要是有还没结婚的,媒婆争相上门说媒。
三叔不读学堂后,晚上还点着番油(方言,煤油)灯看书到鸡啼才睡觉,爹娘心疼番油,一上床就把番油灯收了起来。看这破书有什么用?能填饱肚子?能换来钱银?净费番油。三叔抖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使劲儿甩上屋门,融化在夜色中。三叔夜里如夜游神到处游荡,早上日头晒屁股也不起床,任娘喊破喉咙也没动静。爹气得冲进房,掀开蒙在三叔头上的被子。干吗?三叔好像比爹还来气,不去地里干活,哪来吃的? 那活不是我干的,我要下南洋。三叔把衣服搭在肩上,撂下这话,头也不回就走了。
败家仔啊!娘哀嚎一声,如丧考妣。爹气得操起了扁担,浑身抽搐要打人,但最后,重重地把扁担砸在了墙上。
一想到身板单薄、眼睛近视得跟半瞎子无异的三叔,爹娘就愁云密布,长吁短叹。
三叔常常一个人坐在木麻黄林的沙地上痴痴地看着海的远方,海面越远越蓝,似乎比沙滩还高,最后和蓝得如水洗般洁净的天空融成了一片,此时,海浪轻摇,大海温柔得像个小姑娘,可三叔知道,大海不会一直这么可亲可爱,这个喜怒无常的家伙,连在上面漂了大半辈子的老渔夫也琢磨不透她的喜怒哀乐。海面空荡荡的,看不到一只船,连一只海鸟也没有,但三叔知道,他的未来就在海的那一边。
南洋不是走几步就到,或扎个猛子就能上岸,隔着茫茫大海,三叔连南洋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一听说有南洋客还乡,三叔便觍着脸上门,由于没有交情,三叔被晾在一边。一说起去南洋,人家便转移话题,或以种种借口把三叔支出了门,三叔却死皮赖脸不走,闹出不少笑话。
听说姨婆有个远房亲戚从南洋回来,三叔便央求姨婆带他去见面,托姨婆的情面,对方应了下来。
踏上南洋的土地,三叔才发现南洋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三叔四处游荡,寻找活干,那些老板只看一眼三叔单薄的小身板就像轰苍蝇般挥手。语言不通,找不到工作,三叔饿得脚步发颤。听到乡音,三叔如对上暗号般凑了过去,总能得到一些救济,虽然吃不饱,还能撑得住。看到一家写着国文的店铺招人,三叔也跟着排队,管事的从眼镜后抬起眼,拉长声调问:能干些什么呢?三叔拍了拍鸡胸,响亮地应道:别看我矮瘦,力气一点也不小。识字啵?当然识了,一肚子都是字。三叔鼓了鼓快贴到后背的肚皮,管事的让三叔用毛笔写几个字,三叔的小楷工整又好看,接着叫三叔打一通算盘,三叔便留在了店里。
店里卖的是来自家乡的货物,来买的大多是南洋客,遇到讲乡音的,彼此留下名字,得知三叔要随老板到家乡进货,便托三叔递侨批。顺路的,三叔趁购货空隙,匆匆送达。可大多时候不便,留给三叔时间不多,对那些路程较远的,则不敢应承。
没有本地人当水客,寄侨批只得托长岛那边的水客。长岛离我们隔着两个海湾,那边的水客摇着小舢板,走过宽宽的沙滩,穿过茂密的木麻黄林和长着刺的野菠萝丛,走水路还要走陆路,因此,那边的水客要么拒绝,要么提高路费。
渐渐地,三叔联络上了从家乡出来的南洋客。我们那里得有个水客,像头牛劳碌挣点血汗钱银就是想让家里过好日子,我们都不识字,没有个可靠的人当水客,递侨批我们不放心啊。
我曾听乡亲说过水客揩油的故事,有个水客交给侨眷23个光银,面对递过来的光银,侨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南洋客递来只有23个光银吗?侨眷盯着信纸上画的2只狗和2个寺,灵机一动,大哥,我老公寄给我应该是26个光银啊,你怎么只给我23个呢?水客变了神色,吱吱唔唔半天也说不清楚,最后只得补侨眷3块光银。旁人不解,侨眷指着2只狗:狗(方言)就是9,2只就是18,又指着2座寺:寺(方言)就是4,2个是8,合起来不是26吗?幸亏这个侨眷平时贩卖海鲜,会算账,不然就让那水客占了便宜。
三叔用侨汇购买大米、棉花等货物,运回售出,兑换成钱款再送给侨眷;返回南洋时,又换当地的土特产运到南洋贩卖。一来二去,才三年,三叔便在县城建起了一座三层的楼房。现在那条街还叫三楼。
那楼真气派,门前是廊道,擎立着粗大的卷花柱子,楼上飘凸出拱窗,窗台、檐口还有窗楣装饰着精美繁复的花纹,彩色玻璃窗在阳光下跳着迷人的光彩,楼顶立有三角山墙。入宅那天,裕成商行也开张了,那鞭炮,炸得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红色炮屑。”江爹眯缝着眼,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热闹喜庆的场面。“可也有说怪话的,说什么三叔拿侨汇做生意,只顾自个儿的口袋,赚的都是昧心钱。什么时候都一样,树大招风。可说归说,下次递侨批还是找三叔。”
听着江爹这些话,少年也想象着鞭炮连天的情景。
三
“我十九岁那年跟三叔去南洋,到了南洋才知道南洋客光鲜背后的苦楚。”江爹悠悠地说,当年的景象如电影般在他脑海回映。
“下了船,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听到的都是叽哩哇啦不知是说什么的声音,我攥紧三叔的衣角,三叔双手合什,眉飞色舞地跟那些人叽哩哇啦到了一块。三叔告诉我,当好水客,就要学会他们的话语,知道他们的习俗,不然,那些人得知你不懂他们的话,便会动歪点子。遇到困难就向讲乡音的人求助,不管认不认识,只要都讲乡音,便会得到帮助。
端午节快到了,三叔带我走水(行话,递侨批),那些南洋客一见到三叔,便放下手头的活,紧紧地握住三叔的手,憋在心底的乡音如泉水般涌了出來,才坐下,又是点水烟筒,又是端好吃的食物。三叔不抽烟,可也把水烟筒凑到嘴边。三叔介绍道,这是我的侄儿。你的侄儿就是我的侄儿。他们拿起食物往我手里塞,热情得让我难为情。三叔不急收侨批,而是坐着巡村(方言,聊天),说说他们现在干的活,聊聊家里的老人小孩,凡是不好意思提及老婆的,三叔起身前必补上。水烟筒的烟丝燃尽了,三叔掏出红条封和笔写侨批,不识字的,便口述给三叔写,三叔写好了,又念一遍,确认无误了,才装进信封。其实,信纸没写多少内容,倒是三叔口头补充的信息量更大。他们总爱拉着三叔问这问那,三叔脸上溢着笑意,有问必答,偶尔开句玩笑,逗得南洋客露出疲惫的笑容。
在家时以为南洋客多风光,可随着三叔的脚步,我才知道他们大多在乡村或农场里割橡胶,收胡椒,每天扛着农具,日晒雨淋,衣服常带着汗酸味和臭粪味,光着的脚板粘着泥土,比在家乡还辛苦。
不能和家乡比,这里每个月都有现钱。三叔说。
南洋客中要数德叔干活的地方最偏远,两边灌木侵占了牛绳般的山道,三叔拿着镰刀在前面开路,我踩着荒草紧跟在后面,荆棘划花了皮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一个矿区。三叔说,这是周边最大的铁矿。一个大坑的旁边有几排油毡搭成的简易工棚,从大坑挖出来的铁矿石装到矿车,沿着索道骨碌碌向山下滑去。
走那么远的路,就为一个人。我忍不住怨道。
话可不能这样说,只要有南洋客的地方,走水时一定要来问一问要不要递侨批。三叔实了脸。
德叔,德叔。三叔站在坑沿朝一群正弯腰撅腚挖矿的人挥手喊起来。有一个人抬起头朝这边张望,丢下工具,快步走过来。
一个被日头晒得像铁屎一样黝黑,衣服被汗水湿透了的中年男人来到面前,他捣了三叔一拳,爽朗地笑道: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也该挪挪屁股了,这也是人待的地方?
条件是差了点,可工钱高,咱出来就是挣钱。村里的学堂建好了没有?还有围墙?那我再捐20个光银。
德叔,你的钱来得也不容易。
咱出来受罪,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舒坦些。村里的仔不识字不行啊,你看我,就像一头牛,只会干苦力活。要是识字,早坐办公室了。
德叔匆匆把侨批交给我们,又去大坑底下干活了。”
“你说的就是捐钱建我们学校的德叔?”少年问道。因为村里有学校,少年不用像别的村的小孩,要走好长的路上学。少年无法把捐钱给村里修学堂光鲜的南洋客与在铁矿上的苦力划上等号。
“对啊,可惜后来德叔去世后只得埋葬在异国他乡,没有实现他最后的愿望。”江爹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
“三叔归来便是海边乡村侨眷的节日。春节、中秋、端午、清明节这几个大节日,只要船还开,哪怕刮着台风,三叔也会挎着布袋,拎着竹篮,撑着雨伞,穿行在被绿树环绕的村子里。
三叔提前把侨批放在竹篮里,等候在村口榕树下的侨眷一见到三叔,如见到了亲人,侬啊、侬啊唤个不停,欢喜迎了过来。别急,别急,都有,一个一个来,别让我搞乱了。三叔笑呵呵在石板坐下,掏出侨批,念一个名字递一封。侨眷抖着手拆开侨批,抽出家书,神情随着家书的内容起伏变幻,动情处眼泪淌了出来。读罢信,侨眷又反复问了南洋客那边的情况。遇到不识字的,三叔还得先念信,再逐一回答侨眷的问题,没有一丝厌烦。大家都夸三叔脑袋瓜好,那么多人那么多事记得那么清楚。待侨眷平静下来,三叔才依着侨批兑现银钱。双方确认无误后,三叔让侨眷写回批,三叔还要带着这些回批交给南洋客。
牛路村婆的儿子亚海去了南洋,家里破败的土砖房,只有多病的老婆、年幼的儿子和没走几步就气喘如牛的牛路村婆,一家人的生活就等着儿子的侨批开灶。见到三叔,牛路村婆脸上的皱纹就像荡开的水波,搬来凳子,用衣袖擦了又擦。又操起长长的竹竿到门前的椰树捅下椰子,拿来镰刀砍开,双手捧到了三叔面前。才招呼儿媳还有孙子围着三叔坐下。三叔说,阿婆,又不是外人,你那么客气,下次我再不敢来了。
下次不来,我老婆子就到你家吃,你怕啵?
好呀,我带你去南洋吃好吃的。三叔贫嘴。
牛路村婆却没了诳闲话的耐心,急问,侨批呢?亚海的侨批呢?
牛路村婆看着耀眼的红条封,脸上的喜气浮了上来,她把侨批递给儿媳,儿媳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抚摸,侨批的红色浸润到了她苍白的脸上,儿媳又把侨批递给孙子,柔声道:阿侬,阿爸想侬啦。阿侬撕,看看阿爸跟阿侬说了什么,寄了什么。孙子沿着信封的边沿细细地撕出一条纸边来,有的地方还没撕开,孙子越急越慌乱,儿媳几次欲伸手帮助都被牛路村婆拦住。终于把信纸掏了出来,孙子恭敬地递给三叔,三叔清了清嗓门,念了起来。
亚海寄的钱银不多,但足够一家人应对到下次侨批回来。牛路村婆一家都不识字,写回执时,三叔拿着笔等她们口述,她们满肚子的话,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三叔笑了笑,收起笔,说:你们好好想想,过两天我再来。
看着亚海一家欢喜的样子,我的鼻子酸酸的,三叔悄悄踩了踩我的脚。
回国的当晚,三叔把一个红条封交给我,是亚海的侨批,访了那么多南洋客,我记得清楚,没有亚海这个人,怎么冒出亚海的侨批来。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就不在了,从脚手架摔下来,一声不吭就走了,黑心老板把尸体往围墙外一丢就不管了,一帮老乡也闹过,可一闹,警察就过来,毕竟是人家的地盘。三叔声音低沉。
这……我扬了扬手中的侨批。
亚海一家老的老,小的小,老母亲还生病,没有侨批,怎么活。你回去千万别把亚海的情况跟她们说。三叔嘱道。”
五
“当水客最起码得会讲番话。三叔马上教我说些吃饭之类的日常用话,平时和我讲的也多是教过的番话,这样的训练很有效,我很快就能如水般流畅地用番话跟当地人交流。
三叔帶我认识了所有讲乡音的南洋客,知道他们在哪干活,收集、递送侨批就熟门熟路。三叔让我单独走一次水后,大手一挥,你可以出师了。真的把水客的担子交给了我。
我利用收侨批的机会向南洋客打听父亲的下落。我还没满周岁,父亲就坐船向南洋漂去,此后,杳无音信。有人说,父亲染上疟疾在深山不治身亡;有人说,父亲在南洋挣到大钱,在那边住上了别墅,另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过上了乐不思蜀的生活。时光冷了母亲期待的心,不管是生是死,父亲彻底从母亲的生活消失了。母亲把父亲的衣服套在稻草人身上,挑了个日子,放到海水里浸湿,埋在了海边的木麻黄林里。
问了好些人,他们都没有父亲这个人的印象,后来,有个与同乡南洋客一个工地干活的依稀记起有这个人,说是上了日本人运劳工的车。那个人好像在安慰我,补了句,也不那么确定是不是你要找的人。那一刻,我心存的最后一点微弱的光芒彻底熄灭了。
春节快到了,我却没有一丝要过节的喜悦,神经被悚人的时政新闻绷紧。战火同时漫卷了南洋和家乡。有南洋客发动募捐筹款,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南洋客热情高涨,纷纷掏口袋。三叔却不让我沾边,得知我也上街游行示威,如知道我干了坏事般对我发火,你的任务就是做一个水客,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谁都像你那样,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和三叔吵了起来,三叔苦口婆心说要对我母亲负责,还隐含胁迫的言外之意。我对三叔警惕了起来。
毕竟日本人执的是刀把,握着刀刃的民众怎么能对抗得了日本兵,上街游行示威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民众遭到日本兵开枪镇压。鲜血没有让民众畏惧,反而激起更多人的斗志,南洋客悄悄传着日本兵被伏击的消息。火药味越来越浓,巡逻的日本兵一队刚开过去,另一队又接踵而来。街头垒起哨卡,进出都要严查细问。晚上实行宵禁,半夜三更常骇然响起日本兵骂骂咧咧的砸门声。
日本兵加强了码头管控,行李都要打开检查,不少民用轮船不让靠岸,中秋节时侨批已没法送出去。春节一定要走一次水啊,家里人等着钱买阉鸡过年呢。有南洋客找到三叔说。
先收集僑批。三叔带着我联络南洋客。
这小日本不让人活了,唉,给家人报个平安,免得他们担心。说起形势,南洋客满脸气愤,除了骂几句,更强烈感受到家书抵万金。
南洋客把侨批给我时,又递一些钱款给三叔。这不记吗?我指了指三叔手中的钱。这不用记的。南洋客忙说。管好你那些就行了,别那么多话。三叔撸了一下我的头发。
一日,天才蒙蒙亮,三叔就兴奋地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打听清楚了,有一艘客轮运日本人的货物,我们可以搭这船离开。
我们到港口时,轮船前已排起长长的队伍。三叔让我背侨批排在前面,看到日本兵查得那么严,搜完箱子还搜身子,连鞋子也要脱下来检查,一不顺眼就没收。我身不由己地慌乱起来,豆大的虚汗止不住冒出来,好几次想溜出队伍。犹犹豫豫中,流动的队伍把我推到日本兵面前。
一个梳着二分头的翻译把我背的布袋拽了过去,底朝天哗哗把侨批都倒在了地上。
这是什么?翻译用文明棍翻着侨批,厉声喝问。
长官,这些都是帮乡亲带的信。我忙赔着笑脸解释,我听到我的声音发颤。
信?翻译把其中的一封侨批撕开,看了看,又撕开另一封,这是什么信?什么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还有钱款,分明是联合起来跟太君作对。他转过脸,躬着腰叽哩咕噜对那个人中留着黑胡子的日本军官说一通,黑胡子神色立变,八嘎。手一挥,两个日本兵冲过来扭住了我的肩膀。
太君,太君,抓错人了,我真的是送侨批的。我喊着,急切转头朝三叔求救。
三叔却不看我,站着一动不动,好像他不认识我。
在昏暗窄小的牢房里,每次挨过严刑拷打,皮开肉绽的疼痛提醒我,三叔当初带我去南洋当水客是有预谋的。
三叔每次从南洋回来,都给我带迎路(方言,礼物),新奇好玩的玩具,好吃的糖果饼干,过年的时候,还给我买衣服。接过三叔手中的迎路,我羡慕道:三叔,南洋真好。想不想跟三叔去南洋?当然想了,三叔,什么时候带我去南洋啊?我欢喜得蹦了起来。等你长大了再说。三叔用手抚了抚我的头。那一年,三叔还这样说的时候,我站起来跟三叔比个子,我高出了三叔半个头,三叔,我还没长大吗?好好,过完这个生日,三叔就回来带你去南洋。
侬啊,去南洋可不像你想的那么好,我们这一带去南洋的,都有一肚子泪啊。母亲颤着声吟唱起歌谣:一船泪水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始过七洋洲,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时能回还。
歌谣如咒语般让母亲心慌意乱,身体发抖,似乎看到儿子受了罪,泪水涌了出来,可我一点也不动容,反而厌烦母亲胡思乱想。
我知道母亲多在乎我,孤儿寡母日子虽过得艰难,可不管多苦多累,母亲一见到我就脸露笑容。刮台风的夜晚,母亲把我抱得紧紧的,我能感受得到母亲轻微的颤抖。
三叔提出带我去南洋后,母亲就把三叔视同仇人,三叔再拎着一个鼓鼓的袋子跨进我家的门槛,还没掏出袋子里的麦乳精、点心还有布料,就被母亲丢到门外,别来害我儿子,母亲发疯般挥着手喊道。
阿妈,你就一百个放心,现在跟以往不一样了,有三叔带着我,怕什么。我开始还耐着性子安慰母亲,可母亲神经质的唠叨,让我一见到母亲就远远地躲开,连饭都不想跟她同桌吃。
说不动我,母亲只得求三叔,阿叔,亚江大了,听不得我的话,你劝劝他,别走他阿爸的路了,你就劝他一下吧,求求你了,我给你下跪了。母亲说着,膝盖一折,就要跪下,三叔手快,一手挽住了她。
阿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把心好好地放在肚子里吧,我把亚江带在身边,跟我一起做水客,每年来回好几趟,你们母子俩还可以经常见面嘛。
可是,亚江还是个孩子啊,再等几年吧。母亲眼巴巴地看着三叔,一副可怜的样子。
阿嫂,亚江长大了,当年我下南洋,比他还小一岁呢,你看,亚江都长胡子了。阿嫂,你也清楚,咱这地方,不下南洋,啥时生活才出头啊。说实在的,求我带去南洋的人还不少,可我从小看着亚江长大,这孩子实诚、机灵还识字,去南洋,会有出息之日的,你就等着享福吧。三叔打气道。
那,那就劳阿叔多费心,亚江没出过远门,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唉,那地方那么远,那么陌生,说话也听不懂,我真的放心不下呀。母亲用手紧紧地捂住胸口,脸上满是痛苦的神情,她转过脸来看着我,嘱道,亚江,到那边后,一定要听阿叔的话,知道啵?
船头劈开海水,缓缓离开码头,母亲站在岸上,摘下草帽,朝我用力地挥着,好像还喊了什么话,可全被发动机声湮没了。我心中的欢喜瞬间被海风吹跑,难受鼓胀得眼泪淌了出来。我緊紧地抓住船的栏杆,踮起脚跟,朝母亲的方向眺望,母亲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连码头那三棵高高的椰子树也看不到了,四周唯有茫茫一片水云天。
三叔在不远处站着,没有走过来。”
六
“日本鬼子真歹毒啊,简直就是从阴间跑出来的恶鬼,你看,好好的腿给打成了这样。”江爹抚摸着残腿,愤恨还在脸上激荡。
“日本兵对我上刑,手段的残忍,你可想象不出来,现在,我还经常做噩梦。我除了送侨批,别的一点也不知道。或许日本兵也了解水客送侨批的情况,盘问了我周边的人,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便把我丢出监狱。
侨批在我手中被没收,一想到南洋客的血汗钱还有侨眷期盼的眼光,我要是不把这些侨批兑现,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了。
凭着记忆,我把侨批的钱款记在一张牛皮纸上,虽然那数目如山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时常给自个儿鼓劲,只要拼命,总有还清的那一天。
兵荒马乱,城市空荡荡的,找工作很难,只要能挣到钱,不管多苦多累的活,我都抢着去干。
战争结束那年,我揣着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凭着记忆敲开了当年寄侨批的家门,可他们告诉我,当年,虽家书没看到,可钱银三叔已给了。”
“三叔把骑楼卖了。”江爹的神情似乎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你三叔呢,后来找到他了吗?”少年追问。
江爹抬起枯竹般的手指往虚空中一指,少年不理解江爹的意思,可他知道那是海的方向,虽听不到涛声,可少年能感觉到风自海上来,他捕捉到了风中飘荡着若隐若现海的味道。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个故乡……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这个名为“风从南洋来”的图片雕塑展已展好几天了,听了江爹的南洋故事,这天放学,少年路过展览馆时,被歌声拴住了脚步。少年刹住单车,走进展厅,一张一张观看灯光下的历史照片,在一长串牺牲的华侨机工的名单前,少年逐个名字察看,虽然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他莫名有一股熟悉感。少年记得江爹曾跟他说过,三公在南洋时专门去学了开车,他想,明天载江爹过来认认,看能否找到三公的名字。
责任编辑 徐远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