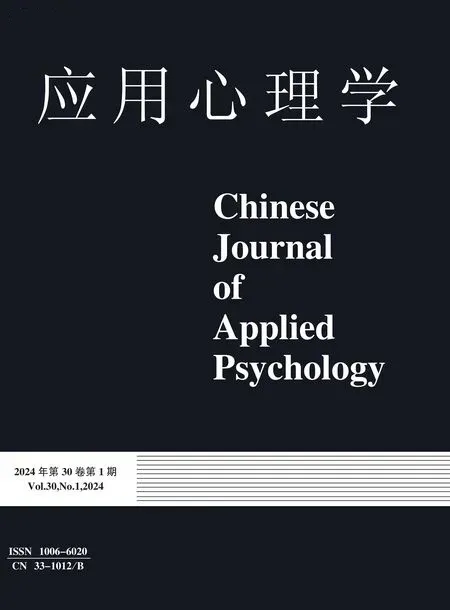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现状及展望*
莫李澄 李宜伟 张丹丹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成都,610066)
1 引 言
人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物种,社会关系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在失去亲人、失恋、被同伴排斥时,常常形容自己“心如刀割”“心痛不已”,这种因社会关系或社会价值受到破坏或威胁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被称为社会疼痛(social pain;Eisenberger,2012)。社会疼痛常带给我们灾难性的情绪感受:约四分之三的人将“失去某位亲友”列为人生中“第一难受”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有过至少一段由失恋引起的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经历;媒体报道的因家庭虐待、校园欺凌而自残自杀的儿童青少年案例层出不穷。社会疼痛会减弱人们的归属感、控制感、有意义的存在感,导致习得性无助和社交回避,进而引发社交焦虑、创伤后应激、抑郁等精神障碍(Durodié &Wainwright,2019;Richman & Leary,2009;Wang et al.,2017)。据统计,社会疼痛是精神障碍的主要诱因,人际危机是精神障碍患者寻求医疗救助时的最常见主诉(Rappaport & Barch,2020;Reinhard et al.,2020;Schilbach,2016)。近年,因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医疗和居家隔离、亲友离世、失业等负性社会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疼痛对全球心理健康的威胁(Brooks et al.,2020;Holt-Lunstad,2021)。
情绪调节是一种可有效消减社会疼痛的应对策略。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我们影响自己情绪的过程,包括我们什么时候产生情绪,以及我们如何体验和表 达 这 些 情 绪(Gross,2015;McRae &Gross,2020)。由于本文的关注点为社会疼痛,后文中提及的情绪调节主要指对负性情绪的下调,即降低负性情绪强度。几十年以来,大量研究在揭示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Etkin et al.,2015;Silvers & Guassi Moreira,2019;Zilverstand et al.,2017)。然而绝大部分已有的情绪调节研究采用国际情绪图片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Lang et al.,1999)作为诱发情绪的材料,库内的负性图片主要涉及高唤醒、低自我相关的非社会事件。社会疼痛作为一种具有社会认知属性的特殊负性情绪,具有低唤醒、高自我相关的特点。已知的在非社会情境发挥作用的情绪调节脑网络在社会疼痛情境下还能完全适用吗?
本文关注围绕“社会疼痛”展开的情绪调节研究。揭示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理论方面,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研究是对已知的、主要基于非社会性事件的情绪调节脑机制的必要拓展,其研究发现可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情绪调节脑机制的了解,促进情绪理论的发展。基于IAPS 的研究往往将蛇、枪支、血腥尸体、脏乱环境等多类负性图片混杂使用,材料的高异质性可能降低情绪调节效果(Morawetz et al.,2017)。与之相比,社会疼痛诱发材料的高同质性有利于在实验中形成高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此外社会疼痛的高自我相关性可增强情绪调节的动机(Nasso et al.,2020)。社会疼痛的这两个特点有望增强情绪调节研究的效力(power),使研究发现更接近情绪调节脑机制的真实面貌。实践方面,研究发现有望帮助临床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疼痛治疗方案。已知情绪调节障碍是精神障碍群体的一个跨诊断特征(Sloan et al.,2017),而人际危机又是精神障碍的主要诱因。围绕社会疼痛情绪调节开展的基础研究,其实验方法和结果发现可直接迁移到临床干预性研究中,为神经调控和神经反馈治疗提供潜在的神经靶点(张丹丹等,2019;莫李澄等,2021),加速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转化,帮助精神障碍患者以及由新冠疫情等原因导致的大量亚临床群体(Brooks et al.,2020),缓解社会疼痛、恢复社会功能。
尽管不少研究者已开始关注社会疼痛的情绪调节,但相比于非社会情境中的情绪调节,我们对社会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了解得还远远不够。本文分别总结非社会性和社会性情绪调节研究的已有发现,分析目前该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并给出具体可行的研究思路,帮助研究者在未来工作中深入揭示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脑机制。
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2.1 非社会性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
本部分涉及情绪调节领域的主要关注对象,即人们对非社会性事件诱发的情绪进行的调节,例如采用IAPS 材料诱发情绪反应后进行的情绪调节。根据Gross 团队提出的情绪调节框架(Braunstein et al.,2017),最典型的两类情绪调节为:自动化内隐和主动外显调节。自动化内隐调节由刺激唤起,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非适应性的情绪进行的调节。主动外显调节需要通过意识启动,同时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监控,在实验室研究中常利用情绪调节指导语来实现(Etkin et al.,2015)。在主动外显调节中,人们最常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是分心、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经典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Gross,1998)认为,分心策略在早期注意分配阶段起作用,它要求个体将自己的注意分配至当前情境的中性方面或分配到无关事件上;认知重评在晚期认知改变阶段起作用,它要求个体对当前的情绪性情境进行重新解释;表达抑制在情绪体验生成后的行为抑制阶段起作用,它要求个体压抑当前情绪的表达(Ochsner &Gross,2005)。其中,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能有效且持久减弱负性情绪体验及情绪相关的神经反应,是值得推广和应用于临床训练的情绪调节策略,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McRae&Gross,2020)。
大量研究表明,情绪调节是自动或主动地利用前额叶为代表的皮层控制系统,去抑制杏仁核为代表的皮层下情绪反应系统的过程(Etkin et al.,2015;Frank et al.,2014;Zilverstand et al.,2017)。自动化内隐调节主要依赖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特别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FC,vmPFC)(Braunstein et al.,2017;Fitzgerald et al.,2020)。vmPFC通过与颞叶皮层、杏仁核和腹侧纹状体的功能连接,自动提取与刺激相关的先验信息,对刺激进行识别和评估,计算和更新刺激的情感价值,从而让个体对刺激的情境进行恰当的反应(Delgado et al.,2016;Hiser& Koenigs,2018;Roy et al.,2012)。主动外显情绪调节需要额外调用外侧前额叶皮层,后者包括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FC,dlPFC)和腹外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FC,vlPFC)(Etkin et al.,2015;Frank et al.,2014;Morawetz et al.,2017,2020;Rive et al.,2013)。其中,vlPFC 是在不同调节策略间(认知重评、分心、表达抑制等)、两个调节方向上(上调、下调)被一致性激活的脑区(Morawetz et al.,2017;Ochsner et al.,2012)。
目前针对情绪调节的大部分脑成像研究都围绕认知重评展开,因此我们对认知重评脑机制的了解也最为深入。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是通过改变对当前情绪情境的解释从而改变情绪体验的认知过程,此过程需要抑制不适当的负性情绪评价,并从记忆中检索出适当的替代解释,同时还涉及目标维持、语义加工等认知过程(Ochsner et al.,2012)。脑成像研究发现,认知重评过程通常激活vlPFC、dlPFC、背内侧前额叶(dorsomedial PFC,dmPFC)、后顶叶、辅助运动区等皮层区域(Buhle et al.,2014;Kohn et al.,2014;Morawetz et al.,2017)。其中,dlPFC 和后顶叶构成背侧注意系统,负责对注意的主动控制,同时dlPFC 在工作记忆中维持多个对当前情境的解释选项;vlPFC 负责从工作记忆中选取与调节目标相符的语义解释对当前情境进行重新评估,随后抑制dlPFC 的神经活动。在这个过程中,vlPFC 和dlPFC 需要有序发挥各自的功能,以确保认知重评过程的顺利推进(Silvers&Guassi Moreira,2019)。至今仅发现一项脑成像研究对这两个脑区在认知重评中的协作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者采用动态因果模型发现:dlPFC 到vlPFC 具有正向功能连接,而vlPFC 到dlPFC 具有负向功能连接(Morawetz et al.,2016)。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功能连接发挥作用是否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同时,如前文所述,以认知重评为代表的情绪调节过程依赖于前额叶控制系统对情绪反应系统的自上而下的调控。然而关于认知重评过程中这两个系统间的连接通路一直存在两种观点(Ochsner et al.,2012)。直接通路模型认为,外侧前额叶可直接影响皮层下区域以实现对负性情绪的下调。例如Wager 等(2008)发现,认知重评过程依赖于vlPFC 分别与杏仁核和腹侧纹状体之间的功能连接。间接通路模型认为,前额叶的其他区域需要通过vmPFC 才能调控皮层下情绪反应脑区(Hiser&Koenigs,2018;Roy et al.,2012)。例如Johnstone 等(2007)发现,vmPFC 在认知重评中介导了vlPFC 与杏仁核的负相关;Steward 等(2021)采用动态因果模型发现,vmPFC 是前额叶调节杏仁核活动的重要枢纽。
2.2 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
与非社会性情绪调节不同,社会疼痛调节领域最早关注的脑区是背侧前扣带回(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dACC)。Eisenberger 等(2003)首次观测了社会排斥激活的脑网络,发现dACC 的激活水平与主观报告的社会疼痛强度呈正相关,推测dACC 在社会疼痛情境下的作用类似于杏仁核等情绪反应脑区,负责疼痛警觉加工(Lieberman & Eisenberger,2015)。 Eisenberger 等(2003)还发现dACC 介导了右侧vlPFC 与主观社会疼痛强度的负相关,提示vlPFC 通过影响dACC 的活动来调节社会疼痛。与该观点一致,后续的两项社会疼痛研究也发现,右侧vlPFC/vmPFC 与dACC/脑岛分别具有负向功能连接(Maurage et al.,2012;Onoda et al.,2010)。虽然社会疼痛领域的不少经典研究都突出了dACC 的重要作用(又如Woo et al.,2014),近年的两项元分析却表明,社会疼痛显著激活的脑区除了前额叶的vlPFC、dlPFC、vmPFC,还有腹侧前扣带回(ventrol ACC,vACC),而非dACC(Mwilambwe-Tshilobo&Spreng,2021;Vijayakumar et al.,2017)。社会疼痛的核心情绪反应脑区到底是dACC 还是vACC,目前尚无定论。
除了脑成像研究,学者们还利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 和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 等神经调控手段,发现无论是情绪的自动或主动调节,vlPFC 和dlPFC 均在社会疼痛调节中发挥着因果作用(Riva et al.,2015;Zhao et al.,2021)。在自动化内隐调节方面,Riva 等(2012,2015)利用tDCS 激活正遭受社会排斥被试的右侧vlPFC,发现tDCS 实验组比对照组报告了更低的社会疼痛强度。类似的,Fitzgibbon 等(2017)利用TMS 证明了dlPFC 在社会疼痛下调中的因果作用。在主动外显调节方面,我们课题组的系列研究发现,当利用tDCS/TMS 激活右侧vlPFC并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时,被试报告的社会疼痛强度明显降低(He et al.,2018,2020a,2020b;Li et al.,2022);当采用TMS 分别激活两组被试的vlPFC 和dlPFC,并要求他们采用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下调社会疼痛时,vlPFC 激活组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获得最好的情绪调节效果,而dlPFC激活组采用分心策略能获得最好的调节效果(Zhao et al.,2021),该发现首次揭示了外侧前额叶的两个子区域在两种调节策略间的双分离,加深了我们对情绪调节认知神经机制的了解。
综上,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神经环路与非社会性情绪调节的神经环路相似,主要是vlPFC、dlPFC 等前额叶脑区对脑岛、杏仁核、dACC 或vACC 神经活动的下调(Vijayakumar et al.,2017;Wang et al.,2017)。然而,由于此领域尚缺乏“脑调控+ 脑观测”的双向证据链,让我们无法确信:以社会疼痛调节为代表的情绪调节过程是否真的是由前额叶发起的、对皮层下情绪反应系统的抑制。
当然,社会疼痛是一种具有社会认知属性的负性情绪,对社会疼痛进行调节所涉及的脑网络与非社会性情绪调节脑网络相比,不仅具有相似性还具有特殊性。许多研究表明,社会疼痛情境显著激活了负责心理理论、自传体记忆、自我参照、社会认知等功能的脑区,主要包括dmPFC(Eisenberger et al.,2011)、颞顶联合区(Morese et al.,2019)、 后 扣 带 回 等(Mwilambwe-Tshilobo & Spreng,2021)。至今仅发现了两项直接对比社会和非社会负性情绪下调的研究。 Vrtˇicka等(2011)早期的研究发现,社会条件比非社会条件更显著地激活了mPFC、vlPFC、内侧眶额叶、颞上沟、后扣带回等脑区;而非社会比社会条件更显著地激活了dlPFC、腹外侧眶额叶等脑区。这说明前额叶的不同区域在下调由社会和非社会事件引起的负性情绪时出现了功能分离,同时调节社会情绪需要额外调用社会认知脑网络。我们课题组采用TMS 激活vlPFC,让被试分别下调社会疼痛和非社会负性情绪,发现vlPFC 对社会疼痛的下调作用更显著(He et al.,2020a)。但这两项研究都存在情绪诱发材料的缺陷:前者采用社会互动图片对比物品/风景图片(混淆因素:是否有人类图像),后者采用社会排斥图片(Zheng et al.,2021)对比单人负性情绪图片(混淆因素:单人负性情绪的诱因可能是社会事件)。
除了上述区别于非社会性情绪调节的特殊性,社会疼痛的神经表征还经常被研究者们用于与生理疼痛(physical pain)的神经表征进行比较(Eisenberger,2015)。基于数据驱动的脑成像研究表明,加工社会疼痛和生理疼痛的神经环路既有共性也有差异。首先,以dACC 为重要节点的两种疼痛的神经表征存在差异:dACC 在生理疼痛条件与丘脑、后脑岛、内侧前额叶等具有更强的功能连接,在社会疼痛条件则与vlPFC、dlPFC、颞顶联合区等存在更强的功能连接(Woo et al.,2014)。其次,利用次级体感皮层和后脑岛的激活特征,可特异性地区分社会疼痛和生理疼痛(Wager et al.,2013),提示生理(而非社会)疼痛显著激活了躯体感觉加工脑区。然而,这两项研究侧重考察社会疼痛和生理疼痛的神经表征(可能涉及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并未探讨主动外显情绪调节在两种疼痛条件间的差异。我们课题组关注vlPFC 的TMS 研究发现,该脑区对社会疼痛的下调作用强于对生理疼痛的下调(He et al.,2020b),提示vlPFC 对社会疼痛调节具有相对的特异性。另一项关注dlPFC 的安慰剂效应研究发现,dlPFC在调节生理疼痛和社会疼痛时调用了不同的子区域(Koban et al.,2017)。尽管如此,我们对情绪调节脑网络在社会疼痛和生理疼痛条件间的差异仍缺乏全面认识。
3 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在情绪调节特别是社会疼痛调节领域,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第一,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有待进一步澄清。首先,情绪调节过程是否的确是由前额叶发起的、对皮层下情绪反应系统的抑制?对此问题的肯定答复尚缺乏“脑调控+脑观测”的双向证据链(Kim et al.,2019)。其次,外侧前额叶对皮层下情绪反应系统的调控是否必须通过vmPFC 才能完成?虽然目前更多的研究支持“间接通路模型”,即认为vmPFC 是前额叶控制系统和皮层下情绪反应系统的枢纽(Hiser&Koenigs,2018),但已有的证据均来自脑成像研究,尚缺乏有力的因果性证据。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可利用TMS 激活以vlPFC 或dlPFC 为代表的前额叶控制脑区,观测由TMS 效应引起的情绪调节神经环路的连锁反应,借助动态因果模型等有向脑连接分析方法,考察vmPFC 在该环路中的枢纽作用,以及情绪反应系统的神经活动改变(主要考察杏仁核,同时观测脑岛、vACC 等)。
第二,外侧前额叶不同区域在认知重评中协同工作的时序尚不清楚。综合现有的脑成像证据推测,认知重评首先由以dlPFC 为主的注意控制系统启动,同时dlPFC 在工作记忆中维持多个对当前情境的解释以供vlPFC 进行选择;vlPFC 选取与调节目标相符的语义解释并对当前情境进行重新评估,随后抑制dlPFC 的神经活动(Silvers&Guassi Moreira,2019)。目前尚无研究考察dlPFC 和vlPFC 协同工作的时间进程。就此问题,我们建议首先使用双线圈TMS 瞄准dlPFC/vlPFC,在认知重评的不同时间点,利用单脉冲TMS(single pulse TMS,spTMS)分别“一次性地”抑制dlPFC和vlPFC 的功能,并观察情绪调节效果的变化。在澄清两个脑区何时卷入认知重评之后,再借助交替式的spTMS 和fMRI 技术(interleaved spTMS/fMRI)考察两个脑区的协同工作时序以及与他们相连脑区的反应,从时空两个维度揭示认知重评的认知神经机制。
第三,社会疼痛的核心情绪反应脑区仍存在争议。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靶点脑区是dACC 还是vACC?尽管不少经典研究发现dACC 的激活水平反映了社会疼痛强度(Eisenberger et al.,2003;Woo et al.,2014),但脑成像元分析结果却更支持vACC 对社会疼痛的编码(Mwilambwe-Tshilobo & Spreng,2021;Vijayakumar et al.,2017)。目前推测,dACC 和vACC 同时参与社会疼痛加工(Rotge et al.,2015),其中 dACC 负 责 冲 突 监 控(Eisenberger,2015),对“预期违反”敏感;而vACC 负责对情绪的效价或强度进行编码(Somerville et al.,2006),对社会疼痛敏感。为阐明dACC 和vACC 在社会疼痛加工中的作用,我们建议未来研究设置不同水平的预期违反和社会疼痛,利用基于实时fMRI 的神经反馈技术,要求被试分别调控vlPFC-dACC(Woo et al.,2014)和vlPFC-vACC(Morawetz et al.,2017)两条通路的功能连接强度,观测被试报告的“惊讶程度”和“社会疼痛强度”的改变,从而分离dACC 和vACC 在社会疼痛加工中的功能,明确社会疼痛的核心情绪反应脑区。
第四,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特异性脑网络尚不明确。首先,社会疼痛调节特异于非社会情绪调节的脑网络是什么?已有的两项研究发现,社会比非社会情绪调节条件更显著地激活vlPFC、mPFC、颞上沟等脑区(V rtˇicka et al.,2011),进一步的因果证据表明vlPFC 对社会疼痛的下调作用强于对非社会负性情绪的下调(He et al.,2020a)。然而这两项研究的情绪诱发材料存在混淆因素。我们建议后续研究采用严格控制的社会和非社会负性情绪诱发材料,通过脑成像技术明确两种负性情绪调控的脑网络的异同。例如,可采用社会疼痛和非社会负性图片诱发情绪,控制两套图片之间的负性情绪强度、图片中的人数等。社会疼痛图片可包含亲人离世、校园欺凌、失恋/情侣冷战等场景,非社会负性图片可包含个人业绩不佳、个人物品损坏、个人失误等场景。其次,社会疼痛调节特异于生理疼痛调节的脑网络是什么?目前尚缺乏采用主动外显调节任务直接对比两种疼痛调节的脑成像研究,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在此方向进行尝试。例如,在严格控制疼痛诱发强度的基础上,采用“回忆前任”范式诱发社会疼痛(Woo et al.,2014),采用电刺激仪的直流电模式诱发生理疼痛,进而利用fMRI 揭示社会疼痛调节与生理疼痛调节脑网络的异同。揭示社会疼痛与非社会负性情绪/生理疼痛的情绪调节的重叠脑区和特异性脑区,有助于发现三者间的潜在交互影响因素,提高临床对不同负性情绪和疼痛诱因的甄别效率和治疗效果。
4 总 结
本文以“社会疼痛”这一特殊的负性情绪为切入点,综述了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考察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脑机制,一方面可深化我们对情绪调节理论的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临床制定有效的社会疼痛治疗方案,帮助精神病患者恢复社会功能。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目前该领域主要有四个问题需要解答,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希望本文的观点能帮助情绪领域的研究者,在社会疼痛情绪调节方向进一步深耕,早日全面揭示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并通过转化研究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