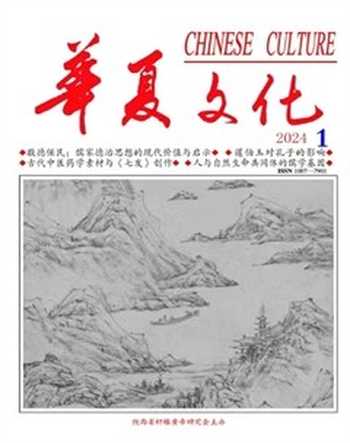古代中医药学素材与《七发》创作
刘明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以中医药为主要内容的中医药学,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所形成的中医药文化也凝聚着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哲理思想,孕育出辨证论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初作家枚乘创作的《七发》既是作为新体赋的汉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观察汉初中医药学具体实践及诊治理念的典范性作品,突出表现在枚乘创作中的中医药学素材书写。中医药学素材提供了解读《七发》的新视角,对于深入理解作品何以名“七”、创作旨趣及汉代赋作“讽谏”功能的生成,都颇具触类旁通的启示意义。
秦汉时期的中医药学,初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且与中华民族的集中统一、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融为一体,体现出精诚仁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凝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核。古人称:“方技(含医家在内)者,皆生生之具”(《汉书·艺文志》),“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四库全书总目》),即是对中医药学“济世寿民佑苍生”理念的高度概括。传统的中医药学在汉代的传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司马迁《史记》首次为医家扁鹊和淳于意立传,记录诊治疾病的方法体系和辩证观念,医家及其所代表的中医药学自此之后进入史学书写的范围。司马迁称誉扁鹊的医道:“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称淳于意“可谓进之矣”(《史记·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扁鹊开创中医药学以方技诊断施治的基本体系,内容包括切脉、望色、听声、写形、热熨、针石和汤液等,而且深谙血脉阴阳调和之法,诊治效果显著,为医家所遵循,文帝时的淳于意便是发扬扁鹊中医药学实践和理论的代表性医家。其二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设立“医经”和“经方”两类,属于先秦以来中医药学文献的学术总结。“医经”重在结合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征象,采用针石汤火的手段,调节适宜的百药齐和之度,以达到阴阳的平衡协调。“经方”则重在方药,即“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班固将此两者皆视为“方技”,视之为“生生之具”的方技,也就是“生死系焉”。这些中医药学的理论观念与实践体系,构成了枚乘创作《七发》中医药学素材的基本来源。
枚乘创作的《七发》,基本内容围绕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展开,为了治疗楚太子之病,吴客陈述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畋猎、观涛和诸子论说的“要言妙道”七件事,而以最后一件治愈楚太子之病。至于篇题缘何称“七”?李善解释称“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又称:“七者,少阳之数,欲发扬明于君也。”南朝的刘勰则认为寓意“七窍所发”,即楚太子以嗜欲为开端,终归以正道,借此而戒膏粱之子(参见《文心雕龙·杂文》)。俞樾《文体通释叙》云:“古人之词,少则日一,多则日九……大半日七。是以枚乘《七发》,至七而止,屈原《九歌》,至九而终……若欲举其实,则《管子》有《七臣》《七主》篇,可以释七。”至于创作的背景,唐代的李善认为是枚乘恐梁孝王谋反的劝谏之作,今人陈直则认为《七发》里的“吴客”是枚乘自称,而“楚太子”指参加七国之乱的楚王戊(参见《汉书新证》),此意见值得重视。结合韦孟创作的《讽谏诗》,楚王戊因在景帝前元二年(前155)遭汉廷削黜而心怀怨恨,滋生谋反之意。枚乘作为吴王濞的谋臣出使楚国,使命当然是沟通吴楚两国反汉的讯息,但枚乘是反对吴王谋反的,他的两篇劝谏吴王书已完全流露出该倾向。他自然也察觉到楚王戊的谋反迹象,于是创作《七发》,在劝谏楚王戊的同时也有警醒吴王濞之意。枚乘以假托的楚太子之病,譬喻偏离正道,以治病的七件事譬喻返归正道的七种手段,亦即托意于“病”、寓谏于“病”,“病”是《七发》谋篇布局的核心质素。
既然以“病”领起全文创作,必然涉及治“病”,因此笔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传统的中医药学素材,也留下了管窥汉初中医药学第一手的材料。《七发》里的楚太子之病,枚乘写道:“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人辇,命日蹷痿之机。洞房清官,命日寒热之媒。”这里提到了两种病:
其一是“蹷痿”之病,该病《吕氏春秋·本生》也有记载,称之为“招蹷”。古人较笼统地解释“蹷”是“不足能行”,“痿”是“瘅也”,而且认为:“舆辇之安,乃为此病之几兆也。”(参见《文选》,吕向注)按照字面理解,“蹷痿”是一种因贪于安逸,不事锻炼,而造成血脉不周通的疾病,呈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全身萎靡无力(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注释为:“不肯锻炼,结果就会引起肢体的瘫痪。”)。此即《七发》所称:“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血脉淫濯,手足惰窳”,其病因在于“伤血脉之和”。其二是寒热病,即阴阳失调之病。据《吕氏春秋·重己》云:“多阴则蹷,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看来“蹷痿”本质上是一种阴阳不调和所导致的疾病,表现为邪气逆袭。《灵枢经》“寒热病”有“骨痹”病症,“举节不用而痛,汗注、烦心”,似可为佐证。枚乘也多次用“气”和“阴阳”的笔调,描写楚太子的病情,如写道:“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格。”文中有三次写到楚太子病情有所好转,前两次都是出现在畋猎环节,表现是“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幾满大宅”,“有起色矣”,缘由就在于打猎有助于体育锻炼,促使体内的阴阳二气趋向平衡。第三次是观涛,写道楚太子虽是“淹病滞疾”,但出现“伸伛起蹷,发瞽披聋而观望之”的好转迹象,原因则在于太子观涛是与大自然的阴阴之气融为谐和一体。畋猎和观涛,即从事锻炼和感受天地自然之气,在枚乘眼里是治疗“庭痿”病的重要方法。
《史记·扁鹊列传》也记载扁鹊治疗一种称“尸蹷”的病,病者同样是太子。这种病症,太子侍医描述道:“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蹷而死。”扁鹊的诊断,则写道:“夫以阳人阴中……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综合两者的诊治,“尸蹷”之病是血气也就是阴阳之气不协调,造成邪气畜积,形成“中害”(脏腑的病害),当即枚乘笔下的“中若结辖”。扁鹊还进一步将阴阳之气运用到临床诊断,形成阴脉与阳脉的中医学实践和理论,此即司马迁所称的“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仓公列传》也记载淳于意多次诊治“蹶(同蹷)”病,有“风蹶”“热蹶”诸称,发病者基本为王公贵族,与楚太子相近。如诊治济北王,称:“风蹶胸满”,“切其脉时,风气也,心脉浊。病法‘过人其阳,阳气尽而阴气人。阴气人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淳于意提出“心脉”的说法,继承的还是扁鹊的脉学理论。至于阴阳失调而致“胸满”,或即扁鹊所说的“气闭而不通”,《七发》所写的“中若结辖”,只是淳于意说得更为浅切明白。这里包括“尸蹷”在内的各类蹷病的发病机理,与枚乘笔下的“蹷痿”病有相通之处,都是阴阳失调而形成邪气逆袭,遂造成心血气脉郁结不通而致病。实际病因是由于严重缺乏锻炼,饮食又极为奢靡,即枚乘所写的楚太子“饮食则温淳甘膬,腥醲肥厚”,导致心血瘀阻、血气不畅,严重者会昏迷不醒,即所谓的“蹷”。要之,枚乘关于“蹷痿”病理的认知,不仅是对先秦以来扁鹊所代表的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扬,还进一步综合“阴(阳)脉”与“血气”之说,提出“血脉之和”的理念,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也反映出古人注重强身健体、阴阳调和的健康养生理念。
枚乘针对楚太子之病,还提出了融合中医药材的食疗方案,主要有“肥狗”“山肤”“安胡”和“熊蹯”等。据《普济方》所载,肥狗有治腹肚胀满的功效,恰合乎《七发》所称的楚太子饮食肥腻而“恣支体之安”之症。山肤,古人不详何物,或注释为“雄白”(参见《文选》,张铣注),实即石耳菜。安胡指肜胡,据《本草纲目》所载具有“解烦热”的功效,楚太子着衣“杂遝曼煖”而致“燂烁热暑”,正是热症的表现。至于熊掌,据《神农本草经疏》所载则有“益气力”之效。这些食物呈现荤素搭配,又内含中药材,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方药治病理念,通过饮食即食疗的手段来实现。贾学鸿即认为:“吴客不仅是美食家,还是良医。他的饮食方案确实属于天下至美之餐,浓淡组合、荤素搭配、粗细互补、滋养有度,既契合中医养生的辨证思维,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又能满足楚太子的口腹嗜欲,同时,还纠正了太子终日营养过剩的偏颇。”(参见《说说(七发)的生命训导和“以劝为刺”》,载《文史知识> 2022年第3期)除食疗外,枚乘对药石、针刺和灸疗的手段也很熟悉,他写道:“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他更注重通过辅助中医药材的食疗、听琴观涛的心理放松,以及游观畋猎的身体锻炼等达到治病的目的,恰如《史记·仓公列传》所云:“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泄气。”应该说,强调“血脉之和”是一种更为综合的传统医学理念,折射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燮理调平、阴阳平衡的中和观,以及健康生活、防治未病的养生观,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邃智慧。
枚乘自觉运用传统的中医药学素材创作出这篇汉赋名作《七发》。篇题何以称“七”,以及创作的旨意也可以从中医药学的角度予以解读。《史记》记载扁鹊诊治赵简子之病有“七日而寤”的说法,并且援引了秦穆公患病也是“七日而寤”的先例。七日在传统医学里视为从生病至康复(或病重)的一个周期,类似于今之感冒也是一周(七日)至十天自愈,若不自愈即转向重症。医学典籍《金匮玉函经》云:“(病症)发于阳者,七日愈。”又《伤寒论注释》云:“伤寒至七日为邪正争之时,正胜则生,邪胜则死。”故“七日而寤”并非无根玄谈,而是有着生理上的科学规律性。枚乘以说七件事治愈太子之病,暗合“七日而寤”的传统医学经验。枚乘劝谏楚太子勿谋反汉廷,是一项严肃的政治议题,但先秦以来的纵横家传统,是通过譬喻说理的“迂回”方式完成劝谏的使命。枚乘即选择讲治愈楚太子之病的故事,间接传递或达成劝谏楚太子安守本分的政治用意(不安守本分则病不治)。这样,《七发》的创作构建出疾病、劝谏(或者说是讽喻)和政治三个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医治疾病与治国理政形成隐喻的类同性,劝谏是实现这种类同性的具体方式。此近似于《老子》所称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病与治国(或治政)具有了内在的联系性,此即《汉书·艺文志》所称的“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枚乘表面上是在写治病,实际也是在阐发治国的道理,通过劝谕楚太子治病来传达如何治政的道理。比如所写的听琴,从治病角度是劝谕楚太子听健康积极的音乐,从治政角度是希望楚太子明白“乐与政通”的道理,所谓“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政乖”(《毛诗序》),由此进一步深化了对“七发”内涵的理解。
治病与治政的关联性,也是管窥汉赋讽谏功能生成的新角度。最早阐述汉赋具有讽谏功能的应该是司马迁,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司马迁很明确将汉赋的讽谏功能,视为是对《诗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毛诗序》之语)讽谏传统的继承。此后的扬雄也持同样的看法,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至班固,仍是此观点,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汉赋成立的标志性作品是枚乘创作的《七发》,他的讽谏之源除可认为来自《诗经》传统之外,还可以理解为来自传统医学的治病传统,不妨概括为“病与政通”,是观察汉赋讽谏“渊源”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汉书·艺文志》将中医药学归于“方技略”,但却并不以其为“方技”而轻视,而是将它上升到“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的高度,言外之意是为政之道不能忽略治病救人、寿民佑生的医者传统。枚乘正是站在这样的层面,将他对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解熔铸到具有讽谏性质的《七发》创作中,以治病譬喻治政,以劝治疾病的医者仁心寄托劝谏政事的谋士之志,反映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政治智慧。
结合传统的中医药学素材重新解读《七发》,从小的方面说是延伸了古代作品乃至文学史的理解视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反观中国,其实古代文学中一直蕴藏着‘涉医的丰富资源,疾病书写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辞赋为医学提供了大量诊疗的依据和途径,反过来,医学也促进了辞赋在体裁、素材空间方面的拓展,有助于文学研究者从文学与治疗的交互视野中激活文学本身具备却一度被遗忘的特性。”(参见丁涵:《‘话疗与‘梦疗:论汉赋中的治疗主题与祛疾机理》,载《中国诗歌研究》第23辑)从大的方面说是拓宽了对古代作家的认识,他们并不局限于“文学家”的身份藩篱,而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集聚者,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质素,故其作品创作的价值意义不是“文学史”的范畴所能概括或覆盖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审视《七发》中医药学素材的书写,揭橥出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杰出代表,还是强调“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里的灿烂母题之一,由其所形成的厚重深邃的文学遗产值得细致归纳、分析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