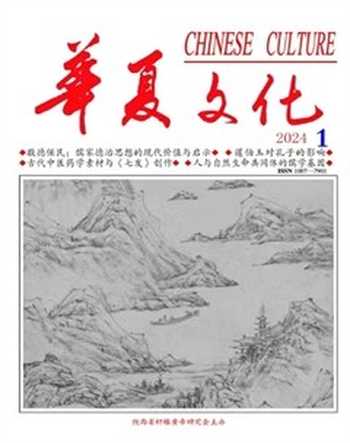《诗经》中的天人关系思想简析
李文博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一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那样基本且无可替代。在天人关系的探讨中,客体通常是天,而主体则必然是人。人通过对天的观察、思考所形成的认识就成为天人关系的基本内容。据统计,“天”字在《诗经》里一共出现了205次,遍及《风》《雅》《颂》三种题材。在《诗经》以外,专门讨论“天”以及天人关系的古代思想史文献还有很多,例如墨子的《天志》、屈原的《天问》、荀子的《天论》、柳宗元的《天对》等等。而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天”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之“天”仅只与大地相对而言的天空,广义之“天”则指除了人与人类社会以外的广袤的、拥有无限生机与可能的自然界。当然,除了原本意义上的自然之天,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天”还拥有多重的引申含义,譬如宗教意义上的主宰之天,或日神灵之天、意志之天;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之天,或日义理之天、公理之天。当然,本文所讨论的《豳风·七月》更多地侧重于展示人与自然之天的和谐关系。
一、循天而作,法天而行
《易·乾卦》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坤卦》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是人行为处事的榜样。身为君子,既要效法天的刚健有力,直面困难,自强不息;又要效法地的厚重宽广,涵养德性,立己达人。按照前述广义之“天”的解释,坤卦所代表的“地”,当然也可以被纳入“天”的范畴之内。此外,还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揭示了同样的道理。由此,我们便得出了天人关系的第一层含义:人应该向天学习,按照天的规律办事。或者说,循天而作,法天而行。
《豳风·七月》一诗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开头,其中的“七月流火”意即天上的大火星逐渐向西下沉,预示着天气由热变凉。为了应对“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这一年之中最寒冷时节的到来,避免出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窘境,人们必须提早着手准备过冬要用的衣物。如此看来,“九月授衣”这个动作便是人们在认识到了自然界季节更替客观的规律之后所做出的必要反应。下文紧接着的内容“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所展示的修理农具、举足而耕则是天气转暖、阳气上升之后,农业劳动者的必要动作。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旦偷懒,错过了最佳的播种时间,则必然会影响到当年秋季的农作物产量!再如后文的“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如果农人们在九月份不按照农时及时修筑场圃,那么等到了十月份收割庄稼的时节,便没有合适的场地来堆放和晾日西已经收获的粮食,倘若不幸遇到了阴雨天气则极有可能导致粮食出芽或霉变。正如荀子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荀子·天论》)这也体现了循天而作,法天而行的重要意义。荀子指出,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应充分发挥人自身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生存,进而生活得更好。
二、取用于天,天人和谐
人类是自然之子,总是在不停地向自然索取着生命的养料。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无不依赖于自然的恩赐。尽管在《七月》创作的时代,古豳地的人民早已从渔猎采集文明步人了农耕文明,但那也只不过是在“天生之,地养之”的基础上,加上了“人成之”的环节(《春秋繁露·立元神》),至多是从一种无秩序、无计划的取用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有秩序、有计划的取用而已。但是,人类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料这种行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当然,既然自然与人类是母子关系,那么人类务必要感念自然的生养之恩,与自然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不能向自然过度索取,更不能肆意破坏自然。这便是孟子所讲的:“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不使用过于细密的渔网捕捞,那么河湖里的鱼鳖就永远吃不完;不在春夏季节进入山林砍伐树木,那么木材就永远够用。由此,我们便得出了天人关系的第二层含义:取用于天,天人和谐。
温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在《豳风·七月》里,诗歌作者给我们描绘了许多“取用于天”以解决温饱问题的生产生活场景。譬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受求柔桑”,在温暖的春天里,黄鹂鸟在树梢上歌唱,有一位妙龄女子,手里拿着深而美的箩筐沿着小路行走,她正要去采摘那柔嫩鲜美的桑叶。采桑以养蚕,养蚕以缫丝,缫丝以纺线,纺线以织布,织布以制衣,制衣以护身。这便是“取用于天”的具体实践。还有后文的“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即在寒冷一月份的某天,人们猎取狐狸,制作皮衣,给公子御寒。这种行为,同样也是取用于天,以解决人的穿衣问题。接下来,便是解决人的吃饭问题。诗中说:“六月食郁及莫,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此处的“郁”类似于李子,“奠”指一种野葡萄,“葵”是一种蔬菜,“菽”是豆类的统称,“壶”是葫芦,“苴”是麻子,“荼”是指苦菜,上述这些食物和诗中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枣”以及将要被酿成“春酒”的“稻”,都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可以用来补充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能量。这不仅是“取用于天”的具体实践,同时也“透露着人与自然通过劳动所缔结的物质置换关系”,“宛然显现着人与自然保持的最质朴、最密切的天成母子关系”。(孙敏:《<七月>所映现的天人关系》,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因此,对于“天”,即自然界,人类除了从中攫取资源为我所用以外,还可以持一种柔和而温情的态度,去静静地观察那田野上的一根根枯草,去耐心地聆听那枯草间的一声声虫鸣。其间所暗含着的季节更替与物候流转的讯息,不待多言,便可明了。正如《豳风·七月》中所描写的那样:“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人我床下。”朱熹认为,这里的“斯螽”“莎鸡”“蟋蟀”为同一物种,只是“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朱熹:《詩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20页),然而据现代自然科学的考证,上述三项名称实际上指代的是三种不同的昆虫。但无论如何,诗句中所展现的那种天人和谐的画面都令人欣喜、令人动容。那些昆虫“暑则在野,寒则依人”(同上),仿佛是人类的好朋友一般,这也正应了张载那句“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的感慨。
三、结语
《豳风·七月》是一首极为出色的农事诗。对于研究《诗经》中的天人关系而言,它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典型性。通过上文的阐述与分析可知,该诗描写的农业生产活动很好地体现了循天而行、法天而作的实践智慧,同时也清楚地展示了取用于天、天人和谐的关系法则。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如今看来,如果不学诗,尤其是不学习《豳风·七月》,我们就不能更好地谈论天人关系问题。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汲取《诗经》中的古老智慧,慎重处理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天人关系问题,与向海洋排放核污水这样自私而且短视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