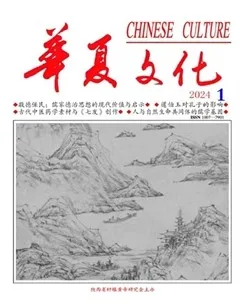浅析焦循的人性论
曹江涛
关于焦循的人性论,前人多有研究,但是很少有人通过人性和物性的差别与联系来研究。而焦循本身正是通过人性、物性之辩来彰显人所独有的“人性”,进而阐发人性善、物性不善的观点。而焦循关于人性和物性的差别与联系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正义》中对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与物性的辩论所做的注疏。因此,通过研究这一注疏,就可以梳理焦循人性论思想的内涵以及和前人思想的关系。
一、人性和物性的共同点
焦循对于人性和物性的研究,不再像前人一样夸大人性贬低物性,而是进行理性的分析,进而探究人性和物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焦循把人性和物性的连接点,就落在对“性”的定义上。他在给告子“生之谓性”作的注疏中引用了《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白虎通·性情》“性者,生也”、《论衡·初禀》“性,生而然者也”、《说文解字·心部》“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等五家注释,认为“性从生,故生之谓性也。”(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2015年,第792页)可见,焦循是继承了前代的“气性论”思想,这里的“性”就是指人和物生而具有的自然属性。他又直接指出:“告子但言‘生之谓性未见其非。”(《孟子正义》,第793页)这表明他是认同告子的这一说法,也就是说他也认为人和物的性在自然属性方面是有其共同点的。并且他在解释引用的《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时说:“静者,未感于物也。性已赋之,是天赋之也。感于物而有好恶,此欲也,即出于性。”(《孟子正义》,第793页)他認为人生下来后,性就有了,而且这是“天”所赋予的,这里的“天”就是指自然生化,而非义理的天。
其次,焦循进一步指出:“人之性善,物之性不善。盖浑人物而言,则性有善有不善。专以人言,则无不善。”(《孟子正义》,第793页)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就专指人性和物性而言的,其善恶非常分明(当然这涉及后天人性变化的问题),但是浑论人性和物性而言,性有善和不善。他随后征引了戴震和程瑶田有关“性”的看法,戴震认为人性就是在阴阳五行分化过程中产生的,程瑶田认为有质有形有气才有性,可见他们二者也都是以气来论性,认为“性”是一种随着形质产生而产生的属性。焦循征引二者的观点,就是认可他们关于性的看法,这是承继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焦循在注释“食色,性也”时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孟子正义》,第798页)他认为“饮食男女”这些基本的“欲望”就是人的性,而在这一方面人性和物性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人性和物性在“生之谓性”的基础上是相通的,这也是二者能够联系起来的基础。这也说明在人性论的思想上,他是肯定人欲,并且将人欲视为人性的一部分。
二、人性和物性的差别
(一)人性与物性不同类
儒家学者在关于人性和物性的问题上,就十分强调人性和物性不同类的问题,像孟子、荀子等都在各自的学说当中,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而后的儒家学者都继承了这一观点,像赵岐就说:“凡物生同类者,皆同性。”这就指出了不同类别物种之间的“性”是不同的,同类之间“性”才相同。焦循也很强调这一点,他说:“‘人生而静首出人字,明其异乎禽兽。”(《孟子正义》,第793页)“物生同类者,谓人与人同类,物与物同类。物之中则犬与犬同类,牛与牛同类。人与物不同类,则人与物之性不同类。”(《孟子正义》,第792页)这就给人性和物性划清了界线,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工作。只有先把人性和物性分开之后,才能进一步探究人性和物性的不同。因为当人性和物性二者混杂的时候,就很难从对比的角度探究人性和物性的差异。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问题,虽然人性和物性在自然属性上有其共同点,但是不能就直接认为人性和物性是完全相同的。就如同他说的“犬与犬同类”“牛与牛同类”,在物性当中都有不同,何况人性和物性分属两个大类。人性、物性的差异是儒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只不过儒者大多研究的是人性,要么以气论性、要么以理论性.而对物性是较少有探讨的。譬如朱熹就认为在气上而言人和物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有性即有仁义礼智之禀而物没有。虽然焦循和朱熹对于性的定义不同,但是他们都秉承儒家一贯的主张,就是人和物绝对是两个大类不能够浑论而言,所以焦循也更加强调在类的基础上人性和物性的不同。
(二)人性能变与物性不能变
在不同“类”的基础之上,焦循进一步探讨了人性和物性的差别,而其中贯穿的主线就是“变通”。
首先,焦循就通过反驳赵岐所注的“告子以为人性为才干,义为成器”(《孟子正义》,第786页)的观点,认为人性是可变的。他说:“故赵氏以人性为才干,桮棬是器,故赵氏以义为成器。杞柳本非桮棬,其为桮棬也,有人力以之也。以喻人性本非仁义,其为仁义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力则杞柳不可以为桮棬,非人力则人性不可以为仁义。”(《孟子正义》,第786页)告子的意思是人性之中是没有仁义的,仁义等都是后天改变人性而后才有的,不是人性中先天就有的。而赵岐认为告子的意思是人性就好像是杞柳才干一样,人性变成仁义,就好像杞柳才干变成了器具,是一种“自然”而成的,这与告子的原意有出入。而焦循就返回到告子的原意,认为杞柳变成桮棬和人性中有仁义都是“有人力以之也”,而不是先天就成为这样的,并引荀子的《性恶》篇来佐证,认为这和告子的说法一样。
其次,焦循阐述了通过变通来“变现”仁义的观点。他在解释前人注释的“转性以为仁义,若转木以成器”中的“转”字时认为:“转木谓矫戾其木,转性谓矫戾其性矣。”并且接下来认为:“变亦谓矫,戾与转同义,非变通转运之谓。”可见他认为变通是内在“矫戾”人性。所以他说:“盖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孟子正义》,第789页)人性有仁义不是外求,而是内在“矫戾”人性之后才有的。人正是有这样的“变通”,所以才“异乎物之性也”。而且他认为“仁义”也是以“变通”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他说:“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孟子正义》,第789页)在他看来,仁就是自己的心相通于别人的心,义就是知道那些不合乎道理的,从而改变为合乎道理。最后,焦循认为:“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岂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孟子正义》,第789页)人性之所以不同于物性就在于能够变通,人性在变通之中就产生出了仁义。也正是因为能够变通,所以人性才能够性善;而物性不能变通,所以不能够性善。因此人性和物性是不同的,也是不能够相比的。而且他认为:“杞柳为桮棬,在形体不在性,性不可变也。人为仁义,在性不在形体,性能变也。”(《孟子正义》,第789页)杞柳转变为桮棬是在形体而不是在性,人获得仁义是在性而不是在形体,因为人性是可变的而物性是不可变的。
(三)人性与物性在“知”上差别
变通正是人性和物性的大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只是一种“表象”,也就是说在变通之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知”。这个“知”是使人能变通的动力,也是人性、物性不同的根本原因。他说:“杞柳之性可戕贼之以为桮棬,不可顺之为仁义,何也?无所知也。人有所知,异于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变通,异乎禽兽,故顺其能变者而变通之,即能仁义也。”(《孟子正义》,第789页)正是因为人有所知,才能变通,也才能“矫戾”人性获得仁义。他认为:“以人力转戾杞柳以为桮棬,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顺人性为仁义,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转戾也。”(《孟子正义》,第789页)杞柳转化成桮棬它本身是不自知、不自觉的,只是外力的扭转作用。而人性获得仁义是人“自知自悟”的结果,不是单纯靠外力扭转的。也就是说,这个“知”反映出来了人的自觉性,这是人的主体精神所在。
焦循区分了两种“知”:一种是感官之知,一种是思维之知,并且就二者在人和物之上的不同与联系做了详细的说明。首先,他认为就第一种基础的感官之知来说,是人和物都共有的,这也是焦循对“生之谓性”的进一步发展,把人和物的自然属性联系起来。其次,他就第二种变通所依赖的“知”而言,认为是人所独有的。他认为只有人能“知而又知”,而禽兽只能“知生不能知音,不能一知又知。”(《孟子正义》,第793页)因此他进一步说:“故非不知色,不知好研而恶丑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恶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恶腐也;非不知声,不知好清而恶浊也。”(《孟子正义》,第793页)这就是阐述动物和人都有基础的感官之知,但是思维之知是动物所没有的,因此动物只知道基本的感受而不能进一步推演和仔细分辨,也就没有关于价值的判断,只知色不知道好研和恶丑,只知道食不知道好精和恶疏,只知道臭不知道好香和恶腐,只知道声不知道好清和恶浊。
焦循进一步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饮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禽兽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饮食男女,圣人教之,则知有耕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性所以无不善也。”(《孟子正义》,第798页)禽兽因为没有“知”,所以只知道“饮食男女”这些基本的生理活动。而人正因为有“知”,所以才有“耕凿之宜,嫁娶之宜”。“宜”就是凡事都有条理,不至于过和不及。“宜”就是通过“知知”或者说“知而又知”才彰显的,而这样人性也才能达到善。正是因為这样,他才认为:“惟人知知,故人之欲异于禽兽之欲,即人之性异于禽兽之性。”(《孟子正义》,第793页)只有人有“知知”,所以人的欲求才异于禽兽的欲求,人性也才异于禽兽之性,这是人性和物性不同的一条根本性准则。像刘瑾辉就总结并认为:“焦循从九个方面论证了人性善而物性不善”(刘瑾辉《焦循人性论辨析》),而在其总结的九个方面当中有四个都直接涉及关于“知”的问题。可见“知”正是人性和物性不同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焦循虽然秉持的是人性善的思想,但是我们通过其人性与物性的对比可以看出,他的性善论思想是复杂的。因为从焦循肯定“生之谓性”以及直接赞许告子的思想来看,他对告子的部分学说是赞同的,而从其引用荀子的一些思想进行注解来看,他对荀子的部分思想也是持肯定意见的,但是他在人禽之辩上又肯定孟子的说法,所以他的思想不单纯的是偏向某一家的学说,当然也并非简单的杂糅,而是综合考量,广采众说,融合荀子、告子、孟子、易学等诸家思想。这表现出他讲求变通、崇尚理性的精神,这和宋儒“义理”生硬强解是有区别的,并且也不是单纯的注疏考据而在其中也阐发了自己的思想。
焦循在坚持儒家性善论的基础上,不再强调先验的人性论而是强调后天的、经验的人性论,也正是通过这样来论证人的性善不是固定不变、先天就确定了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变通”和“知”来塑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继承明末以来对宋明理学家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的反思与批判,不再拥护一个先天的、先验的性善论,而是从自然人欲来肯定人性,从“继善成性”的角度来说明人性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阐明了后天教化的重要性。